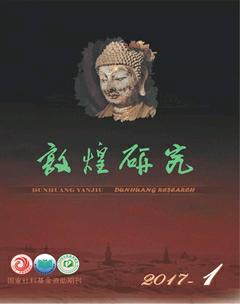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動態
榮新江
中圖分類號:K87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7)01-0002-02
感謝敦煌研究院邀請我來參加這次會議。趙聲良副院長讓我講一下近年來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的研究動態,但是這個題目比較大,所以我擇要把跟敦煌有關的話題就我所了解的近年發展的趨勢,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從動態方面來講,現在絲綢之路講得非常熱,但是過去沒有一門絲綢之路專業,主要有中外文化交流史,或者中外關系史,或者中西交通史專業。過去對做絲綢之路,我們覺得有點不太專業一樣,但是近年有所改觀。這種改觀,我不是說它不對。作為中西交通史這樣的中國傳統學科發展來講,早期有幾位大家,像張星烺、馮承鈞、向達、陳垣、陳寅恪、岑仲勉,等等。前面三位是專門做中西交通史的“三大家”。新中國成立后的這一代,像孫毓棠、張廣達等也做了很多中外關系史的研究。但是他們畢竟受了中國政治社會發展的影響,孫毓棠改行搞近代史,但是他們帶了一些學生,到了改革開放以后,就逐漸見了成果,像余太山、劉迎勝等先生。這是總的學科上的人物大致的脈絡情況。
在中外關系史方面,分別為傳統史籍、外文古籍、胡語文獻、考古資料幾個方面。這是大家比較集中研究中外關系史的話題。
傳統古籍方面,有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外交通史籍叢刊》,從《大唐西域記》、《法顯傳》到《東西洋考》,關于這些的研究好像已經窮盡了一樣。近年僅出版了朱玉麒整理的徐松《西域水道記》。但是我覺得,其實很多是可以重新做的。比如《大唐西域記校注》一卷應該有一本,《大唐西域記》里面沒有一張玄奘看到的佛教遺跡的圖片。以現在的研究條件是可以加上圖的。比如考古學家的遺址平面圖,還有玄奘看到的很多尊像,只要現在還存在的,都可以加在《大唐西域記》中。
外文古籍方面的研究,實際上是很薄弱的,但是前景很好。過去,對于希臘、拉丁史料,耿昇翻譯過,現在又出版了英文版,可以對照著再做工作。可以從西方整理的希臘、拉丁文本里重新輯錄有關東方的文獻。這些東西,目前沒有人做。另外,波斯、阿拉伯文獻的量相當大。在中國,除了穆根來、汶江、黃倬漢翻譯的《中國印度見聞錄》、宋峴翻譯的《道里邦國志》外,其他都沒有人做。西方的殖民主義時代已經結束,他們越來越不關心這些,而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提出,中國學者應該接著繼續做下去。像塔巴里《年代記》的完整英譯本已經出版了,《史集》版本的調查都已經結束,但是沒有很好的譯本翻譯出來。我們現在所用的《馬可波羅行紀》的版本是20世紀30年代馮承鈞翻譯的。他依據的底本是沙海昂本,非常差的。而國際通行的是伯希和和穆爾合作的百衲本,中國學者很少用它,調查國內圖書館所藏也沒有幾本,完全不能和現在的我國關于蒙元時代中西交通研究切合。這些都是非常緊迫的東西。
另外一個跟敦煌吐魯番相關的是胡語文獻。過去講,中國學者要奪回敦煌學研究的中心,并且我們已經奪回了這個中心。但是胡語這一塊還不是中心。其實我們沒有一個人能讀通粟特文和吐火羅文。季羨林先生不在了,我們沒有一個人能讀懂吐火羅文。實際這方面的天地非常大,包括敦煌、吐魯番都可以做很多工作。然后是梵文寫本。我們的期刊發表很多研究北道、南道的造像的論文。這些造像不是根據漢文本畫上去的,而是根據當地的梵文本和吐火羅文本畫出來的。梵本和吐火羅本經過了一百年,都已經被翻譯出來了。所以應該可以和洞窟的這些壁畫做重新的對照。關于摩尼教的東西,現在更多的關注點在霞浦文書上。葡萄溝水盤遺址出的文書最近全部都已經編了目錄。德國人在不斷地推進這個事情,他們有一個黑皮的《德國東方寫本目錄叢刊》,還有《柏林吐魯番文獻叢刊》。其實它們跟我們的敦煌吐魯番研究非常密切。當然石窟考古是不斷地推進中外關系史的一個有力的強點。像安家瑤做的玻璃器研究,趙豐做的絲綢研究,齊東方做的金銀器研究,林梅村做的西域文明,還有錢幣、石刻研究,等等。比如洛陽的景教經幢,實際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印證敦煌抄本重要性的材料。但是基本上是在景教的圈里在用,在敦煌的圈里沒有用。但是從寫本上來看,拿一個經幢和寫本來對照,可以復原這個卷子。
近年比較有推動的還是粟特方面。不客氣地說,粟特人在中國,中國人已經占據了話語權。從蔡鴻生先生、姜伯勤先生,一代代學者的努力還是很明顯的。關于粟特本土的研究還差很多。中國學者反應比較慢。隨著“一帶一路”的說法提出之后,對絲綢之路的研究是一個非常大的推進。但是現在到市場上找關于絲綢之路的書,真正上學術層面的就是劉迎勝的《絲綢之路》、吳芳思的《絲綢之路2000年》、韓森的《絲綢之路新史》,等等。
以上我粗糙地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學科背景和發展做了一個簡單介紹。
從刊物上來講,《敦煌研究》的整體發展是非常好的。從試刊到今天的確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過程。今天我們的期刊得到了優秀期刊的稱號,也得到了一個很大的資助。其實,敦煌研究院一直是我們的期刊最強有力的支持。
對比《敦煌吐魯番研究》、《敦煌學輯刊》、《敦煌學》、《吐魯番學研究》,我們的這個期刊是非常拔尖的,非常有特色。但是也要考慮到現在的雜志越來越多,比如現在有《西域研究》、《西域文史》、《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歐亞學刊》、《絲瓷之路》,以及將要創辦的三個雜志《絲綢之路研究》、《絲綢之路研究集刊》、《絲路文明》,這些期刊都是搶奪我們的稿源的。所以我們要給自己一個很好的定位,那就是:敦煌石窟、敦煌文獻、敦煌簡牘。這三條是我們的生命線。我們要立足這些才能保持我們的特色。另外,我覺得《敦煌研究》成功的一點,就是它辦刊早。在它創辦的時候,全國的石窟寺沒有雜志,所以我們期刊過去占了一個先機。過去我們把各個石窟佛教美術考古都囊括在敦煌研究中,所以現在應該按照絲綢之路沿線,輻射到全國,同時應該要走出去,一定要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吉爾吉斯、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然后到日本、朝鮮、韓國,所有的佛教美術、粟特文化考古的東西都囊括在這里。
最后一點:一本雜志,我們將它辦到這個程度,我們有很多自豪感和成就感,我們應該考慮怎樣更上一層樓。
1. 把住學術關。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一個高手推薦來的文章,我們要相信它就是一篇好文章。我們可以接受這種人情稿,但是這種人情稿是要有學術含量的,要把握住文章質量。如果進來的稿子真的不行的話,不要勉強,不要發表。
2. 推進國際化和全球化。加強自己期刊英文的推廣,建立自己的網站和微信。
3. 解決胡語文獻的排版問題。中國目前的排版還是頭疼于胡語文獻的上邊一個點或下邊一個撇,這些問題一定要解決,并且是可以解決的。
4. 發揮編委和專家的作用。編輯部審不了的稿子,一定要請專家,并且不一定是編委來審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