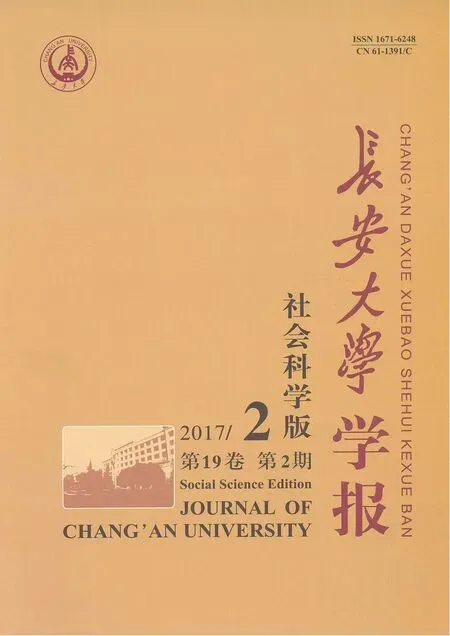略論《漢書·藝文志》中的“黃帝書”及其思想文化史意義
夏紹熙
(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陜西西安 710069)
略論《漢書·藝文志》中的“黃帝書”及其思想文化史意義
夏紹熙
(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陜西西安 710069)
在《漢書·藝文志》知識系統中“黃帝書”展現出來的“六略”之間的密切關系問題,對《漢藝·藝文志》中與“黃帝書”有關的內容進行統計分析,對“黃帝書”的性質和特點進行研究。研究發現,“黃帝書”在《漢書·藝文志》中共有34種656篇(卷)和6卷圖,廣泛分布于“諸子略”“兵書略”和“方技略”之中,是依托黃帝傳說而發揮思想、傳播知識技能的一種書籍載體,是許多學派或技術門類所依托的著述形式,它們借重黃帝事跡或傳說來闡述某種觀點,傳承某些技藝,與古人的日常生活和生產實踐密切相關,偏重于實用技術的專業知識;中國古人將宗法世系一脈相承的觀念引入技術文明的傳統,為各種實用的技術尋根,追溯某位先王為思想或技藝的發源,“黃帝書”采取黃帝立言的形式,反映了血緣宗法制對中華文明發展與古代社會特殊發展路徑的密切關系,《諸子略·道家》著錄“黃帝書”5種100篇,其治國用兵、修身養性、哲理玄思的內涵與“黃帝書”為代表的實用知識和技術中的身體技術、社會技術、自然技術有內在聯系,這種聯系是道法玄之又玄的哲學理論的基礎,也為理解古代知識系統的內在聯系提供了范例,中國傳統技術知識注重通過言傳身教和體悟來進行傳承,比較缺乏命題性知識理論的建構,這與現代科學技術知識相比有較大不同,需要我們多方位系統化地進一步認識中國傳統技術的特點。
“黃帝書”;黃帝傳說;實用技術;技術文明;血法宗緣;道家
東漢時期史學家班固(32~92年)編撰的《漢書·藝文志》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著錄先秦至西漢時期中華文化典籍共計596種13 269篇(卷),而且將這些典籍進行歸類和整理,按照六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38種門類劃分,涉及中國古代哲學、歷史學、文學、軍事學、自然科學、醫藥衛生等領域,構成中國古代文化知識的一個系統,被稱為“學問之眉目,著述之門戶”[1]。“漢志”著錄的古書流傳于世的很少,大部分都已經散佚(流失特別多的是“兵書略”“數術略”和“方技略”中著錄的書),但它仍具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作用,能為人們研究先秦至西漢時期主要學術流派及其代表著作提供線索。更為重要的是,“漢志”當中“六略”之間的相互關系值得深入探討,亦即將“漢志”作為一個整體看待,有助于我們了解古代知識系統的社會基礎、哲學基礎、邏輯基礎、科學技術基礎及它們之間的互動,從而為研究中華文化傳統提供新的視角和必要的背景知識。本文嘗試考察“漢志”中著錄的一類比較特別的書——“黃帝書”,目前學界研究“黃帝書”的論著不多,主要有李零《說“黃老”》[2]和蘇曉威《論黃帝書的兩大主題:技術發明和政治思想——兼論其在道家文獻中的地位》[3]等論文,以及張豈之主編的《中國思想學說史》[4]中的相關章節。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從“黃帝書”出發來看“漢志”中“六略”之間的密切聯系,說明探索中國思想文化史需要運用復雜性和系統性思維才能把握古代知識的深廣背景。
一、《漢書·藝文志》中著錄的“黃帝書”
“黃帝書”是指戰國以來出現的“依托黃帝而立言,名冠黃帝或與之有關人物的著述。”[4]“黃帝書”不是一種書或一部書,而是一種書籍體裁,依托黃帝傳說發揮思想、傳播知識技能,它們種類繁多、數量可觀。《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兵書略”“數術略”和“方技略”中都著錄了“黃帝書”,其基本情況如下[4-6]:
《諸子略·道家》著錄5種100篇:《黃帝四經》4篇;《黃帝銘》6篇;《黃帝君臣》10篇(注: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雜黃帝》58篇(注:六國時賢者所作);《力牧》22篇(注:六國時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黃帝相)。
《諸子略·陰陽家》有2種34篇:《黃帝太素》20篇(注: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容成子》14篇*《世本》曰:“黃帝使容成作調歷。”亦見《呂覽·勿躬篇》。(班固,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30頁)。
《諸子略·雜家》著錄1種26篇:孔甲《盤盂》26篇(注: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七略》曰:“盤盂書者,其傳言孔甲為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為誡法,或于鼎,名曰銘。”班氏非之,似近苛也。(班固,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51頁))。
《諸子略·小說家》著錄1種40篇:《黃帝說》40篇(注:迂誕依托)。
《兵書略·兵形勢》有1種2篇:《蚩尤》2篇。
《兵書略·兵陰陽》有7種59篇,圖6卷:《黃帝》16篇(注:圖2卷);《封胡》5篇(注:黃帝臣,依托也);《風后》13篇(注:圖2卷。黃帝臣,依托也);《力牧》15篇(注:黃帝臣,依托也);《鵊冶子》1篇(注:圖1卷);《鬼容區》3篇(注:圖1卷。黃帝臣,依托);《地典》6篇。
《兵書略·兵技巧》有1種25篇:《蹴鞠》25篇*“蹴鞠是古代的足球,屬于軍事體育……此書是依托黃帝殺蚩尤的故事,可能與上兵形勢類的《蚩尤》、兵陰陽類的《黃帝》有關。” (李零《蘭臺萬卷:讀〈漢書·藝文志〉》,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第165頁)。
《數術略·天文》著錄2種33篇又1卷:《黃帝雜子氣》33篇;《泰階六符》1卷*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也。” (班固,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10頁)。
《數術略·歷譜》有1種33卷:《黃帝五家歷》33卷。
《數術略·五行》有3種70卷:《黃帝陰陽》25卷;《黃帝諸子論陰陽》25卷;《風后孤虛》20卷。
《數術略·雜占》有1種11卷:《黃帝長柳占夢》11卷。
《方技略·醫經》有2種55卷:《黃帝內經》18卷;《黃帝外經》37卷。
《方技略·經方》著錄2種30卷:《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23卷;《神農黃帝食禁》7卷。
《方技略·房中》有3種71卷:《容成陰道》26卷;《天老雜子陰道》25卷;《黃帝三王養陽方》20卷。
《方技略·神仙》著錄4種61卷:《黃帝雜子步引》12卷;《黃帝岐伯按摩》10卷;《黃帝雜子芝菌》18卷;《黃帝雜子十九家方》21卷。
《漢書·藝文志》著錄的“黃帝書”總計有34種656篇(卷),圖6卷。其中,以《諸子略·道家》著錄的篇數最多,共有5種100篇,除此則廣泛分布在在后“三略”即“兵書略”“數術略”和“方技略”中。“黃帝書”的這種布局,為探索先秦至西漢時期知識系統的內在關聯提供了條件。
二、“黃帝書”的性質和特點
“漢志”著錄的“黃帝書”雖然種類以及篇卷數目不少,但是散佚極為嚴重,我們現在能看到的只有《黃帝內經》一種傳世,另外如《諸子略·道家》著錄的《黃帝銘》可從《太平御覽》卷390引黃帝《金人銘》和《路史·后紀》卷5引黃帝《巾幾銘》中看到一些零散的記載。值得關注的還有歷年來考古發掘的出土文獻,如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中有《孫子兵法》佚篇《黃帝伐赤帝》和《地典》,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中《十六經》《十問》中的一些篇章也屬于“黃帝書”。其中《黃帝伐赤帝》和《地典》屬于兵陰陽類古書,《十六經》偏重于理論,借黃帝君臣問對的形式講陰陽刑德和法術思想,《十問》則是古代房中書的摘抄,這些出土文獻對研究“黃帝書”是極為重要的補充。
今天所能見到的“黃帝書”雖然不多,但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黃帝書”在“漢志”中分布廣泛,只有“六藝略”和“詩賦略”中不見其蹤影,其余“諸子略”“兵書略”“數術略”和“方技略”中都有著錄。可以說“黃帝書”具有較強的滲透性,它不屬于某個學派的專門著作,而是許多學派或技術門類所依托的著述形式,它們借重黃帝事跡或傳說來闡述某種觀點、傳承某些技藝,這與黃帝的史實本身已經沒有多少實質上的關系了。
我們只有從整體上來看“漢志”六略之間聯系,才能理解“黃帝書”的性質和特點。“漢志”是一個復雜的有機聯系的知識系統,這個知識系統反映著先秦至西漢時期所積累的中華文明的重要成果。從結構上看,有學者認為:“應注意有專業知識的后三略,進一步則必須了解專業知識與六藝諸子之關系。”[7]這為我們全面認識“漢志”提供了重要啟示。
就后三略而言,“兵書略”是古代軍事知識、技術的匯總。先秦時期的對天道和人道的探索離不開對軍事和戰爭的思考,因為社會沖突最極端的表現方式就是戰爭,嚴密的組織形式、高超的計謀策略都被用于戰爭,而且戰爭對實用技術也有迫切的需要和極高的要求。《管子·五行》說:“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8]通過黃帝戰勝蚩尤的傳說說明只有掌握天道才能在戰爭中掌握主動。《鶡冠子·近迭》記載:“龐子問鶡冠子曰:‘圣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人。’龐子曰:‘人道何先?’鶡冠子曰:‘先兵。’”[9]這段對話認為戰爭是人道中首當其沖的問題。可見,不管是說天道還是人道,戰爭問題都是極其重要的。
“兵書略”中的“黃帝書”主要集中在“兵形勢”“兵陰陽”和“兵技巧”,專門著錄戰略即研究戰爭全局大計的“兵權謀”中沒有“黃帝書”。“兵形勢”中著錄《蚩尤》2篇,“蚩尤是所謂兵主,即中國的戰神,也是五兵的發明者。《世本·作篇》:‘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黃帝誅之涿鹿之野。’五兵都是青銅兵器。”[10]“兵陰陽”中著錄的書主要講古代軍事技術,班固在“小序”里說:“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6]。“陰陽”主要是和天文、氣象、地理、地形、地貌有關的軍事技術,它是數術之學在軍事上的應用。“順時而發”,是選擇時日的技術。“推刑德”也是一種選擇術。“隨斗擊”屬于求斗術。古人認為,北斗斗柄所指為兇,所背為吉。“因五勝”,講五行相勝。“假鬼神而為助”是借上述方術,求鬼神助戰[10]。“兵陰陽”中的“黃帝書”都是依托之作。《封胡》,封胡是黃帝身邊的大臣,所長不詳;《風后》,風后是黃帝七輔之一,擅長式法,在戰爭中推式法來布陣。“數術略”五行類還著錄《風后孤虛》20卷;《力牧》,力牧也是黃帝七輔之一,擅長推步。“諸子略”道家類也有《力牧》22篇。《鵊冶子》,鵊冶子亦黃帝七輔之一,擅長決法;《鬼容區》,鬼容區亦黃帝臣,擅長占星;《地典》,地典亦黃帝七輔之一,長于地形。銀雀山漢墓出土有《地典》篇殘簡[10]。上述文獻依托黃帝及其輔臣而作,這些人都有一技之長。
“數術略”是以天文、歷算、數學等知識為基礎來進行占卜、預測、選擇,有巫術的成分,也包含古人對宇宙萬物演化生成的認識。“數術略”天文類既包括對星象和云氣的觀察記錄,也包含吉兇占驗。歷譜類包含歷法和譜牒,后世也叫歷數或歷算,古代的算術屬于這一類。五行類主要是選擇術的總稱,又分許多小類,大興于戰國秦漢,代替卜筮成為當時最重要的占卜術,陰陽五行學說就是以這類數術為知識背景。雜占類是無法歸類的小術,其中以占夢最為重要,其次是各種鎮壓妖祥和解除妖祥的巫術。天文類、歷譜類、五行類、雜占類中所著錄的“黃帝書”與各類所涉及的專門知識相關,也是依托之作。
“方技略”屬于古代醫藥衛生知識和養生理論,包含古人對人體生理、病理的認識,以及植物、動物、礦物之藥用功效。如果說數術是古人對“天道”的認識,那么方技就是古人對“人道”的認識,是醫藥養生之學的總稱*古人所謂“養生”,都是養其所生(即養性),首先是保存這種生命力,進而是祛病延年,最后是要達到畢天地而不朽,叫作“通于神明”。(李零《李零自選集》,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86頁)。“方技略”中最重要的是醫經類——理論性和綜合性的醫學著作,《黃帝內經》最重要,為醫經類之首。它是依托黃帝君臣,以黃帝問道岐伯、少師、雷公、伯高、少俞的形式闡述醫學理論。經方類主要收錄藥方、療方類文獻,講對癥下藥療病之術。其中《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和《神農黃帝食禁》為“黃帝書”。房中類著錄與房事有關的書,包括求子嗣、優生、房中禁忌等內容。其中的“黃帝書”有《容成陰道》《天老雜子陰道》中容成、天老都是黃帝的重要輔臣;《黃帝三王養陽方》是依托黃帝、禹、湯、文、武等古代圣王講男性保養。神仙類是講除房中以外養生之術,其中的“黃帝書”有:《黃帝雜子步引》《黃帝岐伯按摩》講導引、按摩之術;《黃帝雜子芝菌》講神仙服食五芝(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11]之法;《黃帝雜子十九家方》屬于黃帝方。
綜上所述,“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中的知識具有很強的專業性,與古人的日常生活和生產實踐密切相關,偏重于實用技術方面。“黃帝書”廣泛分布于這三略之中,講的就是實用的專門技術。但同時這三略也是書籍流失最多的,在傳世文獻中只能見到三種:《兵書略·兵權謀》中著錄的《孫子兵法》,《數術略·形法》中著錄的《山海經》,《方技略·醫經》著錄的《黃帝內經》。在“兵書略”“數術略”和“方技略”這些專業知識的基礎上有前三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它們更多是思想上的創造和闡發,理論性更強,其中《諸子略·道家》和《陰陽家》著錄有“黃帝書”,這說明道家和陰陽家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兵書略”“數術略”和“方技略”中的成果并將其轉化為哲學理論。
三、“黃帝書”的思想文化史意義
從思想文化史的角度來看,研究《漢書·藝文志》中的“黃帝書”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一,“黃帝書”采取依托黃帝而立言的形式,從根本上反映了血緣宗法制對中華文明發展的影響,與中國古代社會的特殊路徑緊密相關。
中國古代社會從氏族社會走向文明社會和古希臘不同,保留了氏族組織的殘余,在氏族血緣的基礎上建立起國家,并由此演變為血緣的宗法制。這一特點反映在知識系統中,表現為對古代先王發明創造事跡的特別尊崇。例如在專門講血統宗法的典籍《世本》中,有記述帝王、王侯、卿大夫、姓氏之世系的《帝系》《王侯》《卿大夫》《氏姓》等篇,同時也有記述各種發明創造的《作》篇。將宗法世系一脈相承的觀念引入技術文明的傳統,用以解釋發明創造的生生不息、綿延不絕,這是古人對技術在人類發展中所扮演重要角色的獨特認識。趙紀彬對此評論:“所謂‘先王’一詞,不僅是政治上的盛世,倫理上的楷模,而且是立論的出發點、推理的大前提,更進一步,對于衡量一個時代,批判一個人物,分析一種制度,莫不以‘先王’為最高尺度。”[12]在這種意識的影響下,古人為各種實用的技術尋根,往往都會追溯到某位古代先王,以之為思想或技藝的最初發源地,因此才會出現依托“黃帝”的現象。“世之所高,莫若黃帝”(《莊子·盜跖》);“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于神農、黃帝而后入說”(《淮南子·修務訓》)。要在知識上不斷積淀、獲得傳承、形成傳統,需要黃帝這樣的先王,這是中國古代實用專業知識發展的特點。
第二,“黃帝書”與道家的密切關系為我們理解古代知識系統的內在聯系提供了一個范例。
《諸子略·道家》著錄“黃帝書”共5種100篇,這表明道家與“兵書略”“數術略”和“方技略”中涉及的知識有內在聯系。這種聯系是道家玄之又玄的哲學理論的基礎。王明說:“自西漢初迄三國,老學盛行凡三變,其宗旨各自不同。一、西漢初年,以黃老為政術,主治國經世。二、東漢中葉以下至東漢末年,以黃老為長生之道術,主治身養性。三、三國之時,習老者既不在治國經世,亦不為治身養性,大率為虛無自然之玄論。”[13]這種歷時的描述也可理解為道家思想固有的三方面內涵,也就是道家有治國用兵的一面、有修身養性的一面、也有哲理玄思的一面,這三個方面的內涵在不同的時代環境中各有突出的表現。而以“黃帝書”為代表的實用知識和技術就涉及這三方面的內容,如果我們從廣義上理解人類技術,從身體技術、社會技術、自然技術[14]三個方面來看“黃帝書”與道家的關系,那么修身養性的身體技術、治國用兵的社會技術是道家最為借重的,而脫離身體技術與社會技術的孤立改造使用自然物的自然技術是道家所反對的智巧或“機心”。也就是說,道家對技術的理解與對人類心靈和人性的理解是結合在一起的,我們研究道家思想不能僅重視其哲理上的闡述,也要看到這些哲理是以兵書、數術和方技中的知識聯系在一起的,只把關于哲理的部分抽出來討論是不夠的。
第三,對《漢書·藝文志》中“黃帝書”所代表的相關技術知識的考察有助于加深我們對中國傳統技術的認識。
文化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智慧的結晶,是民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體現,中華傳統技術知識是中華民族在與自然及社會環境的互動中形成的,是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之一,對傳統技術的研究是理解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個關鍵環節。從比較寬泛的意義上,可以認為技術知識是一個復雜系統,不斷嘗試描述、預測、解釋身體、社會和自然現象。中國古代的技術知識有自身的特點,“中國古代研究‘天道’的學問是叫‘數術之學’,而研究‘生命’的學問是叫‘方技之學’。它們都有自己的學術傳統、知識體系和概念術語。”[15]這些傳統技術知識和現代科學技術知識相比有很大不同,中國傳統技術知識注重通過言傳身教和體悟來進行傳承,比較缺乏命題性知識理論的建構,“技術認知的具身性和默會性很早就被一些先哲所認識并加以闡述和強調。”[16]不重視系統化、邏輯化的技術知識體系建構,而注重實用性、經驗性和體驗的特殊性*經驗科學范式是:因為前人通過A過程得到B結果,所以后人也可以通過操作A過程得到B結果。且A過程和B結果均為定性和半定量描述,帶有主觀痕跡。(葉高翔《科學思辨二十四則》,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5頁),這也是“黃帝書”大量散佚流失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從探尋中國文化特點的角度,近年來有學者主張從博物學(或自然志)的意義上來考察諸如數術、方技(也就是“黃帝書”的知識基礎)等中國古代學問,“博物學文化尊重大自然的變化過程和巨大力量,不過分夸耀人類的征服能力,不會高喊‘人定勝天’,也不會盲目崇拜強力與速度。天地之大德曰生,和諧共生、生生不息是博物學文化的終極旨趣。”[17]人們已經開始從博物學的角度來檢視以天、地、農、醫為主干的中國傳統自然知識領域,認為“對于未來的中國古代科學史研究而言,一種博物學的編史綱領是大有前途的。”[18]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能對中國傳統技術的特點有進一步的認識。
四、結語
從思想文化史的意義來看《漢書·藝文志》中的“黃帝書”給我們提供了審視古代中國文化知識系統的新視角,幫助我們深入理解古人對知識的分類、傳承及其應用,從而避免不加反思地用當代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去剪裁古人的思想世界。如果歷史研究的使命是為了未來,在現在對過去進行思考,那么應該以寬容和開放的心態探討歷史上存在過的知識體系的完整背景,努力建起當代人與古人對話的橋梁。
[1] 班固.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 李零.說“黃老”[C]//陳鼓應.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42-157.
[3] 蘇曉威.論黃帝書的兩大主題:技術發明和政治思想——兼論其在道家文獻中的地位[J].諸子學刊,2010(2):199-221.
[4] 張豈之.中國思想學說史:秦漢卷[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5] 李零.李零自選集[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6] 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7] 潘雨廷.潘雨廷著作集:第十卷·道教史叢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8] 黎翔鳳.管子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4.
[9] 黃懷信.鶡冠子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4.
[10] 李零.蘭臺萬卷:讀《漢書·藝文志》[M].北京:三聯書店,2011.
[11] 王明.抱樸子內篇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5.
[12] 趙紀彬.困知錄:上[M].北京:中華書局,1963.
[13] 王明.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14] 吳國盛.技術哲學講演錄[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15] 李零.中國方術正考[M].北京:中華書局,2006.
[16] 酈全民.中國傳統技術的認知特征及其當代價值[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46(1):27-32,151.
[17] 劉華杰.博物學文化與編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18] 吳國盛.什么是科學[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A brief view on “Emperor Book” inYiwenzhiofHanshuand its significance of culture and ideology
XIA Shao-xi
(Institute of Chinese ldeology and Cul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Shaanxi, China)
Based on close relationship of “Six Strategies” showed by “Emperor Book” inYiwenzhiofHanshuknowledge system, the related content of “Emperor Book” inYiwenzhiofHanshuwas carried out a statistical analysis. Besides,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mperor Book”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Emperor Book” inYiwenzhiofHanshutotally has 34 kinds, 656 articles (volume) and 6 volume figures, which widely distributes in “philosophers strategy”, “military strategy” and “medical strategy”. It is a kind of book carrier to develop ideas and disseminate knowledge skills on the basis of emperor legend. It is a kind of writing form relied on by many schools and technical categories, and they use emperor’s stories or legends to elaborate a certain point of view and inherit some skills. And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daily life and production practice of ancients with an emphasis o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practical technology; Chinese ancients introduce tradition of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 to concepts of patriarchal lineage to seek roots for a variety of practical technology and trace back to a king as the origin of thoughts or skills. “Emperor Book” takes form of the emperor’s creation of theory, which reflects close relationship of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betwee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pecial development path of ancient society. Chinese traditional technical knowledge lays emphasis on words and deeds, as well as comprehension to inherit, it relatively lacks of construction of propositional knowledge theory. Compared with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which needs us to systematically further underst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echnology in multiple directions.
“Emperor Book”; legend of the yellow emperor; practical technology; technical civilization; consanguinity patriarchal clan; the Taoist
2017-03-01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西部項目(14XZX024);陜西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0C004);陜西省教育廳科學研究項目(2010JK306)
夏紹熙(1980-),男,云南會譯人,講師,歷史學博士。
K203
A
1671-6248(2017)02-0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