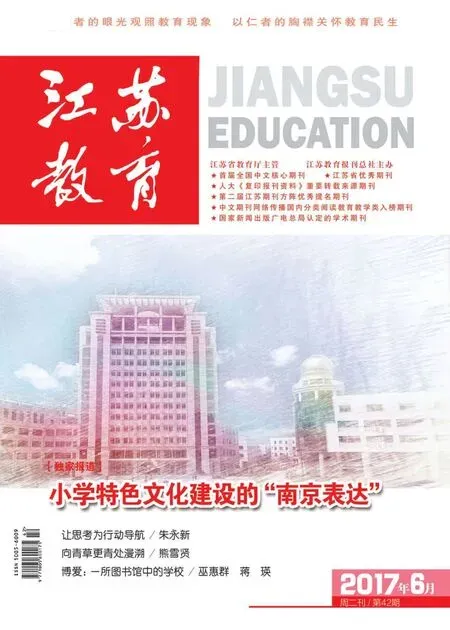情懷,重于權力
萬 恒
情懷,重于權力
萬 恒
本文基于問卷調查以及對近20位校長的個人訪談,了解到我國校長負責制下,校長們需要財權、人權的自主,更需要學校發展、課程改革的自主權。除了政府、教育主管部門需要改變“管控”的思路,真正采用現代化管理模式,給予學校獨立、界限清晰的辦學自主權,也需要校長更具教育情懷,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用于自己的專業素養提升,專注于學校教育教學的改革,為每一個孩子提供更適合的教育服務。
辦學自主權;教育情懷;校長
校長辦學自主權,并不是一個新話題。產權合一、兩權分離、辦學自主權擴大和辦學自主權法制化這四個階段,是我國中小學校長所經歷過的四個改革進程。隨著時代進步,信息技術的發展,學生個性化需求等,學校教育教學管理越來越復雜多變,政府、校長、教師、家長這幾個方面的利益相關人,都對對方有著很高的期望,但似乎,相互又都很失望。
為了了解校長對辦學自主權的真實想法,筆者以問卷星的形式,向2013年~2016年在教育部中學校長培訓中心接受過培訓的6批初高中校長發放了問卷,有125位認真填寫了問卷,回答了相關問題。第一道題,校長眼中辦學“自主權”的大小。有40%的校長認為一般,28%認為比較小,25.6%的校長認為非常小。進一步追問可以發現,各地區、校際之間校長的辦學自主權存在著巨大差別,是造成不同學校在辦學條件、師資隊伍、福利待遇、辦學特色乃至辦學質量上不均衡的重要原因。
我們都知道,只有真正落實校長負責制,保障校長辦學自主權,才可能實現學生的全面而個性化發展,捍衛教師的福祉,實現學校特色化及可持續發展,同時發揮學校作為社會文明創建者的作用,拓展學習空間,滿足社區資源共享,滿足公民休閑、娛樂、鍛煉的需要。為此,筆者對比了一下澳大利亞、英國、美國、加拿大、日韓等國教育管理情況,中國校長負責制下,法律法規所賦予的權力并不小,甚至可以說是比較大的。但是,由于政府、教育主管部門的越權、越位現象時有發生,導致校長在很多教育教學管理與領導上,難以按照自己的辦學思路去探索與實踐,尤其體現在教師聘任制度、薪酬分配、教育教學改革等帶來的約束。校長們期望自己能夠成為學校真正拿主意、想辦法、承擔責任的第一領導者,期望在教學改進的指導、信息技術在學校中的應用,管理結構的現代化以及為學校所有孩子提供必需的教育服務中發揮重要作用,也為改善社會環境將學校建設成為 “多功能”的文化場所而努力。
在“期望被賦予哪方面的辦學自主權”排序上,學校管理決策權、課程開發領導權高居前列。當教育行政部門存在“該管的未必真管,不該管的未必不管”的情況時,校長真的能做出適時的決策?決策,是管理過程的起始環節,決定著辦一所怎樣的學校,也決定著這所學校為誰辦學。這一方面,考驗著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對教育管理能力現代化的理解,是采用“管控”的思路,還是支持、服務的思路。過多的行政干預導致校長們被動地等待上級主管部門的指示、通知,久而久之失去工作激情,走上墨守成規的道路,教育創新、辦學特色成為一紙空談。另一方面,也考驗著校長的學校發展觀、育人觀、課程觀、評價觀等,反映了校長辦學格局的高低。顯然,我們需要更多能夠跳出傳統的管理思維框架,將追求每一個學生接受公平有質量的教育放在第一位,堅持把教師的福祉放在重要的位置,以不犧牲他們的健康、家庭幸福為基本決策原則的校長。我們也需要改變以往學校作為政府的附屬機構,哪個部門都可以管一管的局面,還學校內部決策與辦學自主權,使其成為獨立享有法律規定的權利與承擔法律責任的辦學實體。
那么,校長辦學自主權受到限制將帶來什么問題呢?首先是對校長領導力的挑戰或限制太多,參與調查的125人中有55位校長認為,“教師可以自由辭職,校長無權解聘”“沒有人事任免權”“受預算管理限制,校長使用經費受困,無法按照校長的想法辦學校”等嚴重制約著教育教學質量的改進,尤其是學校的內涵、特色發展。其次,面臨著“無限責任”的領導壓力,校長付出了巨大的身心健康的代價。時間、心力都耗費在大大小小的會議、解決教師職業倦怠、籌措學校辦學經費等事務上,無法真正思考學校課程開發與管理方面的實際問題。一些受困于辦學自主權的校長想要逃離,這兩年一些公辦中小學校長辭職自己辦學或者受聘到民辦學校的現象時有發生。
對于 “如何保障校長學校領導與管理權”這一問題,70位校長建議真正落實“管、辦、評”分離,變事前指導、事中督導為事后審計、監管,而不是事無巨細,從頭管到腳。30位校長認為行政部門應該放權,保障校長辦學過程中的人權、財權。也有校長認為,需要完善校長選拔和評價機制,充分發揮校長的創造性。由此可見,校長們期望教育主管部門,“放對權、選對人、辦對事”,尤其是不應該對校長的學校課程領導進行指手畫腳,以外行指揮內行,導致很多學校只能奉行“國家課程等于教材”這一狹隘的學校課程觀,阻礙了校長在探索學校特色項目,開發多樣的校本課程以滿足學生個性化發展需求等方面的多種努力。現實中,校長們尊重辦學規律,堅守教育教學常識、常規,比狂妄自大或胡亂應付還困難。領導是一個包括理性和情感因素的社會影響過程。[1]我們不能過高估計校長對抗外部環境的理性和能力,而應該真正界定學校擁有哪些獨立的、邊界清晰的辦學自主權。
最后一問是校長如果有足夠人權、財權,學校將發生什么變化?50位校長認為將提升對教師的激勵效果,25人認為將實現自主辦學,有利于學校特色發展。另外,有30位校長認為,這將對校長的德行和職業素養提出更高要求,也要警惕專權與腐敗的發生。值得肯定的是,大多數校長有著作為領導者的自律與自省精神,認識到“權力”始終是一把雙刃劍,背后是巨大責任。但必須指出,校長通過人權、財權來改變當下教師的職業倦怠,或者解除一些弱勢教師或者反對自己決策的人的教職,實際上是不夠理性的。須知,表面的和諧往往限制有建設性的爭執,如果一個團隊沒有充分的討論與爭執,領導者的決策質量往往低于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保護、尊重和盡可能發揮一些弱勢教師的優勢,實際上就是在保護我們自己。給學校的“后發”教師足夠的幫助與機會,暢通溝通渠道,實施以“成長為中心”的策略,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會成長為對學校、對學生有貢獻的人。
從這個角度而言,很多校長自身還是未表現出對學校內涵與特色發展,具有足夠的自主性和主動性,尤其是對“權威”的理解上,有較大偏差。校長的“權威”大小和持續性,絕對不應僅僅體現在“人”和“財”上。一方面,校長要從經驗型管理、交易型領導走向專業型領導,真正理解校長作為一校之長,承擔著管理領導、課程領導,尤其是價值領導(道德領導者)的重要責任。依據豪斯的路徑—目標領導理論,下屬需要上級清晰的路徑—目標澄清,既強調績效或目標,又關注下屬的動機取向,才能使得教師的需要和偏好依據高效能績效而變。[2]校長需要自我發展一種能力,即為學校的美好未來描繪一個清晰的愿景或理想的目標,激發實現愿景或目標的激情,使得教師的自我價值與領導的使命相符合。
另一方面,調研發現,同儕領導(peer leadership)通常比正規的管理者(formal administrators)實施的領導更有效力。[3]校長的決策,主要分為主動性決策、采納性決策和選擇性決策。[4]從教師對學校事務決策過程的觀感來看,學校領導還是較少采用采納性決策和選擇性決策,較少傾聽家長的意見、鼓勵教師的主動參與,真正發揮教師、家長和社區的力量。校長需要理順學校內部的權責關系,盡量民主管理,促使教育教學活動的相關主體能夠主動積極創造性地教與學。
筆者認為,我國校長負責制下,校長們需要財權、人權的自主,更需要學校發展、課程改革的自主。財權和人權,是服務和支持學校發展、課程自主的充分條件而不是必要條件,而學校發展、課程的自主,應該是辦學自主權的核心。多年來,從筆者走進學校、走進課堂,走近師生的觀察中,發現很多校長對校內事務的管理與領導,實際上是較為粗放的。尤其在課程與教學的改革方面,缺乏與社會良性互動的能力,不能深刻理解信息化時代下先進的教育理念與育人模式對教育教學行為選擇的重要意義,僅僅從外部單一評價教師的教學行為,以至于教師不能有效進行課程體系和教學方式的創新,導致師生的集體“成長倦怠”。正如筆者最近走進學校,通過聽評課,與教師、家長座談,訪談學生得出的學校診斷意見,主要集中在:如何進行貼合學校實際的國家課程校本化?如何通過課程開發(特指國家課程校本化)促進教師反思自己的課堂教學?家長對孩子的品德教育、技能掌握、社會實踐活動及藝術體育等提出了強烈訴求,如何回應?課業負擔沉重,家長孩子抱怨聲極高,如何改進作業設計?語文、英語學科教師的教研能力,如何得到有效提升……而這些問題,恰恰是校長課程領導力的核心所在,是需要校長專業引領的領域。
校長負責制下,校長既要有專業行為,更要有教育情懷。因為管理方法始終只是戰術,教育情懷、教育自覺才是實現教育現代化、進行學校特色化發展戰略要求。領導不僅僅只是工具性和行為性的活動,也是具有象征性和文化性的活動。[5]因此,作為學校組織精神支柱的校長應該是不受束縛的思考者,他們需要不斷超越傳統思維方式,接受新的觀念,幫助學校和教師了解自己。他們還必須常常幫助教師接受新的觀念,讓他們意識到學校的發展需要以彼此作為合作伙伴,共同促進學校專業發展和綜合改革。
在當前辦學自主權受到制度因素影響下,很多校長總是處于一種“痛苦的逃離狀態”,因為他們擁有一顆覺醒的靈魂,它的覺醒的鮮明征兆是對虛假的生活突然有了敏銳的覺察和強烈的排斥,[6]他們因為清醒而感到痛苦,痛苦于自己不能專注于真正的教育,不能真正將教師的質量、內部的和諧、師生的努力程度、學生學業成就等作為學校組織效能的評價指標,而不得不順應、屈服于一些外部評價。為此,他們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才能保持自我,因為擁有高貴、覺醒靈魂的人,更易向內訴求,而不會把所有的責任歸因于外部環境。顯然,不假思索,放棄對教育常識、常規的堅守,對一些校長是極其痛苦的事情。
筆者常常對校長提到“教育自覺”,其實更多的是指人性覺醒,就是從自己所隱身的角色中抽身出來,成長成獨立、完整并為自己一舉一動負責的人,努力從制度的深井中一點點爬上來,在更廣闊的天空下,看雨滴如何成為洪水。校長們也需要常常停下來想一想自己的辦學自主權,主要用在哪里?可以用在哪里?在追尋辦學自主權之余,更應該認識到,真正的力量來自我們內心,內心的力量才可以戰勝外界的恐懼,使我們走向教育的自由。
這也是為何,教育情懷重于、高于權力的原因。
[1][2][3][5]韋恩·K.霍伊,塞西爾·G.米斯克爾.教育管理學:理論·研究·實踐[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7.
[4]杰拉爾德·C·厄本恩,拉里·W·休斯,辛西婭·J·諾里斯.校長論:有效學習的創新型領導[M].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4.
[6]周國平.內在的從容[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3.
G471.2
B
1005-6009(2017)42-0057-03
萬恒,教育部中學校長培訓中心(上海,200062)港澳臺與海外教育研究室主任,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教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