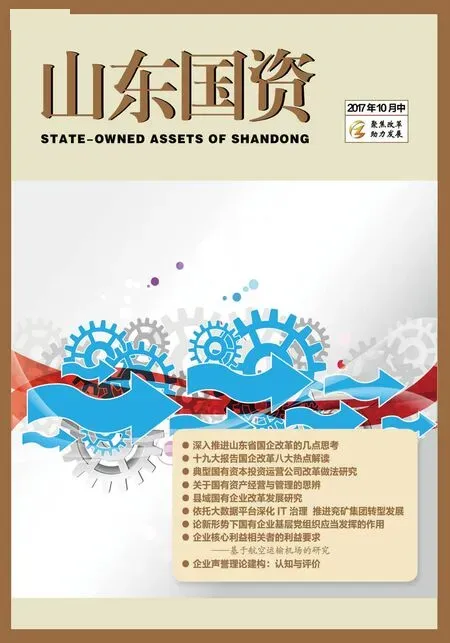企業聲譽理論建構:認知與評價
汪帥東
一、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加之“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去”,積極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在海外,企業的產品和技術是硬實力,企業的聲譽和形象是軟實力,它們是提升企業競爭力的核心要素,缺一不可,尤其是企業形象的塑造與企業聲譽的建構直接關系到企業在國際市場的地位及影響。不勝枚舉的案例表明,沒有明效大驗的措施,企業難以樹立良好的形象;沒有良好的形象,企業難以博得良好的聲譽;沒有良好的聲譽,企業難以贏得發展與壯大的空間。因此,只有樹立正面的海外形象,構建良好的國際聲譽,企業才能獲得國外政府及民眾的支持和認可,也才能在當前“大減速的時代”脫穎而出。
二、“企業聲譽”概念認知及理論闡釋
“企業聲譽”作為一個學術概念,肇始于20世紀60年代。1965年,美國學者Theodore Levitt在《工業購買行為:傳播效果研究》中給企業聲譽下了一個定義:“消費者對企業知名度、好或壞、可信度、可靠性、美譽度和信任度等的感知。”①此后,“企業聲譽”一詞層出疊見。
就筆者目力所及,迄今國內外學者為“企業聲譽”所下的定義已達40余種,不同的學科對其含義的闡釋也不盡相同。1998年,Fombrun與Van Riel從不同學科出發對企業聲譽進行了系統歸納:從經濟學視角將企業聲譽看做一種屬性或信號;從戰略視角將企業聲譽看做一種資產或進入壁壘;從社會學視角認為企業聲譽代表了有關評價對象聲望的綜合評價,描繪出評價對象及其所處社會系統的層次,同時聲譽還是反映組織合法性的指標;從營銷學視角強調企業聲譽是外部主體對企業的直接或間接感受或信息加工過程;從組織學視角將企業聲譽植根于企業文化和身份之中;從會計學視角更多地將企業聲譽看做企業的一種無形資產,等等。②目前,國際認可度較高的是Fombrun、Manfred Schwaiger兩位學者提出的闡釋:Fombrun認為,企業聲譽是與其他競爭對手相比較而言,基于對企業過去的行為以及未來前景的感知度而產生的對企業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吸引力;Manfred Schwaiger則認為,企業聲譽是利益相關者的一種態度結構,包括認知和情感兩個因子以及經營狀況、質量、責任和吸引力四個方面。
在國內,最早對企業聲譽做出概念性解釋的是白永秀與徐鴻,他們認為企業聲譽是“在公眾的頭腦中留下的一個總體印象”。③同年,干勤也為企業聲譽下了定義,即“一個企業獲得社會公眾信任和贊美的程度”。在其后出現的相關定義中,筆者認為鄭文哲與王水嫩給出的定義最為科學,他們提出企業聲譽是“公眾在對企業的各種因素認知基礎上所得出的一種綜合評價”。盡管國內學界涉及企業聲譽定義的論述俯拾皆是,但都有完善和修正的空間。筆者認為,關于企業聲譽的定義應該從狹義與廣義兩個維度來認知。從狹義上講,企業聲譽是指企業在長期經營活動中銖積錙累的聲望和名譽;從廣義上講,則是指公眾在對企業的經營業績、創新能力、社會責任與戰略傳播等因素認知的基礎上所得出的一種綜合評價。作為一種無形資產,良好的企業聲譽建構不僅有利于招攬優秀的人才,贏得投資者的信賴,促進消費者對企業產品的購買,而且容易獲得更多的外部資源,從而降低融資成本。
在企業管理分野中,Kreps是第一位提出企業聲譽理論的研究者。他把企業作為一個聲譽的載體,并借助重復博弈論中的思想闡釋了企業聲譽的建構。Kreps認為“權威”源于企業聲譽,指出任何經濟活動都可能面臨不可預見的突發事件,一家企業如何應對危機將直接影響到企業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如果缺乏建構或維持聲譽的能力,企業就很難東山再起。聲譽的高低是隨著它被使用的次數而疊加的,既不易建構亦不易消匿,所以一家企業的早期歷史可能在該企業聲譽的形成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同年,Holmstrom提出了關于聲譽激勵的若干問題,他總結并提煉的代理人市場模型是對Fama思想的模型化表述,用以說明市場上的聲譽可以作為顯性激勵契約的替代物。Berger認為聲譽是消費者網絡口頭交流的結果。Cole和Kehoe提出聲譽網絡的溢出效應,即聲譽的效果往往會超越交易范圍而對范圍之外的個體產生影響。Shenkar和Yuchtmann-Yaar提出,聲譽是社會機制的運作結果,在這種社會機制中各利益群體可以看成網絡中的成員,他們之間以不同的社會距離相互聯系。Wilhelm研究了團隊設置中的聲譽性,探討了通過何種方式實現團隊中的激勵相容問題。Tadelis用一個包含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聲譽市場對企業經營者努力的生命周期激勵的影響,認為在聲譽市場上,激勵與年齡無關,并且在均衡中更有能力的代理人不能比相對無能的代理人的要價更高。
三、企業聲譽建構關聯因素及評價指標
(一)橫向建構關聯因素
在當今國際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中國企業在全球享有的美譽度與其貢獻度存在明顯的不匹配。從美國《財富》雜志發布的2017年世界500強企業排行榜來看,中國國有企業表現強勢,國家電網、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分列第二、第三與第四位,但在2017年全球最受贊譽企業排行榜中,中國企業的表現則相形失色,這充分暴露了中國國有企業“大而不美”的問題。從宏觀的視角來看,影響企業聲譽的是企業信譽和企業形象兩大要素。從三者的相互關系來看,企業形象是外在美或者說現象美,企業信譽是內在美或者說本質美,而企業聲譽則是基于企業形象和企業信譽建構起來的綜合美或者說整體美。要而言之,企業聲譽的建構既離不開修煉內在美的企業信譽,亦離不開塑造外在美的企業形象。
企業信譽與企業形象的構建主體只是企業本身,而企業聲譽的構建主體則是企業與公眾,即企業負責生產,公眾負責傳播,二者必須共同參與,才能實現企業聲譽的終極建構。只是急功近利地追求外部形象的企業,常常因缺乏需要長期考驗才能積攢起來的信譽而難以獲得良好的聲譽;而一味故步自封地堅守內部信譽的企業,也往往會因忽視需要對外宣傳才能樹立起來的形象而難以獲得良好的聲譽。企業信譽是企業行為能力的一種表現,是企業能否履行其對社會、對市場、對客戶的承諾的一種標識度,也是建設企業聲譽、打造企業形象的核心要素。建立并維護良好的企業信譽,可以促使企業擁有更多的商業優勢,如增加顧客對產品和服務的信心,建立更高的客戶忠誠度,促使企業保持長期的超額利潤等。因此,只有長期不懈地狠抓信譽管理,企業才能更好地維護自身的形象和聲譽,也才能在激烈而殘酷的市場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
(二)縱向建構關聯因素
關于企業聲譽的評價指標,目前影響最大的是美國《財富》雜志的“美國最受尊敬企業”評選活動。從評選標準來看,該活動主要是根據企業內部管理能力、產品或服務質量、企業創新能力、長期投資的價值回報、財務報表的真實性、吸引優秀員工的能力、社會責任及環境責任、企業資產使用的合理性、全球經營能力等9個指標進行判定,英國、德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的主流經濟媒體對企業聲譽評價指標的設定與其相差無幾。從上榜企業的排名來看,這些國家對于聲譽的評價普遍傾向于財務方面的表現。質言之,財務表現越好,企業排名越高。毋庸贅述,這種評價體系存在著很大問題,最嚴重的是沒能對聲譽本身與影響聲譽的因素加以區分。基于此,筆者擬從經營業績、創新能力、社會責任與戰略傳播4個維度重新提煉出15個評價指標。


1.經營業績
經營業績直觀反映由企業經營活動而帶來的整體財務狀況與經營成果,它既是傳統企業參與市場競爭最穩定的基礎要素,也是現代企業聲譽評價體系中最核心的檢驗指標。除財務表現外,產品質量、服務質量、管理水平、人才吸引力等指標都直接關系著企業聲譽的內部塑造和外部評價。
2.創新能力
創新能力是指在外部環境動態變革產生的機會或內部能力模塊間發展不均衡產生的價值潛力驅動下的一種系統性應變或求變獲利、最終獲得競爭優勢的系列組織活動。因此,創新能力是企業知覺變異、解讀變異、創新決策與有效實施的組織活動。④在企業聲譽評價體系中,創新能力體現在技術創新、產品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3個方面。
3.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是指企業在商業運作中對利害關系者應負的責任。就企業自身而言,承擔社會責任意味著要為自己介入或影響人們、社會以及環境的一切行為承擔責任,也就是在創造利潤的同時,企業應該承擔對員工、消費者、社區、環境的相關責任,在企業聲譽評價體系中可將其提煉為合規經營、環境保護、社區融入與社會效益4個指標。
4.戰略傳播
對于企業而言,戰略傳播的核心思想是通過調動自身資源,協調其內部各部門的努力,使關鍵受眾理解并參與企業行為,從而為企業贏得內部團結并提升外部形象,構建有利于企業長期發展的運營環境。⑤在企業聲譽評價體系中,品牌傳播、形象公關與危機管理既是企業戰略傳播的三條主線,也是影響其傳播效果的三大要素。
四、結語
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全球化市場環境中,企業聲譽作為一種獨特且不可替代的無形資產,逐漸顯現其后發優勢。對于企業而言,擁有良好的聲譽既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也是奪取戰略性競爭優勢的窾要和關鍵。因此,我國企業應該積極建立、維護和提升自身聲譽,將聲譽建構納入企業管理體系中,并使之成為企業不斷發展壯大的隱形力量。
注:本文系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項目《國企形象建設與聲譽傳播》(20172000471)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面上一等資助項目(2017M61007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Theodore Levitt:“Industrial Purchasing Behavior:A Study of Communication Effect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②潘月杰 耿冬梅:《企業聲譽危機預警與管控》[M],經濟管理出版社,2014年版,第4頁
③白永秀 徐鴻:《論市場秩序和企業聲譽》[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6期,第71頁
④張軍 許慶瑞:《知識積累、創新能力與企業成長關系研究》[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4年第8期,第88頁
⑤Paul A. Argenti,Robert A. Howell and Karen A. Beck:“Th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Imperative”[J],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2005 (3):8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