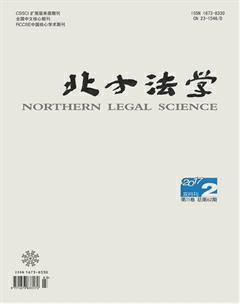土地開發權與我國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
摘 要:集體建設用地入市改革是當前研究的焦點和難點問題,亟須引入新的研究視角。從法理來看,立足于土地開發權視角,允許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實現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國有建設用地的“同地、同權、同價”,其本質是回歸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之開發權的處分權能,以實現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之開發權與國有建設用地之開發權的法律上平等。回到土地開發權制度平臺層面,借鑒國有建設用地之開發權的法制資源,加強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法律制度建設,乃是當下解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法制需求的理性選擇。此外,這亦是實現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的內在需要。
關鍵詞: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 土地開發權 集體土地所有權
中圖分類號:DF4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330(2017)02-0110-10
一、問題緣起: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引發的法制課題
在1998年我國《土地管理法》修訂前的一段時間內,允許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市場化流轉,具有明確的政策和法律依據。①然而,由于當時土地管理制度不健全,對耕地資源保護制度缺乏,在集體建設用地市場化流轉所帶來的巨大利益的誘惑下,大量的耕地資源被隨意開發,嚴重威脅到國家的糧食安全。②1998年我國《土地管理法》在修訂時,關閉了這一市場,即對于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而言,只能在法律嚴格限制的范圍內從事開發建設,而不能進行市場化的流轉,簡言之,集體土地被征收轉為國有土地后方可從事市場化開發建設。立法和政策的轉變,帶來的結果是城鄉建設用地的地權結構配置形態的二元化。③
然而,在城鄉地權二元配置備受社會詬病的當下,如何實現城鄉地權的同地、同權,參見劉守英:《中國城鄉二元土地制度的特征、問題與改革》,載《國際經濟評論》2014年第3期,第9頁。已成為當下我國土地法律制度改革的重大法制課題。2004年頒布的《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指出:“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村莊、集鎮、建制鎮中的農民集體所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可以依法流轉。”這一決定的出臺,一方面宣示了當下地權配置不公平改革應以集體建設用地作為切入口,另一方面賦予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流轉的權利,但其規定過于簡單,存在諸多不明朗的弊病,由此,十七屆三中全會、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及中央一號文件對于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流轉做了更為深入、細化的規定。為此,2008年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對依法取得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必須通過統一有形的土地市場、以公開規范的方式轉讓土地使用權,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與國有土地享有平等權益。”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指出:“建設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出租、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此外,2014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中央一號文件)亦同樣指出:“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加快建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產權流轉和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有關部門要盡快提出具體指導意見,并推動修訂相關法律法規。各地要按照中央統一部署,規范有序推進這項工作。”另外,十八屆四中、五中全會《決定》,2015年的中央農村經濟工作會議等中央政策亦同樣重申了這一規定。
由此而言,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已具有了明確的政策依據。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實現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這一重大政策問題的法律化?這需要回答以下幾個問題,如何從法理層面解讀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之本質?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會給現行的地權規范配置帶來何種影響?就其影響而言,現行法須做出何種應對?等等。目前,雖然學界圍繞這一主題展開了諸多理論研究,對相關法律制度建設起到了重大的理論指導作用,參見陳小君:《構筑土地制度改革中集體建設用地的新規則體系》,載《法學家》2014年第2期;溫世揚:《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同等入市”的法制革新》,載《中國法學》2015年第4期;陸劍:《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實證解析與立法回應》,載《法商研究》2015年第3期;房紹坤:《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幾個法律問題》,載《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但客觀而言,這些研究存在視角單一、理論不夠深入以及實踐可行性值得進一步檢討等弊端。鑒于此,筆者擬轉換研究視角,立足于土地開發權理論層面,筆者近幾年已就土地開發權理論展開了系統性研究,將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置于土地開發權制度平臺上展開深入理論研究,相關理論參見張先貴:《中國法語境下土地開發權是如何生成的——基于“新權利”生成一般原理之展開》,載《求是學刊》2015年第6期;張先貴:《容積率指標交易的法律性質及其規制》,載《法商研究》2016年第1期;張先貴:《地票交易之地役權屬性的理性檢視》,載《社會科學研究》2016年第1期;張先貴:《土地開發權的用益物權屬性論》,載《現代經濟探討》2015年第8期;張先貴:《土地開發權與土地發展權的區分及其法律意義》,載《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5年第4期;張先貴:《土地開發權與我國土地征收制度之改革》,載《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張先貴:《中國法語境下土地開發權歸屬及類型的法理研判》,載《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張先貴:《土地開發權與我國土地管理制度之改革》,載《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將建設用地入市相關法制建設置于土地開發權制度平臺上展開深入的理論探討。
二、本質透視: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法理解讀
在我國,鑒于土地公有制的基本國情,就國家土地所有權而言,無論是“雙階說”、參見稅兵:《自然資源國家所有權雙階構造說》,載《法學研究》2013年第4期。 “公權說”、參見鞏固:《自然資源國家所有權公權說》,載《法學研究》2013年第4期。 “三層結構說” 、參見王涌:《自然資源國家所有權三層結構說》,載《法學研究》2013年第4期。 “國家所有制說”,參見徐祥民:《自然資源國家所有權之國家所有制說》,載《法學研究》2013年第4期。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并非是一項單純財產權的私權屬性。再以集體土地所有權為例,有學者指出,“我國集體土地所有權既具有公權力的強制性,也具有財產權利的資源收益性,換言之,集體土地所有權具有公私混融的特征。”李鳳章:《從公私合一到公私分離——論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使用權化》,載《環球法律評論》2015年第3期,第79頁。實際上,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土地改革實踐逐漸塑造了土地使用權的財產權地位,提供了土地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接軌的制度工具,可以說,土地使用權已成為我國的基礎土地權利。通過“做實”土地使用權,“做虛”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方式來剝離集體土地所有權中的財產權內容,在功能層面實現我國的土地使用權類似于大陸法系私人土地所有權,類似于英美法系土地保有權,已為學界所達成共識。高富平:《土地使用權的物權法定位》,載《北方法學》2010年第4期,第11頁;趙萬一、汪青松:《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功能轉型和權能實現》,載《法學研究》2014年第1期,第80頁。以上關涉我國土地權利的這一實踐特征不僅成為解讀當下中國土地法律制度本質所無法缺少的智識資源,亦構成了我們檢討現行土地法律制度之弊病,加強其理論建設的共識性平臺。
既然我國的土地改革實踐已使土地使用權成為基礎性物權,解決了土地市場開展的基礎性難題,并在功能上具有了類似于大陸法系私人土地所有權的基本特征,那么,理論上需要進一步延伸的是,我國現行法上不同類型土地使用權的差異何在?為何存在諸多差異?如何改革?等等,在筆者看來,要想在理論上對這些問題做出清晰的回答,需要立足于中國特有的地權結構形態,引入“土地使用權權能”理論。盡管學界并沒有專門立足于我國獨特的地權結構形態,就“土地使用權權能”這一主題展開相應的理論研究,但從某些研究成果來看,都在不同程度上宣示這一理論在中國法語境下的成立。相關資料參見張少鵬:《“土地使用權”是獨立的不動產物權》,載《中國法學》1998年第6期;劉俊:《土地所有權權利結構重構》,載《現代法學》2006年第3期;高海:《農場國有農用地使用權的權利屬性與物權構造》,載《法商研究》2015年第2期。另外,在“權能權利化”參見宋亞輝:《新權利的生成:以“戶外廣告發布權”為例》,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0年第3期,第91頁。的趨勢下,土地使用權的各項權能在一定條件下亦可進一步上升為一項獨立的財產。
在交代了上述理論后,回到本文所探討的主題,同樣作為土地使用權的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和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雖然都可以從事開發建設,但二者在權利內容的安排上卻存在顯著的差異,顯然,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權能配置層面的區別化對待。為解決二者之差異,中央文件層面賦予了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政策目標,以實現其與國有建設用地“同地”、“同權”、“同價”。當然,認識這一點并沒有為問題的解決提供實質性的進展,仍然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二者之間最大的差異體現在哪項權能?在權能不斷權利化的趨勢下,能否將二者統一到同一權利層面展開制度建設?顯然,上述問題亟需從法理層面予以準確的廓清。
在筆者看來,立足于“土地使用權權能”和“權能權利化”理論,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其本質是回歸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之開發權的處分權能,以實現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之開發權與國有建設用地之開發權的平等法律地位。有學者認為,我國“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以及“宅基地使用權”等術語可用統一土地開發權(亦即土地發展權)術語替代(參見程雪陽:《土地發展權與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載《法學研究》2014年第5期,第86—87頁)。筆者認為這一觀點有欠妥當,基于正文的論述,在我國,土地開發權應視為土地使用權處分權能之權利化的結果,依此類推,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之開發權乃是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之處分權能權利化的結果。實際上,我國土地制度的最大弊病是集體土地與國有土地同地不同權,賦予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國有建設用地同地、同權,其本質就是實現二者之開發權的平等。準確地把握這一點,乃是對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進行法律規制的前提和基礎。
所謂土地開發權,主要是指土地用途能否變更和土地利用集約度能否提高的權利,張先貴:《中國法語境下土地開發權理論之展開》,載《東方法學》2015年第6期。與土地發展權主要解決土地用途變更和土地利用集約度提高后的增值收益歸屬權利相比,其主要解決的是土地用途變更和土地利用集約度提高之權利歸屬問題。參見前引⑦張先貴:《土地開發權與土地發展權區分及其法律意義》一文。從域外的經驗來看,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承認土地開發權為一項獨立的財產權已無爭論。參見 Norman Marcus,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 A Current Appraisal, 1 Prob,pp.40—43 (1987).實際上,作為土地財產權中最為活躍的財產權——土地開發權,參見Vicki Been & John Infranca,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 Programs: Post-Zoning, 78 Brook.L.Rev.435,435—466 (2012—2013).已廣泛地存在于我國的土地管理實踐中,譬如耕地資源的保護、生態脆弱地的維護、文物古跡的保存以及歷史街區更新中所廣泛采納的土地開發權交易,就是較為典型的例證。參見李家才:《開發權交易、區域農田保護及其國際經驗借鑒》,載《改革》2009年第5期;劉文敬、方瑜:《基于開發權轉移的歷史街區開發模式初探》,載《山西建筑》2009年第4期;張先貴:《地票交易的法律性質及其規制》,載《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然而,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土地開發權并沒有作為一項獨立的財產權為我國實證法所明定,理論上圍繞這一權利的探討亦主要集中于域外經驗的介紹,而很少基于我國特有的地權結構形態,展開深入的研究。參見劉明明:《英美土地開發權制度比較研究及借鑒》,載《河北法學》2009年第2期;黃瀧一:《美國可轉讓土地開發權的歷史發展及相關法律問題》,載《環球法律評論》2013年第1期;丁成日:《美國土地開發權轉讓制度及其對中國耕地保護的啟示》,載《中國土地科學》2008年第3期。
實際上,作為一項獨立的土地財產權——土地開發權,雖然在我國現行實證法層面尚處于缺位狀態,但無論是我國的土地管理理論還是實踐,都存在諸多與土地開發權相關或者可用土地開發權來解釋的法律現象。譬如,就我國現行的土地規劃制度而言,政府行使土地規劃權的過程,其本質是土地開發權如何分配和實現的體現;參見黃莉、宋勁松:《實現和分配土地開發權的公共政策——城鄉規劃體系的核心要義和創新方向》,載《城市規劃》2008年第12期,第16頁。我國現行的土地用途管制法律制度,其本質是對農用地開發權的限制;參見張鵬、高波:《土地準征收與補償:土地發展權視角》,載《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第64頁;郭潔:《土地用途管制模式的立法轉變》,載《法學研究》2013年第2期,第79頁;任世丹:《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補償正當性理論新探》,載《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第20頁。我國現行的土地征收制度,無論是農村集體土地征收還是國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其本質乃是土地開發權的實現、變動或者重新配置的過程;參見顧長浩、李萍:《城鎮化進程中集體土地開發利用若干法律問題分析》,載《東方法學》2014年第3期,第85、88頁。我國現行的土地開發許可制度,其本質亦是土地開發權的實現方式或者變動的體現。金儉、呂翾:《論臺灣土地開發許可制及其對大陸地區的啟示》,載《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3年第3期,第52—53頁;李泠燁:《土地使用的行政規制及其憲法解釋——以德國建設許可證為例》,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第154頁。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由此而言,我國土地管理制度的本質,乃是土地開發權配置或者變動或者實現的體現,土地開發權已成為土地管理的實質性工具。張先貴:《中國法語境下土地開發權歸屬及類型的法理研判》,載《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第35頁。可以說,當下我國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諸多地方試點方案、中央層面的土地政策以及理論上長期爭論的諸多主題,均與土地開發權相關或者說是這一權利的本質體現。筆者在此所談及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就是典型的例證。
具體而言,我國現行的土地按照用途主要分為農用地、建設用地和未利用地三大類。根據《土地管理法》的規定,在土地用途管制法律制度背景下,農用地只能是從事農業生產,而不能隨意變更為建設用地從事非農化的開發建設,因此,農用地之開發權是被土地用途管制所限制。理論上,對農用地開發權之形式上的限制已類似于實質上的剝奪,被學界視為農用地開發權的準征收。參見金儉、張先貴:《財產權準征收的判定基準》,載《比較法研究》2014年第2期,第42—43頁。而對于建設用地而言,從我國現行法的規定來看,雖然允許其被開發建設,但根據其權利主體不同,具體分為城市集體建設用地和農村建設用地兩大類型。對于城市建設用地而言,其權利人在符合法定條件下可自由處分該建設用地,譬如轉讓、出租、抵押等等。對此,立足于土地開發權理論,可以說現行法層面賦予了城市建設用地之開發權的自由處分權能,而這亦構成了城市建設用地能夠在市場上自由處分的根本保證。
然而,與之相反的是,對于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而言,雖然中央政策層面已賦予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之市場化流轉的權利,但現行《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規仍然是禁止這一權利的自由處分,尤其是面向市場化的自由轉讓、出租、抵押等活動。因此,可以說,在實證法層面,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城市建設用地之間是不平等的,而這種不平等的實質主要體現在開發權配置不公平層面。
當然,在此須指出的是,立法上對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之開發權自由處分功能的諸多限制,并不意味著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之開發權被完全剝奪。換句話說,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人仍然享有在一定范圍內的開發建設權利,只是其內容受到諸多明顯的限制,即不能像城市建設用地一樣進行市場化的出讓、出租、抵押等自由流轉。另外,需交代的是,對于城市建設用地而言,根據用地性質的不同,又可進一步區分為城市公益性建設用地和城市經營性建設用地。有學者就公益性建設用地的經濟開發屬性作了相應探討,但在現行法層面并沒有得到允許。參見徐文:《集體公益性建設用地經濟屬性開發論》,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8期;徐文:《集體公益性建設用地政治與經濟屬性平衡論》,載《中國土地科學》2015年第9期。筆者在此所談及的城市建設用地之開發權能夠在法律權限范圍內的市場化自由處分,主要針對的是城市經營性建設用地之開發權。
基于上述論證,不難看出,現行政策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就其本質而言,一方面是賦予或者回歸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之開發權的處分權能的體現,即能夠實現市場化的出讓、租賃、入股等流轉;另一方面是實現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之開發權與國有建設用地之開發權的法律上平等,打破城鄉二元分割狀態下的城鄉建設用地差異化的地權配置模式。實際上,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實現城市建設用地與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法律上的平等,其最大的現實和法律障礙在于兩項建設用地之開發權能否實現法律上的平等對待。
三、應對方案:亟待建設統一的土地開發權制度平臺
在解釋了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本質在于回歸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之開發權的處分權能,以實現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之開發權與國有建設用地之開發權的法律上平等,進而真正實現“同地、同權”的改革目標。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從法律層面保障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順利進行?或者說推動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需要立法上做出何種回應?在筆者看來,回到土地開發權制度平臺層面,借鑒國有建設用地之開發權的法制資源,建設統一的土地開發權制度平臺,以加強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法律制度建設,乃是當下解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法制需求的理性選擇。此外,這亦是實現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的內在需要。具體而言:
其一,明確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用益物權屬性,這是開展土地開發權統一平臺制度建設的邏輯前提。理論上,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包括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主要是集體鄉鎮企業用地)和集體公益性建設用地兩大類。因此,明確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法律屬性亦就回答了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法律屬性。就我國現行的實證法來看,并沒有明確規定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用益物權屬性,那么這是否由此認為,根據物權法定原則,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并非一項用益物權呢?在筆者看來,在中國法學界開始擺脫“立法中心主義”的當下,陳甦:《體系前研究到體系后研究的范式轉型》,載《法學研究》2011年第5期。無須修改現行立法,重新解讀現行的法律文本,借助解釋論范式,宜將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確定為一項用益物權:一方面,我國《物權法》第十二章就建設用地使用權的規定,從第135條到第150條乃是針對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而設置的規定。對此,有學者指出物權法就建設用地用益物權屬性的界定,只是針對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而言,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沒有被物權法視為一項用益物權,須通過修改物權法,確定這一權利的用益物權屬性,方可明確其法律屬性。參見韓松:《論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載《蘇州大學學報》2014年第3期,第71—72頁。顯然,這一論斷有待商榷,實際上,我國《物權法》在建設用地使用權的規范設置上,亦涉及到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規定,譬如,根據《物權法》第151條規定:“集體所有的土地作為建設用地的,應當依照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規定辦理。”只不過,物權法圍繞集體建設用地的規定較為簡單,即如有學者所言:“我國物權法對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制度規定并未給予足夠的重視與規范,而是通過轉介條款將規制的依據直接指向了《土地管理法》。”參見陳小君等:《后農業稅時代農地權利體系與運行機理研究論綱——以對我國十省農地問題立法調查為基礎》,載《法律科學》2010年第1期。因此,從體系解釋來看,作為建設用地使用權的兩種類型: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和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在我國現行的物權法上都有明確規定。從規范類型來看,《物權法》第151條對集體建設用地的規定屬于不完全法條,須結合《土地管理法》等法律的相關規定方可實現規制的完整性。從規范的性質來看,物權法屬于確權性規范,而土地管理法屬于管制性規范。兩類規范相互配合,共同實現公私法相互合作的目標。現行法賦予建設用地的用益物權屬性,亦即意味著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都屬于用益物權。
另一方面,我國《物權法》第151條對集體建設用地所做的規定雖是一種轉介條款,對集體建設用地規定得較為原則和簡單,但并沒有否認集體建設用地的用益物權屬性。立法做這樣的處理,至少具有兩個方面優點:一是為將來集體建設用地的修改提供緩沖余地。實際上,從立法釋義書的解釋來看,恰好印證這一點,即,物權法之所以對此問題僅做了原則性規定,主要是考慮到我國土地制度改革正在深化,各地的情況差異較大,土地行政主管部門正在進行土地制度試點和研究,等待總結實踐經驗,并在此基礎上規范和完善。目前物權法對此做出規定的時機還不成熟。但是,作為民事基本法律的物權法,還是有必要做出原則且靈活的規定,為今后土地制度改革留下空間;參見胡康生:《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頁。二是為集體建設用地法律性質等諸多事項提供廣闊的解釋余地。
此外,還須指出的是,將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解釋為用益物權,亦是順應當下集體建設用地改革政策的需要,是實現這一政策法律化的保障。既然中央政策指出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賦予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國有建設用地“同地”、“同權”、“同價”,那么,循此邏輯,就應該視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國有建設用地具有相同的法律屬性,這是同權之內涵的最基本要求。
其二,借鑒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的制度經驗,加強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的制度設計和規范配置,是開展土地開發權統一平臺制度建設的核心和內在要求。前文已述,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在制度設計和規范配置層面最大的差異主要體現在處分權能層面,即前者可在市場上自由流轉,而后者受到法律的嚴格限制性規定。二者之間的差異,就其本質而言,主要體現在土地開發權配置內容的不平等對待。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實現其與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的同等對待,其實質在于實現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之開發權與國有建設用地之開發權的平等對待。因而,現行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之開發權的制度設計和規范配置,當然亦同時為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之開發權的市場化流轉提供了經驗借鑒。
具體而言,目前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市場主要包括兩個:一是通過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等方式形成的一級市場;二是通過國有土地使用權轉讓等方式形成的二級市場。相應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市場亦應該包括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一級市場上,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的方式主要包括出讓、租賃、入股等;二級市場上,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的方式主要包括轉讓、出租、抵押、入股等。有關具體流轉方式的詳細規定,可參考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的相關規定。
在此,需指出的是,雖然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可為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提供經驗借鑒,但由于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是在集體土地上開展的交易,存在諸多特殊的因素,譬如,流轉交易的主體如何界定、流轉交易的客體如何界定以及流轉后土地用途如何規制等,仍須進一步論證。具體而言:
首先,關于交易主體之確定問題。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交易主體包括流轉方和受讓方。對于流轉方,亦即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所有權人,根據我國《物權法》的規定,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主體應包括權利的享有主體和權利的行使主體。前者是本集體成員集體所有,具體分為:村農民集體所有、村內兩個以上農民集體所有、鄉鎮農民集體所有;而后者主要包括: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委會、村內各該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小組、鄉鎮集體經濟組織。參見張先貴:《集體土地所有權改革的法理辨識》,載《中國土地科學》2013年第10期。因此,如果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話,其流轉方應為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委會;如果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屬于村內兩個以上農民集體所有的話,其流轉方應為村內各該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小組;如果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屬于鄉鎮農民集體所有的話,其流轉方應為鄉鎮集體經濟組織。
對于受讓方而言,參考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時對受讓方無主體資格和范圍限制的規定,對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的受讓方亦不應作出相應的限制,符合法定條件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都可以成為受讓方。但需注意的是,由于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所有權人是本集體成員集體所有,相對于民法上的財產所有權,顯然存在明顯的差異,即集體土地所有權主要是保障本集體組織范圍內集體成員的生存目標而設置的,參見韓松:《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權能》,載《法學研究》2014年第6期,第63頁。因而在本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出租或者入股時,賦予本集體成員優先購買權,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具有正當性。實際上,現行農村土地承包法所規定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時,同等條件下本集體成員享有的優先受讓權,就是較為典型的體現出集體土地所有權所具有的這一保障屬性。參見高圣平:《新型農業經營體系下農地產權結構的法律邏輯》,載《法學研究》2014年第4期,第79頁。另外,就法律具有的治理功能而言,這一做法亦有助于鄉村治理目標的實現。參見朱虎:《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中的發包方同意》,載《中國法學》2010年第2期,第70頁。
其次,關于交易客體之確定問題。主要存在以下兩大難題:一是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土地范圍究竟是城鎮規劃區范圍內還是城鎮規劃區范圍外?二是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土地范圍究竟是存量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還是增量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對于第一個難題,在筆者看來,應堅持公平原則,實行同等對待,即無論是城鎮規劃區內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還是城鎮規劃區外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都應享有與城市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同等入市的權利。但需注意的是,在當下改革試點階段,應將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限制在城鎮規劃區范圍外的土地。待時機成熟后,再將其擴大到城鎮規劃區范圍內的土地。這一做法主要有三點理由:一是基于改革策略的考慮,遵循漸進式的改革路線,賦予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范圍不宜全面鋪開,而應先從外圍即城鎮規劃區范圍外的土地試點開始,通過不斷地積累經驗,再做全面鋪開;二是在現行立法和實踐中,如果允許城鎮規劃區范圍內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直接入市,則勢必會出現城市內的土地存在國有所有和集體所有二元并立的局面,而這與我國現行《憲法》第10條“城市土地屬于國家所有”的規定存在沖突和矛盾。參見傅鼎生:《“入城”集體土地之歸屬——“城中村”進程中不可回避的憲法問題》,載《政治與法律》2010年第12期,第17頁。針對這一悖論的化解策略,雖然有學者借助解釋論開出的良方,即可以將城市土地解釋為“可以屬于國家所有,也可以不屬于國家所有;城市可以建設在國有土地上,也可以建設在非國有土地上” 。程雪陽:《論“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的憲法解釋》,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4年第1期,第169頁。但在筆者看來,雖然理論上這一主張可化解上述困惑,但若踐行這一做法,卻存在諸多實踐弊病:一是不利于當下“城中村”問題的解決。“城中村”作為城市管理中的一道傷疤,一直是國家治理中的難題。參見陸影:《社會空間視域下的“城中村”隔離問題》,載《學術研究》2015年第12期。如何減少甚至杜絕“城中村”現象的存在和蔓延,乃是國家治理“城中村”的基本立場。李小靜等:《“城中村”包容性治理路徑探析——以河北省為例》,載《世紀橋》2015年第12期;吳喆、孫亭:《上海松江區“十三五”城中村改造規劃研究》,載《上海房地》2015年第12期。將城市的土地解釋為可以集體所有,實為“城中村”在城市中的繼續存在提供了正當性辯護;二是不利于城市規劃管理的統一化和法制化。對于在城市的土地上既有國家所有的情形,亦有集體所有的情形,顯然是繼續沿襲城鄉二元化的管理模式的體現,不利于城市規劃管理的法制化和統一化。參見張磊:《“新常態”下城市更新治理模式比較與轉型路徑》,載《城市發展研究》2015年第12期;李太淼:《論逐步推進農村建設用地國有化》,載《中州學刊》2013年第4期,第20頁;田莉:《城鄉統籌規劃實施的二元土地困境:基于產權創新的破解之道》,載《城市規劃學刊》2013年第1期。另外,亦有學者指出,長遠來看,《憲法》第10條第1款關于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的規定仍應維持。但針對“入城”集體土地之歸屬的憲法難題的解決,則需要以人的市民化,尤其是農民的真正的市民化為基礎,來對《憲法》第10條第1款作出新的理解,即當某一城市的公民(尤其是原來的農民)均得享有平等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項權利時,該“入城”的集體土地才能屬于國家所有。參見黃忠:《初始化與“入城”集體土地的歸屬》,載《法學研究》2014年第4期,第47頁。同樣如此,這一建議亦存在明顯弊病,即間接承認了“入城”的集體土地的農民在沒有市民化之前,關涉該“入城”的集體土地應保持原狀,不能轉為國有土地,顯然,這一做法不利于城鄉規劃管理的統一化、規范化和法制化;三是如果在現階段讓城鎮規劃區內和規劃區外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同等入市,基于地理位置的區位優勢,真正能夠實現入市這一目標的主要是城鎮規劃區范圍內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顯然,這勢必會不利于城鎮規范區范圍外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之財產權價值的實現,不利于集體經濟的有效實現,并由此帶來城郊村和偏遠農村之間新的不平等。參見賀雪峰:《論土地資源與土地價值——當前土地制度改革的幾個重大問題》,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5年第3期,第36頁。
對于第二個問題,在筆者看來,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的土地范圍不僅包括存量,而且應該包括增量。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點:一是從形式層面而言,現行的政策并沒有否定增量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流轉,因此,從解釋學角度宜將存量和增量都納入其解釋范圍,不僅要允許存量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流轉,還應該允許增量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流轉;二是從價值層面而言,現行政策賦予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權利,其本質就是回歸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城市國有建設用地的“同地”、“同權”、“同價”,實現二者之開發權的平等保護,如果在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內部又區隔增量和存量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流轉,顯然,有違法律的平等原則;參見郭明瑞:《城鄉一體化建設的私法原則》,載《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第37頁。三是從實質層面來看,由于存量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數量相對有限,如果否定增量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那么也很難真正實現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市場價值,目前,我國存量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即鄉鎮企業建設用地總量僅約03億畝,多數村莊并無存量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參見蔣省三、劉守英、李青:《中國土地政策改革:政策演進與地方實踐》,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245頁。更遑論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的有效實現,參見耿卓:《農民土地財產權保護的觀念轉變及其立法回應——以農村集體經濟有效實現為視角》,載《法學研究》2014年第5期。甚至可以說,中央政策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并無多少實際意義。當然,從改革的策略來看,遵循改革的漸近路線,先允許存量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盤活存量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參見郭勇:《存量盤活:城市升級背景下集體建設用地開發模式創新——以佛山為例》,載《廣東土地科學》2015年第1期;姚勇:《存量集體建設用地和新增建設用地利用方式的理性思考》,載《浙江國土資源》2013年第12期。待經驗成熟后,再賦予其增量流轉權利,進而在立法上統一設計可行的法律制度規范體系,是立足于我國當下現實較為明智的選擇。
其三,積極回應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法效應,加強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配套法律制度建設,是實現土地開發權統一平臺制度建設的保障。由于我國現行的立法是禁止農村建設用地入市的,因而,在立法層面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勢必會沖擊現行法的秩序,帶來法的體系效應、制度效應和規范效應等諸多問題。具體而言,在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背景下,如何修改現行《土地管理法》第43條的規定?如何解釋城市土地的歸屬問題?如何處理好“小產權房”問題?等等,這些都是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所必然面對的難題,有力地解決這些問題,顯然是順利實現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的內在要求和保障。
在筆者看來,我國現行《土地管理法》第43條所確立的“先征后用”原則,即不區分公益性和經營性建設用地需要,一律通過征收來解決項目建設用地問題,成為中國土地征收制度引發諸多社會問題的根源。允許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顯然是對“先征后用”原則的部分否認,更具體地講,是對現行過寬的征地模式的否認。參見前引⑦張先貴:《土地開發權與我國土地征收制度之改革》;劉俊:《城市擴展加快背景下的征地制度改革》,載《江西社會科學》2009年第10期,第154頁。因此,縮小征地范圍,將集體土地征收嚴格限制在公共利益范圍內,是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配套制度建設的內在需要。至于這一目標的實現,則需要行政規劃權科學、民主的行使。參見劉玉姿:《征收的規劃控制》,載《城市規劃》2015年第8期,第56頁;張墨寧:《土地征收背后的規劃之弊》,載《南風窗》2011年第21期,第68頁。另外,上文已述,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尤其是允許城市規劃區范圍內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從事房地產開發項目建設,有可能使得集體土地上出現城市的現象。而這顯然與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的規定相矛盾。對這一問題的破解,在考察學界現有方案的基礎上,依筆者拙見,對于“入城”的集體土地之歸屬應該堅持一元化的國家歸屬模式,但在具體的實現方式層面,可選擇集體土地“概括國有化”參見陳甦:《城市化過程中集體土地的概括國有化》,載《法學研究》2000年第3期,第108頁。或者“整體轉權” 參見宋志紅:《城市化進程中集體土地的整體轉權》,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第14頁。模式。但在此需指出的是,在實施集體土地概括國有化或者整體轉權模式時,須嚴格遵守其相應的條件,踐行以保障原集體土地上的農民權益為中心的指導思想,即原集體農民已享有與該城市市民平等的市民待遇后,方可將該集體土地轉為國有。最后,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對于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上的“小產權房”問題如何處理自然成為無法回避的現實課題。在筆者看來,既然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可以進行房地產開發建設,那么承認其“小產權房”的合法性亦應被接受。當然,在具體處理時需注意的是,應根據不同類型的“小產權房”作不同的處理:對于符合規劃、質量合格的小產權房,應認定其合法,并對其予以登記確認,頒發其相應的產權證書;而對于不符合規劃、質量不合格的“小產權房”,應認定為違法建筑予以拆除。
四、未競之課題:面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更深層次思考
基于我國城鄉分割的差異性土地政策,使得我國現行法上的地權結構形態呈現出明顯的獨特性和復雜性面相。因而,解決中國當下的土地問題,須透視其本質,抽絲剝繭,揭開紛繁復雜之地權配置背后的面紗,無疑是面對這一問題的復雜性,尋找有效解決方案的理性選擇。伴隨著當下改革我國地權結構形態的呼聲日益高漲、地方土地改革試點政策的日益增加以及改革方案的漸趨成熟,不難看出,隱藏在現行地權配置背后的秘密亦逐漸明朗化,即,由國家獨占土地開發權來實施土地資源的管理,應成為解釋當下我國地權配置背后諸多問題的有力工具。
法律追求的終極價值是人之自由,農民亦有自由之追求。參見李勤通:《農村集體土地制度的憲法解釋》,載《北方法學》2015年第6期,第151頁。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實現其與城市國有建設用地的“同地”、“同權”、“同價”目標,實際上是將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之開發權回歸為集體享有的本質體現,更具體地講,是“做實”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之開發權的實質表達。當然,這一回歸僅僅是針對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領域。而對于長期備受社會各界爭議的宅基地使用權、承包地使用權等領域,雖然改革的呼聲亦較為激烈,但無論是現行政策還是立法,均沒有邁出實質性的步伐。立足于土地開發權視角,著眼于財產權保障原則和物權平等保護理念,從保障承包地使用權人受限的土地開發權角度來加快承包地使用權制度改革;從實現宅基地之開發權與國有建設用地之開發權的平等保護角度來加快宅基地使用權制度改革,無疑是從縱深的角度推動改革的實質表現。總之,改革我國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制度,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其改革的輻射和帶動效應是巨大的,可以說是我國當下農村地權制度改革的一個成功的縮影。未來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亦應該以此為方向,引入新的視角,立足于土地開發權層面,展開系統性的改革,方可取得實質性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