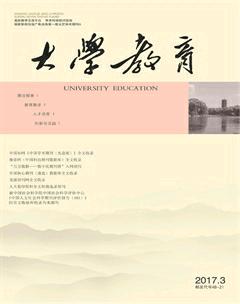多變與奴性:《動物莊園》中人性的探討
周萍 陳建平
[摘 要]《動物莊園》是喬治·奧威爾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反極權主義的政治寓言體小說。奧威爾用淺顯、明晰的文字呈現出了內容豐富、寓意深刻的種種可怕社會現象,毫無保留地攻擊當時所謂的“俄國神話”。當人們在品評其濃厚的政治色彩,談論其令人窒息的極權主義思想,研究其深刻的修辭的時候,卻很少關注背后導致這一悲劇發生的致命因素——人性。正是因為人性中的多變、奴性才導致了理想的破滅。
[關鍵詞]喬治·奧威爾;《動物莊園》;人性;多變;奴性
[中圖分類號] I10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437(2017)03-0092-03
喬治·奧威爾在西班牙內戰(1936—1939)時深受共和政府內部黨派之爭帶來的沉重打擊,這讓他重新思考“捍衛民主社會主義”的問題。[1]也正是斯大林這一時期在國際和國內政治上搞的一系列錯誤的決策讓奧威爾深入思考“民主”的問題。奧威爾稱斯大林在國內搞的“大清洗”實際上是控制一切左翼勢力而為了所謂的“俄國神話”,他認為斯大林這種集權的體現是對社會主義的破壞。為了揭露斯大林的這種罪行,奧威爾在1944年寫了《動物莊園》來反抗極權主義,反抗專制,捍衛民主社會主義。《動物莊園》描述的是一場動物革命的醞釀、興起和最終的蛻變:一個莊園的動物難以忍受人類主人的壓迫,由兩頭豬——拿破侖(Napoleon)和雪球(Snowball)作為領導者,帶領莊園所有的動物起來反抗,趕走了原來的農場主瓊斯(Mr. Jones),最終實現了牲畜統領莊園的愿望。農場也更名為“動物農場”,并且制定了農場的憲法——《七戒》。但不久,在領導者之間出現了分裂,名為雪球的領導者被名為拿破侖的領導者宣判為革命的敵人,為達到一人統領莊園的目的,拿破侖不惜捏造一切虛假證據,散發虛有消息,利用一切勢力趕跑了雪球這個政敵。然而擁有了絕對領導權的拿破侖,其特殊待遇不斷增加,最終演變成為和人類完全一樣的剝削者。憲法也由原來的《七戒》變為“一戒”,即“所有的動物都一律平等,但是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2]
一、革命的失敗
《動物莊園》中的動物們通過革命欲建立一個民主的動物王國,很明顯,他們最終失敗了。在豬成為新的特權階級之后,最初的革命理想早已被扭曲,被拋棄,動物們的生活比以前更糟糕,稍有不慎就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招致血腥與鎮壓。集權、血腥、暴力、謊言彌漫著整個莊園。然而這時候卻再也沒有一個“老少校”來奏響革命的樂章,動物們被奴役得連革命的意識都喪失了。人性中因權力誘發的多變和集權統治下的奴性在奧威爾辛辣的文筆下展現得淋漓盡致。
二、人性中的多變——拿破侖的體現
人性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然的精神屬性,人類所有的社會現象都是基于自身本性的映射。在心理學中,人的本能分為兩種,一是生的本能,即善良、包容等積極樂觀向上的行為;一是死的本能,即貪婪、殺戮和其他邪惡的行為。本能是人類的本性,是主導人們行為最強大的力量,亦是最基本的驅動動力。
心理學上的研究表明,不管人性是善良還是邪惡,其最終的目的都是利己——即心理利己主義(認為個人利益是人行動的終極目的[3])。一切驅使人類行為的動機都是為了獲得自我滿足感,故曰:利己是區分善惡的唯一標準。正如Joel Feinberg在他的著作《心理學利己主義》中提到的“任何人最終所能夠欲求或尋求的(作為目的自身)東西只能是他自己的個人利益”。[4]所以說,利己是一切行為的根本原因。因此,人性是會隨著自我的利益因素發生改變的,即當環境發生改變的時候,人性也是在不知不覺中隨之改變的,然而人們往往忽略了這一點[5],這也是最可怕的一點:當人們“合法”地做著罪惡的事情時,不但不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羞愧,而且還認為自己做得很對。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環境對人的影響在群體中將被放大到極致,那時,人們將全失去自我,成為環境的產物,而且還促其發展。從本質上來說這是自我利益所驅使的,由權力所誘發的。[6]
在老麥哲(old Major)的一番說教下,所有的動物都開始思考人與動物之間的關系。“人是與動物不共戴天的敵人”這點星星之火也隨著每晚大倉庫里的秘密聚會被撩起來。在那首《英格蘭獸》的旋律下,全體動物的腦中都涌現出絢麗的愿景。拿破侖和雪球在老麥哲去世后擔起了革命的重擔。很快在這兩頭公豬的領導和斯奎拉(Squealer)的游說之下,莊園的革命取得了成功。拿破侖他們開始制定《七戒》以管理莊園,一切的收割,播種也都井然有序地進行著。然而當豬成為統治階級時,拿破侖的性情卻發生了轉變。他代表特權階級,開始把牛奶滲入豬飼料中,接著又把原本用來平均分配的風吹落的蘋果收集起來專供豬使用,美其名曰自己是腦力勞動者,要保護健康以更好的管理莊園。拿破侖還將杰西(Jessie)和布魯拜爾(Bluebell)的小崽以對他們的教育負責的理由偷偷地養著,為自己所利用。這時的拿破侖獲得了統治權,漸漸地失去了革命的初衷。然而拿破侖的改變還不止這些,接下來他和雪球因意見不合在斯奎拉顛倒黑白的游說下煽動大家一起將雪球趕出了莊園;后來又開始和人做交易,搬進瓊斯住的房舍,睡覺,喝酒,做著人做的事情,并且在對莊園進行清洗的時候將許多無辜的動物也都暴利地解決掉,他認為作為統治階級的豬是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和高貴的,這一思想在《七戒》最后僅有的一條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2]拿破侖這一形象一點一點地改變都是由權力所引發的,隨著他權力的不斷擴張,他的特權也變得越來越多,他的心理也在一點一點地因為這種權力的膨脹而發生改變。正如Philip George Zimbardo在他的著作《路西法效應:好人是如何變成惡心惡魔的》中就有提到權力是釋放魔鬼的真正誘因。[7]拿破侖革命的初衷是在聽了老麥哲的一席話,為了那個理想的王國而革命,在那個王國里沒有壓迫,沒有奴役,人人平等而有富裕的食物,人人只為自己而努力。可是,拿破侖在嘗到權力所帶來的甜蜜時,在他成了莊園的領導之后,他就是極權的代表,他也就已經破壞了《七戒》,開始為自己的極權主義思想構建更多的合法性。為了鞏固自己的這種至高無上的權力和領導地位,拿破侖利用各種手段傷害一起革命的同志,通過內部的斗爭排除異己,驅逐政敵,獲得最高領導權,篡奪革命勝利的果實,最終和曾經的敵人——人類一同沆瀣一氣,壓榨曾經一起革命的同志們,成為不折不扣的極權主義者。
三、人性中的奴性——鮑克瑟的體現
在剖析鮑克瑟(Boxer)的時候,就已經看到了他身上的奴性,正如別爾嘉耶夫所說的“人的純粹的社會性即人的社會性的完全抽象,這會把人鑄成抽象的生存。剖析人時,視人為純粹的社會生存,也就把人放在了奴役的位置上”。[8]可以說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保證自我的生存狀態,才產生了不可避免的奴性。作為社會中的一分子,人類發現成群結隊的生存和生活在奴役之下,得到的利益比自由生活更大。于是,這種“趨利避害”的本能使得他們選擇了奴性的生活,這就是他們本性中的奴性。[9]
鮑克瑟可謂是莊園中的“勞動楷模”。他在瓊斯統治時期就一直持之以恒地工作,在拿破侖的統治下“他更是一個頂三,常常承擔了莊園里所有的活計”。[10]他讓公雞提前半小時叫醒他,他愿意比別人多干一些活,后來修建風車,他又提前三刻鐘起床。他對莊園的付出比誰都多,他有著一顆對莊園忠誠的心,但他的忠誠在集權統治下卻變成了奴性,愚昧。他那兩句口頭禪“我要更加努力工作”和“拿破侖同志永遠正確”就充分體現了他性格中的奴性。
在拿破侖集權主義之下,充滿的不是平等,是奴役。莊園的動物們干得越來越多,得到的卻越來越少。莊園里也沒有了一開始革命的平等、自由,取而代之的是階級化,一方面是以拿破侖為代表的集權統治階級,一方面是以鮑克瑟為代表的被奴役階級。集權統治的出現,必然導致奴性的出現。在沒有推翻瓊斯的殘暴統治的時候,所有的動物都過著十分痛苦的奴役生活。老麥哲曾經對動物們從一歲之后就忙碌著,不知道什么是空閑,什么是幸福,過著奴役般的生活提出質疑,認為這一切都不應該是命中注定。[11]這番質疑可以看出動物對集權主義存在著思考,他們看到了人性的丑惡,卻沒有看到動物身上也存在著這種極權主義的人性丑惡[12],恰恰這種丑惡在拿破侖革命后期的統治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他們性格中的奴性讓他們連思考的意識都已經被消磨得不存在了。斯奎拉對豬自己使用蘋果和牛奶這件事用這樣的語句解釋道:“實際上,我們中有許多豬根本不喜歡牛奶和蘋果。我自己就不喜歡。我們使用這些東西的唯一目的是要保護我們的健康。牛奶和蘋果(這一點已經被科學證明,同志們)包含的營養對豬的健康來說是絕對必需的。我們豬是腦力勞動者。莊園的全部管理和組織工作都要依靠我們。我們夜以繼日地為大家的幸福費盡心機。因此,正是為了你們,我們才喝牛奶,才吃蘋果的。”[13]然而斯奎拉的話從頭至尾都是與事實相違背的謊言,這是一個清晰可見的事實。但是,動物們對他的謊言一直都深信不疑,認為這是他做出的合理解釋,還對豬的統治感激涕零。在集權統治下這些動物已麻木。動物們面對拿破侖血腥屠殺的噤若寒蟬和屈從都是他們奴性的體現。動物們相信斯奎拉的謊言,他們根本不清楚這些問題背后的實質,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缺乏應有的智商,而是他們依賴于別人的控制,他們的服從是內心潛移默化的[14],也就是他們的奴性導致的。再說鮑克瑟,他將奴隸生涯的一生演繹到了極致,可是最后卻因為勞累過度而死亡,而他所擁戴的,一直都堅信的拿破侖同志,轉手卻將他的尸體賣給了屠馬場,以此換來一箱專供豬享用的威士忌。
在奧威爾的《動物莊園》中,豬最后成了統治者,成了集權主義者,權力成了人性多變的誘發因子。強權的背后,并不是為了維持所謂的莊園秩序,而是為了他自己的集權主義思想構建,其實,他也是權利的奴役者。而其他的動物則成了奴隸,過著奴役的生活,他們對此還沒有一點的思想領悟,沒有抱怨卻還加以感激地活著。正如列寧在《紀念葛伊甸伯爵》一文中指出:“不意識到自己的奴隸地位而過著默默無言、渾渾噩噩的奴隸生活的奴隸,是十足的奴隸。”[15]因此,可以說莊園中的動物都是十足的奴隸!實際上這就是人性中的多變與奴性導致的。
[ 參 考 文 獻 ]
[1][2][10][11][13] 喬治·奧威爾,著.張毅,高孝先,譯.動物莊園[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3] 劉余莉.中國倫理學中的利己主義[J].玉溪師范學院學報,2003(11):6-11.
[4] 陳真.心理學利己主義和倫理學利己主義[J].求是學刊,2005(6):48-54.
[5][6][7] Philip George Zimbardo,著.孫佩妏,譯.路西法效應: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
[8] 別爾嘉耶夫.人的奴役與自由[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
[9][14][15] 姚麗霞.從《動物莊園》談人的奴性[J].文藝生活,2012(3):106-107.
[12] 王雪.解讀奧威爾《動物莊園》里對人性的諷刺[J].短篇小說(原創),2015:65-66.
[16] 張桂鳳.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范式研究[J].大學教育,2014(15):76.
[責任編輯:鐘 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