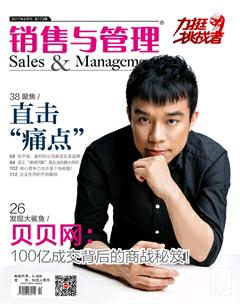振興實體經濟,不是追求要素低成本
穆勝
2016,據說是“黑天鵝”不停起飛的一年,“黑天鵝事件”的出現引發反思,一些人發現了新趨勢,一些人回歸了舊常識。
2016,振興實體經濟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網紅們不斷刷屏,吃瓜群眾一路點贊,互聯網上的情緒開始淹沒邏輯……
反思2016,本來應該是心靈雞湯式的按摩,但一群人的邏輯卻像是體育老師教的,所謂的反思變成了商業偽邏輯的復辟,的確有必要花點時間來澄清。
振興實體經濟,不是重農抑商
2016年,實體經濟是備受委屈的“萌寶寶”,高舉“實體經濟”的大旗就能自帶正義光環。而“實體經濟”的扛旗者們對于互聯網流通企業罵聲一片,仿佛流通不死,中國不富。
振興實體經濟,不是要做新時代的“重農抑商”,在古代,這就已經被證明是無知政策。生產和消費是天然分離的,兩者之間需要流通環節(或者稱為渠道、分銷)來連接。流通起到幾個作用,主要來說:一是信息傳遞,二是信譽背書,三是物料流轉。這樣一來,消費者才可能買到自己喜歡的產品。流通越發達,生產才能越受刺激,否則,實體經濟如何振興?
我們一度以為世界是平的,任何用戶都可以直連任何產品,任何廠商也可以直連用戶,但實際上,過于離散的兩端形成了龐大的信息,無論是供需哪方,依然是無所適從,依然需要一個“中介”。
如果是京東,你可以叫它“自營”;如果是阿里,你可以叫它“平臺”;如果是美麗說、蘑菇街,你可以叫它“社群”;如果是羅輯思維,你可以叫他“IP”……這就衍生了自營電商、平臺電商、社群電商、IP電商……
互聯網形成的去中介化,實際上是去串聯中介(層層分銷),形成一個個并行的、新的“大中介”和若干并行的、場景化的“小中介”。從春蘭、格力等空調廠商在上世紀“殺大戶”,自建渠道排斥蘇寧等流通企業,到現在廠商們高喊“打掉馬云,中國實體經濟才有未來”,甚至成為了一種“政治正確”。其實,廠商想要甩掉流通都是必然的天性,但是,除非你找到方法做“產銷(銷售)一體化”,甚至“產消(消費)一體化”,一切都是基于自己利益出發的套路,一樣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批評馬云,可以說阿里的假貨問題,可以說平臺太強勢的問題,但卻不能批評流通,流通無罪。
振興實體經濟,不是反金融
2016年,險資不斷興風作浪。自從姚員外舉牌萬科、格力,險資就成為了一股淹沒實體經濟的洪流。隨后,上面強勢發聲,打壓之下,姚員外服軟,承諾逐步退出。
一時間,振興實體經濟的聲音此起彼伏,金融成了十惡不赦。有人甚至拿出美國次貸危機來說明金融工具制造了多大的罪惡,還有人拿出老干媽作坊式經營的思路說明遠離金融有多明智。
中國真的不需要金融了嗎?哪個所謂“實體經濟”的企業敢說自己不需要金融?資金作為企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是任何企業都不可缺少的。而在企業(項目)缺少資金的情況下,資本通過吸納社會閑散資金,并投入退出企業的過程獲得收益,本來就是天經地義。
進入哪些企業?肯定是價值被低估的企業,所以,萬科、格力等優質企業才會成為資本進入的對象。所以,回過頭來看險資舉牌的現象,你很難用道德來批評他。即使用道德作為理由打壓市場行為,這也不是程序正義,根本不值得吃瓜群眾們叫好。要怪,只能怪制度沒有設計好,修改制度才是長久之計。
其實,股權和債權融資都是手段,一級市場、一級半市場、二級市場,所有可能的市場都是企業融資的有效途徑。進入哪種市場就要遵守哪種市場的規則,不能規則有利于你的時候就變成圣人,規則不利于你的時候就變成小人。你要嫌股權融資會帶來野蠻人,你就像華為一樣不上市不就得了?
中國不是金融產品泛濫的問題,而是有效金融產品不足的問題,是金融市場不規范的問題。典型的現象就是,“錢多”與“錢少”矛盾并存,即金融機構錢多,貸不出去,但是需要用錢的企業錢少,貸不出來。拿著牌照的金融機構缺乏對于市場的精準判斷,行情稍好就催企業來貸款,稍微有風吹草動就抽貸,翻臉比翻書還快,搞得真正的“實體經濟”叫苦不迭,這才是問題。進一步,這種矛盾催生了大量的地下錢莊、影子銀行,造成了監管的真空地帶,這才是更大的風險。
金融不邪惡,邪惡的是沒有規則的金融,邪惡的是規則只為一部分人服務的金融。
振興實體經濟,不是追求要素低成本
2016年,還有個關鍵詞是“死亡稅率”。財政學者李煒光批評中國征稅過重,認為40%的稅負對中國企業意味著死亡,可以叫“死亡稅率”。玻璃大王曹德旺也對“中國稅收全球最高”進行吐槽,直言中國“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國貴”,并宣布將投資10億美金到美國建廠。一石激起千層浪,關于中國失去實體經濟的成本優勢的說法甚囂塵上,恨不得所有的企業都遷往美國。
中國經濟長期靠投資拉動,缺乏內生性的消費拉動,造成了增長的瓶頸,這是不爭的事實。在投資的拉動邊際效用遞減的背景下,減稅、補貼,讓企業休養生息是應有之義,我完全贊成。
但實體經濟的崛起,絕對不能僅僅依靠減稅,甚至,大多企業把目光盯在這類要素成本上,是誤入歧途。當前,實體經濟最大的問題是“粗放型”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下,由于缺乏技術創新,大量的企業長期生產同質品,處于一個價格區間且進行價格血戰,最后導致價格被壓到最低。
這種模式下,消費怎么會有動力?要說中國的產能過剩,絕對是瞎說,不是產能過剩,而是落后產能過剩,而是有效產能過剩。不是我們的消費能力不行,是產品不行。
當產品乏力,企業的生存自然會依賴生產要素的低價,說白了,就是賺點辛苦錢。所以,他們才會對生產要素的價格如此敏感,因為,一旦某種要素價格上漲,立即就會讓其盈利為負。
但是,真正的成本優勢并不是要素成本最低,而是整體成本優勢。整體成本優勢不是要素價格的樸素相加,而是依靠管理釋放的紅利。舉例來說,華為在2003年到2007年期間營收規模高速增長,但營業利潤率卻從19%下降到10%,凈利潤率從14%下降到了5%。任正非清晰地認識到了管理出現的問題,決心徹底變革。2007年初,他親自給IBM公司CEO彭明盛致信,要求把IBM規范的財務流程植入到華為的運營流程中,實現收入與利潤的協調發展。于是,華為上馬了著名的IFS項目(集成財務系統),基于同一的IT構架,重塑了公司的業務流,讓每個業務環節都能把賬算清楚,這就根除了“跑冒滴漏”,形成了巨大的成本優勢。
這才是正道。
振興實體經濟,不是反管理變革
2014年開始,“管理變革”和“組織轉型”成為了企業頻繁提及的主題詞。大多企業都意識到了科層制帶來的問題,老板們看得見商業模式的變化趨勢,但企業卻猶如一艘大船,尾大不掉。毫無疑問,為了應對互聯網時代的不確定性,企業需要變得更輕、更快、更強。
恰逢此時,海爾、華為、萬科等傳統企業在組織轉型上風生水起,谷歌、Facebook、Netflix、小米等互聯網企業又在組織模式上標新立異,加上KK的《失控》、安德森的《創客》、克萊·舍基的《人人時代》等書籍的推動……幾乎所有的企業都開始高喊要“自組織、平臺化、無邊界、去中心”。于是,阿米巴、合弄制、合伙制、無邊界組織、項目制……一系列“新組織模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被企業引用。
但一股風潮之后,企業的組織轉型卻陷入了沉寂,真正轉型成功的企業少之又少。這讓不少企業直呼上當,一面高呼海爾、華為學不會,一面又開始高呼“回歸常識”。自己在心中幻想了一個林志玲,和她在夢里戀愛了一番,然后就說人家脾氣不好,不能過日子,這實在讓人嘀笑皆非。
這里需要澄清。
一方面,企業在從0到1的“種子期”,需要科層制。科層制帶來秩序、效率和穩定性,并依賴這些優勢為企業累積基礎的資源優勢,是繞不過去的。要激活這種組織,屏蔽掉科層制的問題,依賴流程再造、完整的KPI體系,甚至依賴創業初期的團隊熱情,這都沒有問題。
但很多企業,爬都還沒學會就想飛,基礎的部門分工、業務流程、授權體系都沒有建立,就強行要平臺化,建筑在沙堆基礎上的高樓,結果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企業在從1到n的“發展期”,必須要面臨科層制還是平臺制的選擇。這個時候,如果你確認要走“平臺制”,就必須以“自殺重生”的心態推動變革,這種變革絕對不是改良式的、漸進式的。
有不少企業,雖然走過了種子期,但在轉型時卻往往是拿到一個名詞就放到企業里去按自己的想象實踐,結果自然也是四處碰壁。我的團隊最近做了一個研究,基于40多家企業樣本梳理了轉型的陷阱,發現了很多“想當然”。比如,有的企業依然是強管控型,財權、人權、事權都沒有下放下去,但卻要求部門按照經營體來運作,這是典型的異想天開。再比如,有的企業把三權下放下去了,卻沒有綁定經營者的利益,沒有事后風控,這也是癡人說夢話。
進一步看,這些企業的問題在于根本沒有轉型的決心。海爾人單合一做了10年才算是步入正軌,開始釋放紅利。華為的IPD(集成產品研發)、ISC(集成供應鏈)、IFS(集成財務管理)也扎根做了10年左右,才有今天在行業中的江湖地位。你沒有研究他們走過的路,憑什么說自己一定能復制出別人的輝煌?難道說你比張瑞敏、任正非還聰明?
德魯克說,管理不是一門藝術,也不是絕對的科學,而是一門實踐。實踐不是喊口號,你袖子擼得再高,不干實事,也是枉然。
振興實體經濟,不是反互聯網
2016年,所謂代表“實體經濟”的幾位網紅宗慶后、董明珠、李東生集體向互聯網勢力開炮,炮火集中砸向馬云提到的五新理論,即“新零售,新制造,新技術,新金融與新資源”。娃哈哈董事長宗慶后更是言辭激烈,認為除了“新技術”其他都是“胡說八道”。
幾位網紅對于實體經濟的認識真是讓人亮瞎雙眼,如果用這樣的思路去振興實體經濟,的確讓人看不到中國制造的未來。商業社會發展到現在,互聯網已經成為底層邏輯,不是你拒絕不拒絕的問題,這就是你呼吸的空氣。另外,互聯網也不反動,反動的是固步自封的心。
其實,互聯網并沒有衰減實體經濟的活力,反而帶來了契機,關鍵是你看不看得見而已。振興實體經濟,一定要走向實業+互聯網。事實上,馬云說的“五新”,并不遙遠。
新零售——遍布傳感器與交互設施的場景,線上線下一體化,后端供應鏈由無人機、無人車、X倉(無人倉)連接。當前,幾個大的電商企業已經在這方面進行了布局,像京東已經將X倉變成了現實,并成立了專門的X事業部來研發無人機和無人車。
新制造——用戶鼠標點擊決定供應鏈形態,幽靈工廠分布式存在,生產力隨需調用,云端共享,全鏈條數據化。需要強調的是,這絕對不是幾個老人想的“機器換人”,而是基于互聯網的大規模定制,所有的機器必須由用戶來指揮。這方面,GE已經上線了Predix,西門子已經上線了Mindsphere,國內,海爾上線了Cosmo,沈陽機床做了Sesol……
新金融——基于供應鏈全數據化的“數據貸”,風控模型算法化,隨時迭代,秒級響應的放款。阿里金融、中興飛貸等等企業都是數據貸的典型,他們的放款效率和風控水平遠遠高于傳統金融機構。
另外,不得不提到的是,人工智能并不遙遠,其會成為改變商業世界的關鍵變量。當商業的世界里遍布傳感器,數據會急速膨脹。此時,算法必須快速進化,人工智能成為了必須的選擇,而人工智能的強大也會成為改變商業進程的一股強大力量,大量以數據分析為生的人將被淘汰。當每個工廠、每個倉庫、每個場景都遍布CPU,數據會變成可執行的指令,而這些指令的執行直接通過機器來實現,不再需要那些藍領工人。
幾位網紅肯定是聰明人,但為什么他們看不到這些“新”?要么是老人家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懂新世界;要么是老人家們活在自己的利益里,不愿承認新趨勢。前者好比對一個穿慣了大貨(量產服裝)的人講高定(高級定制)的好處一樣,講不通。后者好比讓柯達做數碼,沉沒成本太大,為何要做?
真不懂,假不懂,沒有關系,時間會證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