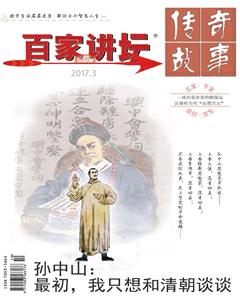關(guān)山月夫婦:執(zhí)手相攜,共聞花香
潘彩霞
1934年,冬天的廣州仍舊細(xì)雨纏綿,小學(xué)老師關(guān)山月正在煤油燈下批改作業(yè),一篇日記讓他頓生憐惜:“父親病倒了,沒錢請醫(yī)生,也許我要被迫退學(xué)……”關(guān)山月翻到封面一看,學(xué)生姓名是:李小平。
這個16歲姑娘是關(guān)山月班上年齡最大、成績最好的學(xué)生,曾經(jīng)同樣窮困的關(guān)山月頓時對她起了惻隱之心。為了幫助李小平,他出錢為她父親看病,為她申請到免費的三餐,可命運還是不可逆轉(zhuǎn),不久,李小平的父親去世了。
屋漏偏逢連夜雨,李小平之前為了給父親治病,借了不少錢,此時債主找上門來,逼迫她“沒錢就拿人抵債”!走投無路之下,李小平奔向珠江邊準(zhǔn)備一死了之,幸好被學(xué)校的一名雜工相救。從此,她住在學(xué)校里,靠兼做雜工維持生計。那時,身為教師的關(guān)山月帶著弟弟也住在學(xué)校,李小平便常常幫他洗衣掃地,時間一長,彼此印象頗好,漸漸有了愛意。第二年秋天,在其他老師的撮合下,24歲的關(guān)山月和17歲的李小平結(jié)婚了。
婚后,李小平承擔(dān)了所有家務(wù),幫丈夫照顧起年幼的弟弟,時間充裕后,關(guān)山月終于有機會拾起了自己最愛的畫筆。
但關(guān)山月一個人的工資養(yǎng)活三個人,日子捉襟見肘。為了讓家人吃好,李小平悄悄勒緊了自己的褲腰帶。一個傍晚,關(guān)山月看完畫展回到家里,見桌上放了三碗米飯,他端起一碗便吃,不料剛扒拉了兩口就呆住了—淺淺的一層米飯下赫然反扣著一個小碟子。關(guān)山月再一看,這是妻子常坐的位置,難怪她吃飯時經(jīng)常裝作干活,一個人躲到廚房去吃。
關(guān)山月的心被浸濕了,此后更加疼愛妻子,努力作畫,以補貼家用。關(guān)山月的繪畫風(fēng)格一天天成熟起來,并被嶺南畫派領(lǐng)袖收為入室弟子,原名關(guān)澤霈也改名為關(guān)山月。
眼看著一家人的日子漸漸好轉(zhuǎn),1938年,廣州不幸淪陷。炮火硝煙中,關(guān)山月與妻子失散,無奈之下,只好追隨老師棲身澳門普濟寺。因身無長物,關(guān)山月每餐只能買一個面包充饑,寺里的和尚勸他:“不如出家吧,好歹有口飯吃。”想到國內(nèi)戰(zhàn)火連天,妻子和弟弟生死不明,關(guān)山月嘆息著說:“我妻子早早失去父母,無依無靠,跟著我這幾年,也沒過上一天好日子。現(xiàn)在我們雖然失散了,我無論如何也要找到她。”
關(guān)山月一邊在澳門滿懷悲憤地作畫,一邊連連給李小平寫信,可是,尋妻信如石沉大海。幾經(jīng)周折,關(guān)山月才終于打聽到妻子的住處,立馬寫信前去問候情況。突然接到丈夫的來信,李小平雙淚長流。
有感于身世飄零、國家動蕩,關(guān)山月用滿腔悲情繪就了《從城市撤退》《中山難民》等宣傳抗日的作品。其間,“抗日畫展”在澳門、香港展出后,引起了文化界高度重視,媒體稱其為“嶺南畫界升起的一顆新星”。
一舉成名天下知,關(guān)山月告別恩師回到內(nèi)地,分別三年后,在廣東韶關(guān),關(guān)山月終于和妻子、弟弟團聚。當(dāng)天晚上,關(guān)山月刻了一枚印章作為紀(jì)念,上面寫著“關(guān)山無恙明月重圓。”
患難夫妻情更堅。之后,關(guān)山月執(zhí)著于名山大川,李小平便伴隨他走遍大江南北。他深入生活,收集素材,邊寫生,邊創(chuàng)作,并沿途舉辦個人畫展,以賣畫維持生活。遇到賣畫收入不佳時,李小平便瞞著丈夫,悄悄變賣衣物、首飾來籌生活費。但即使這樣,她也從來沒有想過要放棄。畫完桂林山水,又到貴州花溪,再沿岷江入川,漫漫旅途中,他們執(zhí)手相攜,共聞花香。
緩慢的愛更易長久,時間已經(jīng)讓他們成為對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為了畫下黃果樹瀑布的全貌,關(guān)山月不顧危險,堅持爬上危巖,李小平隨后也一步一步爬上去,悄悄站在他的身后,生怕他摔下去。他畫完了,她松一口氣,這才發(fā)現(xiàn),因為緊張和害怕,自己的全身已經(jīng)濕透了。入川后,李小平得了肺水腫,關(guān)山月衣不解帶,全心全意照顧她。看著病床上的妻子,他忍不住感慨:“你對我那么好,現(xiàn)在該我對你好了。”一段時間后,李小平的病情有了極大好轉(zhuǎn),二人再次踏上了寫生的路。
愛,是彼此精神上的共同成長。盡管多年苦行僧一樣四處漂泊,但她從未抱怨過,反而受他的影響,也愛上了畫畫。
1943年,關(guān)山月決定進(jìn)軍敦煌。在敦煌石窟,他著魔一樣地臨摹佛像,有時爬在佛龕里,有時半跪在供桌上,他臨摹到哪里,她就舉著蠟燭跟到哪里,除了遞上紙筆顏料,還全神貫注地注視著他:他頭頂上有蜘蛛網(wǎng),她就悄悄替他撥開;他一舔嘴唇,她趕緊遞上水壺,可是,自己的嘴唇干裂,她卻絲毫沒有察覺。在他的影響下,她也迷上了那些菩薩、飛天,二人心照不宣的默契極大地鼓舞了關(guān)山月,他臨摹的速度也加快了。他筆下的80幅壁畫,每一幅都是在她高舉的燭光下完成的。
從敦煌歸來,關(guān)山月舉辦了《西北紀(jì)游畫展》,各界為之轟動。郭沫若稱他是“中國國畫的曙光”,朱光潛參觀后稱贊:“先生之畫法,備中西之長,兼具雄奇幽美之勝,竿頭日進(jìn),必能獨樹一幟……”甚至有人出重金要全部收購,均被關(guān)山月斷然拒絕。
敦煌壁畫是他和她愛情的結(jié)晶。此后,她取“煌”的諧音,改名李秋璜,以此來紀(jì)念那段在敦煌的難忘時光。
八年抗戰(zhàn)結(jié)束后,關(guān)山月帶著妻子回到了闊別十年的廣州。1948年1月,關(guān)山月在廣州市藝專擔(dān)任教授兼國畫課主任。1959年,關(guān)山月和著名山水畫家傅抱石受邀到北京,為人民大會堂畫《江山如此多嬌》。這一藝術(shù)成就使得關(guān)山月蜚聲中外。
他好不容易迎來了人生最順?biāo)斓臅r光,卻于1966年再次被關(guān)了起來。因為眉心有痣容易被認(rèn)出,關(guān)山月經(jīng)常遭到對方的拳打腳踢。李秋璜被嚇得膽戰(zhàn)心驚,她用膠布把關(guān)山月的痣蓋住,給他做了厚厚的棉背心以防被打傷內(nèi)臟,后來,全家都被趕到豬圈居住。有人勸李秋璜離婚,她面色凜然:“我們早就是一個人了,要死也要死在一塊兒。”
十年后,噩夢般的日子終于煙消云散,關(guān)山月重新拿起了畫筆,此時,李秋璜也有了一定的國畫造詣,她陪他到西沙群島、到尼亞加拉大瀑布觀光寫生,去美國講學(xué),到日本開畫展,夫婦情深似海。
關(guān)山月的名片上始終印著兩個人的名字:關(guān)山月、李秋璜。是深沉的愛讓他們彼此活成了對方的樣子。
1993年,李秋璜因腦溢血去世,關(guān)山月憶起妻子在敦煌為他秉燭照亮壁畫的往事,心潮起伏,含淚作挽幅:“敦煌燭光長明。”斯人雖已去,她對他的愛卻如燭光長明,照亮世界。接下來的日子,關(guān)山月帶著妻子的愛度過了幾個春秋,于2000年夏天與世長辭。他和妻子終于又可以在另一個世界里互相依偎、陪伴了。
編 輯/夏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