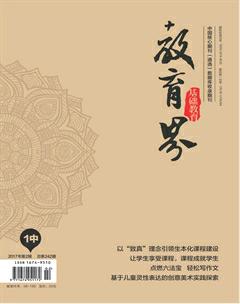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陸嘉明
(續前)
42
少時讀三國,最是敬佩和喜歡的不是別人,而是諸葛亮,孔明是也。昔有論者臆斷羅氏筆下斯人已被“神化”抑或“妖化”了,愚卻不以為然。迄今暮年再三賞讀,栩栩如生于目前的依然不是“神”不是“妖”,明明是活生生的人,一個有血有肉有靈魂的人,一個叱咤風云且從容應對于亂世并卓然超群屢建奇功的智慧人物。
當然,羅氏用筆時或浪漫點染,甚至撲朔迷離呈現出神秘色彩和“魔幻”情景,然其筆觸多為白描和寫實,鋪敘間細節精微,對話時情理互滲,一一皆在大起大落的情節跌宕中風起云涌,在時緩時急的節奏間潮起汐落,人物個性和豐神于斯歷歷呈現,凸顯無遺,給人以難以磨滅的深刻印象。
毫無疑問,諸葛亮,確是文學藝苑中一個難得的典型人物,其審美魅力不僅在英雄功業和品操風范,不僅在經緯奇才和人生傳奇,而在不負蒼生的大胸襟,大智慧,大氣魄,大氣象,更在以儒學行世且兼及老莊哲學和諸子雜家學說之精華,以一種富有時代和個性特征的文化智慧左右逢源于三國亂世,神出鬼沒于紛紜爭斗,審時度勢獨觀大略,雜糅諸說獨辟蹊徑,每每以奇思妙想出人意表,以瑰異謀略出奇制勝,在當時高明之士層出不窮,然無一人可望其項背,時人無一不佩而服之,甚至敬而畏之。
千百年來流傳青史和民間,并經文學、戲劇、傳說、評書、話本、曲藝等藝術形式的反復加工、想象和渲染,諸葛亮的形象,日漸演化為代人心中的智慧化身,庶幾成為一種智慧的象征,抑或智慧的文化符號了。
43
智慧,是知、智、慧的水乳交融,不分彼此,然三者雖俱同義復合的意思,皆有聰明才能的內涵,但細究起來,又各有側重和不同。因其同而能諧,因其不同而能和,從而譜成一首和諧動聽意味悠長的協奏曲。
古人說,凡有智慧者,能方能園,可動可靜:園是乾,方是坤;動則園,靜則方,正所謂“方若合義,園若用智”,二者相和相合,即是一種天地精神與文化情懷。又,園是晝,方是夜;動如陽,如晝之日,靜為陰,如夜之月,體現為日與月周而復始的時間節奏和陰陽相長與流變而平衡的生態節律。可見,方園動靜,既是空間概念,又是時間概念。人處特定的時空之中,智慧的萌生和成熟,是天賦和實踐經驗以及后天習得相與作用的結果,自始至終或多或少都會受到這一富有哲學意味的滋潤和制約,從而形成各個體高低深淺不同的智慧水平。
當智慧運用于人類活動時,則表現為處事應世的認知力、思考力、思辨力、解析力、判斷力、決策力、鑒賞力、應變力……悉皆呈現出“美和力”的生動形態。“美”是感性態,“力”是理性態,感性與理性的和解,也即是形而下和形而上的自然溝通和協調。培根曾說“知識即力量”,愚卻別出奇想:“智慧即力量”。不知讀者諸君可認同否?
44
那么,就讓我們來細加考察一番,就此打開思路,汲取靈泉,或可于評判歷史是非和臧否人物有所裨益。
知,看似平常而簡單的一個詞,體現在諸葛亮身上,則呈現出邈遠的時代視野和深厚的文化內涵。雖說常人皆有知,但深淺高低優劣差之遠矣。
諸葛亮所知出乎常人者也遠矣。從大處論,其知有三,即知天;知地;知人。如果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仰觀天象之變化,俯察地理之利弊,通常所知者,充其量只是一種知識,一種經驗,或一種能力一種學問,那么,諸葛先生最為令人贊賞的是,可藉此靈活變通地運用于亂世政治形勢的分析和發展趨向,這恰是《隆中對》最為精彩的筆墨,不妨細研其意以賞就中況味。當劉備向其討教天下方略時:
孔明曰:“自董卓造逆以來,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勢不及袁紹,而竟能克紹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用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今劉璋暗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此亮所以為將軍謀者也。惟將軍圖之。”言罷,命童子取出畫一軸,掛于中堂,指謂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圖也。將軍欲成霸業,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先取荊州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后可圖中原也。”
孔明雖自謙“年幼才疏”“乃一耕夫”,卻傲然獨立時代的文化制高點,縱論天下形勢,穿越于歷史與現實之間,壯思遄飛出入于時空內外,既揮灑自如地運用天、地、人的“本位”之知于動亂局勢,又氣定神閑地漫出三足鼎立的“出位”之思于未來走向,真可謂融天地之意與人間情懷于一爐,合方略大觀與分治之術于一體,呈現出那個特定時代的文化智慧和思維張力。
知者遇知音,一個胸次磊落坦蕩,直言大略痛快淋漓,浩浩然立言運斤如風,鏗鏗然金石擲地有聲,一個誠心茅廬三顧,聞之如醍醐灌頂茅塞頓開,平生素志于斯盡意矣。一個深感知遇之恩從此永結亂世之緣,出山輔助明主南征北戰,不負平生之愿和經緯之才,終而三分天下得其一,留得青史美名;一個求賢若渴如魚得水,就此待若知己,歷盡艱難曲折成敗得失,終而開創了一朝蜀漢帝業,并完成了踐行儒家文化的人格范式。
愚欲試問:劉備若無諸葛之助,果能圓其幼時所立的桑樹之夢嗎?
愚又試問:諸葛亮若不知遇一代明主,果能出山建功立業而踐行德智雙馨的非凡人生嗎?
不是嗎?水流青山而澄明山依流水而蔥郁。正因為諸葛亮和劉備的這段曠世奇緣,歷史越過金戈鐵馬的非常歲月,收藏了一個亂世的波詭云譎的史詩故事。
不是嗎?古老的滄桑深處,也會閃現出有溫度的光明。時間在春秋代序的曉風殘月中,也收割了一個民族的文化智慧啊。
45
智慧,籠統地說是聰明才智,也許太粗疏了。這是人之所特具的處事處世的高端智力和能力。如若細研起來,“智”和“慧”作為詞素組合自有上述通義,但二者也有所區別,起到相與側重和互補的作用。
智,從知,從日,有說:日以感知萬物見識久積而生智。愚則還有一解:日,行于天而光耀萬物,使之形態畢現,此可借指天下一切可以感覺的有形事物,人即可通過視聽等感覺器官由表入里產生感知活動,并由對外界的感知經驗形成新的見識和日以漸進的主觀感受,乃至提升為規律性的認識和知識結構。這就是人的由外而內、由形而質、由感而知、由“知”化“智”的思維過程和認知成果。
可見這種智力活動,始于感“器”(外物)而終于認知(內質),即感于外物進乎心智而如日之明,頗有“形而下謂之器”的意味。
慧,從豐,從心,意為睿智才情發乎內心而顯現于外象則豐盈無限,恰如風行水上漣漪滉漾而生氣靈動,又如云馳空濛含潤閃耀而無幽不照。可謂心出慧悟機思若流,無論是由外而內再由內而外,抑或由實而虛再由虛而實,悉皆慧智圓通豐沛,不逆心靈卻能悟得世間至理,則大有“形而上謂之道”的意味。
智慧,作為“智”與“慧”二者語義相近而略異的詞素組合,表現了人類智力和能力高端綜合的思維品質,以及語言與行為的表達才情,除個體所特具的天賦慧質之外,皆為社會實踐經驗的人文積淀和間接經驗的知識習得,每每因人而異,因時而異,相距迥遠矣。
因之故,人有智慧者,也有無智慧者;有大智慧者,也有小智慧者。諸葛先生無疑已為歷史證明,“知性”其識,通曉古今而知一萬畢;“智性”其思,韜略絕倫而道濟天下;“慧性”其心,天資超拔而機思若流,真大智慧者也。
香為佛燃,才為世用。諸葛亮所處的時代,世是亂的,路是亂的,人心也是亂的。因其亂,才需要大智慧者的指點迷津,強者的擇路而從,蕓蕓眾生的人心所向;因其亂,智者才更有機遇發揮超常的大智能,強者方可揮戈向向平定天下,黎民百姓定能安居樂業娛樂升平矣。
亂世,是苦難深重的時代,也是英雄輩出的時代。由亂而治,是智者、強者和人心相與作用的時間過程,也是諸方力量斗智斗勇并付出慘痛代價的血腥過程,在這由亂而治的非常過程,有大智慧者,聽得見天風地籟,也聽得見人喧馬嘶,更聽得見從雜音噪聲交渾的世間傳出來的正義之聲和對英雄的深情召喚。
于是,身居山野草廬卻志存高遠的諸葛亮應聲而出了。
鳥擇良木而棲,人隨明主而起,從此一發不可收。
天生其才必有用,滄海橫流方見英雄本色。劉備當時寄人籬下,唯據新野這一彈丸之地,與曹、孫相比力量相差懸殊,雖處弱勢,幸得諸葛之助啊。非常的世道,遭遇非凡的智慧,依然縱橫捭闔于強者之間,運籌帷幄決戰千里之外。智謀頻出,每每出奇制勝,瀕臨危境,每每化險為夷。其智慧一時為天下之冠。
在你死我活的殘酷殺伐中,自有一種從容,恰如淡香拂云;一種慧骨,恰如雪瑩梅間,敬者愛者有之,嫉者恨者有之,甚至為各自利益計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者也有之。因而在各方的較量角逐中,演繹出各臻其妙爭奇斗勝的故事,呈現出潮起潮落的歷史節奏和風生水起的文化風致。不知此為智者之幸,還是智者之悲呢?
46
以愚之見,諸葛亮的大智大慧,光照四射卻聚焦在一個“應”字上。
應,人處山谷幽壑,遠山呼而近谷應,一呼一應,響應寥廓,天籟無邊。這是一種合乎天地節律的自然之聲,人處其境聞呼而應,則是一種天人相和的激發之聲,既具胸臆抒發的痛快,又有慧心為之一振的感動和徹悟,其中深蘊的是一種人生的達觀和生命的大智慧。
應,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相互關系中,表現出千姿百態的感性形態和深淺互襯的理性內涵,諸如有應而和之,應而答之,應而付之,應而承之,應而受之,應而對之,應而變之……往往是矛盾的碰撞和統一,是感性與理性的表里和互滲,其中意味令人深長思之。
應,是哲學,一種關乎智慧理性的哲學。
應,也是美學,一種付諸感覺呈現的智慧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