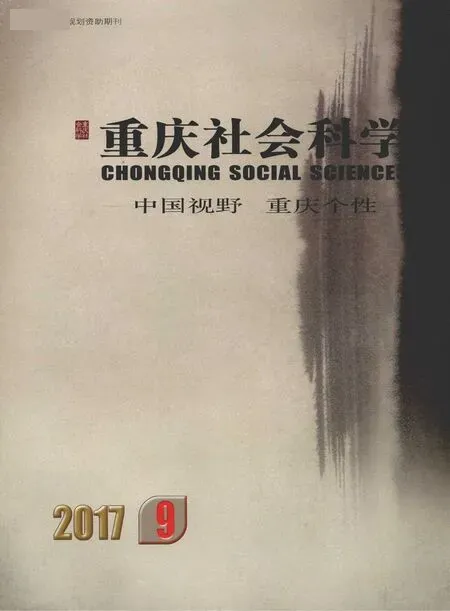高麗時期詩論《補閑集》與《破閑集》比較*
姜 夏 尹允鎮
高麗時期詩論《補閑集》與《破閑集》比較*
姜 夏 尹允鎮
高麗時期是朝鮮古代漢文學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期,朝鮮詩話也出現于此時。這里重點研究高麗時期的詩話集《補閑集》,將之與《破閑集》進行比較,從中窺探朝鮮古代詩學思想的早期構建。分析發現《補閑集》中收錄的作家和詩作在數量上遠多于《破閑集》,所反映的文學批評觀點也更加客觀和系統,同時在歐陽修《歸田錄》的影響下添加了“笑談”和“國史補”要素,兼具文學意義和史料價值,是一部接受并融合了本國傳統和外國文學的著作。
崔滋 《補閑集》《破閑集》 文學批評 外國文學
朝鮮高麗時期,特別是高麗中后期,是朝鮮漢文學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期。韓國學者趙鐘業早在70年代便對高麗王朝的漢詩創作有高度評價。
大抵韓國之詩,莫盛于高麗也。蓋自三韓已有詩歌,而新羅以前,則未過輸入之過程,至羅季崔致遠入唐(晚唐)修學,以后東方之文大振,于是乎高麗之詩大盛矣。是以當世之秀才,莫不有詩,不問儒釋,無不知韻,以詩出世,以詩國交,以詩交友,詩之盛豈得己耶?然至近世朝鮮,性理之學,為道學之本,道學又當時教民之本,由是詩人詞客,自然萎縮乎道學,詩道自不及前代矣。”[1]
由于沒有本民族文字,高麗貴族從小便學習漢字,他們熟讀諸子百家,以詩、書、畫作為必修科目,熟練創作漢詩。958年,光宗(949-975年在位)接受了后周人雙翼的建議,效仿唐朝實行了科舉制度,此舉進一步加速了漢文學在朝鮮半島的普及。可以說,在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影響下,高麗上層社會以詩“出世”“國交”“交友”,漢詩創作已經達到了一定水準。隨著1170年高麗中期武臣政變的爆發,國家內外局勢混亂,文人遭受迫害,迫使他們回歸文學本身。文學創作不再僅僅是文人用于提升從政能力的手段,他們創作漢詩,并且開始對詩文進行審美判斷,在高麗中后期首次出現了《破閑集》《白云小說》《補閑集》《櫟翁稗說》等詩話著作。
其中,《破閑集》開創了朝鮮詩歌評論的先河,是高麗中期著名文人李仁老(1151-1220年)晚年著成。①“遂收拾中外題詠可為法者,編而次之為三卷,名之曰破閑(中略)集既成,未及聞于上,而不幸微恙,卒于紅桃井第。”(《破閑集》卷下,跋文)其后幾十年間,朝鮮文壇人才輩出。為了收錄涌現的詩人詩作及日益革新的文學思想,崔怡②崔怡(?-1249年),高麗王朝武臣政權領袖,崔忠獻之子。命崔滋(1188-1260年)對《破閑集》進行了補充和續寫,在1254年刊行了《補閑集》一書。大體看來,《補閑集》與《破閑集》較為相似,均分為上、中、下三卷,且其中文段未附題目。書中收錄了上至高麗帝王,下至士大夫、僧侶的詩作,從詩人趣事到詩歌品評,采用隨筆式閑談中蘊含詩論的敘述模式,內容豐富繁雜,充分展現了朝鮮詩人對于文藝理論的早期實踐精神。
一、《補閑集》的創作背景
《高麗史》中,對《破閑集》的作者李仁老有著這樣的記載:
自幼聰悟,能屬文,善草隸。鄭仲夫之亂祝發以避,亂定歸俗。明宗十年擢魁科,補桂陽管記,遷直史館出入史翰。凡十有四年,與當世名儒吳世才、林椿、趙通、皇甫抗、咸淳、李湛之,結為忘年友,以詩酒相娛,世比江左七賢。神宗朝,累遷禮部員外郎。高宗初,拜秘書監右諫議大夫,卒年六十九。以詩名于時,性偏急,忤當世,不為大用。[2]
《高麗史》中稱李仁老“以詩名于時”,可見他確實有較高的文學才能。除了《破閑集》之外,他還著有《銀臺集》二十卷、后集四卷,據說載有1500余首漢詩,可惜并未傳至現世。他參加了雙明齋海東耆老會,編纂了《雙明齋集》三卷。并仿效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人團體 “竹林七賢”主導了高麗時期“海左七賢”的活動。與他在文壇上的成就相比,其仕途經歷明顯并不如意。李仁老待武臣政變局勢暫緩,便復出參加科舉考試,一生在官場沉浮,升遷緩慢,時時抱有“壯志難酬”之感。苦悶時他情難自抑寫下求官心緒,不如意時他借自然之法開解自己。在為仕途不順苦悶之時,他解救自己之路便是“破閑”。
李仁老所處的時代正是武臣崔忠獻時期,崔忠獻周圍聚集了一批如李奎報般年輕有為之士,故而無暇青睞李仁老。這種在仕途上的無望和滿腔抱負卻無法大展宏圖的“閑之病”,李仁老都傾注在了《破閑集》中。此外,李仁老同樣有著自己身為文士的抱負,他在《破閑集》卷下還有這樣一段描述:
我本朝境接蓬瀛,自古號為神仙之國。其鐘靈琉秀間生五百,現美于中國者,崔學士孤云唱之于前,樸參政寅亮和之于后,而名儒韻釋,工于題詠,聲馳異域者,代有之矣。如吾輩等,茍不收錄傳于后世,則湮沒不傳決無疑矣。[3]
可見,李仁老對于高麗及新羅詩作佚失嚴重很是痛心,他想盡自己一份微薄之力,使優秀詩作可以流傳后世,這也是他創作《破閑集》的原因之一。確實,在《破閑集》三卷中,上至新羅時期的崔致遠,下及同時代的林椿、李湛之等人,李仁老選錄了文人詩作、作詩軼事,記載了當時的文學活動,發表了個人文學見解……此外,《破閑集》中還談及了九名中國詩人,可見當時中國文學的影響之大以及李仁老開放的文學視野。遺憾的是,李仁老在書中雖然表達了對文學的純粹追求,但闡述的詩歌理論和評論不多,成體系的評論也很少。
《破閑集》之后的四、五十年間,崔忠獻之子崔怡繼承了父親的權力。崔怡常常讀書作詩、與文人交往,文學素養頗高。加之宋代詩話的傳入,朝鮮文人也意識到了《破閑集》的不足,《補閑集》便應運而生。無獨有偶,《補閑集》在序言中也如此提到了成書緣由:
我本朝以人文化成,賢俊間出,贊揚風化……金石間作,星月交輝,漢文唐詩于斯為盛。然而古今諸名賢編成文集者,唯止數十家,自余名章秀句皆湮沒無聞。李學士仁老略集成編,命曰《破閑》,晉陽公以其書未廣,命予續補。強拾廢忘之余,得近體若干聯,或至于浮屠兒女輩,有一二事可以資于談笑者,其詩雖不嘉,亦錄之。共一部分為三卷。[4]
上文所說的“晉陽公”,即崔忠獻之子崔怡,在他的授意之下,《補閑集》是因“以其書未廣”對《破閑集》的一種“續補”,也是“名篇秀句皆湮沒無聞”之下的一種努力。如果說《破閑集》是以李仁老為中心的個人產物,詩歌理論和批評是破碎又主觀的,那么《補閑集》背負著官方委命,則以一個更加宏觀、客觀的視角審視了高麗中期及以前的文壇,展現了高麗文學批評的發展面貌。細細讀來,《補閑集》在書體構成、詩論觀點都有所變化,因此我們有必要對《補閑集》的詩學思想進行深入研究。
二、《補閑集》比之《破閑集》
1254年刊行的《補閑集》在詩人詩作的數量、詩論文論的質量和對中國文學的接受方面,都不同于《破閑集》。
(一)“續”破閑——詩人詩作的續擴
從《補閑集》的序言中我們可以看出,《補閑集》最大的成書原因是為了續補《破閑集》未收錄的“名章秀句”。兩本書均為上、中、下三卷,其中篇章皆未附題目。經統計,《破閑集》中文段數是82個,《補閑集》是147個,增多了65個。《破閑集》中所涉及作家數(包括無名氏)是72人,而《補閑集》是144人,其中共同涉及的作家僅20名,《補閑集》的作家數翻了一倍。在詩歌數量上,《破閑集》共收錄了169首詩作,而《補閑集》則收錄了397首詩作,確實完成了“續”破閑的任務。
《補閑集》上卷主要談論了從高麗初期到當代士大夫(及逸士)的詩作,詩作大體以高麗前期為主,按照時間順序排列,從光宗年間的趙翼到崔承老、王融、崔沖、金行瓊、崔惟善、樸寅亮、權適、鄭知常、李知深、金敦時、趙沖、琴儀、吳世才(逸士)等;中卷記載了武臣執政時期士大夫中代表文人的詩作,以俞升旦、金仁鏡、李奎報、李仁老、李公老、金克己、金君綏、吳世材、安淳之、李允甫、林椿、陳澕等十二人為代表,內容文學性更強;下卷的前半部(文段1-21)收錄了士大夫文人的詩論文論,而中間部分 (文段22-39)集中收錄了僧侶詩作,結尾部分(文段40-49)記載了幾篇奇幻故事和妓女詩作。可以說,《補閑集》六分之五的內容是儒家士大夫文人的詩作詩論,而其余六分之一是僧侶漢詩、鬼怪故事及妓女之作。
在收錄的作家類型上,《破閑集》包括皇帝、文人、僧侶及外國文人(即中國文人),《補閑集》在此基礎上增加了對妓女詩作的收錄。妓女因為社會地位低,往往是詩歌受贈的對象,或是詩作談及的內容,其漢詩創作在前代從未被收錄和認可。然而,她們大多熟讀漢詩名作,經常與貴族士大夫交往應酬,具備一定的詩歌創作能力。她們有不俗的才情,能夠周旋于官宦文人之間,侍酒宴樂之時,用詩歌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補閑集》在下卷卷尾對兩名妓女的漢詩創作進行了具體記載:
動人紅彭原倡妓也,頗知文句。有一兵馬分道,與太守圍棋,因宿酲未解曰:“都護博州千杯酒,醉未分東西。”動人紅在傍曰:“太守分營一局棋,蒙不知生死。”嘗從一書生欲學韓文,書生曰:“不作詩不教授”。遂作八韻曰:“買酒羅裳解,招君玉手搖。”又贈趙舉子曰:“幸逢溱洧會,芍藥贈如何。”自敘云:“倡女與良家,其心間幾何。可憐柏舟節,自誓死靡他。”自敘之意似乎貞烈。[5]
上面這段文字記錄了名為動人紅的詩作。在高麗時期,宮中舉行宴會或是歡迎外國使節之時,經常需要官妓表演音樂、歌舞。更多的時候,官妓要侍奉地方長官,或是接受他們的命令接待兩班士大夫。兩班貴族應和酬答,和名士的交流也要求她們的詩歌修養達到一定的水準。妓女的境遇飄忽不定,過著迎來送往的生活,卻也渴望被人愛護和理解,動人紅在詩歌中就表白自己,拋出了“倡女與良家,其心間幾何”的反問。漢詩同樣是當時妓女抒發感情和渴望的工具,通過《補閑集》中記載的這兩段文字,我們可以窺見高麗時期社會底層女子的心聲。
此外,在“續”《破閑集》的過程中,崔滋減少了個人詩作的收錄,轉為更加關注本國作家及作家創作的思想背景。《破閑集》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李仁老自己創作的詩歌,且不論作家的思想傾向是儒釋道,僅以詩作優劣判定擇錄與否,比如居士郭興、僧侶李資玄等的詩作便都收錄其中。而崔滋的標準則不同,他在《補閑集》中更重視尊揚儒教道理,擇詩錄詩亦是如此。比如在《補閑集》中,崔滋對于儒家新興士大夫李奎報的漢詩作品收錄最多,高達29首,且每次提及道教或佛教思想都呈批判態度。可見,高麗王朝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儒家思想在士大夫階層占據了主導地位,《補閑集》的根本著書立場是扎根于儒家思想的。
(二)“補”破閑——詩論文論的補充
《補閑集》“補”的實質所在,在其序言伊始便顯露端倪:
文者,蹈道之門,不涉不經之語,然欲鼓氣肆言,竦動時聽,或涉于險怪。況詩之作,本乎比興諷喻,故必寓托奇詭。然后其氣壯其意深其辭顯,足以感悟人心,發揚微旨,終歸于正。若剽竊刻畫,夸耀青紅,儒者固不為也。雖詩家有琢煉四格,所取者,琢句煉意而耳。今之后進,尚聲律章句,琢字必欲新,故其語生;煉對比以類,故其意拙。雄杰老成之風,由是喪矣。[6]
從引文可以看出,崔滋著書的目的沒有停留在擴大收錄詩作的數量上,他對文學的思考很深入,用“文者,蹈道之門”提出了文與道的關系以及詩歌的本質問題。《破閑集》主要以漢詩為主,君王、文人、僧侶的漢詩都混雜記載于其中,其中罕見一些對漢詩的評論,且帶有李仁老強烈的主觀色彩。《破閑集》是一本無序的、詩話特性不濃厚的著作。與此相比,《補閑集》更為注重批評理論的摸索,在作家點評、評詩標準及文體定義上都有所涉獵。
首先在作家點評方面,崔滋在中卷點出了武臣執政期間的文學“宗匠十二人”,分別對其詩作詩風加以評論:
今之詩人評曰俞文安公升旦,語勁意淳用事精簡;金貞肅公仁鏡,凡使字必欲清新。故每出一篇,動驚時俗;李文順公奎報,氣壯辭雄,創意新奇;李學士仁老,言皆格勝,使事如神,雖有躡古人畦畛處,琢煉之巧青于藍也;李承制公老,辭語遒麗,尤長于演誥對偶之文;金翰林克己,屬辭清曠言多益富;金諫議君綏,辭旨和裕;吳先生世材,安處士淳之,富瞻渾厚;李史館允甫,林先生椿,簡古精雋;陳補闕澕,清雄華靡,變態百出。此者一時宗匠也。[7]
上文提到的的俞升旦、金仁鏡、李奎報、李仁老、李公老、金克己、金君綏、吳世材、安淳之、李允甫、林椿、陳澕十二人,即崔滋選出的武臣執政時期文學的代表人物,他用寥寥幾句先概述了每個人的作詩特點,并在后文分別用一、二個文段對每位宗匠進行了點評。文中結合其具體漢詩,或圍繞詩歌題材、或側重作詩方法,著筆墨于每位宗匠的詩歌特點。其中李奎報出現的次數最多,崔滋在闡述個人詩論觀點時,也時時舉李奎報詩作為例。
其次,崔滋將評詩標準逐漸趨于客觀化。文學創作是復雜多樣的,詩歌批評卻應該是客觀統一的,這就要求文學批評者進行理性分析。崔滋在 《補閑集》中對批評對象進行了分析和研究,明確了詩評的一些標準,總結了一定的理論,使高麗時期的詩歌批評逐步趨于客觀。首先,崔滋將詩歌分為上品、中品、下品:
若詩則新奇絕妙,逸越含蓄,險怪俊邁,豪壯富貴,雄深古雅上也;精雋遒緊,爽豁清峭,飄逸勁直,宏瞻和裕,炳煥激切,平淡高邈,優閑夷曠,清玩巧麗次之;生拙野疎,蹇澀寒枯,淺俗蕪雜,衰弱淫靡病也。[8]
引文中,崔滋總結了“上”“次”“病”的評判標準,這其實與崔滋所說的“先以氣骨意格,次以辭語聲律”統一呼應,氣骨意格為首,辭語聲律其次,氣骨意格及辭語聲律都不及的詩作只能是詩中下品了。“氣骨意格”即是作家修養和詩歌所反映的精神內容,是以詩歌的豪氣為核心的美的標準。[9]作為一個儒家士大夫,崔滋表達了其所追求的文學至高至美的境界。
關于評判詩歌優劣,崔滋還記述過這樣一段話:
文烈公和慧素師貓兒云:螻蟻道存狼虎仁,不須遣妄始求真。吾師慧眼無分別,物物皆呈清凈身;文順公蟾云:痱磊形可憎,爬行亦澁。群蟲且莫輕,解向月中入;眉叟蟻云:身動牛應斗,穴深山恐頹。功名珠幾曲,富貴夢初回。文順公形容甚工,李學士句句皆用事,文烈公寄意浮屠言理最深。大抵體物之作,用事不如言理,言理不如形容,然其工拙,在乎構意造辭耳。[10]
金富軾、李奎報、李仁老分別以貓、蟾蜍、蜘蛛為題材作詩。崔滋認為,每種動物都具備自身的特色,評論此類詩作好壞可以依次按照形態刻畫是否如實、內容是否符合事理、能否巧妙運用典故等三方面進行評判,即按照“用事不如言理,言理不如形容”的評判標準,將金富軾、李奎報、李仁老三者的詩作高低盡述其中。這種詩歌批評,與李仁老在《破閑集》的主觀觀點不同,增加了詩評的客觀性和可信度。
其實,我國北宋大文學家蘇軾在《凈因院畫記》中也有過類似的看法,他說“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煙云,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11]蘇軾認為,畫既要符合事物的本來面貌,又應該體現內在神韻,既應將客觀事物如實再現,又應將畫家的主觀意趣完滿表達。可以說,在自然之中體現自然之物的生命和性情,這是中朝兩國古代文人墨客的共同追求。
在文體方面,崔滋在下卷(文段13-21)用了九個文段,結合具體例子簡要整理了每種文體的概念、必要條件和演變歷史:
書命之作,始于畢命囧命。秦改命為制改令為詔,漢因之……本朝詞誥古有典則,及睿王代一變華靡,今又三變,皆繁辭虛美,甚者至類俳優戲贊。[12]
古四六龜鑒,非韓柳則宋,三賢不及此者,以文烈公為模范可矣。文順公以逸氣豪才,驅文辭必弘長,至于箋表必約辭短章,不愆聯律……凡箋表限四六聯對者,欲謙檢而不越也,以辭約義盡為優。[13]
上文第一段引文,崔滋說明了文章名稱伴隨時代變遷所發生的改變,從我國的秦、漢到高麗朝時期詞誥的幾番變化。第二段以李奎報為例,闡述了士大夫應該精通詩、四六文、箋記、表章等各種文體,且創作要符合每個文體的規范特點。
總結來說,《補閑集》或以隨筆中包含詩歌的形式,或僅僅是隨筆的形式,有的記錄了詩歌的創作背景及創作前后的軼事,有的評價了詩作及所反映的作家思想,有的立足于詩作和文體進行了點評。可以說,《補閑集》是集詩作、詩評、詩論于一體的豐富集合,特別是詩論在寬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擴大和深化,補充了《破閑集》之所短。
(三)“脫”破閑——笑談及國史補要素的添加
《補閑集》結尾幾個文段還記錄了幾篇人鬼奇幻故事和男女交往情事,崔滋將其稱為“淫怪事”,在跋文中對此作了如下解釋:
唐李肇國史補序云:“敘鬼神,近帷箔,悉去之。”歐陽公作歸田錄,以肇言為法,此古今儒者選述之常也。今此書,非敢以文章增廣國華,又非撰錄盛朝遺事,姑集雕篆之余,以資笑語。故于末篇,記數段淫怪事,欲使新進苦學者,游焉息焉,有所縱也,且有鑒戒存乎數字中。覽者詳之。[14]
如果說《補閑集》的序言表明了要續補《破閑集》的成書緣由,那么跋文中就提到了書體內容所效仿的對象,即我國宋代歐陽修所著的《歸田錄》。《歸田錄》的跋文中同樣有這樣一段話:
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敘鬼神,述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采風俗,助談笑,則書之。”余之所錄,大抵以肇為法,而小異于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志也。覽者詳之。[15]
可以看出,《補閑集》與《歸田錄》的跋文有很多相似之處,第一句都以唐朝李肇著《唐國史補》開篇,最后一句均以“覽者詳之”結尾。跋文中記載了李肇的著書原則,即去除一切 “言報應、敘鬼神、述夢卜、近帷箔”,這樣才能保證所記內容翔實可靠,補史書之缺漏。歐陽修晚年閑居,稱以《唐國史補》為標格,遵其體例創作《歸田錄》,其中記載了宋代著名文學家楊億、晏殊、林逋、石延年、梅堯臣等人的事跡,具有一定的文學研究價值。不僅如此,歐陽修還結合親身見聞在《歸田錄》中記錄了北宋前期的典章制度、官場軼聞等,同樣使其具有史料價值。關于《歸田錄》所記載的內容,歐陽修說“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士夫大夫笑談之余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這與崔滋在序言中所說的“或至于浮屠兒女輩,有一二事可以資談笑著,其詩雖不嘉,并錄之”有異曲同工之妙。
依照崔滋所說,《補閑集》中記錄的這些“淫怪事”是為了供“新進苦學者”休息娛樂所用,可為“笑談”。在下卷40至48的九個文段中,記錄了一篇貞肅公與妓女白蓮的愛情故事,三篇奇聞怪事,一篇李寅甫與女鬼的韻事以及一篇癡愚人子林的故事。這些故事文字質樸、內容各式各樣,與《破閑集》中篇幅較小、記載隱晦的“笑談”相比,有了很大的進步。《補閑集》之后,高麗后期李齊賢所作的 《櫟翁稗說》中也載有 “笑談”,李朝初期徐居正所作《太平閑話滑稽傳》更是搜集了一整本可作笑料的奇文逸事,可見《補閑集》對后世文學的影響不可忽視。
《補閑集》對《歸田錄》的接受,還體現在類似“國史補”的記述上。崔滋在文中曾用一長段文字記錄了一位無名僧侶的行跡,然后說“以補僧史之闕遺”,可見他記述的重點不在于僧侶,而在于對歷史的記載。崔滋在《補閑集》中還收錄了君王的詩作,將君王和士大夫的詩作同列于一卷雖然不合儒家規矩,但是書中解釋“載此御制者,因紀事,他皆如此”。既然主旨是“因詩紀事”,那么比起君王詩作的文學性,與御制相關的歷史事實便更為重要了。此外,《補閑集》中還記載了九城役,即高麗王朝時期尹琯與吳延寵帶領軍隊征伐女真的歷史戰役,在這些段落里,其中也夾雜有部分詩歌,但史實重于詩作,詩作是為了說明歷史事件而服務的。
與續擴詩人詩作、補充詩論文論的意圖相比,“笑談”及“國史補”要素的添加在《補閑集》中所占比重有限。也就是說,《補閑集》雖然以李仁老的《破閑集》和歐陽修的《歸田錄》兩部書為模范進行創作,重點繼承的依然是本國著作《破閑集》的傳統。
三、結語
《破閑集》與《補閑集》是接受并融合了本國傳統和外國文學的著作,通過它們可以了解高麗時期文學和文化的面貌。《補閑集》的成書緣自對李仁老所著《破閑集》的續補,但《補閑集》書中內容取材范圍更廣、更全面。在文人不斷發展的審美要求下,《補閑集》中所反映的詩論文論也更加多樣和客觀,從“十二宗匠”的作家點評,到劃分漢詩優劣等級的“氣骨意格”“辭語聲律”,再到四六文、箋記、表章等各種文體的定義,崔滋所展現的文學批評豐富而細致。同時,在北宋歐陽修《歸田錄》的影響下,《補閑集》擺脫了單純的“續補”,在文中添加了滑稽“笑談”和“國史補”的史料要素,在文學意義之外,還兼具了史料價值。可以看出,朝鮮古代的詩學思想在高麗王朝剛剛萌芽,高麗文人接受了中國文學的精華,并進行了改造和批判性的吸收,與朝鮮民族獨特的思想文化與傳統相結合,結出了獨屬于古代朝鮮的璀璨果實。
[1](韓)趙鐘業:《高麗詩論之唐宋詩風影響研究》,《語文研究》(第 7 輯),1971 年,第 100 頁
[2](朝)鄭麟趾:《高麗史》,亞細亞文化社,1972年,102卷,李仁老條
[3][4][5][6][7][8][10][12][13][14](朝)李仁老 崔滋:《破閑集·補閑集》,亞細亞文化社,1972年,第53、56、162、56、93、139、99、139、143、162 頁
[9]蔡美花:《高麗文學的審美心理結構探析》,《東疆學刊》2011年第28卷第2期,第7頁
[11]李福順:《蘇軾與書畫文獻集》,榮寶齋出版社,2008年,第58頁
[15](北宋)歐陽修:《歸田錄》,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167頁
ComparingBohanJiptoPahanJipin the Period of Kaokouli in Korea
Jiang Xia Yin Yunzhen
Goryo Dynasty is the golden age in the history of Korean-Chinese literatures.Korean poetical talks are also appeared at that time.With the angle of comparison,We mainly explo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BohanJipandPahanJipand try to outline theearly ancient Korean literary criticism.BohanJipincluded more poets and poems thanPahanJipand literary criticisms are more objective and more systematic.Under the influence of OuYangxiu’sGuitianlu,BohanJipalso added elements of funny stories and supplyment of the nation history.As a result,BohanJipnot only has literary significance but also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combines ancient Korea’s traditional and elements of foreign literature as a whole.
ChoiJa,BohanJip,PahanJip,literary criticism,foreign literature
吉林大學文學院 吉林長春 130012;吉林大學外國語學院 吉林長春 130012
吉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高麗時期朝鮮詩人對中國文論的吸收與改造”(批準號:2016BS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