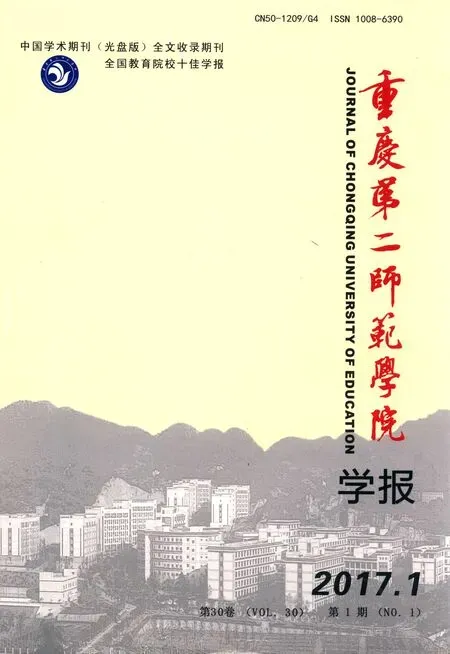《黑貓》的異化主題分析
戴星辰,王孝存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xué) 外國語學(xué)院,南京 211100)
《黑貓》的異化主題分析
戴星辰,王孝存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xué) 外國語學(xué)院,南京 211100)
在埃德加·愛倫·坡的小說《黑貓》中,男主人公與貓、妻子以及自身之間存在不和諧的異化關(guān)系。小說通過男主人公與兩只貓的互虐來展示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異化,通過丈夫?qū)ζ拮拥呐皻⒁约澳兄魅斯c社會群體的脫離來表現(xiàn)人與他人關(guān)系的異化,通過男主人公人格的分裂與人性的扭曲來揭示人與自身關(guān)系的異化。
黑貓;異化;自然;人性
一、引言
從黑格爾第一次在哲學(xué)領(lǐng)域提出“異化”這一概念,到費爾巴哈的“宗教異化”、馬克思的“異化勞動”、弗洛姆的“人性異化”,異化研究從未停止。對于“異化”這一理論范疇,現(xiàn)代學(xué)界的研究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拓展,異化現(xiàn)象的研究范圍在宏觀上涉及民族、種族和心理學(xué)等領(lǐng)域,微觀上囊括人際交往、科技、消費等的異化。“在馬克思的異化理論中,異化的內(nèi)涵主要是指‘分離、疏遠(yuǎn)’,即本屬于人的東西或人活動的結(jié)果,在人的對象化活動中,取得了獨立性,并反過來制約人,統(tǒng)治人的力量。”[1]隨著人類力量的不斷增強(qiáng),人想要凌駕于自然之上、他人之上,掌控一切來滿足欲望,獲得安全,最終卻換來了人與自然、人與他人的疏離,導(dǎo)致人與自身的異化。埃德加·愛倫·坡“因為其獨特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在說教文本盛行的19世紀(jì)末獨樹一幟,成為文學(xué)花園里的一朵奇花”[2]23,其小說以怪誕、恐怖的哥特風(fēng)格而著稱。學(xué)術(shù)界對其代表作《黑貓》的研究多以精神分析以及對恐怖、死亡主題的單維度探討為主,而異化理論卻撩開驚悚的帷幕,多方面、多層次地揭示并整合了小說《黑貓》中作者對廣泛的人性及人類生存問題的深思。
二、異化分析
(一)人與自然的異化
人與自然的異化主要表現(xiàn)為“人一方面來源于自然并依賴于自然,另一方面人又征服自然、破壞自然”,“最終導(dǎo)致人類生存面臨危機(jī)”。[1]動物作為自然界重要的一分子,人與動物的相處方式往往被看作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一種反映。從生態(tài)批評角度探討動物意象所蘊含的人與動物關(guān)系的文學(xué)作品比比皆是。《黑貓》就是通過男主人公與兩只貓的錯綜復(fù)雜的情感與命運糾葛,揭示了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扭曲,這種扭曲最終導(dǎo)致男主人公自身的毀滅。
馬克思、恩格斯分別從存在論、價值論、實踐論的角度詮釋了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
從存在論的角度看,“人本身是自然界的產(chǎn)物”,由此決定了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是“部分與整體的關(guān)系”,人對自然的態(tài)度是“敬畏自然、依賴自然”。[3]人的自然屬性是人存在的基礎(chǔ),人與動物有著生物共同性,也就是說如同其他動物一樣,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既然同屬于自然界這個整體,那么人與動物的關(guān)系應(yīng)當(dāng)是和諧共生的。人的社會屬性使人區(qū)別于其他動物,從這個角度看,動物、植物和各種生態(tài)系統(tǒng)被視為自然界的一種代表,人的勞動和生存也是依賴于動物的,因而應(yīng)當(dāng)尊重動物以求得自身的長遠(yuǎn)發(fā)展。在《黑貓》中,人與動物的關(guān)系扭曲為人對動物的統(tǒng)治,分別表現(xiàn)在對動物精神上和肉體上的絕對擁有。在精神上,動物作為人類緩解孤獨和悲傷的手段。在男主人公小時候,因為喜歡動物,父母就給他買了許多寵物,以此打發(fā)了大部分時間。當(dāng)男主人公在自己現(xiàn)實的人際交往中受挫時,當(dāng)他“嘗到人類那種薄情寡義的滋味”時,“獸類那種自我犧牲的無私的愛”[4]1便能使他得到慰藉。而這里的人與動物所體現(xiàn)出來的并不是互相陪伴的和諧關(guān)系,而是動物單方面地?zé)o償付出,無私奉獻(xiàn),“自我犧牲”,這種觀點本身就是以人類為中心,動物附屬化的一種表現(xiàn)。當(dāng)男主人公酗酒后性情大變時,這些動物對主人的忠誠的感情,日久的喜愛,親昵的接近,就會招致主人不念舊情的“肆無忌憚的糟蹋”[4]2。這種對寵物需要時的所謂的“喜愛”,暴躁時的虐待,實則是把動物當(dāng)成了精神消費品。在肉體上,人對動物任性地虐殺。爛醉的男主人公,不管是對普通寵物,還是自己最“喜愛”的那只黑貓都施以暴行,僅僅因為那只貓在自己手中掙扎時咬傷了自己,男主人公就“居心不良地把它眼珠剜了出來”[4]2,最后又因為“人心本能的一股沖動”[4]3,沒有任何正當(dāng)理由地把這只黑貓吊死了。人對動物想打便打,要殺便殺的殘害肉體的行為,揭示了在人類社會中動物的物化身份,動物被動地失去感覺,肉體完全被人控制。人類通過對動物精神和肉體上的控制,實現(xiàn)了對其的絕對擁有。這種單方面的索取、暴力性的統(tǒng)治和附屬關(guān)系與互相依賴、尊重的和諧關(guān)系背道而馳。
從價值角度看,“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是需要與滿足的關(guān)系,人對自然的態(tài)度是善待自然,呵護(hù)自然”[3]。人對自然的需要與依賴反映了自然對人類的重要性,“人靠自然界而生活,因而決定了人對自然的態(tài)度只能是善待與呵護(hù)”[3]。否則,當(dāng)人類把自然界掠奪一空之后,自然界將無法再滿足人類的需求。在小說中,作為寵物的黑貓是精神上的陪伴,常常給男主人公“滿足感”和“感動”。當(dāng)黑貓被男主人公挖去一只眼睛、肉體受到傷害之后,它開始遠(yuǎn)離、躲避他,只要男主人公“走近,就不出所料地嚇得拼命逃走”[4]3。此時的男主人公已無法從黑貓那里得到慰藉,感受到的只是黑貓對他的“惱怒”,不久之后就殺死了黑貓,而這種對黑貓肉體的虐待、生命的剝奪顯然不在黑貓或是任何生命體的可承受范圍內(nèi)。男主人公漠視給予其慰藉的黑貓的重要性,展現(xiàn)出來的是一種隨意的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也最終導(dǎo)致他永遠(yuǎn)地失去了黑貓的陪伴。隨后男主人公“開始后悔害死這貓”[4]4,于是試圖再找一只相似的貓來彌補空缺。但是與男主人公預(yù)期相反的是,新找來的這只貓給他帶來的是“厭惡”“生氣”“痛恨”,甚至是“害怕”[4]5,此時男主人公的需求再也無法得到滿足。
從實踐論角度看,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是主體和客體的關(guān)系,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馬克思強(qiáng)調(diào),在認(rèn)識自然的過程中應(yīng)兼顧主體和客體對象這兩個尺度。如果僅以主體為尺度,則會導(dǎo)致人與自然之間的隔閡和分裂。”[3]小說中男主人公對動物的感情是漠然的,體現(xiàn)的是完全的主體尺度——人的隨意性。挖去貓眼后的男主人公“沉湎醉鄉(xiāng),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早已統(tǒng)統(tǒng)忘光”,“靈魂還是毫無觸動”[4]3,對黑貓所受的剜眼之痛以麻木視之。在殺死貓之后,男主人公自己給出的解釋是:“我知道這貓愛過我,就因為我知道這貓沒冒犯過我。”[4]3這種明知故犯的心理,是對受害者——動物的無視,因為認(rèn)為無關(guān)緊要,所以任意妄為,肆意地殘害動物。
人對貓的統(tǒng)治、掠奪與殘害,最終換來了貓的報復(fù)。這只新來的復(fù)仇的貓,開始折磨男主人公的精神,以胸前絞刑臺形狀的白毛,給男主人公帶來對死亡的恐懼。“無論白天,還是黑夜”,男主人公“再也不得安寧了”[4]6。接著,它惹怒男主人公,“誘使”他殺死了自己的妻子,以致“招來那么些災(zāi)害”[4]8。最后,男主人公把妻子的尸體砌進(jìn)了墻里,但在警察來搜查的時候,這只黑貓“用叫喚聲報了警”,把男主人公“送到了劊子手的手里”[4]9。這一步步有計劃的復(fù)仇,使男主人公的死亡成為必然。在《黑貓》中,人虐貓殺貓、貓報復(fù)殺人,折射出的人與自然的異化警示我們:人不是自然的主宰者、統(tǒng)治者和征服者,自然是人類生命的母體,精神的依歸,“善待自然就是善待人本身,損害自然就是損害人本身,自然的崩潰就是人自身的衰亡,自然的命運就是人自身的命運”。[3]毀壞了自然,人類將無處汲取營養(yǎng),延續(xù)存在。
(二)人與他人的異化
隨著異化理論的不斷發(fā)展,其維度也不斷擴(kuò)展,“異化”運用于人際關(guān)系上主要“是指人與人之間關(guān)系上的疏遠(yuǎn)和分離”[1]。《黑貓》中展現(xiàn)的是丈夫與妻子之間兩性關(guān)系的異化,以及男主人公與其他人關(guān)系的異化。19世紀(jì)下半葉的女權(quán)運動興起之前,父權(quán)社會中的女性處于邊緣化、被歧視的屈從地位,完全沒有話語權(quán)。小說中的妻子就是這樣無聲無息的存在。丈夫?qū)ζ拮酉碛薪^對統(tǒng)治權(quán)力,妻子對丈夫不可違抗。在男性中心的文化氛圍里,為了替男人的專橫找出理由,人們提出許多巧妙的論點:“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世間有自然的等級,等級高的應(yīng)當(dāng)統(tǒng)治等級低的生物”[5]23,“男人在理性方面比女人更高一籌,應(yīng)當(dāng)統(tǒng)治女人”[6]34。小說中給妻子的筆墨寥寥無幾,且大都落筆于妻子的迷信思想之上。開篇不久,丈夫作為小說敘述者就告訴讀者:“我妻子生來就好迷信,她一說到貓的靈性,往往就要扯上古老傳說,認(rèn)為凡是貓都是巫婆變化的。”[4]2在描述與第二只貓的糾葛時,又是“妻子不止一次地”提醒丈夫“留神看這片白色的斑記”[4]6,告知丈夫貓胸前絞刑臺形狀的白斑預(yù)示著死亡。當(dāng)丈夫暴怒得想要殺這第二只貓時,一向順從的妻子,竟然抓住了丈夫的手試圖阻止。妻子這一反常態(tài)的舉動其潛在原因分析有多種,其中一種與小說中妻子形象相貫通的解釋是她相信:“解救黑貓,就是解救丈夫,黑貓得救了,更重要的是丈夫也將免遭黑貓之靈的報復(fù)。”[7]自中世紀(jì)以來,黑貓被認(rèn)為是女巫的魔寵,西方宗教一直給黑貓冠以邪惡之名,賦予其詭秘色彩,稱之為地獄的使者,由此可見,妻子已深受這種思想的影響。從丈夫敘述中所展現(xiàn)的如此沒有邏輯、毫無理性可言的妻子,就理所應(yīng)當(dāng)、名正言順地附屬于丈夫,受其統(tǒng)治。處于統(tǒng)治下的妻子受盡了丈夫的虐待。酒后性情大變的丈夫“任性污言穢語地辱罵起妻子來了,最后還對她拳打腳踢”[4]2。在丈夫被第二只貓折磨的煎熬中,性情越發(fā)暴躁,最后完全喪失良知,“開始痛恨一切事物”,“經(jīng)常遭殃、逆來順受的”就是“毫無怨言的妻子”[4]6。這種打罵隨性,并且無任何反抗的形象似乎已經(jīng)不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無感情、無知覺的物體。在這樣的男權(quán)世界中,女性已被物化,成為男性的附屬品。人們意識里的人只是“男人”,而“女人”只是相對于男人的一種客觀存在,女性肉體甚至生命都屬于男性。在小說中,妻子因阻攔丈夫殺貓,就被丈夫殺害了,丈夫甚至沒有任何猶豫,他“趁勢掙脫胳膊,對準(zhǔn)她腦殼就砍了一斧”[4]7,動作完成得流暢、利索,沒有對妻子生命的分毫顧忌。這一方面體現(xiàn)出妻子的一切為丈夫所有,另一方面表現(xiàn)出丈夫的不可違抗。一直“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的妻子,至少還可以保全性命。僅僅是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違背丈夫的意愿,就招致殺身之禍。《黑貓》中展現(xiàn)的是父權(quán)社會下男性與女性的統(tǒng)治與附屬關(guān)系,整篇小說沒有妻子的聲音,不公平的兩性關(guān)系使得夫妻之間無法交流,兩性關(guān)系異化。
“個體和社會的異化”具體表現(xiàn)為“個人從集體中分離出來,陷入孤獨和獨立的狀態(tài)”[1]29。《黑貓》中的男主人公就呈現(xiàn)出與社會群體及他人相脫離,與他人關(guān)系疏遠(yuǎn)的孤立狀態(tài)。整篇小說都是圍繞男主人公與他的愛寵黑貓展開的,故事的開頭男主人公就介紹自己“特別喜歡動物”,因此父母給自己買了許多寵物,并且男主人公“大半時間都泡在與這些小動物嬉戲上面”[4]1,寵物著實給男主人公帶來了很多歡樂,但男主人公已經(jīng)把養(yǎng)寵物發(fā)展成了一種“癖性”,以及生活“主要樂趣”的來源。也就是說離開這些小動物,男主人公的生活幾乎沒有什么樂趣可言了。顯然,寵物已成為男主人公不可或缺的“玩伴”。事實上,“對寵物貓狗的眷念常常與孤獨有關(guān)”[8]。馬克思認(rèn)為人的社會屬性是人的本質(zhì)屬性,決定人作為一種社會存在物,需要與社會相聯(lián)系,與他人相交往,以便“分享快樂,彼此相互幫助,并從中獲得群體感和安全感”[9]。當(dāng)人際關(guān)系疏離,人們往往會通過飼養(yǎng)動物來彌補內(nèi)心的孤獨,小說中的男主人公就是用寵物替代他人作為自己的陪伴。而對寵物的依賴感越強(qiáng),反映出的個人與現(xiàn)實生活中的他人的關(guān)系越疏遠(yuǎn)。男主人公殺死第一只貓之后,家里經(jīng)歷了一場火災(zāi),所有財物統(tǒng)統(tǒng)化為烏有,可是此時的男主人公只是在“到處物色一只外貌相似的貓來作為填補”[4]1。對他而言,只有這只貓才是此刻最不能失去的,男主人公對這只貓已是極度依賴。直觀上,男主人公與他人的關(guān)系相當(dāng)冷淡,火災(zāi)之后,來的人都是看熱鬧的,議論紛紛,卻沒人幫助,任由貧困潦倒的男主人公一家住在破舊的老房子里。與他人關(guān)系的異化往往導(dǎo)致個體被孤立,作為社會存在物,主體的人失去了人的本質(zhì),導(dǎo)致人與自身異化。
(三)人與自身的異化
《黑貓》中所體現(xiàn)的人與自身的異化主要表現(xiàn)為男主人公人格的分裂與人性的扭曲。小說以男主人公的懺悔開篇,男主人公要在臨死前把事“說出來好讓靈魂安生”[4]1,小說中事件的敘述與反思交替出現(xiàn),男主人公在反思者和被反思者的角色中來回轉(zhuǎn)換。在描述完自己挖貓眼“這一幕”后,作為敘述者,男主人公對自己的暴行“面紅耳赤,不寒而栗”[4]2。在說到殺死黑貓的時候,男主人公再次跳出故事本身,以敘述者的角度說“就是這股邪念終于斷送了”自己的一生。隨后,他直接用敘述者的口吻提醒讀者“我上面已經(jīng)說過”[4]5,妻子富有同情心,所以對被挖了眼的貓格外憐惜。接著,他又評價自己的殺妻行為是“傷天害理的殺人勾當(dāng)”。整個故事中,男主人公的雙重身份所表現(xiàn)出來的觀點是不一致的,往往是“敘述者”角色對“主人公”角色的批判,體現(xiàn)出反思及人格分裂的表征。同時,小說中的男主人公也顯示了雙重人格特征。行兇虐殺黑貓和妻子時的男主人公具有歇斯底里的個性,而反思時的男主人公卻顯示了冷靜、理智的個性。男主人公染上酒癮后,變得“喜怒無常”,對妻子“拳打腳踢”,對動物“肆無忌憚地糟蹋”。在“怒不可遏”時,他“兇相畢露”,挖去貓眼,那股“狠勁”“賽過兇神惡煞”。被黑貓激怒得“直發(fā)瘋”后“盛怒”忘己,意圖殺死黑貓,被阻止后“暴跳如雷”,砍死了妻子。這一連串形容詞,刻畫了一個易怒、過于情緒化、無自制力、喪失理智的暴徒形象。但是,在對殺死黑貓的“邪念”的解釋中,他說這是“人心本能的一股沖動”,使邪念客觀化,以逃脫自己主觀的責(zé)任,并宣稱“誰沒有無意中多次干下壞事或蠢事呢”,使得自己的暴行普遍化,一般化,言下之意既然大家都這樣,那么自己的行為也算正常。在盤算藏匿妻子尸首的時候,男主人公并未因殺了人而不知所措,而是相當(dāng)冷靜,對尸體的處理方式考慮周全,排除了尸體外運、毀尸滅跡的選擇后,經(jīng)過一番深思熟慮,最終制訂了藏尸于爐壁的縝密計劃,行動起來更是“小心翼翼”,顯示出極強(qiáng)的計劃性和邏輯性。小說中男主人公的雙重身份、雙重人格,展現(xiàn)出來的是一個與自身分裂、疏離,喪失內(nèi)在和諧與個體統(tǒng)一性的人物形象。
《黑貓》中人與自身的異化還表現(xiàn)為男主人公人性的扭曲。馬克思的勞動異化觀點認(rèn)為,在異化勞動中人與人的類本質(zhì)相異化。人的類本質(zhì)使人與動物相區(qū)分,當(dāng)人與類本質(zhì)相異化后,以自我為中心,弱肉強(qiáng)食等具有暴力傾向的動物性占據(jù)人性,小說中男主人公的人性扭曲主要通過他的“報復(fù)性暴力”和“反映性暴力”體現(xiàn)出來。由于男主人公認(rèn)為黑貓普路托在躲避自己并且咬傷自己,有負(fù)自己多年來對它的喜愛,就對黑貓實施了挖眼這一報復(fù)性暴力。弗洛姆認(rèn)為“反映性暴力”“旨在阻止威脅的傷害,根源于恐懼,這種恐懼可能是真實的,也可能是想象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10]9。男主人公對那只胸前擁有絞刑臺形狀的白毛的黑貓“害怕極了”,唯恐這“送人性命的刑具”會要了自己的性命,于是這種空穴來風(fēng),臆想出來的恐懼帶來的“煎熬”使男主人公“心里僅剩的一點良性也喪失了”,最終犯下了殺貓未遂,轉(zhuǎn)而殺妻的暴行。人與類本質(zhì)的異化使得“動物的東西變成人的東西,人的東西變成動物的東西”,從而喪失人類本質(zhì)。“自然狀態(tài)下的人性”,“本應(yīng)該自由自覺全面地發(fā)展”[11],當(dāng)人的本質(zhì)為動物性所壓制,“馬克思所說的能動的、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和獨立的人”,就不復(fù)存在了。男主人公吊死自己心愛的貓是“出于內(nèi)心這股深奧難測的渴望,渴望自我煩惱,違背本性,為作惡而作惡”的邪念,卻同時又“眼淚汪汪,心里痛悔不已”[4]3,似乎是被某種力量所控制、驅(qū)使,處于一種被動的、喪失自我主動性的不健全的病態(tài)。人性被動物性所替代,扭曲的人性與健康的人性發(fā)展方向相背離,失去自由,走向滅亡,男主人公精神的淪陷最終導(dǎo)致肉體的死亡。
三、結(jié)語
在當(dāng)代,異化的時代個性具體表現(xiàn)為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摩擦式前進(jìn),人與人之間謙和面紗下的冷漠,以及人自身的孤獨和精神危機(jī)。從“歷史評價優(yōu)先”的視角出發(fā),“異化”有其“作為歷史現(xiàn)象的客觀必然性”[12]105,那么廣泛的揭示與正視,以有意識地推動其揚棄的過程,加速其消亡,便是緩和異化時代的焦灼感的良方。在小說《黑貓》中,人與自然、社會及自身的病態(tài)的異化關(guān)系,在埃德加·愛倫·坡的戲劇化手段下得以揭露,并以藝術(shù)的張力和震撼力刺激著人類對自身生存狀態(tài)的思索。
[1]關(guān)健.西方馬克思主義異化理論研究[D].長春:東北師范大學(xué),2012.
[2]朱振武.愛倫·坡小說全解[M].上海:學(xué)林出版社,2008.
[3]李桂花.馬克思、恩格斯哲學(xué)視域中的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J].探索,2011(2):153-158.
[4]埃德加·愛倫·坡.紅死魔的面具[M].陳良廷,等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1.
[5]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女權(quán)辯護(hù)/婦女的屈從地位[M].王蓁,汪溪,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5.
[6]Taylor,A. Animals and Ethics: An Overview of the Philosophical Debate[M]. London: Barnes & Noble, 2003.
[7]曹永科,姜禮福.“驚悚”背后的女人:《黑貓》中的“三無”妻子[J].南京航空航天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5(2):75-79.
[8]黃梅.萊辛與貓[J].書城,2008(4):98-101.
[9]馮兆香.弗洛姆人性異化思想研究[D].長春:東北師范大學(xué),2012.
[10]弗洛姆.人心——人的善惡天性[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
[11]李變變.論馬克思的人性觀[D].濟(jì)南:山東大學(xué),2014.
[12]俞吾金.從“道德評價優(yōu)先”到“歷史評價優(yōu)先”——馬克思異化理論發(fā)展中的視角轉(zhuǎn)換[J].中國社會科學(xué),2003(2):95-105.
[責(zé)任編輯 亦 筱]
2016-08-22
戴星辰(1991— ),女,安徽滁州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國語言學(xué)及應(yīng)用語言學(xué);王孝存(1970— ),男,江蘇海安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外國語言學(xué)及應(yīng)用語言學(xué),專門用途英語等。
I106.4
A
1008-6390(2017)01-007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