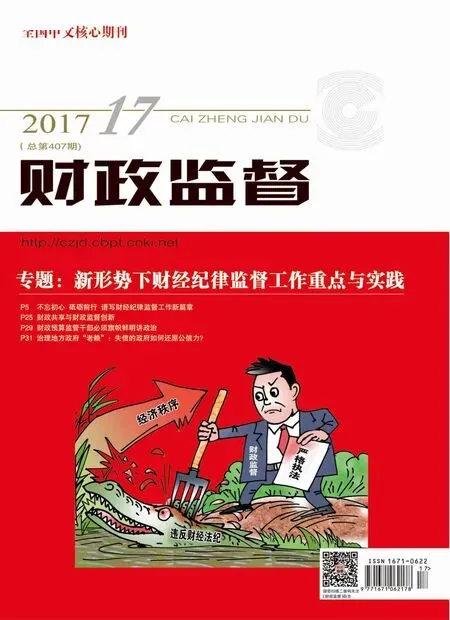地方政府性債務持續擴張的邏輯探析與對策
●董承勇
地方政府性債務持續擴張的邏輯探析與對策
●董承勇
新《預算法》實施后,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明顯增強,財政部通過限額管理、預算管理、發行置換債券等一系列措施,將風險置于可控范圍,大大提升了財政可持續發展能力。但是,在GDP增長目標驅動下,地方政府的融資沖動依然十足,新增政府債務限額、PPP仍然難以滿足其融資需求,政府購買服務、保底收益承諾等“金融創新”層出不窮。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警報不斷,金融系統如鯁在喉。本文對地方政府性融資行為的邏輯進行了分析,對不同利益主體的經濟特征分別作了闡述,點明了省級地方政府性債務監管盲區,并據此針對性地提出了改進建議。
地方政府債務 地方政府性債務 監管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做好地方政府性債務審計工作的通知》(國辦發明電〔2011〕6號)首次對地方政府性債務提出了工作要求,對地方政府性債務的內容進行了明確,具體包括三類:政府有償還責任的債務、政府有擔保責任的債務、政府具有救助責任的債務。此后審計署于2011、2013年分別開展了全國性的審計,地方政府性債務總體規模呈大幅上升趨勢。《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國發〔2014〕43號)推動審計署、財政部于2014年相繼開展了全國性的審計、核查工作,確定了地方政府債務余額。新《預算法》于2015年正式實施后,地方政府債務的監管部門確定為財政部,地方政府融資渠道和違法融資行為界定更為明確。目前,在財政部的高壓下,地方政府債務管理規范度明顯提升,增長規模也與赤字率等指標相掛鉤,總體風險可控。但概念更廣的地方政府性債務監管卻明顯滯后,隨著地方政府融資行為多樣化,地方政府性債務范圍和規模持續擴大,總體急速增長,不僅財政可持續性大大降低,金融市場也如鯁在喉,甚至會對國民經濟基礎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國際評級機構調低我國主權債務評級等級就是警示信號之一。本文認為,地方政府性債務不僅包含了地方政府債務,還囊括了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如地方政府或有負債、融資平臺債務以及地方財政未來支出責任等,國務院已經提出了限期解決的要求,必須對此高度重視,并實施有效管理。
一、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現狀
為了緩解地方政府債務償付風險和增長風險,財政部通過置換債券的形式,幫助地方政府債務實現了展期,短期內避免了償付危機。同時,借助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地方政府債務的利息支出壓力也得到了有效緩解。一定時期內,地方政府債務的風險確實控制在了一定范圍內,出現全國性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埋在金融體系中的危機暫時得以解除。當然,少數地區區域性地方政府債務危機仍然存在,這些地區債務規模遠遠超過了自身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還債壓力非常大,償付風險非常高,財政未來可持續發展能力極度弱化。尤其是在財政收入增長難、擠水分等措施壓力下,這些地區的危機警報仍未實際解除,需要上級財政支援、救助。
為了保持地方經濟發展的動力,同時控制地方政府債務規模不合理增長,新《預算法》首先從法律層面明確中央財政不會實施救助。與此同時,財政部、國家發改委等部委力推PPP,希望借助社會資本力量,引入風險共擔機制,把地方政府債務關進PPP項目之中。同時,財政部對地方政府的新增債務進行限額管理,基本思想是,負債高、風險高的地區新增債務額度較低;反之則新增債務限額相對較高。事實上,經過近幾年的發展,地方政府債務增長得到了有效控制,總體增長幅度較往年有所降低。但是,地方政府性債務規模增長仍然異常迅猛,遠遠超出了財政的可承受范圍,多個省份已經出現了新的危機苗頭。很明顯,地方政府性債務在金融體系中隱藏著巨大風險,這些債務尚未實行全面監控,增長方式粗放,缺少明確的管理主體,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
之所以如此,關鍵在于地方政府在融資過程中的逆向選擇——即不論現有財力如何,總之盡可能多地融資負債。地方政府融資過程中的“金融創新”層出不窮,產業投資基金的明股實債、PPP中承諾的保底收益、應收賬款融資、注資承諾融資等等。參與地方政府融資的投資企業、金融機構無不以固定收益的方式,鎖定自身的收益,把參與風險降低到最小。除了部分確實有現金流的項目外,純公益類的PPP項目,投資企業要獲得穩定收益,必須通過地方政府的“最低消費”承諾予以解決,而這些承諾要納入地方政府年度預算,經人大表決通過方可真正生效。一旦如此操作,地方政府將邁入違規融資行列。財政部作為地方政府債務的監督部門,已經對多起違規融資進行了亮劍。但是,這種查處的覆蓋面仍然十分有限,很難對急速擴張的地方政府性債務實施有效管理,遏制地方政府性債務快速增長勢頭。多個省份債務率超警戒線,風險在持續加大,相關管理已明顯遲滯,長此以往,將嚴重偏離國務院的管理目標和要求。
二、地方政府性債務急速擴張的原因分析
地方政府性債務快速擴張有其特有的邏輯特點。本文將從不同主體角度分析其中的邏輯關系,以更清晰地揭示其內在聯系。
一是GDP增長目標驅動。“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期盼。其中,具體數據要求是到2020年我國GDP要達到90萬億元,而2016年的GDP是74萬億元,增幅6.7%,也就是未來四年內要實現總共21.6%的增幅。雖然按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完成預期目標的可能性很大,但是,維持速度的難度并不小。2017年,政府預計全年GDP增速為6.5%,已經較2016年下調了0.2%。未來,我國GDP中高速增長將是趨勢,隨著GDP總量越來越大,增幅減小、增速減慢也是大概率事件。另外,僅憑投資要素和外向型經濟拉動的GDP增長乏力越來越明顯,基礎設施建設、外貿出口增長的空間也相對固定,難以發揮爆發式增長的促進作用。但為了保持現有的增速,繼續保持高投資拉動仍是主要選擇,各地新城建設如火如荼,污水處理設施、垃圾處理設施已經延伸到了鄉鎮,很多設施建設已經比較超前,浪費現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二是地方政府的理性經濟人選擇。理性人假設是經濟學最重要的假設基礎,地方政府作為由多個個人進行管理的組織機構,也具有明顯的理性經濟人特征。在我國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下,地方長官意志對地區經濟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站在地方長官的角度,加快地區發展是其不二選擇,既是實現發展目標的需要,也是最大化個人價值的必然路徑,這既包括個人仕途的升遷,也包括為地區發展而帶來的個人聲譽提升。更為關鍵的是,快速發展能夠有效掩飾、彌補地區的短板,把弱的一面最小化。在地方政府性債務擴張過程中,如果不加快地區發展,原有債務的償還壓力就會使得當期執政政府喘不過氣來;相反,如果能夠實現資本集聚,加快地區形象提升,從而提升土地價值,吸引優質企業,不僅可以獲得更大的土地出讓收益,還可以獲得更好的遠期稅收收益。所以,加快融資舉債,引入有實力的投資者是當務之急、重中之重。這就是地方政府性債務快速擴張的驅動力。地方財政部門、地方融資平臺、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等各主體為地方政府融資,都是實現長官意志、地方政府理性經濟人選擇的最終結果。因為不是所有的地區都有足夠優質的項目開展合規性融資,加上地方融資平臺的融資功能已經使用殆盡,違規融資行為自然而然就會出現,而且不會因為監管而消失。
三是金融機構和投資企業的固定收益思維。我國的資本市場仍然不成熟,尤其是投資者,既包括個人投資者也包括機構投資者。風險和收益是孿生兄弟,必然是對等的,但是,投資者并不買賬,很任性地就是要求有固定收益、保底收益。如信托公司在募集資金時承諾的是固定收益,沒有固定收益很難吸引到投資者參與。那么為了保證自身風險最小化,募集資金再投資過程中,信托公司必須以固定收益為基本條件。在參與地方政府的融資過程中,信托公司要獲得固定收益,就需要地方政府出具承諾函等各種形式的保底收益承諾。其他如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融資租賃公司等金融機構,甚至是建設企業等投資方,也都抱著同樣的固定收益思維。對資金渴望程度極高的地方政府,為了盡快獲得融資,什么條件都可以答應,即便跨過法律紅線也不例外。
四是省級層面的監管盲區。現在常說金融混業經營,導致出現監管漏洞,進而形成金融風險。事實上,地方政府性債務過度膨脹,與省級層面的行政單位間監管盲區不無關系。從地方債務管理層面來看,省級財政是地方政府債務的主管部門,理應對本省各地區地方政府債務情況進行監督,并嚴格控制高風險地區地方政府性債務的增長規模。但是,現階段省級財政的監管積極性不高,一方面是省級財政撼動地區地方長官意志的難度很大;另一方面省級財政與地市、縣區財政是利益共同體,如果下級財政不能通過自己的力量化解地方債務,省級財政需要承擔一定的救助責任,而且地方通過自己舉債發展,還可以減輕省級財政的調節壓力。同時,過度打壓本省地方政府的融資行為,不利于本省在全國范圍內的比較,有可能拉低本省在全國的GDP排名。另外,地方政府性債務監管所涉及的利益主體較地方政府債務更多,不僅涉及了地方政府及其融資平臺、地方財政,金融機構、投資機構、社會中介機構等多個利益主體,還有人行、銀監、保監、證監等行政管理部門、行業監管部門及其自律協會等機構,參與地方政府融資的投資機構還可能歸屬國家國資委管理,省級財政更是無權干涉其經營行為。所以,省級財政難以有效協調上述機構,從操作層面難以對違規投融資行為進行合理處罰。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如果地方政府違規融資行為處罰標準不統一,不僅會弱化法律權威,還會形成更為明顯的羊群效應,處罰輕的違規方式會成為大多數人的選擇,而產生更多的違規行為。因為存在監管盲區,地方政府性債務危機將成為金融危機的重要隱患。
五是社會中介機構的非獨立性。融資過程中,如律師事務所、資產評估機構、會計師事務所等傳統中介機構,需要從獨立審慎角度對項目的投資收益、資產標的等進行合理評價。但因為業務依附原因,這些機構長期以來都處于從屬地位,為甲方服務,而不是為公正服務。為了實現自身的經濟目標,以結果為導向,按照甲方的要求出具意見,毫不夸張地說,各種類型的報告都可以找到適用方法,以佐證事先確立的結論。這使得原本不合規的融資、不合理的項目仍然能夠一路綠燈,堂而皇之地通過各類評審。僅憑政府有形的手進行有效監管,實現難度很大,一方面是政府和行業的力量做不到事中全面監管,另一方面是中介機構準入制逐步放開,市場行為越來越多。更何況,其中許多中介還是紅頂中介,與有關政府部門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其獨立性可想而知。從某種意義上說,中介機構的非獨立性,使得政府融資行為的結果導向更為明顯。
三、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建議
只有抓住地方政府性債務的邏輯原點,才能夠為解決地方政府性債務危機提供切實可行的操作方式。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建議從以下方面予以改進:
一是放棄GDP增長論。如果中國夢的“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必須和GDP數據掛鉤,而不是看重GDP的增長質量和國民實際收入增長水平,那么在現行管理體制下,地方政府的融資沖動永遠無法抑制,地方長官的理性經濟人選擇依然突顯。所以,要達到釜底抽薪的效果,必須從放棄GDP增長論先期著手。這需要上至中央下至地方政府,均改變傳統觀念,從地方政績考核機制、地方長官晉升渠道等方面進行徹底改革。中央相關文件和規劃中,不再就GDP增長方面作要求,對于地區經濟增長情況,借助更為廣泛的指標進行評判,如包含城鎮化率、人口增長率、R&D投入增長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長率等,分別設定權重,綜合考量。這既可以避免地方政府過于注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還可以更健康地評判地區經濟發展情況。
二是合理評價地方經濟健康增長情況。為了防止地方政府理性經濟人選擇極致性地發揮,還需要從機制上進行約束,提高其盲目擴大融資選擇的機會成本,特別是違規融資的代價。當前,根據新《預算法》九十四條的頂格處理,確實可以對地方長官、地方財政發揮很強的警示作用,但處理的層級和覆蓋面還是有限。所以,建議盡快完成《預算法實施條例》修訂工作,明確違規融資行為的處理細則。同時,對地方政府性債務進行信息化、動態化監控,數據來源須借助資金供給方——金融機構、投資企業,以及資金需求方——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地方融資平臺等進行統計,實現數據對碰。工作形式需從中央層面進行統一部署,明確為一項常態化工作,多部委共同參與。對于監控發現的地方政府性債務增長速度過快或異常的地區,由財政部對其亮紅牌,組織開展突擊檢查,判斷是否存在違規融資行為,并進行相應的處置。
三是打破投資者必須獲取固定收益的投資思維。投資者對固定收益的過度要求,不利于資本市場的市場化進程。要打破這種固化思維和不合理要求,還是得借助市場手段。一方面,提升地方政府的融資談判能力,形成統一的預期和認識,即金融機構、投資企業參與地方建設是投資行為,必須承擔風險。建議從全國財政干部、地方長官的專業性培訓開始,提高地方政府的談判技能,使其敢于拒絕金融機構、投資企業的不合理收益要求。另一方面,鼓勵金融機構、投資企業苦練內功,從項目管理、運營方面提升盈利能力。對于通過提升管理水平、提高項目質量,在浮動收益項目中實現最終盈利的機構和企業,要重點推薦,實現金融機構和投資企業的優勝劣汰。建議借鑒魯班獎的設定標準和操作方式,在全國范圍設立政府PPP投融資項目的國家級獎項,對優質金融機構、投資企業進行最高獎勵表彰,全國范圍內進行宣介。
四是利用專員辦職能優勢彌補省級監管盲區。必須要有獨立于省級財政的第三方,來組織開展省級層面的地方政府性債務監管工作。從法定角度來看,專員辦具備接受該項職能的先天優勢,財政部作為主管機構在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方面已經做了充分的授權,地方政府性債務監管的職權在此基礎上延伸即可。具體操作可先由中央授權財政部牽頭負責,財政部再授權專員辦牽頭省級監督。當然,專員辦目前的機構配備在履職方面還存在一定的不足,這既需要中央層面對財政部地方政府性債務監管給予更大的力量支持,也需要財政部對專員辦的職能做更深層次的加強。一方面,財政部可以減少專員辦過于零散的工作職責,使其擁有更為核心的業務和更為聚集的人力;另一方面加強專員辦的機構建設和人員配備,使其具備全面擔負起該項工作的軟硬件條件。專員辦作為獨立第三方,能夠在駐地串起金融行業管理部門、中央直屬金融機構與國有企業、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建立大監管框架。能夠將中央關于地方政府性債務的監管要求傳導給各地區和各利益主體,督促各方遵守相關法律和政策要求,監控區域性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這樣既解決了財政部對地方政府性債務增長鞭長莫及的困擾,也彌補了省級監管空白。
五是加快社會中介機構的獨立性體系構建。除了紅頂中介要加快與主管部門的徹底脫鉤外,還應該鼓勵社會中介機構獨立審慎地開展評價,鼓勵其注重長期構建良好的企業形象。因此建議組織中介行業的執業質量評比,對于那些不負責任地開展評價的中介機構,行業組織評價后,主管部門對其實行末位淘汰,強制性要求退出該行業市場。同時,對于評價報告質量低劣的情況,除中介機構退出市場外,還應對其所有者、管理者、項目經理等的不誠信行為計入社會征信系統,對情形惡劣的實施市場準入限制,促使經理人更注重職業性。同理,對于能夠獨立審慎地開展評價、評價報告優質的社會中介機構,應由行業進行評比后,主管部門對其進行表彰、宣介。通過優勝劣汰,實現社會中介機構的獨立性體系構建。■
(作者單位:財政部駐廣東專員辦)
[1]財政部.關于印發《財政部駐各地財政監察專員辦事處實施地方政府債務監督暫行辦法》的通知[EB/OL].(2016-11-24).http://ys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 ceguizhang/201612/t20161220_2485417.htm l.
[2]蔡寧,劉勇.中國省級地方政府債務規模預測——基于全口徑財政收支框架的研究[J].金融論壇,2017,(02). [3]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EB/ OL].(2014-09-21).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410/t20141008_1146374.htm.
[4]柯燕凌.政策取向下的我國地方政府債務融資“羊群效應”及其管控[J].武漢冶金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5,(04).
[5]劉亭亭.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現狀、影響及化解路徑[J].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12).
[6]馬金華,宋曉丹.地方政府債務:過去、現在和未來[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4,(08).
[7]馬金華.地方政府債務:現狀、成因與對策[J].中國行政管理,2011,(04).
[8]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調研組.關于規范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工作情況的調研報告 [J].中國人大,2016,(05).
[9]譚建立,范樂康.我國地方政府債務之確認、計量及報告研究[J].會計之友,2016,(07).
[10]俞喬,范為.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及治理研究[J].經濟研究參考,201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