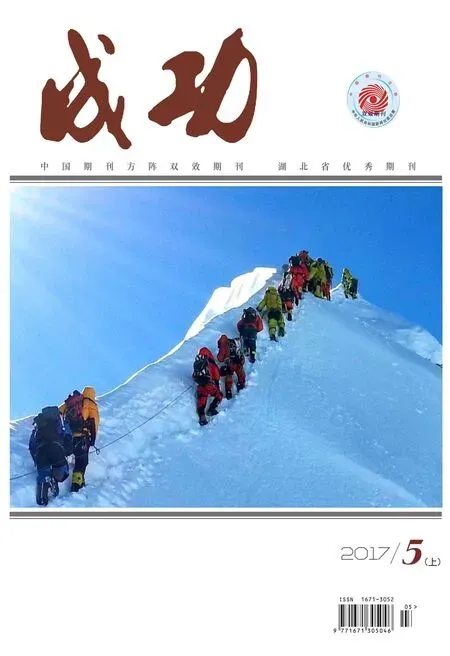也談大學教學與科研關系的歷史演變
陳龍
武漢理工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湖北武漢430070
也談大學教學與科研關系的歷史演變
陳龍
武漢理工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湖北武漢430070
自大學產生起,其教學與研究的關系是不斷演變的,古希臘的呂克昂與歐洲中世紀的大學,由于教學職能突出,科研尚為成為大學公開的職能,此時教學與科研處于一種自然融合的狀態。18世紀初期的柏林大學,由于洪堡等人的倡導與實踐,此時教學與科研的關系是統一的。19世紀下半葉特別是20世紀以來,隨著政治論哲學的主導以及高等教育逐步走向大眾化等,大學從理性大學走向學術資本大學,科研逐漸從教學中脫離出來,教學與科研的問題日漸突出,二者逐漸由分離走向對立。以歷史的視角回顧大學教學與科研的關系發展史,是現代大學選擇未來之路的重要借鑒。
大學;教學;科研;關系;演變
“在現代大學教育中,沒有任何問題比教學與科研之間的關系更為根本。”[1]如何處理二者的關系事關大學的興衰成敗與未來,但長久以來,教學與科研之間的不和諧幾乎影響著每一所高校。哈羅德·珀金告訴我們:雖然歷史并不是可作語言的水晶球,也不是可供占卜的魔鏡,但它至少能幫助我們了解我們曾去過哪兒。[2]為此,有必要追本溯源,對大學教學與科研的關系做出探索,這樣才能引導我們理性地選擇未來之路。
一、古希臘與中世紀時期二者的自然融合
科學研究是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雖然按照近代科學的范式來看,古希臘與歐洲中世紀的大學不存在科學研究,近代自然科學也是產生于15世紀后半期。而且洪堡也是在19世紀初才提出了“教學與科研相統一”的原則,但是洪堡所謂的科學研究是基于“純科學”的研究,舍棄了科學育人之外的外在功用,這似乎也為我們從大學開始誕生起就來討論教學與科研關系提供的合法性。
社會學家約瑟夫·本·戴維認為,自古以來,高等院校就是研究的場所。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及中世紀許多學者都把教學和科研結合起來,這種做法在今天仍是值得模仿的。[3]
(一)古希臘時期的呂克昂
公元前335年,亞里士多德效仿自己的老師柏拉圖創辦的學園,在雅典創辦了呂克昂。歷史學家佩德森認為亞里士多德的呂克昂是古代第一所具有大學性質的學校。呂克昂除了以為社會培養良好的、融洽的成員為教育目標外,其另一個重要的職能是進行學科與科學研究:柏拉圖尋求通過教學來進行教育,而亞里士多德則希望除訓練之外,還采用研究的方法來進行教育。[4]亞里士多德認為:要想進行正確的學科研究,不僅要對基本哲學問題進行理論思考,還要進行直接的實驗。[5]因此,呂克昂除教學之外,也是一個真正的研究機構。“學校中有序地陳列著各種學科的材料;在博物館中開設一個規模很大的手稿圖書館,學校保存了大量的教學材料;在柱廊中,懸掛著許多地圖,上面標示的地區都是古希臘地理學家和其他旅行家曾經考察過的;常常還有裝載了當時未知的東方的動物的船只來到呂克昂,其中一些是亞里士多德以前的學生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送給老師的禮物。亞歷山大在軍事遠征中,沒有忘記給老師送去這些新的研究資料。在呂克昂,亞里士多德親自從事研究,他在《動物自然史》一書中,描述了540種動物并將它們分類,從而創建了動物學。他對雞的生長過程的描述成為胚胎學的肇始。他還對希臘各城邦的體制進程進行了比較研究……繼亞里士多德之后,其后繼者泰奧弗拉斯托斯繼續從事教學,并開展亞里士多德生前已經開始的博物學和哲學史的合作研究計劃。其友人歐德摩斯寫了希臘數學史,希臘天文學史,還進行了宗教史的研究。”[6]
該時期的呂克昂,亞里士多德融教學與研究于一體。諷刺的是,近現代的研究觀點很少將呂克昂列入他們討論大學教學與科研關系的范圍,一方面是因為有學者認為學園才是世界第一所大學;另一方面,當時的“研究”跟中世紀時期的研究一樣,是一種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并未上升為大學的公開職能。因此,古希臘時期大學教學與科研是一種自然融合的關系。
(二)中世紀大學
近現代大學發軔于歐洲中世紀。受宗教神學的束縛,黑格爾與馬克思等人將中世紀形容成為黑暗的中世紀,根本沒有科學可言。中世紀大學也往往被看成僅僅具有教學功能而研究的重要性被忽視,似乎教學與研究的結合或統一是洪堡創立柏林大學以后的事了。但反對的聲音認為這是由于歷史產生的錯覺而導致的:一方面,如果只具有教學的功能,為什么稱其為大學呢?“從認識論的角度講,中世紀大學興起的真正根源就在于研究而非教學”[7],早先意大利南部的薩萊諾大學不僅僅培養醫學生,阿弗里卡納斯等人同樣致力于對古希臘與阿拉伯世界醫學著作的翻譯研究工作以及醫學理論的發展工作;另一方面,啟蒙運動以及近代科學范式變遷造成了中世紀大學缺乏科學研究,這本身其實就是不科學的。而如果單從“研究”的角度來看,中世紀大學除了教學之外還主要是一個探究的場所。“幾棵疏落的科學樹苗,必須在始終阻遇生機的曠野密菁中生長”。[8]
首先,探求高深知識(研究)是學術職業的首要使命,也是學者的“本能”。
歐洲中世紀后期,源自于古希臘的自由之風促進了中世紀歐洲自由思想的復興。人們對于知識的追求與渴望蔚然成風,除了生存之外,共同的興趣驅使學者們組成一個個行會組織,而這些行會即是中世紀大學的前身。因此,“對于高深學問的探求促進了學術職業的形成,并成為學術職業的首要使命。”[9]
研究是學者的本能。費希特有言,求知是人的本性,而學者必須深刻理解和發展高深知識。正如費希特所說:“誰獻身于獲得這些知識,誰就叫做學者……每一個學者,以及每一個選擇了特殊階層的人,都本能地要求進一步發展科學,特別是發展他們所選定的那部分科學……他的進步決定著人類發展的一切其他領域的進步;他應該永遠走在其他領域的前頭,以便為他們開辟道路……只要他活著,他就能夠不斷推動學科前進。”[10]因此,他們不僅是知識的賣藝人,他們更是學者!
其次,在中世紀的大學,由于沒有現代的所謂“出版”或“發表”之說,教學與研究之間并沒有明確的組織和制度邊界。每一個教師既是高深知識的傳播者也是研究者,這個時期的教學與科研也是結合在一起的:包爾生認為19世紀的德國大學又重新具有了早期大學傳統特征的一部分。[11]JamesAlfred Perkins認為,19世紀之前,以個體學習、反思和寫作為形式的學術或研究“幾乎一直被看作是教師做好工作的關鍵要素,因為它可以使教師保持敏銳的頭腦,授課內容新穎并能促使學生心智活躍”。[12]
相較于古希臘的呂克昂,中世紀大學教學與科研的關系屬于一種隱秘的結合。除了源于“研究”的功能在教學面前顯得“相形見絀”以及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并無法像現在這樣發表而是融入了自己的教學中之外,在約瑟夫·本·戴維看來,“在十九世紀以前的大學中,包括在首先實現改革的德國大學中,教學與研究一體化是教授個人的事。可是,他的教學是公開的,而研究則是在家中書房里或者在私人實驗室里非公開地進行的。”[13]
二、洪堡時期柏林大學的“教學與科研相統一”
15世紀下半葉,近代科學應運而生。由于種種原因,近代科學并未產生于大學之內,盡管在16世紀的某些大學已經有了一些少量的科學研究活動,但整體而言直到18世紀末,大學教學與科研的關系仍舊沿著中世紀大學教學與科研關系的歷史軌跡緩緩前行著。
1810年,洪堡建立柏林大學,正式確立了科研在大學中的重要地位,并倡導教學與科研相統一的原則。柏林大學建立起至19世紀中葉之前的這段時期,由于洪堡與費希特等人的倡導與實踐,教學與科研的關系是統一的。洪堡認為:如果規定大學的任務是傳播知識,科學院則是發展科學,這對大學是不公平的,因為大學教師的貢獻絲毫不亞于科學院的研究者,而且大學有大批青年人在不斷探索科學,也能促進科學蓬勃地發展。[14]因此,洪堡等人倡導將教學從傳統的講課聽課擴展到科學研究的全過程,認為研究的過程就是教學的過程并認為“近代大學里教學與科研只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而不是兩個不同的事物,只要教師和學生共同聚焦于研究,統一是自然而然的狀態[15];
有學者認為,洪堡等人提倡的“教學與科研相統一”有其發生的歷史必然性。洪堡提倡的教學與科研在內源上具有其一致性:就教學來說,洪堡時期的高等教育依然是一種精英教育,高等教育的對象局限于有閑階層,而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則僅僅是為了滿足“閑逸的好奇”——對新知的向往和追求。與之相適應,教學的主要目的則在于“在于培養人的自由探索和追求真理的精神,造就致力于發現真理的研究者。”[16]而這個時期由于大學仍然是脫離于社會的象牙之塔的“純大學”,因此所開展的科學研究往往不帶有實用與功利的目的而是去發現真理,即“為科學而科學”。而洪堡是“純科學”觀的堅持者,即使在他所處的年代,科學的實用價值正在顯現。因此他主張的科學研究是一種解釋性的、哲理性的純科學研究。如此,在那個時期,科研是為了發現真理,教學是為了培養發現真理的人。同時,洪堡等人為實現“教學與科研相統一”在柏林大學實施區別于傳統學院制的習明納與實驗室制度等意味著“當科學和大學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純科學和純大學都已成熟同時又走到歷史的交匯點時……教學與科研統一的基礎和條件就成熟了。洪堡的貢獻,就在于他洞察了科學研究與大學教學的過程的內在一致性,洞察了雙方統一條件的成熟,并且給出了成功的推動。”[17]
三、19世紀中葉以后的大學教學與科研:分離走向對抗
19世紀中葉以后,柏林大學的經典模式,包括“教學與科研相統一”的理念和各項改革制度紛紛被其他大學效仿。來自世界范圍內的求知者在德國古典大學受到訓練后回國并竭力以柏林大學為標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數美國研究型大學的興起。1876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創辦并成立教育史上第一所研究生院,事實上標志著美國研究型大學發展的開端,而此時,德國古典大學的經典模式也逐漸被美國模式所取代。并且“隨著學科制度化的推進和學術專門化浪潮的盛行,科研逐漸脫離教學成為大學的第二職能。隨著現代大學對于科研職能的不斷強化,尤其是研究型大學的興起,無論在資源配置還是組織建制上教學逐漸處于次等的地位,無法與科研相提并論”。[18]重科研輕教學現象日益盛行。可以說,柏林大學經典模式后教學與科研關系發展史實為一部逐漸從分離走向對立的歷史。
首先,柏林大學創辦初期的隱患愈演愈烈。其一是由于文化國家理念的破產以及民族國家的全面崛起。“思想根植在新人文主義與德國自由主義土壤的洪堡,其所倡導的大學為國際服務但遠離政府的觀點,在封建集權主義的普魯士遭遇抵抗。更何況,1807年普魯士慘敗在拿破侖的鐵蹄下,民族屈辱使全國上下熱盼國家復興而非個體覺醒,從而一方面直接導致洪堡理念未能在實踐層面得到貫徹,另一方面注定了柏林大學的國家主義取向”。[19]面對如此境況,上任僅僅16個月的洪堡于1810年6月便黯然辭職。其二是教育的非功利性與以充滿活力的經濟以及冉冉上升的自然科學為代表的實用性之間的沖突一觸即發。與洪堡創辦柏林大學初期的景象相比,其內部出現了這樣一幅景象:“早在1818年,時任柏林大學校長菲利普·康拉德·馬萊訥克(PhilippKonrad Marheineke)在一次動員報告中批判了學生學習的‘功利取向’,認為他們把精力消耗在學習那些未來實踐生涯必備的東西。而此時已作為旁觀者的洪堡對柏林大學現狀亦憂心忡忡”。[20]
其次,當初“純科學”一統天下的局面已被打破。洪堡所謂的“科學”與科學研究,完全是出于對未知的探索來實現精神上的富足而舍棄功利性的追求,而現在意義上“科學”的涵義則要豐富得多。1963年,普賴斯在《大科學,小科學》一書中提出大科學的概念。他認為隨著時間的轉移,科學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相比于小科學時代的“探求真知,科學家之間的競爭依賴的是其在學科領域獲得的科學成就,科學與社會的關系更為純粹,在契約上表現為資助和被資助、啟蒙和被啟蒙關系,科學研究帶有很強的自主性和前瞻性”,[21]“而在大科學時代,問題設置的目標導向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科學家個人的興趣和好奇心導向,同時更加需要各學科的協作分工,社會范式對其研究的開展具有較大的制約和影響。科學對社會資源的亟需將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科學的發展和科學家的研究不能對社會需求置之不理,否則將得不到科學研究所必須的社會資源的支持,從而受到一定的限制。科學不再是以往的科學,在研究領域方面范圍更大,研究目標與質量控制一定程度上代表著社會的利益訴求,研究與社會關系之間的紐帶更加緊密。”[22]因此,在現代大學里,一旦純科學被應用科學所取代,教學與科研的統一就只能是一種奢想!
再次,威斯康星思想的蔓延以及政治論哲學的絕對主導讓洪堡的純科學構想失去了現實可行性。到19世紀末,政治論哲學和認識論哲學在美國的大學里并存且已都被牢固地建立起來了。到20世紀初期,范海斯的威斯康星思想明確了大學為社會服務的第三大職能,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大學或科研被要求服務于國家與社會或戰時需要,斯福大學與MIT等研究型大學的興起已然說明了這一點。而在二戰以后,高等教育發展中的政治論哲學取代認識論哲學居于絕對主導地位,這也意味著大學沒有辦法脫離于社會而獨善其身,有德國學者如此評論到:“從嚴格和傳統意義上講堅持教學與科研統一的原理不存在了……教學與科研緊密結合已失去了它神圣不可侵犯和不可懷疑性,它們的分工關系被削弱了。”[23]特別是二戰后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的來臨,大學傳統的運作方式與內部活動都在發生改變,教學與科研也被賦予新的意蘊,教學目標的多元化與科研類型的多樣化使得二者賴以統一的紐帶愈發脆弱甚至產生斷裂現象。伯頓·克拉克所謂的“教學漂移”(教學從以科研為中心的系和大學拉出來,移到專門負責教學的機構和大學[24])與“科研漂移”(它們明確把科研活動從大學的教學單位和中心的課程架構中分離出去[25])也就不可避免。
四、未來之路:復歸
對于現代大學而言,并沒有足夠的科學的證據可以證明教學與科研的統一曾經發生過抑或可能發生,但大學史可以表明,教學與科研的統一的確源于近代大學。柏林大學經典模式已經是過去式,科學與科學研究的外延也早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追求現代大學教學與科研的統一似乎已成為一種“迷思”與神話。如果脫離了傳統的“教學與科學相統一”,是否還會存在如此多的對教學科研關系的大討論?更進一步,現代大學所真正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意義又是什么?畢竟“知識如果得不到研究的培育,就會凋謝和枯萎。教學如果得不到研究的支持,也會喪失活力”。[26]更進一步講:也許我們是時候回歸洪堡的“由科學而達致修養”,即“在無盡的探索之中,研究者會獲得啟發,進而能把自己從當時束縛著自身頭腦的目的中解放出來,個人天賦完全地發展,各種潛能最圓滿、最協調地發展,最終融合成一個整體,成為真正的完人”。[27]
[1][2][12][13]吳洪富.大學教學與科研關系的歷史演化[J].高教探索,2012,05:98-99.
[3][14][26][27]吳洪富.用神話譜寫現實:“教學與科研相統一”的歷史再造[J].復旦教育論壇,2012,05:17.
[4][5][6]賀國慶,王保星,等.外國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26-27
[7][11][15][18]王建華.重溫“教學與科研相統一”[J].教育學報,2015,03:77.79.
[8]徐兵.歐洲中世紀大學的科學研究與科學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1996,06:86.
[9][10]李志峰,沈紅.學術職業:歐洲中世紀時期的形成與形態[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04:45.
[16]李澤彧,曹如軍.大眾化時期大學教學與科研關系審視[J].高等教育研究,2008,03:52.
[17]周川.從洪堡到博耶:高校科研觀的轉變[J].教育研究, 2005,06:28.
[19][20]俞可.洪堡2010,何去何從[J].復旦教育論壇, 2010,06:26.
[21][22]高曉聲.基于知識生產模式轉型的產學研合作模式創新研究[D].武漢理工大學,2015.
[23]符明娟.比較高等教育[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13.
[24][25]伯頓·克拉克.探究的場所—現代大學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M].王承緒,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