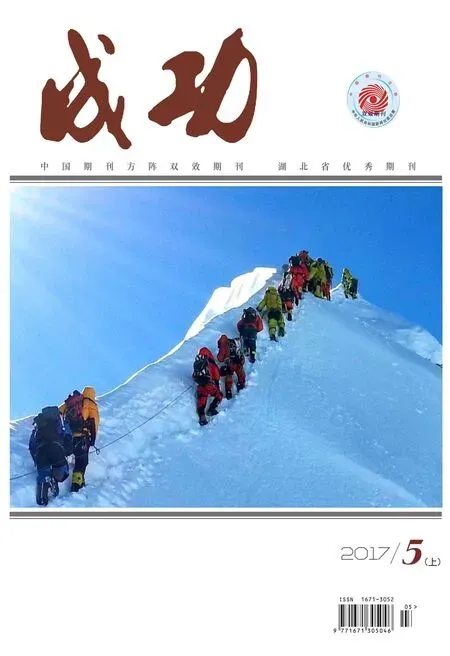親權制度下委托監護人的家庭教育權問題研究
范國
武漢理工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湖北武漢430070
親權制度下委托監護人的家庭教育權問題研究
范國
武漢理工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湖北武漢430070
家庭教育權是親權人以其血緣關系為基礎而存在的。在親權人死亡或者無法履行親權行為時,監護人得以產生。在親權制度下,委托監護人是否擁有家庭教育的權利與資格?本文對親權人、監護人與家庭教育權的關系進行了比較分析,并提出了監護人家庭教育權委托制度的立法建議。
家庭教育權;親權;監護
在大陸法系中,就未成年人的保護而言,監護制度一直被視為親權制度的補充與延續。僅在未成年人雙親死亡或者不能行使親權時,監護才得以存在。自民法法典化以來,親權與監護一直作為兩種獨立的制度發揮著作用。但是在我國民法中并未明確區分親權與監護,一般將監護看作廣義上的理解,采用了大監護的概念,即監護制度包括父母的監護與其他成年人的監護。由此便導致了監護人(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在教育未成年人子女權利與義務立法方面的混亂。
一、親權與監護的區別
在討論親權人與監護人對于未成年子女家庭教育權利的關系之前需要厘清親權與監護的區別。通過對已有文獻的整理,親權是基于父母的身份關系而產生的專屬的、為保護未成年子女利益的權利和義務[1]。其法律特征主要體現在:(1)親權是父母基于其身份所有之權利義務;(2)親權是以保護教養未成年子女為目的,對其具有撫養的義務;(3)親權不但是權利也是義務,父母不得拋棄其權利,也不許濫用;(4)立法對親權采取放任主義,一般奉行親屬自治,不設置監督機構。
而監護是指不在親權照護之下的未成年人以及精神病人等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和限制行為能力人,為了照顧、保護、管理其人身權利和財產而設置的民事法律制度[2]。其法律特征主要體現在:(1)監護是以法律程序為基礎的,不強求親屬的血緣關系;(2)監護的目的在于彌補未成年人行為能力之不足,側重于對被監護人人身權和財產權的保護,但是不包括對被監護人的撫養義務;(3)監護相當程度上只有義務的規定,很少有實質性的權利規定,因此,監護本質上是一種職責;(4)監護往往設置監督機構,監護人在行使監護事務時受到監督。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親權人和監護人在對未成年人的權利與義務、目的與監督等方面的側重點是不相同的。那么對于家庭教育權親權人與監護人的職責在我國立法規定中又存在著怎樣的差異。
二、家庭教育權與親權人、監護人
(一)家庭教育權與親權人
我國法律明確規定受教育權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如《憲法》第46條、《教育法》第9條和第18條等。對于受教育者來說其擁有受教育的權利,而對于實施教育者來說則擁有教育權利。按照大多數學者的觀點,將教育權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狹義的理解是指對受教育者享有施加教育的權利,這個權利的主體是教育者,包括國家、學校、教師和家長等;廣義的理解則不限定在教育者的教育權方面,而且包括受教育者的權利或教育請求權,即把接受教育的兒童及父母、教師、學校、國家等作為教育權利、義務、責任和權限關系的整體去理解,而不是單純的從教育者的行為作用方面去理解教育權[3]。本文中的教育權利主要是指狹義的理解,因此,根據教育主體的不同,將教育權利分為三個層次:國家教育權、學校教育權和家庭教育權。基于以上對于教育權利的界定,我們可以得出,家庭教育權是指家長作為子女的監護人,有權利在法律的范圍內對子女進行教育的權利。
從家庭教育權的起源來說,家庭教育權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而產生存在的。在一個家庭當中,當子女出生父母就自然而然的被賦予了撫養、教育子女的權利。而隨著社會的不斷的發展,國家的日益強大,家庭教育權利的私人性漸漸不再明顯,因為在現今社會,教育不再僅僅是一個家庭的事情,教育的優良關乎著整個國家未來發展的道路。除此之外單純的家庭教育已經不能滿足社會化大生產對于人才的需要,于是國家開始在教育中占據了主導的地位,國家的教育權利逐漸擴大,而家庭的教育權利漸漸的縮小。但是,家庭教育權仍然是一種與生俱來的、任何權利都無法取代的教育權利。
從家庭教育權的內容來說,我國有關親權人職責的內容主要見于《憲法》、《婚姻法》、《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教育法》、《義務教育法》等。概括的來說,家庭教育權不僅指父母在家庭內部享有的對子女的教育權利,還包括外部父母對學校教育所享有的權利。如果將其限定在學校教育或者與學校相關的領域,且根據學校的類型,限定在義務教育階段,從一般意義上來探討其主要內容。實體法上的權利主要包括兩個重要方面:一是父母的教育選擇權,主要是選擇學校的自由以及選擇其它教育形式;二是父母對教育的參加權,主要包括對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義務教育決策制定的參與權、知情權,對學校教育包括教學內容、教學方式等的參與權[4]。
(二)家庭教育權與監護人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家庭教育權是親權人即父母基于其身份所自然產生的權利,當親權人無法履行親權的情況下,將未成年人子女委托給監護人,那么家庭教育權是否可以委托于監護人?關于監護人的職責,其主要散見于《民法通則》、《未成年人保護法》、《義務教育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與親權人涉及家庭教育權的法律文件多有重合。通過對以上法律法規的梳理,這些規定中涉及到監護人與家庭教育權的內容主要有[5][6]:
1.《民法通則》第18條規定:“監護人應當履行監護職責,保護被監護人的人身財產及其他合法權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規定“監護人的職責包括:保護被監護人的身體健康,照顧被監護人的生活,管理和保護被監護人的財產,代理被監護人進行民事活動,對被監護人進行管理和教育。”
2.《未成年人保護法》第10條規定:“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以健康的思想、品行和適當的方法教育未成年人,引導未成年人進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動”;第43條規定“父母或其他監護人應當尊重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權利,必須使適齡未成年人按照規定接受義務教育。不得使在校接受義務教育的未成年人輟學。”
3.《義務教育法》第15條規定:“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必須使適齡的于女或者被監護人按時入學。接受規定年限的義務教育。”
4.《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10條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對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負有直接責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結合學校的教育計劃,針對具體情況進行教育。”第14條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監護人和學校應當教育未成年人不得有下列不良行為……”。
5.《教育法》第49條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為其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監護人受教育提供必要條件。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配合學校及其它教育機構,對其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監護人進行教育”。
三、監護人家庭教育權委托存在的問題
通過以上內容,可以看出在我國現行的立法中由于缺乏完備的監護制度,采用了大監護的概念,對親權人與監護人的職責只是作了合并式的籠統規定,導致親權人與監護人的職責相互重疊,無法區分其差異性。除此之外對于親權人是否可以將家庭教育權委托于監護人,監護人是否擁有家庭教育權的資格也沒有進行明確的規定。法規的條文及其思想近乎于將親權人所有職責等同于監護人的職責,似乎默認了監護人擁有對未成年子女進行家庭教育的權利。但是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實踐中侵害未成年人子女受教育權的情形屢有發生。其中,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問題尤為突出,父母由于常年外出務工無法行使家庭教育權,將未成年子女委托給監護人,而對于監護人是否擁有教育未成年人的能力,對其資格和范圍的認定都存在立法模糊的困境:
首先,對于家庭教育權是否可以委托,《民法通則》若干意見第22條規定“監護人可以將監護職責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給他人。”在此處,監護人應該理解為親權人,那么親權人的監護職責就應該包括對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教育權,那么家庭教育權是否能夠如身上照顧權和財產管理權一并委托給監護人?此處的表述過于抽象化,這樣的法律空隙無疑是為監護人依個人意愿履行家庭教育的監護事務提供了理由。
其次,退一步理解,假設家庭教育權可以被委托于監護人,但是對于監護人教育監護的能力的認定又存在著諸多漏洞。《民法通則》第16條強調了“有監護能力”,卻沒有對家庭教育監護能力認定標準進行規定。《民通意見》第11條規定“認定監護人監護能力,應當根據監護人的身體健康狀況、經濟條件,以及與被監護人在生活上的聯系狀況等因素加以確定”,這樣的規定絲毫未提及監護人教育能力的問題,而且規定過于原則,在現實生活中難以操作,對監護人的任職資格也難以把握。由于缺乏法律法規的理性制約,監護人純粹依各自所想履行家庭教育監護職責,常常無形中忽視或損害了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因此,為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受教育權利,在親權制度下,有必要明確家庭教育權是否可以委托于監護人,并建立相適應的法律制度。
四、監護人家庭教育權委托制度的立法建議
在親權人無法履行對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教育權時,將家庭教育權委托于監護人,同時對監護人進行家庭教育的資格和范圍認定,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護未成年子女家庭中受教育的權益。因此,要解決我國現行法律中關于監護人對未成年子女家庭教育權利義務的規定中存在的概念不全、職責混亂等問題,必須建立監護人家庭教育權的委托制度。
(一)在體例上明確區分親權與監護
我國現行法上已確立了監護制度,《民法通則》擴大了監護概念,將親權強行納入未成年人監護,父母對未成年人的管教保護亦為監護。這種合并立法無視監護與親權之差異,缺乏理論支撐與科學性,并不妥當。退一步講,即使以監護吸收親權,但由于親權不同于監護的特殊性,監護無法完全地包容親權。此外,區分家庭教育權在兩者之間的區別與聯系,這不僅有利于親權制度的建構,使親權人能正確的行使家庭教育權,也有利于監護制度的完善,保護未成年子女在家庭中的受教育權。
(二)詳細規定監護人獲取家庭教育權的資格
監護制度是合同關系,因此雙方當事人理應具有民事行為能力。除此之外,為保障未成年子女受教育的利益,監護人還應具備家庭教育的能力。我國法律已對監護能力有所規定,現需對已有條款進一步細化。由于家庭教育監護能力認定的肯定條件難以細化,設置監護能力認定的消極條件在現實操作中不失為理性選擇。
[1]梁慧星.民商法論叢(第6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年月版,1997,(04):4.
[2]陳智慧.論監護與親權[J].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 2000,(02):105-109.
[3]周明祺.我國家庭教育權利訴求及法律規范研究[D].西南大學,2014.
[4]林婷.家庭教育權保護研究[D].山東大學,2008.
[5]李霞.監護制度比較研究[M].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 2004,(04):371-374.
[6]秦慧民.走入教育法制的深處論教育權的演變[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8,(09):172-174.
范國,1993-,男,安徽蚌埠人,武漢理工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經濟與管理專業,2015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經濟與農村教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