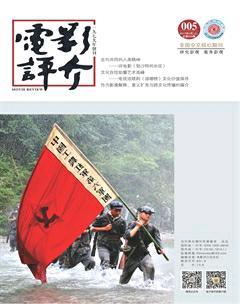從電影《長城》看中美文化的碰撞與融合
李小剛
霍夫斯坦德所定義的文化概念,既將中美文化以其民族性與差異性進行了分野,又將中美文化依其共通性與相融性進行了某種基于形而上的文化式契合。從影視藝術的視角而言,中美文化間的碰撞尤為強烈,但與此同時,中美文化之間,亦越來越呈現出一種美國強勢現代文化,向中華傳統文化的強輸入性與強排斥性下的激烈碰撞,以及中華傳統文化與美國強勢現代文化間,潛移默化的深度融合的漸進式大趨勢。由這種視角觀察,《長城》這部中美合拍影片具有著劃時代的意義,這部影片開啟了一個由中方主導影視創作的新時代,這標志著中國影視產業已經以中國元素崛起于世界影視藝術之林。
一、 中美文化的碰撞
(一)文化異向性
《長城》是由中國萬達影業與美國環球影業聯合公司等中美電影公司共同出品的大作,這是一部由中國著名導演張藝謀執導,由諸多中外影視巨星鼎力加盟合作的一部奇幻動作大片。影片以中規中矩的中國文化的典型恢弘格局開篇,以架空歷史的視域,將饕餮襲城事件作為整部影片展開的關鍵。饕餮本是中國古典神話之中的宮廷守護神獸,《長城》對這種神獸怪獸化的顛覆,顯然源于中美文化的一種表象化碰撞,中國文化更傾向于所有怪獸為我所用俯首稱臣化,而美國文化則明顯傾向于以人類英雄清除所有怪獸的個人英雄主義化。這兩種文化在《長城》這部電影中顯然進行了一種隱性的較量。同時,長城在中國文化中亦有著多重含義,既是守御、屏障、安全,又是文明、象征、驕傲、威權。中美兩種文化在《長城》一片中的碰撞表現為中國文化在左,美國文化在右。[1]
(二)思維異向性
中美文化在《長城》一片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影片中左手的中國文化恢弘典雅,右手的美國文化則一己獨大。究其根源,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全球化的自由主義造就了美國的國家內部氛圍其實是屬于俯就國民且威權弱化的,而中國的國家內部氛圍則在其歷史傳統上是由和諧社會所承托起來的一種君臨天下。事實上,軟文化的碰撞以及由此引發的沖突,更容易成為泛影視藝術的最終硬傷,而軟文化的碰撞與沖突的本質就是文化差異以及由文化差異所帶來的文化接受力問題。其實,文化差異更源于對待文化意識形態的思維方式、思維路徑、思維模式的不同。從《長城》這部影片來看,三個美國人即有三種思維方式,其思維路徑與思維模式亦各不相同,這就是美國文化所最為崇尚的個性化,這種個性化顯然與中國文化思維所強調的整齊劃一大相徑庭。
(三)根性異向性
觀看《長城》這部影片,可能給觀眾留下的最為深刻的印象,就是人類在面對饕餮一般的洪水猛獸時的那種倍感無力,卻不得不掙扎的深深的無奈之感,這其實恰恰是新常態下中美文化碰撞的一種極具直觀性的表象化表現。中美文化不僅存在著文化與思維兩個方面的異向性,而且更存在著根性上的異向性。這也是《長城》這部中美合拍片中過度硬性地植入中國元素,所帶來的人為式的文化碰撞的一個根本原因所在。在影片中,我們亦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其實危脅國家安全的一切饕餮亂象皆源于饕餮幕后的獸王,而這種中國式亂象恰恰在影片中,遭遇到了凸顯個性精神與個人主義的美式英雄。影片中的這種中美文化根性異向性的種種“奇特交錯”,更將對中美文化的既有思維秩序帶來可以預期的一系列碰撞。
二、 中美文化的融合
(一)技術與視效呈現
《長城》這部影片是中美合作影片之中,極為罕見的幾乎全部以外籍演員視角所拍攝的一部雄輝壯麗的史詩級奇幻大作。從《長城》這部影片中的視覺語言處理而言,可謂是極盡了壯闊恢弘之能事。尤其是其中的戰斗場景的處理,更是集結了工業光魔與維塔的天作之合,以及中美其他視覺特效與后期精英團隊等,皆為整部影片的視效增添了許多出彩之處。影片中描繪戰爭場景的史詩般的蒙太奇,更是將觀眾帶入到了身臨其境般的奇幻動作場景之中。從影片細節而言,《長城》一片中,怪獸攻城時的獸王頭部筋膜的顫動,以及眾獸頸部風琴琴腔狀筋膜的同步顫動共鳴等細節表現,更是將美國式現代視效技術,與中國式傳統典籍《山海經》中的想象,精巧逼真、妙手天成般地融冶于一爐,為影片憑添了足以撼動人心的力量。
(二)執導與協同合作
首先,這部《長城》其本身就是一部中美文化深度融合的典范之作,在中美影視文化之間,構筑起了一座溝通中美影視藝術的長城。中美之間傳統的影視藝術交流通常僅限于資本、技術、制作、非主要演員類人員支持等合作。然而,在這部影片之中,由外籍演員擔綱的主要角色就多達三個,這在中美合拍片中不多見。同時,整部影片中的視覺特效與后期制作亦幾乎為中美智慧合作的結晶。其次,《長城》這部影片,與以往的中美合拍片的絕大多數由美方全權執導不同,這部影片由中方執導,并由中方參與了大量的包括劇情等的設定方面的工作。最后,在這部影片中,中美雙方的主要演職人員進行了較多的互動與團結協作。在這部影片的最后,觀眾們看到,在強大的饕餮已經幾乎完全失控的情況下,中美雙方的男女主角以信任的彼此承諾完成了幾乎不可能完成的守衛任務。
(三)交集游離與共性彌合
文化之間的碰撞,以及由文化碰撞所引發的沖突,顯然無法徹底避免;在文化碰撞與沖突中,顯然不可能存在真正意義上的贏家。只有有意識地由雙方均采取主動地進行文化融合,才能最終獲得雙贏乃至于多贏的局面,對于這一點,中美影視文化界雙方,近年來不僅都已經強烈認同,而且正在努力強化著雙邊的密切合作。在中美文化碰撞中,我們看到,中美文化間的碰撞本源,其實就是一種文化交集的失控性游離,無論是文化還是思維,抑或是那種根性碰撞的產生、發展、呈現等,最終都能夠由共性加以彌合。并且,隨著后現代影視文化共生性、共時性、共進性的不斷發展,中美影視文化界之間的交集失控游離,正在共性融合的過程中,不斷地趨于彌合。同時,在事實上,從中國近年來的影視藝術發展觀察,中國的開放性、包容性、前瞻性等,正在與美國文化無縫彌合的過程中獲得了影視文化間的一種更加深度的融合發展。[2]
三、 中美影視文化未來發展
(一)中美影視文化合作話語權
其實,無論是中美影視文化間的無意識碰撞,還是中美影視文化間的有意識融合,其根本利益都是為了尋求一種共贏式發展。共贏式發展已經成為世界影視文化未來世紀同步發展的一種必然。從美方立場剖析來看,一方面,全球化的自由主義立場更符合美國的全球文化政策;另一方面,以影視藝術先聲奪人亦更符合美國的全球文化輸出。在這兩方面來看,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處于文化合作話語權被動狀態。但同時亦應理性地看到,美國的基于文化的全球影響力與全球吸引力,恰恰是美國崛起的真正原因。令人欣喜的是,在中美影視文化合作的過程中,《長城》一片意義重大,這部影片不僅開啟了中國話語權的世代,而且更開啟了中美合拍片的中國決策的世代,中方的決策權在這部影片中明顯地處于主導地位。這也使得中國元素與中國文化價值觀得以全面灌輸到這部影片中來,“中國元素越多,顯然利益越大”,這種中國元素與中國文化價值觀的合體,在這部中美合拍片中,具有著開天辟地的意義。
(二)中美影視文化合作新模式
影視文化的碰撞與融合更考驗執政者的高級文化智慧,中美影視文化的合作話語權的轉變,使得傳統的美方話語權、決策權、文化價值觀等均能夠為中方所左右,這種中美合作方式顯然將在未來開啟一個中國影視文化主導全球的世代。我們看到,當歷史進入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美國的六大紛紛祭出中文化法寶,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快速崛起并不斷走向成熟的影視市場正在深受世界青睞。尤其是中國電影每天15塊銀幕的極速成長,更是使得中國將很快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票倉,在中國放映的電影票房甚至已經開始出現超越美國本土的現象。這就更呼喚中美影視文化合作更多新模式的不斷探索與不斷完善。中美影視文化合作由投資好萊塢作享全球收益的模式,到合作升級中國深度參與到有中國特色的好萊塢影視工業化制過程當中。顯然中國資本、中國渠道、中國受眾、 中國智慧、中國文化在其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而《長城》一片甚至嬗變為由中方主動收購好萊塢公司獨享全球收益,這種中美影視文化深度合作的新模式,對于中國電影未來發展意義重大,必將成為中國電影國際化發展的新起點、新開端、新動力。[3]
(三)中美影視文化合作新發展
近年來,隨著中美影視合作高峰的來臨,已經預示著中美影視文化正在開啟一個由碰撞而融合,由融合而共同發展的共生共進、共同繁榮的偉大的新世代。其實,中美影視文化未來發展,完全可以無關政治,不論中美兩個超級大國的國際關系未來如何,中美影視文化交流都必將成為未來一個世紀的影視藝術發展的主旋律。中國既擁有著好萊塢所迫切需要的數以十億計的成熟觀眾群體,又擁有著好萊塢所迫切需要的無比深厚的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底蘊。在這樣的雙重迫切需求之下,《長城》這部深度合作影片的應運而生,其實更像是一種歷史發展的必然。《長城》這部史上最大規模的中美合拍影片,即便最終票房結果是命途多舛,也已經無關宏旨。因為,中美影視文化界已經在深度融合、深度合作、深度發展的過程中邁出了可喜的一步。展望未來,我們看到,無論中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政治經濟博弈如何,中美兩國間的影視文化方面的合作,正在越來越密切,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和諧。[4]
結語
最大規模的中美合拍片《長城》是一部恢弘壯烈、大氣磅礴的史詩巨制,如果從更加深刻的意象而言,《長城》這部影片其實是以其恢弘的史詩筆觸,發出了凝聚人類共識的強烈召喚,中美影視文化在這種召喚下已經比以往都更加緊密地集結在一起。誠然,美國影視文化作為一種目前全球領先的異域文化,其文化傳播與輸出均處于強勢地位。而近年來美國影視文化向中國影視文化的傾斜越來越明顯。這種中美影視文化的融合發展已經成為中美兩國因應國際間文化合作的明智且共贏之舉,此舉對于塑造與強化更加靈活且成熟的中國影視文化體系大有裨益,《長城》事實上已經邁出了可喜的一大步。中美雙方在這部影片中合作的成功,也昭示著作為中美真正大規模合作的先行者,無論《長城》最終票房若何,其都已經為中美影視文化間真正拋卻文化碰撞,真正進行更加深度的大規模融合的新起點、新開端、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