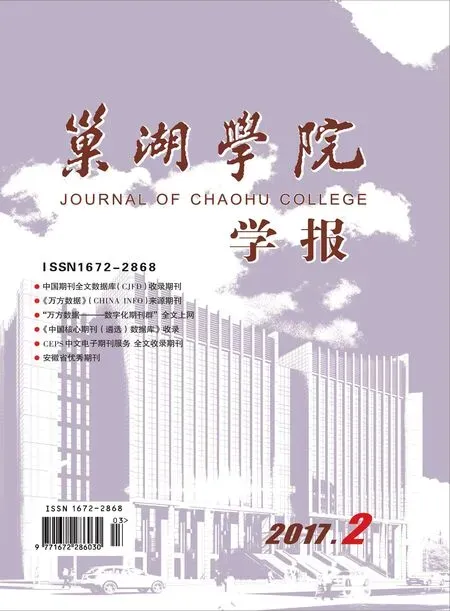傅斯年對傅樂成人品和史學的影響
劉文釗(淮北師范大學,安徽 淮北 235000)
傅斯年對傅樂成人品和史學的影響
劉文釗
(淮北師范大學,安徽 淮北 235000)
作為傅斯年的侄兒,“臺灣秦漢隋唐帝國祖師”傅樂成不負眾望,不僅沒有被伯父的光芒所掩蓋,更是以自己的行動使傅氏史學最終得以延續。在傅樂成眾多成就的背后,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傅斯年對他的影響。這不僅表現在傅樂成的史學研究中,也體現在傅樂成的品德性格之上。
傅樂成;傅斯年;人品和史學影響
對于傅斯年的史學研究,至今仍然是史學界的熱門話題。傅斯年對近現代史學影響深遠,同時也在品性和學問兩方面影響了當時很多史學家。傅樂成作為傅斯年之侄,能夠得到“臺灣秦漢隋唐帝國祖師”之名,受到多方贊譽,自然與其受到伯父的影響息息相關。本文將從傅斯年對傅樂成的人品和史學的影響兩方面著手,為傅樂成后來的史學成就和人品性格追根溯源。
1 傅斯年對傅樂成人品影響
傅斯年學通中西,博古通今。傅氏一門,也是仕官盡出,書香門第。但是傅斯年卻并不以祖上傅以漸為榮,他認為傅以漸沒有民族氣節,給清朝滿人做官,實屬不該。傅斯年的這種觀念來自于祖父傅淦(笠泉公),傅淦飽讀詩書,好做詩文,文武兼修,精通醫道,心懷正氣,年輕時好結識江湖好漢,快意恩仇,頗有俠士風范。對待朝廷宦官,更是直言道“生平不為無鳥之人看病”“生平不要無鳥者之錢”[1]。傅斯年 “受他的影響最深,他可以說是孟真先生學問人格基礎的奠立者”[1]1944年,傅斯年在參政會上炮轟孔祥熙,揭發其在美金公債中貪污舞弊的行為,即便蔣介石出面亦無所作用,最終孔祥熙被免除 “行政院長”和“中央銀行行長”之職,可見傅斯年的正義感與責任心。傅斯年對傅樂成的諄諄教誨,大多記載于傅樂成晚年的回憶文《夢里的典型——回憶先伯傅孟真先生生活的幾個片段》中,傅樂成于北平讀書期間,曾寄住于傅斯年家長達兩年,赴臺后更是得其伯父鼎力相助,傅斯年對傅樂成的影響不僅體現在治史的方式方法上,更是體現在做人的性格與品行中,主要有三:
1.1 勤儉
傅樂成求學期間,個性懶散。伯父傅斯年和伯母俞大彩經常親自輔導傅樂成英文,傅斯年常因為其懶惰怠慢而督促批評;傅樂成不愛整理房間,不免屋內臟亂,傅斯年常常催促其整理打掃;若是遇到雨雪天氣,傅樂成惰性發作,不愿上學,傅斯年便勒令他乖乖去學校:“哪怕是下刀子,你也要去上學!”[2]有次胡適的夫人送了傅樂成一支自來水鋼筆作為禮物,那時候的學生能用蘸水鋼筆便已是十分不易,而自來水鋼筆對于他們則是奢侈品,傅斯年便訓示傅樂成要好好愛惜。傅樂成年少時喜好打架,花錢大手大腳,不知勤儉為何物,常常因為這些原因被傅斯年訓斥,若是起床晚了、鍛煉少了,傅斯年便會頗有微詞,奈何傅樂成深得祖母疼愛,往往傅斯年訓斥他時,祖母總是出來為他說情,有時甚至會對傅斯年發脾氣。傅斯年事親極孝,也不敢忤逆老太太的意思,只得作罷。但是,傅斯年的督促和訓示,卻在記憶中伴隨了傅樂成一生。傅樂成晚年時,仍常常于夢中見到傅斯年的背影,在他的督促和訓導中驚醒,可是故人不在,令其傷感不已。
1.2 禮節
世人多認為傅斯年桀驁不馴,其實“孟真先生最重禮節,這也許是世人所不甚清楚的”[2]。但是,傅斯年只對他尊重的人施以禮節,對于生平所惡之人往往傲然處之或加以刻薄之語。他對蔡元培、胡適、陳寅恪敬重有加,對祖母百依百順,對夫人俞大彩也相敬如賓。傅樂成年少時,若是出言不慎,冒犯長上,必遭傅斯年痛斥。傅樂成赴臺后,在臺灣大學任職,對歷史系的一位老教授敬重有加,那位老教授常常夸獎他有禮貌,傅斯年知道后,甚為高興。傅斯年年少時,因家道中落,生活甚是艱辛,但卻并未有愛財的惡習,對朋友、對窮人甚是仗義。抗戰時在四川李莊,盡管經濟情況不好,傅斯年卻是當時知名的善人。來臺時,曾帶來了一位老媽,這位老媽雖信教(先信佛教后信基督教),但是為人刻薄,眼光勢利,當時家中雇傭了一位年輕工人,老媽給他做飯時,飯量少而劣質,傅斯年見到后大怒:“你為什么這樣欺侮人?你是不是在打發叫花子?”[2]。把老媽罵得痛哭流涕。事后傅斯年將此事說與傅樂成聽,傅樂成亦有所感。傅樂成在臺大教書時,臺灣對大陸來的遷徙者們意見很大,甚至到了仇視的地步,原因是“外省人”(大陸的遷徙者)是臺灣的實際掌權者,總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態面對臺灣本地人。但是傅樂成沒有這么做,對臺灣本地人和大陸人一視同仁,不僅如此,他還經常照顧救濟窮苦的臺灣學生,和學生吃飯時,必然搶先付賬;學生缺錢時,曾故意將錢夾在書里幫助學生;甚至有學生眼睛不好,他便親自給學生買藥。此心此舉,多是受傅斯年的耳濡目染。
1.3 愛國
傅斯年的愛國之心,主要體現在抗日救國上。傅斯年痛恨日本人,本人拒絕也反對別人與日本人進行任何領域的交流合作。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淪陷,傅斯年與丁文江、胡適等人創辦《獨立評論》,宣傳抗日,也常常在會議上痛斥親日派要員。當時的北平,充斥著漢奸與日本特務,傅斯年此舉非常危險也非常勇敢。當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傳出,傅斯年得知此事后,欣喜若狂,提起酒瓶走上大街暢飲,并用手杖挑著帽子,與民眾和軍人狂歡了好一陣。傅斯年的愛國情懷,也深深影響了傅樂成。在“一二·九運動”中,傅樂成作為學生運動代表,毅然為抗日救國獻出自己的力量,后被捕入獄,而那時候,他只是一位中學生。傅樂成熱愛漢唐史,因為它的繁榮昌盛是中華文明的代表,因為它的本位文化深刻影響了世界,每每談及,傅樂成的筆下總是洋溢著自豪感。
傅樂成曾感嘆“只有孟真先生對我最親切”[3],即便傅斯年已然逝去,傅樂成卻仍然時常于夢中聽見伯父的教誨。他更是激勵自己——“余生無多,我必以他為典型,勉力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2]。正是在傅斯年的影響下,傅樂成最終在史學這條路上越走越遠。
2 傅斯年對傅樂成史學的影響
傅斯年在史學領域的建樹眾所周知,而傅樂成作為“臺灣秦漢隋唐帝國祖師”[3],其萬眾矚目的成就背后,必然與傅斯年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
2.1 史學方法影響
史家治史多善考證,而考證方法、考據則淵源各有不同。近代西學傳入后,考據風氣盛行,傅樂成的伯父傅斯年更是新考據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強調純粹客觀的“科學史學”,他否認歷史發展的規律性,注重史料的地位,主張以史料學為根本的史學研究。傅斯年曾留學德國,深受德國歷史語言學派熏陶,歸國后成立“中山大學語言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并于1949年后遷至臺灣,對臺灣史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杜維運在《二次大戰以后我國的史學發展》中說到,“考據仍然是史學的主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可以說完全籠罩在考據風氣之下的,臺灣大學歷史系、歷史研究所與考據有極深的淵源,學術著作的審查以及獎勵,也以是否有考據分量作為最重要的標準之一。”[4]而傅樂成不僅身為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更有“傅大少爺”[3]之名,其本身與考據學派的關系,自然不言而喻。是故嚴耕望曾言:“伯父傅孟真,學通中西,治史尚考證……秀實(傅樂成)先生才思不群,治史得孟真先生意緒”[5]。傅樂成作史,若欲發表觀點或得出結論,必然經過大量史料佐證,其對于史料的引證尤為細致,甚至于苛刻,有些文章所征引的史料部分占據全文的半壁江山。其引用材料不僅占據整體內容較多,而且引用篇幅較長,頗有一種大開大合的氣勢,典型的例如《孫吳與山越之開發》,征引內容以《三國志》為主,《漢書》為輔,多達30處;《唐代宦官與藩鎮的關系》一文,征引內容以《舊唐書》為主,《新唐書》為輔,多達31處;《唐代夷夏觀念之演變》一文,征引內容以《舊唐書》《新唐書》為主,《資治通鑒》《全唐文》《杜詩詳注》《白居易長慶集》為輔,多達 27處。這種直接直白的引用方式,頗有史料學派的風格。
2.2 治史目的影響
經世致用,是我們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中國史學的經世致用思想源遠流長,其最初是用以為君王提供治國經驗,加強統治,鞏固利益既得者的自身利益。傅斯年反對致用,他認為史料是為了尋求歷史真相,研究歷史應是純粹的學術研究,而中國史學界,正是因為好談致用,導致主觀成分過多,反而無所成就。而且他認為政治不應支配學術,但如果某種學術對國家民族有危害的可能,政府應加以取締。但是隨著近現代西學涌入和社會科學的發展,史學的經世致用思想也逐漸趨向于多元化,從愛國圖強到社會精神風貌,史學的經世致用思想已經逐漸滲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身為傅斯年,也依然在抗戰時期作《東北史綱》,為保衛國土盡心盡力。可見,所謂學史以用史,其實在更多時候是不得不用史。在中國,史的影響和地位是難以被取代的,我們常說“古人云”“老祖宗曾經說過”,正反映了史學對當今社會的影響。而西方史學思想駁雜,流派眾多,古往今來從未有過一個統一的史學體系,因而導致西方研究者們對待史學的態度不一、研究史學的目的不一。總而言之,西方史學雖有百家爭鳴之勢,卻無獨領風騷之言。所以,西方史學可以以多種姿態、多種形式被引入中國,然后再引發成為數個“被中國化”后的史學流派。但是不論如何,在中國傳統觀念以及國人的意識形態中,經世致用一直都是中國史學的目的與歸宿。即便傅斯年深受西方史學熏陶,但是身處中國的思想環境下,或許其意識形態并未改變,其行為舉止不免受其左右。傅斯年或許反對致用,但是國難當頭,他也會經世致用以救國。從1969年的《中國民族與外來文化》一文開始,傅樂成的很多學術研究,就是為了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托古言今,為當今社會的許多熱點問題尋求解決之道。面對西方文化的流行、本土文化的缺失,傅樂成的《中國民族與外來文化》一文,從民族融合、胡化、唐朝本位文化的建立、近代本土文化的衰落與西方外來文化的輸入為線索,最后總結出,中國的西化誠然使得中國取得了一些不菲的進步,但是,我們更要效法漢唐,去“擷取西洋文化的長處以創造自身新的文化”[6]。就臺灣社會風氣問題,傅樂成發表《唐人獨特的精神》,總結了唐人的三種精神,分別是勇敢進取的尚武精神、胸襟開闊的博大精神和坦蕩真誠的自由精神,鼓勵人們去效仿,“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今兒改善社會的風氣,充實國家的力量”[7]最后更是感慨到“能如此,則神州重光,必不遠矣!”[7]
傅斯年不僅引領了中國近代史學的繁榮,更是在品性和治學上對侄兒傅樂成產生了深遠影響。在臺灣當代史學界,傅樂成被尊稱為“臺灣秦漢隋唐帝國祖師”,其成就和影響可見一斑,倘若傅斯年泉下有知,定會欣慰不已。
參考文獻:
[1]傅樂成.傅孟真先生的先世[C]//傅樂成.時代的追憶論文集.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4:121、121.
[2]傅樂成.夢里的典型——回憶先伯傅孟真先生生活的幾個片段[C]//傅樂成.時代的追憶論文集.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4:200、200、200、205、201.
[3]高明士.豪邁、傲骨的傅樂成老師[M]//臺大歷史學系系史.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2002:142.
[4]杜維運.二次大戰以后我國的史學發展[C]//史學與社會科學論集.臺北:明文書局,1983.
[5]傅樂成.中國史論集·序言[M].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1.
[6]傅樂成.中國民族與外來文化[M]//傅樂成.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6:428.
[7]傅樂成.唐人獨特的精神[C]//傅樂成.時代的追憶論文集.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4:93、93.
責任編輯:楊松水
K825.81
A
1672-2868(2017)02-0090-04
2017-01-04
劉文釗(1992-),男,安徽巢湖人。淮北師范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史學理論及史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