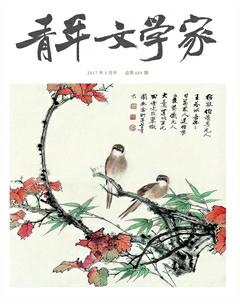“女神”與“神女”
馬海洋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08-0-01
長久以來,女性一直是文學史上被著重描寫的群體之一,父權社會的桎梏使她們常與弱勢,渺小等詞聯系在一起,在外界的形成微小的刻板印象。而女性的生命史常常與國家,城市,民族的衰亡結合起來,帶有普遍的隱喻意義,扶桑和黃得云既是帶有極大歷史隱喻色彩的人物。前者出自著名華文文學作家嚴歌苓的名作《扶桑》,后者則是出自攪動臺灣文壇的著名現代派作家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兩個人人物同曾為良家女子,被拐賣后成為異國與他鄉的娼妓,扶桑稚拙,得云機警,兩人日后的發展道路大相徑庭。嚴歌苓與施叔青同樣選擇了女性/娼妓的故事內核,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的美國與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香港遙相呼應,共同合成了一曲女性命運的悲歌。
一、外化形象的差異
《扶桑》與《香港三部曲》的故事背景分別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的美國和九十年代的香港,同樣是被拐賣的良家女子備受壓榨,為妓的一生。然而,兩人的性格不同,命運各異,帶有民族和歷史的同樣隱喻,然而卻展現出不同的生活軌跡。
扶桑生于中國內地,出身于家世清白的茶戶之家,受人拐騙而被賣到遙遠的“金山”為妓,而由此開始她悲劇的生涯。在嚴歌苓的筆下,扶桑高大,健碩,但是稚拙,常常記不住恩客的名字,因而三番五次地被發賣。面對即將開始的悲劇生活,她無任何的哭鬧,仿佛一切都是理所應當,自始至終,她始終在嘴角掛著神秘的微笑。他周旋在白人小鬼克里斯,此前從未謀面的名義上的丈夫大勇及其他心懷不軌的恩客之間,受到來自幾方面的壓榨,然而,她似不懂世事一般,從未產生反抗的沖動,即使是前一天逃跑,后一天仍會懵懵懂懂地跑回來。扶桑作為妓女,并未體現出妓女應該具有的媚態與微賤,有的只是如地母一般的包容和平和。這打破了原始的大眾的妓女印象。扶桑的身上被賦予了明顯的稚拙,帶著智慧未開的色彩,身為妓女,卻在一次次的事件中展示出驚人的淡定,環境越是惡劣,壓榨越是加深,她的包容一切的地母性就越是明顯。
黃得云有著和扶桑一樣的出身,她同樣出身于中國內地,在給弟弟祈福時“眼前一黑”,再睜眼時已被帶到香港,賣到大寨做妓女。她的境遇要稍好于扶桑,鴇母倚紅精心調理,恩威并施,使得云成為南唐館有名的頭牌。施叔青別出心裁的在得云臉上加了一顆胭脂痣,恰好暗合了中國古代美人痣的憂郁傳說,似乎也恰恰為她的此后的人生軌跡埋下伏筆。得云第一次走出倚紅閣時穿著帶有中國特色的紅云端襟衫,腰系翡翠撒花裙,滿頭珠翠,由此,帶有國家隱喻色彩的形象于焉浮現。得云與扶桑一樣,默默地接受了命運對其的安排,不同的是,前者想過如何逃離,但是進入南唐館后的得云就像是進入了幽禁孤島的女囚,首先無處可逃,此外無處投奔,也就在一天天的迷失中,漸漸的褪去了再次回家鄉的心。成為妓女的得云機警的尋找一切可以帶她逃離苦海的人,此后出現的亞當斯,姜俠魂等都仿佛成為其溺水后的救命稻草,然而她沒有抓住任何一根,最后依靠自己完成了獨立和蛻變。
二、精神意志的殊途
扶桑和得云的悲劇遭際,植根于被迫移民的壓抑,反映出美華移民和殖民地移民同樣的創傷。在異域和他鄉的賣笑生涯逐漸開始,扶桑依舊懵懂混沌的對待一切事物,在壓迫和剝削面前一如既往的平和淡定,吸引了一個白人少年克里斯,并使之終身癡迷。得云則經歷了一個相反的方向,她癡迷于白人亞當斯,卻最終落得被拋棄的下場,之后傾心于姜俠魂,卻怎料其來去無蹤,只是一個華人英雄的精神游魂,此后的屈亞炳也在漸漸的發跡中離她而去,最終,她抓住機會進入當鋪,由此開始了一段新的征程。
扶桑和黃得云的精神氣質大相徑庭,扶桑懵懂而未經開化,面對壓榨顆苦難不覺所以,惟以微笑應對一切。鴇母打她時她不聲不響,克里斯迷戀她時,她只是用盡自己的全部取悅于他,溫順而謙卑,她的心中似乎從來無自己的概念。仿佛生來為人,就是被用來包涵他人的。換個角度說,這種未經開化似乎也代表著不受污染,因而即使是身處于淫男艷窟的艱難處境中,她仍可以永遠保持著自己“神秘的微笑”,默默地去包容一切的骯臟,壓迫和苦難而不受污染。她的身上始終帶有著不同于其妓女身份的本真和純粹。
反觀黃得云,她的一生只對白人亞當斯動過心,卻在滿足了其對東方的幻想之后而慘遭拋棄,與扶桑相比,她簡直是一個雄心勃勃的野心家,誠然,命運將其一步步推向另一條不同的發展道路,但這與黃得云的機警和善于審時度勢密切相關。
黃得云在香港被迫為妓,懷著亞當斯的孩子卻被拋棄,想要與屈亞炳過平常日子卻又慘遭背棄。搬入殘破的瓦屋之后,機緣巧合下她為十一姑讀報,由此漸漸地走入當鋪,學會鑒賞古玩,評定估價,撥打算盤,黃得云一步步的步入男性的話語勢力范圍內,開始了對自我的救贖。在一次當鋪被打劫的生死關頭前,她當機立斷的保護其免遭毒手,由此得到當家的肯定。在之后,她委身王福,一步步的與其囤積居奇,像許多殖民者一樣,開始慢慢地積攢原始資本的第一桶金。妓女出身的黃的云漸漸的改頭換面,變成了有獨到眼光和豐厚資本的小資本家,由此開始了一步步向上走的積淀。
結語:
“神女”與“女神”兩個極為相似的詞語卻在漫長的歷史語境下被賦予了不同的含義,兩部小說中的主人公都被賦予了民族與地理,性別與欲望的深層含義。百年前的移民的墮落史在兩人的身上得到高度的濃縮。王德威曾說“《扶桑》講的是‘神女變女神的故事”,由此可以作為比較二者形象的切入和終結點。兩種的不同的價值選擇和精神向度演繹出移民女性截然不同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