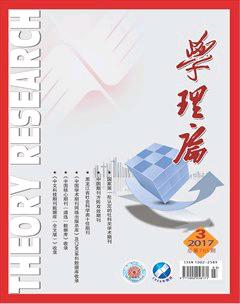刑事“冤假錯案”成因淺析
于平
摘 要:刑事“冤假錯案”的頻發(fā)嚴重地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當(dāng)事人的合法權(quán)益,引起人民大眾對司法公信力、司法權(quán)威的重大質(zhì)疑,浪費司法資源,影響了中國法治建設(shè)進程,摧毀了公眾的法治中國夢。為加強對人權(quán)的進一步保障,提升司法公信力,重樹司法公正的權(quán)威也成為當(dāng)前司法改革背景中的一項重要工作。在法制化不斷加速的進程中,法學(xué)界對刑事“冤假錯案”的預(yù)防機制研究也漸進增多,本文從我國“冤假錯案”的成因入手并參考了國外的相關(guān)規(guī)則進行探索分析。
關(guān)鍵詞:“冤假錯案”;米蘭達規(guī)則;刑事
中圖分類號:D920.5 文獻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7)03-0106-02
2016年11月30日對“聶樹斌案”判決書的做出,“沉冤昭雪”的同時,“死刑錯案”又深深地刺痛著人們的神經(jīng),巨大地挑戰(zhàn)了我國的司法公正。以往的“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趙作海案”等冤假錯案媒體有過深度報道,公眾廣泛關(guān)注,一次次地觸碰社會公眾的心理承受底線,一次次地挑戰(zhàn)法律的權(quán)威與正義。這類“冤假錯案”的產(chǎn)生,不僅嚴重侵犯無辜被追訴人的人身合法權(quán)益,而且某種程度上講是在放縱真正實施違法行為的犯罪者,使其逍遙法外,繼續(xù)侵犯潛在受害者的人權(quán),不斷地危害社會。
重新審視近期被糾正的“冤假錯案”,呈現(xiàn)出與以往錯案的不同特點。像上面提到的“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趙作海案”被司法糾正,基本上是因出現(xiàn)了“真兇再現(xiàn)”或者“亡者歸來”,而近期錯案的糾正并未出現(xiàn)此鬧劇,比如說“聶樹斌案”,其判決書上明確寫明有罪供述的合法性存疑,有罪供述與在卷其他證據(jù)供證一致的真實性、可靠性未形成完整鎖鏈,沒有達到證據(jù)確鑿的定罪要求,原審認定聶樹斌犯故意殺人罪、強奸婦女罪的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根據(jù)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相關(guān)規(guī)定,不能認定聶樹斌有罪。對申訴人及其代理人、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的應(yīng)當(dāng)改判聶樹斌無罪的意見,本院予以采納。判決原審被告人聶樹斌無罪。本判決為終審判決”。①這是案件存疑,重新審理,最終進行了改判。這也正是我國司法的進步,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常務(wù)副院長、一級大法官沈德詠早在2013年5月人民法院報撰文提出“要像防范洪水猛獸一樣來防范‘冤假錯案,寧可錯放,也不可錯判。”[1]同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強調(diào)“健全錯案防止、糾正、責(zé)任追究機制,嚴禁刑訊逼供、體罰虐待,嚴格實行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這些指導(dǎo)性的言辭和決定對防范“冤假錯案”的再發(fā)生起到重要的作用,開啟了司法改革的新篇章。
在我國“冤假錯案”的頻發(fā),不得不讓我們對我國司法制度的深度思考,對于國外的米蘭達規(guī)則、沉默權(quán)制度、律師參與制度等,在我國的司法制度基礎(chǔ)上,探索遏制“冤假錯案”的發(fā)生也許會是有效的借鑒。
一、我國刑事“冤假錯案”的形成原因
“刑事錯案”被稱作“冤案”或“冤假錯案”等,《現(xiàn)代漢語詞典》將其定義為“錯判的案件”[2]。美國律師勒內(nèi)·弗洛里奧在《錯案》一書中將錯案分為兩種:一種是司法機關(guān)由真實的證據(jù)材料,得出了錯誤的結(jié)論;第二種是由錯誤的一個證據(jù)材料卻推出近似正確的結(jié)論。北京大學(xué)法學(xué)院陳興良教授則認為,刑事錯案可以被稱為冤案或者冤獄,完全避免刑事錯案是無法實現(xiàn)的,即“有獄必有冤,無獄則無冤”[3]。中國政法大學(xué)教授顧永忠教授認為,所謂冤案是指審判機關(guān)將無辜之人定罪科刑且判決已生效的案件[4]。“冤假錯案”廣義上講在偵查階段、審判階段及起訴階段其中每個階段都可能發(fā)生;狹義的“冤假錯案”是指審判機關(guān)人民法院基于錯誤的事實認定或者錯誤適用法律而導(dǎo)致無辜的人受到有罪判決科以刑罰,或者有罪的人逍遙法外未被追訴的判決已生效且執(zhí)行的案件。本文所探討的是狹義的刑事錯案中被錯誤追究刑事責(zé)任的“冤假錯案”。
糾問式訴訟中的“有罪推定”觀念還沒有徹底清除,也是“錯案”產(chǎn)生的思想根源。首先,一系列的司法程序都是假定犯罪嫌疑人有罪而展開的,偵查假說認為,偵查機關(guān)會為補強內(nèi)心的確信,反向追溯有力的犯罪證據(jù),有甚者會為此違造證據(jù)或者詭辯證詞;反而對與內(nèi)心確信事實的相反證據(jù)選擇性地忽視;為了論證內(nèi)心確信,還會采取發(fā)源于美國而在中國還尚不成熟的催眠與測謊相結(jié)合的所謂高科技手段,因測謊基本圍繞“有罪事實”,實際上就是為偵破案件事實而讓犯罪嫌疑人自認有罪,杜培武、趙作海等案件均有適用。在發(fā)案率不斷攀升、實現(xiàn)達標(biāo)破案率的巨大壓力下,偵查機關(guān)為收集證據(jù),不惜一切代價,違反司法程序、采取非法手段,“刑訊逼供”便順勢而生。浙江張氏叔侄強奸殺人案,他們在獄中遭到獄霸袁連芳的暴力取證和偵查人員的刑訊逼供,對此做的供述不僅未被非法排除反而成了冤案的重要證據(jù)。口供至上,刑訊逼供是導(dǎo)致冤案的直接原因。其次,審查起訴階段,檢察院-公訴機關(guān)的主要職責(zé)是揭露和指控犯罪。即使檢察機關(guān)在審查起訴過程中發(fā)現(xiàn)非法證據(jù)有違法獲取行為,也采取忽視態(tài)度。最后,進入到審判程序,這樣的事實不清、證據(jù)不真實的矛盾對人民法院的法官是嚴厲的考驗,當(dāng)法官發(fā)現(xiàn)證據(jù)達不到事實清楚、證據(jù)充分的要求時,會秉承疑罪從輕而不是疑罪從無的思想來對此做出判決,“冤假錯案”由此產(chǎn)生。
“民憤”和“社會影響”已嚴重地影響了刑事司法工作,公眾輿論的外在壓力嚴重影響了司法工作的走向。如佘祥林案,到審查起訴之日時,公安機關(guān)、檢察院均未有確鑿證據(jù)證明佘祥林有罪,就在此時被害人家屬組織聯(lián)名上書,司法機關(guān)迫于公眾的壓力,本著“命案必破”的思想,為了提高辦案效率、暫時化解社會矛盾,踐踏刑事訴訟程序,最終釀成了“佘祥林冤案”。
控訴雙方平等對抗,法院居中裁判。在我國刑事司法程序的對抗機制嚴重缺乏。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知識嚴重匱乏,不能充分維護自己的訴訟權(quán)益,因此充分發(fā)揮法律職業(yè)者辯護律師在訴訟過程中的作用,在防范“冤假錯案”的發(fā)生上,是很重要的。在我國,在媒體的曝光下“冤假錯案”是如此的耀眼,而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quán)卻顯得黯淡無光,甚至缺少最起碼的公民的人身權(quán)利、財產(chǎn)權(quán)利、民主權(quán)利和其他權(quán)利的人權(quán)保障。指導(dǎo)刑事司法的最高原則是尊重和保障人權(quán),但犯罪嫌疑人的人權(quán)得不到尊重和保障,刑事“冤假錯案”的不斷攀升當(dāng)然也便不足為奇。
二、國外的刑事“冤假錯案”之米蘭達規(guī)則
“米蘭達規(guī)則”(Miranda Rules)是美國憲法修正案“反對強迫自我歸罪特權(quán)”和程序保障措施。1966年3月1日,聯(lián)邦最高法院就米蘭達一案(Miranda V.Arizona)舉行了聽證。一并聽證還有其他三起同類案件,這四起案件的被告人在接受訊問時,都是在與外界隔離的房間并且未被告知依法享有沉默權(quán),而做出了口頭供述,后有三個被告簽了字,在審判中此口供被作為證據(jù)法庭將其采納,四個被告都被判了有罪判決。這四起案件最高法院進行了一并評議。1966年6月13日,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以5比4的表決做出了裁定推翻原判決。米蘭達規(guī)則自此誕生了。與其相關(guān)的有兩條憲法規(guī)則:一是憲法第五修正案,即任何人都不能在刑事審判中被迫成為證明自己有罪的證人;任何人非經(jīng)正當(dāng)程序不得被剝奪生命、自由或者財產(chǎn)權(quán)利,簡稱為“不得強迫自證其罪”條款。第五修正案適用于聯(lián)邦司法系統(tǒng)的刑事審判程序。二是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即任何人非經(jīng)正當(dāng)法律程序不得被剝奪生命、自由或者財產(chǎn)權(quán)利,簡稱為“正當(dāng)法律程序”條款。這一修正案適用于各州和地方司法系統(tǒng)。米蘭達規(guī)則的程序保障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對抗了警察的羈押性訊問,保護了公民反對強迫自我歸罪的特權(quán)。“米蘭達規(guī)則”包含沉默權(quán)、會見律師權(quán)和獲得法律援助權(quán),這都是值得借鑒的權(quán)利規(guī)則。
三、完善我國刑事“冤假錯案”救濟機制
陳光中教授曾說道:“上帝不犯錯,可法官不是上帝。”[5]我們看到的是“錯案”的判決結(jié)果,但我們不得不思考它的成因及證據(jù)源頭,怎樣能在整個訴訟活動中摒棄“有罪推定”和思想源頭,避免“刑訊逼供”的暴力取證行為。中國《刑事訴訟法》第50條2012年修訂的規(guī)定:“嚴禁刑訊帶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jù),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其中,新增加的“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是此次刑訴修改的一大進步,這也標(biāo)志著接受了當(dāng)今世界范圍具有普適價值的“反對強迫性自證其罪”和刑事訴訟規(guī)則,也就是確認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權(quán)。其中新刑事訴訟法118條保留了“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yīng)當(dāng)如實回答”的規(guī)定。與此同時,有學(xué)者認為可采用這種解釋:“偵查人員對犯罪嫌疑人的提問,他們可以選擇沉默,也可以選擇回答,但如果回答就要如實陳述。”也就是說,“犯罪嫌疑人有沉默權(quán),但沒有說謊權(quán)。”由此可防止“刑訊逼供”的發(fā)生。
總而言之,“錯案”的成因諸多,但“有罪推定”的固有思想及“刑訊逼供”的取證行為等是不可熟視無睹的,當(dāng)然觀念的轉(zhuǎn)變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法律條文”也不能處在沉睡狀態(tài),美國的米蘭達規(guī)則對于沉默權(quán)、會見律師權(quán)和獲得法律援助權(quán)制度在適用過程中也發(fā)揮了不可或缺的借鑒作用,要讓法律規(guī)則運動起來,如此法律規(guī)定才“名副其實”。減少刑訊逼供,對中國的“冤假錯案”預(yù)防機制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命案必破”的目標(biāo)和限期破案、掛牌督辦以及破案率同獎懲掛鉤的績效考核制度的情況下,及證據(jù)獲取能力的不足、有限的偵查資源和日益多樣化犯罪手段等諸多因素的前提下,通過制度改革和機制創(chuàng)新來構(gòu)建良好的法律職業(yè)行為環(huán)境,建立健全我國的錯案成因分析、糾正錯誤、責(zé)任追究、國家賠償機制等幾方面來構(gòu)建一套救濟系統(tǒng),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健全“證據(jù)規(guī)則”,強化“辯護制度”,優(yōu)化“刑事司法環(huán)境”,進一步明晰“司法權(quán)力運行機制”,預(yù)防“冤假錯案”的不斷發(fā)生。
參考文獻:
[1]沈德詠.我們應(yīng)當(dāng)如何防范冤假錯案[N].人民法院報,2013-05-06.
[2]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xiàn)代漢語詞典[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1.
[3]陳興良.錯案何以形成[J].公安學(xué)刊,2005(5).
[4]顧永忠.以最大的責(zé)任防范冤假錯案發(fā)生[N].人民法院報,2013-06-07.
[5]陳光中.上帝不犯錯,可法官不是上帝[N].法制日報,2012-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