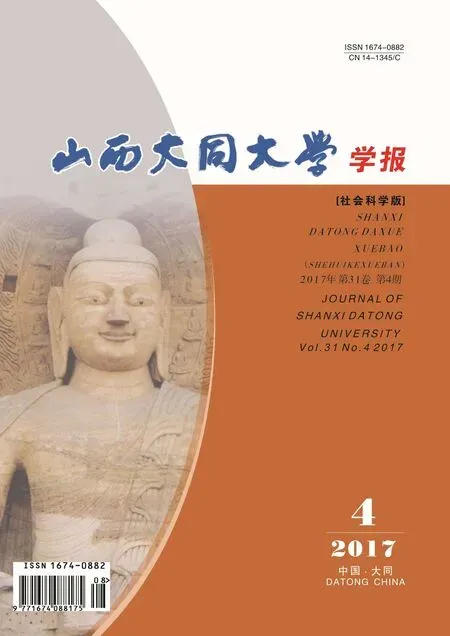《追風箏的人》中阿米爾的“傷”
王 燕
(山西大同大學外國語學院,山西 大同 037009)
《追風箏的人》中阿米爾的“傷”
王 燕
(山西大同大學外國語學院,山西 大同 037009)
《追風箏的人》是阿富汗裔美籍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處女作。小說展示了20世紀70年代的阿富汗社會,講述了富賈之子阿米爾與其仆人哈桑的友誼以及阿米爾童年的心理創傷事件。通過深入探討阿米爾遭受童年創傷前后的心理狀態,揭示童年的心理創傷以及父親帶對他人生成長的深刻影響。創傷記憶也是阿米爾敢于在移居美國多年后重回阿富汗實現自我救贖的根源所在。
創傷;記憶;救贖;復原
小說《追風箏的人》于2003年在美國出版。作者卡勒德·胡塞尼以平淡細膩的語言講述了一個關于愛與友誼、背叛與救贖故事。小說中生動鮮明的人物刻畫、扣人心弦的心理描寫,引人入勝的情節安排,飽滿真摯的情感抒發,令人感慨萬千。因此一出版便受到廣泛的關注,之后又翻譯為42種語言,全球熱銷上千萬冊,創造了銷售奇跡,獲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如今,《追風箏的人》更是作為美國文學的經典之作被德克薩斯大學(阿靈頓)列為新生必讀書。與此同時,該小說也開始受到國內學界的廣泛關注,并從各個角度進行分析。其中,背叛與救贖主題、風箏的隱喻及象征意義、成長小說、離散族群的文化身份認同、戰爭的殘暴與種族歧視等都是研究的熱點。本文試圖以創傷理論解讀主人公阿米爾的心路歷程,從而揭示其童年的創傷以及創傷記憶。
一、創傷與“創傷”理論
眾所周知,創傷屬于心理學范疇。傳統創傷理論主要發軔于弗洛伊德的創傷心理學。他認為,當大腦在抵制有害刺激時有可能發生錯亂,而這種錯亂便是普通的創傷性精神疾病。當有害刺激突如其來令人防不勝防時,人就會感受到巨大的情感沖擊。這種沖擊又會使受傷者一次次地無意識重復傷害事件,并試圖掌控沖擊所帶來的焦慮、驚駭等情緒。[1](P169)20世紀90年代初,耶魯大學教授凱西·卡魯斯將創傷理論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她將“創傷”定義為某些人“對某一突發性的災難事件的一次極不尋常的經歷”。她認為,災難事件發生后,人們的心理上會推遲出現對該災難事件的反應,甚至會反復出現幻覺,根本無法得到控制。換句話說,災難會給人們內心留下創傷,但這種心理創傷并不與災難事件同時發生,或同步進行,而是出現在災難事件發生后的某段時間,出現在人們對災難的回憶中。災難受害者未來的生活也會因災難事件在其心理留下的陰影與傷害而受到巨大影響。[2]
小說《追風箏的人》便講述了這樣一個有關心理創傷的故事:生活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的富家少爺阿米爾與家仆的兒子哈桑從小一起長大,形影不離。盡管兩人身份地位懸殊,但卻絲毫不影響他們的友情。然而,這段純真的友誼卻因十二歲的阿米爾親眼目睹哈桑被強暴卻未加干預而蒙上陰影。為了擺脫痛苦的記憶,同時不再承受良心的煎熬和道德的拷問,阿米爾又栽贓哈桑偷東西從而迫使哈桑隨其父阿里遠走他鄉。然而,阿米爾對自己的背叛行為卻無法釋懷,哈桑像一只順從的待宰羔羊般被阿塞夫欺辱的畫面時常出現在眼前,令其痛苦萬分。作者就這樣用平實的語言向讀者揭示了阿米爾所遭受的童年創傷,講述了阿米爾內心痛苦的掙扎。
二、阿米爾童年時的心理創傷
小說一開篇,作者胡塞尼以倒敘的方式將我們從2001年的美國舊金山帶回到上世紀70年代的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小說的主人公阿米爾出身于喀布爾的首富之家,是普什圖人,也是精英階層的代表。而與其一起長大的哈桑,是阿米爾家仆人的兒子,他是哈拉扎人,代表被邊緣化的少數族裔。[3](P143)然而兩人的共生共存關系并未因為階級的差異受到影響。直到阿米爾遭受到心理創傷,他的成長道路才發生了重大的轉折。
(一)創傷事件前——阿米爾無憂無慮的童年在小說中,作者借助阿米爾的口吻向我們講述了自己12歲前快樂無比的童年時光:阿米爾和哈桑常常一起爬到自家車庫旁邊的白楊樹上,拿一塊鏡子反射日光來搗蛋。他倆面對面坐在樹梢上,光著的小腳丫晃來晃去,褲兜里滿滿塞著各種好吃的小零嘴兒,有桑果干兒,還有核桃。兩個小家伙一邊玩著鏡子,一邊用桑果干兒互相打鬧。哈桑會在阿米爾的再三央求下,用彈弓打鄰居家的獨眼德國牧羊犬,其父阿里得知時常常會責備哈桑,但善良的哈桑卻從來不會告阿米爾的狀。他們一起去看電影、打撲克、爬山、放風箏,阿米爾朗讀故事給尚不識字的哈桑聽,在他們經常玩耍的石榴樹上刻下自己的名字:“阿米爾和哈桑,喀布爾的統治者”。[4](P3)兩個小男孩嬉笑著,打鬧著,一天天長大……作者就這樣用簡單的語言向我們呈現出一幅充滿童趣的畫面。兩個純真的小男孩,兩張稚嫩的笑臉,兩個單純而美好的生命,無憂無慮的童年,一起長大的伙伴。我們似乎已經看到長大后的兩個人,互相依存,成為一生的伙伴,一世的兄弟,一輩子的摯愛朋友,彼此的生命里都留下對方深刻的烙印。然而,命運似乎卻與他們開了一個玩笑,在阿米爾12歲那年發生的一件事,永遠改變了他的人生道路。
(二)創傷事件——阿米爾童年的“殤”在小說中,作者巧妙地將阿米爾童年快樂的巔峰時刻與童年的結束結合在一起,這種安排充滿懸念,張力十足,令讀者心理落差極大。喀布爾的冬天是放風箏的季節,放風箏作為阿富汗古老的習俗,十分受孩子們的歡迎。參賽者需要將自己的風箏放飛到天空中,同時還要用自己的風箏線將對手的風箏線割斷,而最后一只飛翔在天空中的風箏即為獲勝者。而追回那只最后被割斷的風箏的人便會被大家不約而同的看做是勇氣與智慧的化身,成為大家心目中的英雄。[5](P74)每個孩子早早就開始為放風箏比賽做準備,阿米爾和哈桑當然也不例外。起初,他倆總是親手制作風箏,后來由于手藝不佳,便由阿米爾的父親帶他們去喀布爾最著名的風箏匠人處去買風箏。阿米爾12歲的那年冬天,放風箏比賽即將在阿米爾家所在的街區舉行。阿米爾心里明白,在強壯而勇敢的父親眼里,阿米爾一點不像自己的兒子,也不像個男孩子,不喜歡踢足球,相反只喜歡埋頭讀書和安靜地寫故事。他是膽小怯懦的,并不是父親心中期望的“兒子”的樣子。因此,這次比賽對阿米爾非常重要,它是讓父親對自己刮目相看、徹底改觀的唯一途徑。于是阿米爾暗下決心,立志要在風箏比賽中拔得頭籌。風箏比賽如約而至,望著在自家陽臺上觀看比賽的父親,阿米爾既緊張又興奮。阿米爾這次并沒讓父親失望,在比賽的最后關頭,他如愿割斷了那只藍色風箏,獲得比賽的冠軍。就在阿米爾收風箏線時,哈桑上場了。作為追風箏的高手,他為阿米爾追到了那只夢寐以求的藍色風箏,卻在后巷和曾經有過節的惡少阿塞夫狹路相逢。后者提出只要哈桑交出風箏便可放他一馬,然而,為了保護阿米爾的勝利果實,哈桑甘愿選擇自己受辱,他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一樣被阿塞夫強暴了。這一切都被躲在巷口的阿米爾目睹了,但他卻并未加以制止。事實上,阿米爾的內心也曾經有過掙扎,他也想像哈桑曾經無數次奮不顧身替自己解圍一樣不顧一切地沖上前去,制止阿塞夫,救出哈桑,然而他并未這么做。一方面,是他的怯懦的性格使然,他害怕阿塞夫傷害到自己,也害怕失去那只能夠贏回父親的心的藍色風箏。另一方面,在某種意義上,他認同阿塞夫的種族主義觀念,認為哈桑是低賤的哈扎拉人,是在某些利益面前可以舍棄的“車”。為了能夠保住藍色風箏這個“帥”,阿米爾沉默了,背叛了忠誠的哈桑。
至此,在短短的一天之內,阿米爾的內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別人眼里,他是風箏大賽中叱咤風云的人物,在自己心中,他卻是個十足的膽小鬼、懦夫。如此這般,從云端到谷底,情感的落差一落千丈。由于這件事情的刺激突如其來,阿米爾沒有絲毫防備,因此,對他產生了巨大的情感沖擊。同時,在該事件的刺激下,阿米爾無憂無慮的童年生活提前結束,純真的童年也夭折了。[6](P66)這件事情也變成了阿米爾童年揮之不去的“殤”,成為他日后成長道路上揮之不去的痛。同時,也正是由于“殤”的存在,阿米爾才會在多年之后,有勇氣面對自己昔日的過錯,百轉千回地踏上自己的精神救贖之旅。
(三)創傷事件后——阿米爾的創傷記憶心理創傷是創傷理論中最基本的概念。它是指某一事件或災難給受害者的心靈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傷害。[7]該災難性的刺激發生后,阿米爾受到了心理創傷,開始體會到延遲出現的各種刺激反應,后巷發生的那一幕不斷在眼前重演,那只斜倚在角落里的藍色風箏和哈桑被扯掉的棕色燈芯絨褲子就像影子一樣跟隨著他,像來自過去的幽靈般纏著他,令他無法釋懷。以至于在以后的歲月里,阿米爾都感到無所適從,他無法面對哈桑,更懼怕看到哈桑,每次與哈桑相見,當日后巷所發生的一切便會立刻出現在眼前。除了該事件本身令他難以接受之外,刺激發生時,阿米爾轉頭跑掉的處理方式也令他難以接受。事實上,心理創傷的程度除了受災難事件本身影響外,受害者對事件的暴露程度,受害者當時的主觀反應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8](P17-26)面對哈桑一如既往的照顧,阿米爾選擇了逃避,把自己關在房間里,盡可能地減少與哈桑接觸的機會。然而,創傷記憶是如此深刻,根本無法輕易抹平;道德的拷問是如此嚴厲,讓阿米爾終于不能承受。于是,阿米爾開始想辦法將哈桑從他的生命中徹底抽離。阿米爾13歲的生日很快來臨,父親為他籌備了盛大的生日派對,受邀參加派對的客人當中,居然有當日對哈桑施暴的阿塞夫和他的幫兇,看到站在父母中間,朝著自己咧嘴笑的阿塞夫,阿米爾頓時覺得頭暈目眩,聽到父親對阿塞夫親切的稱呼更令阿米爾難過異常。阿米爾終于無法忍受,向門外的空地跑去……事實上,阿米爾與災難施暴者阿塞夫的重逢,意味著現實強迫他再一次重溫該刺激性事件,痛苦的記憶再一次將阿米爾吞噬,他受到了創傷后精神障礙的困擾。為了能夠擺脫內心痛苦的煎熬,阿米爾誣賴哈桑偷了自己的手表。因為他知道,在正直果敢的父親看來,偷盜是罪無可恕的。在阿米爾的設計下,哈桑隨父親阿里搬離了阿米爾家,遠走異鄉。阿米爾的這一舉動,其實是他為了能夠擺脫創傷記憶的折磨,擺脫道德拷問而啟動的一種自我保護機制。
時光荏苒,隨著蘇聯入侵阿富汗,阿米爾與父親移居美國,然而這段創傷的記憶卻無法褪去,相反他卻一直生活在痛苦和自責中。在美國,阿米爾遇到了同是來自阿富汗的姑娘索拉雅,并對她一見傾心。索拉雅開誠布公地將自己曾經不光彩的過去告知了阿米爾,并且得到了阿米爾的諒解。然而,在內心深處,阿米爾期待有朝一日自己能夠有勇氣向妻子坦誠自己過去曾經犯下的罪行,并且獲得妻子的寬恕,從而解開自己身體和靈魂上的雙重枷鎖,開始真正意義上的幸福生活。這一刻,阿米爾等了15年。夫妻二人結婚15年卻沒有孩子,在收養孩子這件事上也一直不愿意松口。而對于沒有孩子這一事實,阿米爾心中也有他自己的解讀:也許在某個地方,我對某個人,做的某件事,否定了我做父親的權利。以此作為對我的懲罰,對我的報復。[4](P204)由此可見,來自于阿米爾童年時代的刺激,在他的心理留下了巨大的陰影和深刻的傷害,而這種心理陰影和傷害持續發生作用,使阿米爾成年后的生活也受到影響。
三、父親與阿米爾童年創傷的關系
(一)父子關系的疏離 阿米爾出生后幾天,他的母親便去世了。阿米爾從小由父親獨自撫養,按道理,這樣的父子關系本應該非常牢靠。然而,作者勾畫出來的圖景卻并非如此。父親是喀布爾赫赫有名的商人,也是阿米爾心中真正的男子漢,是他所崇拜的英雄式人物。也許是因為阿米爾的出生導致了父親深愛的母親的死亡,父親對阿米爾的要求非常嚴苛,在父親眼中,阿米爾卻膽怯軟弱,不具備男孩子應有的勇氣。父親曾經對自己多年的好友拉辛汗抱怨,如果不是親眼見到妻子生下阿米爾,他怎么也不會相信阿米爾是自己的兒子。父親對阿米爾的種種不滿與鄙夷,令阿米爾對深受父親喜愛的哈桑非常厭惡,充滿敵意。他認為哈桑是自己的仆人,是下賤的哈扎拉人,不配得到父親的喜愛。這一切讓阿米爾焦慮異常,唯恐失去父親的愛,不自覺地陷入與哈桑爭奪父親的關愛的漩渦中。因此,一年一度的風箏比賽是阿米爾重新贏回父親的唯一籌碼。在遭遇后巷發生的事情時,阿米爾內心也有過掙扎,但是對于12歲的孩子來講,父親的愛是他必須要爭取的,而哈桑就成了為此必須付出的代價。疏離的父子關系讓阿米爾在遇到后巷事件刺激時,在搭救哈桑和修復破碎的父子關系之間本能地選擇了后者,同時,這件事成為阿米爾童年永久的創傷,成為他一生的隱痛。
(二)父子關系的和諧 到了80年代,蘇聯軍隊入侵阿富汗后,阿米爾先隨父親移居巴基斯坦,然后又移民美國。阿米爾心中十分慶幸,美國對于他而言是埋葬過去、重新開始的地方。相比于阿富汗的戰火紛飛、硝煙彌漫、生靈涂炭,美國充滿了美好的希望:交通便利,物產豐富,生活平靜而優越,更為重要的是沒有了哈桑——這個父愛的爭奪者。[9](P130-135)而對于父親而言,美國卻是極其無奈的選擇,是徹底的失去。由于阿富汗森嚴的等級制度和彌漫的種族主義,父親無法認回自己的私生子哈桑,又為了讓身邊唯一的兒子阿米爾免受戰亂之苦,他們來到了美國。在美國,父親不再是那個出生于名門望族,幾乎能呼風喚雨的富商,不再是主流社會的一員,不再是精英階層,他成了來自阿富汗的難民,成了被邊緣化的少數族裔,在失去往日的光輝歲月的同時也失去了自己的階層。[6](P66)父親在加油站辛苦工作,為了能維持一家的生計終日奔波,雙手布滿老繭。然而,父親卻仍有自己的驕傲,寧肯周末去跳蚤市場擺攤,也不愿接收免費的食品救濟券,用自己的辛勤勞作撐起這個家。阿米爾就這樣與父親相依為命,父子關系回歸和諧。父親去世后,阿米爾從父親的好友拉辛汗處得知哈桑竟是自己同父異母的弟弟。父親隱瞞此事的行為令阿米爾在驚愕之余,更加憤怒不已。父親是有罪的,自己又何嘗是清白的呢?面對折磨了自己二十幾年的創傷記憶,阿米爾必須回到阿富汗,找到哈桑的兒子索拉博,從而真正完成靈魂的救贖。為了救出索拉博,不占任何優勢的阿米爾勇敢地面對他心理創傷始作俑者阿塞夫,被他打得遍體鱗傷,但阿米爾卻大笑著,完成了自我救贖的同時,心理創傷也得到復原。
綜上所述,童年的創傷給阿米爾帶來了巨大的心理陰影和傷害,對他成長心理產生了持續的影響,數十年來阿米爾始終深陷在在創傷記憶中,即使自己一路拼搏,成為一名作家卻無法開始真正地幸福生活。童年時父子關系的疏離是阿米爾遭遇童年創傷事件的主要誘因之一,而父子關系在美國的重新構建也是阿米爾最終能夠有勇氣踏上自我救贖之旅,追求創傷后復原的心理動力。
[1]楊曉.新興“創傷文學”理論對創傷小說的成功詮釋——評米歇爾·巴勒夫《美國創傷小說的實質》[J].外國文學研究,2013(01):169.
[2]Caruth,Cathy.Trauma:Explorations in Memory[M].Baltimore&London:The John Hopkins UP,1995.
[3]Algoo-Baksh,Stella.Ghosts of the Past[J].Canadian Literature,2005(Spring):143.
[4]Hosseini,Khaled.The Kite Runner.New York:Riverhead Books by Penguin,2007.
[5]鄭素華.《追風箏的人》主人阿米爾的人格成長——從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角度解讀阿米爾的三重人格[J].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01):74.
[6]Pearson,Geraldine S.The Kite Runner Book Review[J].Journal of Child&Adolescent Psychiatric Nursing,2007(01):66.
[7]Caruth,Cathy.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 History[M].Baltimore&London:The John Hopkins UP,1996.
[8]Pfefferbaum,Betty.Aspects of Exposure in Childhood Trauma:The Stressor Criterion[J].Acute Reactions to Trauma and Psychotherapy:A multidisciplinary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2005(E.Carden&K.Croyle):17-26.
[9]王慧敏,荊蓁.身份流散下的精神守望與追尋——論《追風箏的人的流散主題與身份建構》[J].外語與外語教學,2016(02):130-135.
On Amir’s Childhood Trauma inThe Kite Runner
WANG 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xi Datong University,Datong Shanxi,037009)
The Kite Runneris a haunting and quite extraordinary first novel by Khaled Hosseini.It’s a touching and memorable story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wo boys,Amir and Hassa,of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and ethnic backgrounds.The brutal assault against Hassan is witnessed by Amir,who did not intervene.And this event haunts Amir like a ghost throughout his life as a childhood trauma,makes him suffer from the traumatic memory.Meanwhile,the father-son relationship has a quite close connection with his trauma and his redemption.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mir’s childhood trauma,and his father’s influence on the traumatic event.
trauma;memory;redemption;recovery
I712.84
A
〔責任編輯 裴興榮〕
1674-0882(2017)04-0070-04
2017-04-25
王 燕(1978-),女,山西大同人,碩士,講師,研究方向:現當代英美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