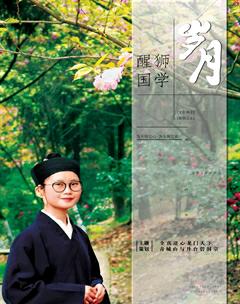大道當歸·君在龍門
姬元玖
曾有君
閔一得又名苕旉,原名思澄,字譜芝,又字補之,別號懶云子,是清代著名道士。
他用半生去明了何為己道,用一生挑起了道人的名號,又用他的半生去記載他所知道的道,終究用他的姓名重新鍛造了龍門一脈。
一得是閔苕旉的道名,他出身于吳興世家,名門望族,龍門派第十一代傳人。閔一得是繼王常月之后,乾隆嘉慶年間全真龍門派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他一生皆在修行,但是對于后世的貢獻卻被規劃在自他主持金蓋山教務后,修立文字,傳揚百載。
后人總結他時,總是說他主張以“三教同修”——儒者讀書窮理,治國齊家;釋者參禪悟道,見性明心;道者修身寡過,利物濟人,如能相和同化,終儀而周始,乃至于律、法、宗、教四家及居家出仕,入山修道,尋師訪友,蓄發易服,均俾有志者自然而行。
如此高遠化身之事,其實,于他而言只是用半生去體悟,用半生去找尋,又用半生去記錄。
直到凡身朽骨,究竟解脫,空余大道于虛空。
故人時
關于閔一得的生卒年,傳說中的記敘已經不是很詳細了。
據考證,他生于公元1749年,于公元1836年仙逝,享年87歲。
無論是閔一得其人,還是他的所作所為,事到如今,在近兩百年的傳說中,他的生平幾乎已經被神化了。這樣的人的出生或是來歷就應當與其他不同尋常的人一樣,有著高遠其來者的迷樣身世。
書中記載,一日閔父睡于夢中,夢到了一位身披羽衣的人來到他的面前,羽衣人沒有多說,只有一句:“余俱懶云也。”就因如此,身投道門的閔一得還有一別號,稱為懶云子。
如果蒲松齡的父親看到的苦行僧人是蒲松齡一生潦倒的本身,那么閔老先生看到的就應是閔一得此生的不凡。
羽衣星冠,向來是神仙的風姿,我們也愿意相信這樣一位經天緯地之才應是天神下降,人間難得。不知是否魂靈過慧,天妒英才,閔苕旉自幼聰穎異常,卻也體弱異常。常人落胞便長,二十月能立,二十五月能行,三十月健步如飛,閔一得卻直到九歲還獨立伶仃,猶艱于行,這幾乎讓人可以立時相見李密的三歲不行,幸而閔一得是修道之人,一切未為晚矣。
既有慧根不掩塵,雖然十年辛苦不尋常,人間初練中的磕磕絆絆并沒有讓他早早放棄,乾隆三十二年丁亥,閔苕旉正式師從祖師高東籬,此后正式定名“一得”,自此從師而習,鍛煉修行,如此三年之后竟然隨身之疾漸漸痊愈,氣息也漸漸充盈起來。
無白丁
乾隆三十三年是很重要的一年,這一年東籬祖師仙去,閔一得并未因此放棄修行,他以尊師之禮從侍于高東籬的弟子沈一炳,修身明志,漸宏漸達。
通過修行,不多久之后的閔一得便脫胎換骨,沒有了凡胎舊癥的拖累,他開始了足下伊始的千里之行,據記載曾出游吳楚燕趙之地,開闊了視野,提升了境界。
人類從很早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行走,行走不僅僅是為了參拜山河,也是為了與這世上有緣的人結下緣分。
在這一段漫游歷程中,閔一得與龍門西竺心宗的金懷王清楚、白馬李清純、李蓬頭這些優秀的歷史文化名人結下了不解之緣,時常相與交往。
乾隆五十五年,閔一得在滇南做官,彼時他親自拜謁云南的雞足山,山不在高有仙則名,在此處有一月支雞足道者,閔一得與之相談甚歡,最后以戒律書授與道者……
道者投桃報李。傳閔一得斗法,此事在龍門諸事中被傳為相扶修行的美談。
留人間
閔一得約于乾隆末年乞骨辭官,回歸吳興,自此以后,閔一得安心隱居于金蓋山中,正式主持該山教務,并且由此正式開始了他對此生所學、所見、所聞、所悟等等諸多道事的整理與著述。
閔一得雖然是晚年落紙,卻也稱得上著述頗豐。
清朝嘉慶年間,他親撰《金蓋心燈》八卷,以紀傳體形式記錄龍門派第一代至第十四代一百余人的生平事跡,稱為龍門派可查的譜系類金色名單和重要依據。同時又因為《缽鑒》《缽鑒續》等書的佚失,愈發使得《金蓋心燈》成為研究龍門派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不僅如此,單是文風筆法方面,“心燈”筆法獨樹一幟,其思想價值更大于史料價值。
若說到修行,閔一得主張“內丹以修性為主,性中兼命,也兼言命術”,此言一出便語驚四座,頗是不同于諸家論調。
書至此處,就不得不提《古書隱樓藏書》,此書是一部非常珍貴的著作,書中收錄了當時清人所著及閔一得自撰的內丹類書二三余種,其中提到的以脊前心后的“黃道”為先天元氣循行路徑,不同于一般丹書所說的循任督兩脈運轉;其功法及思想核心為“醫世”。
不僅如此,其中又收集了一些珍貴的丹書,這些丹書多出自乩筆者之手,雖然數量不多,卻是乩筆中之精品,異常珍貴。據傳《古書隱樓藏書》與丁福保所纂《道藏續編》并稱道教內丹類的兩座高峰,亦是研究明清道教內丹學的重要參考資料。
應歸去
中國人對于一個人的評論多是帶著對于性格的評價,閔一得為人篤實純靜,平易近人,這使得他在道德與境界的呼應間,風姿更加的清秀。
他曾自題一首道詩,是這樣說的:“我忘景豈真,我覺景豈幻。若待罔兩問,已若莊生嘆。省自復省省,真幻持兩端。非省非非省,應作如是觀。渺渺太虛中,贅此一身景。問景是何為,真幻何時省。”世間鉛華,為官數年便足以飛快閱盡,也正是如此放下才是真放下,虛實才是真虛實。
抱樸吞靜之間,匆匆彈指,他在金蓋山的隱居生活便是四十余年,也正是這四十余年的修行使得他練就了一身格外矍鑠的精氣神,能夠身輕體健、寒暑不辟,曾有記載說:“閔一得年七十,仍精力依然,嘗冬日遇一故人,衣薄見寒色,即脫裘衣之。”
于道光十六年飛升仙去,臨仙逝前擬聯:“修道只為求己志,著書未盡度人心。”
道當歸
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那些璀璨的思想又何嘗不是。
曾有人說——
儒家叫人修身立德,做個胸懷天下的君子,把這一腔熱血售予帝王家;
釋家叫人看得透、放得下,今生所善是前生貢獻,今生所苦是前生所欠;
道家最踏實,既不逼著人人都做君子,舍棄小我成就大我,又不埋怨前生、虛妄來世,實實在在地修行,只為了當下更好……
我們幾乎要被這種論調騙了,無論是“君子也”“佛陀耶”還是“大道者”,終歸都是人類對內心的關照,人之初性本善,追究到了源頭與終極需求,又哪里會有什么不同呢?
君在龍門,道歸龍門。
龍門幸甚、三教幸甚、百姓幸甚、天道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