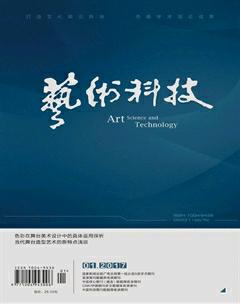跨元、交互、實踐
周倩雯
摘 要:公共藝術教育作為公共精神產品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了社會公平和公共資源的有效配置,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具體實施面。中國的公共藝術教育在藝術教育產品的開發層面取得出可喜的成果。美國公共藝術教育則通過“跨元性”“交互性”以及“實踐性”,充分體現了開放、包容與靈活的機制建設成果,對我國的公共藝術教育發展和基本教育理念更新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關鍵詞:公共藝術教育;跨元性;交互性;實踐性
法國思想家盧梭提出“做中學”,這一理念同樣適用于藝術教育實踐。隨著時代的發展,經典教育理論也需要順應新的時代精神,藝術教育必須跨越橫亙在各傳統藝術門類之間的藩籬,尋求跨元發展;而藝術媒介的更新與迭代,也同樣呼喚著藝術教育實現交互性體驗。歸結到藝術教育的核心,實踐才是所有教育手段所要達成的目標。傳統型的學校課堂教育為學生提供的往往是較為機械刻板的教育模式,將學習的過程簡化為“理論中來,理論中去”。中國教育雖然日益重視實踐教學環節的設置,也注重考核教師在課程中是否注入了實踐環節,但其考察的指標往往只涉及“是”與“否”,以及時間長度的統計考核,而忽略探究實踐教學的成果和循環再利用,即“做中學”到了什么?由“做”而形成的階段性成果如何反哺至教育過程,再成為“學”的第一手資源?當我們身處21世紀,教育越來越重視“因材施教”,立足于信息資源唾手可得的當代以及可見的未來,藝術教育機制必須改變以知識單向傳授為主的傳統教育模式。而相較于普通全日制學校藝術公共課程的普及性,學生的課外培養則更能表現靈活性、平等性以及可持續發展性。少年兒童時期是處于知識學習、創造力培養的關鍵時期,在公共藝術教育平臺,可創造一個較為理想的學習環境:在這里,感性認知、理性歸納判斷二者統一;觸摸、觀察、模仿事物;和同伴合作、交流;在教師的面對面指導下拓展思維創造力。
中國的公共藝術教育平臺一般依托于區縣文化館、群眾藝術館、少年宮等事業單位機構,其次是圖書館、博物館定期或不定期開展的各項公共藝術教育活動,一般的運營方式則是依靠政府撥款,公共藝術教育單位內部組織設計教育產品或對外購買公共藝術教育產品。而在美國,根據筆者在美國東部、中部、南部城市的走訪調查經歷,公共藝術教育活動主要由各區、縣、市的圖書館和博物館承擔,美國的圖書館和博物館并非國有性質,一般為私營,由公益事業基金會、企業、私人提供資金贊助,向社會免費提供公共服務。由于資金來源不確定,即使是像紐約公共圖書館這樣的大型機構,也會因為資金短缺向社會募集捐助。正因為如此,美國各公共教育機構都著力于提高文化產品質量,進而提升社會影響力,塑造機構的品牌效應,從而吸引更多的贊助資金。
2015~2016年,筆者重點考察的是美國公共藝術教育場館。這些公共文化藝術平臺根據各自的展品特色,結合外借展品,按季規劃相關的公共藝術教育產品,根據面向人群的不同年齡層次和文化背景,注重從多層次、多角度以及多形式來展開,在具體工作中充分體現了跨元性、交互性、實踐性的統一。
1 跨元性:藝術門類雜糅的教育情境
美國的公共博物館、藝術館為強化公共藝術教育效果,相當注重各藝術門類的綜合作用,他們并不劃分藝術門類之間的界線,而是鼓勵少年兒童盡情探索各藝術門類之間微妙的聯系。
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館長,地理學家Henry Fairfield Osborn在其著作中指出:“自然并不僅僅是真,同樣還有美,表達自然之美和自然之真這兩者必須攜手共進。因此我們需要藝術家加入我們的行列。”[1]他認為美術、音樂、戲劇以及裝置藝術家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情境設計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無疑,Henry所說的“藝術家的加入”,是指各藝術元素的跨元整合,可服務于自然科學的展示教育活動。
以自然科學教育為己任的博物館尚且如此注重藝術門類的跨元合作,更不必說其他藝術博物館。以費城巴勒斯藝術博物館為例,該館開展的公共藝術教育活動,就注重多感經驗的情境設計。博物館力圖在公共藝術教育領域引領年輕一代的審美觀念,打破單一的藝術欣賞模式,激發他們全方位的藝術體驗。他們的做法是不拘泥于藝術形式,回歸最基本的感官體驗。在“非洲藝術探索專列”這一項目中,該館設計了如下課程:演奏樂器,完成制作一張非洲地理拼圖,聞香料,編辮子,讀書,運用木質面具,看舞蹈,聽首歌,感受真正的材質,組裝家具。在官方網站的介紹文字中,清晰地標明:“這一教育活動的根本目標是凸現‘人與‘地點是如何塑造藝術的。”[2]原本該館陳列的非洲藝術品散落于場館的各處,無法構成自洽的整體。該館將所有的展品(或仿制品)組織成一個整體的場景,展現非洲原始部落的生活樣貌。兒童和少年們在參與過程中充分體驗了非洲土著居民的物質、文化及藝術生活,教育意義更為深遠。
對于費城巴勒斯藝術博物館藝術教育的開展方式,我們不難理解,當公共藝術教育平臺致力于構建一個或多個兼具各藝術門類的教育情境時,其教育產品更具開放性。
2 交互性:公共藝術教育的沉浸式體驗
在現代藝術的歷史進程中,藝術品鑒賞的常規范式在逐步改變。以往,藝術家和藝術品展示機構更注重架上藝術的基本特征,畫框、護欄造成了展品和觀眾之間的距離感,兩者之間形成不可逾越的“第四堵墻”。伴隨著現代藝術觀念的引路,“交互性”成為現代藝術的全新元素及特征,與此同時,這也悄然改變了公共藝術教育的固定思維。兒童在這種全新藝術媒介“游戲”中體驗了何為“交互性”,當他們理解了現代藝術之后,更容易從“交互性”這一角度去理解現代藝術,而年長的藝術觀眾可能還需要更多的適應時間。毫無疑問,豐富且開放的公共藝術教育設計背后是藝術觀念、現代公共藝術教育的基本策略。
紐約MOMA現代藝術博物館作為世界現代藝術旗艦級展館,在其現代工業設計品區,放置了人們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娛樂影音藝術器材以及與之配套的游戲影音軟件。在相應展區內,人們可以體驗各年代不同版本的電子游戲產品,他們體驗游戲產品就是新媒體藝術完整傳達的一個過程。這改變了大家的傳統觀念:“展覽”一詞仿佛意味著觀者需要隔著玻璃墻觀看展品,但在一個游戲藝術“展品”面前,唯有觀者與展品親密融合,進行深度體驗,才能完成其“展覽”的實際過程。MOMA現代藝術館除上文介紹的游戲展區,在各個展區均注重以交互的方式來引導觀眾對現代藝術的認知。
紐約切爾西畫廊區擁有數量眾多的當代藝術家架上藝術作品,但是藝術的“交互性”體驗同樣是重要的主題。日本藝術家yoko ono的裝置藝術展提供了一個實驗平臺,打碎的白瓷片、細麻繩、膠水——這就是藝術實驗場的全部。觀眾必須親身進入實驗場,參與藝術創作,才能理解藝術家創作的本意。藝術家并沒有告訴他們該如何做,但觀眾自發地拿起膠水和麻繩,對瓷片加以拼貼和捆綁,組成形態各異的作品,這是觀眾與藝術素材的一次深入交互體驗。隱身其后的藝術家看似并未呈現“現成”的藝術作品,但他啟發觀眾去“發現”這一藝術展的真正主題:“彌合”——人們在面對破碎的瓷片時,無一例外地選擇“彌合破碎”,并在這其中體會到“彌合”之難。在該藝術展中,由“交互”帶動“創作”,再由“創作”點燃“發現”的火花,這火花既點亮了作品本身,也使觀眾在交互中有所頓悟。這似乎是公共藝術教育和現代藝術觀念傳達的完美結合。
3 “實踐性”:公共藝術教育的生命力所在
藝術館、博物館的展品是公共藝術教育不可多得的資源,相比于學校的教育,實踐性也是其優勢所在。如果沒有開展實踐性教學,則一切將是空談。如何將經典藝術展品“變活”,成為生動的借鑒對象,才是公共藝術教育的生命力所在。美國公共藝術教育機構憑借對于藝術史的深度了解,持續開發一系列藝術實踐課程,通過和中小學校的對接,吸引學生參加工作坊形式的藝術實踐課程。
各藝術場館配備館員教師,為各個年齡層次的學生提供教學。各藝術場館的學生研習中心則常年開放實踐課程,學生可以隨到隨學,隨到隨練。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城市夏洛特明特藝術館也附設設備齊全、場地開闊的“學生藝術教育中心”,館方挑選藝術家案例,并指導學生從模仿入手,進行創作實踐。例如:由美國畫家Romare Howard Bearden創作的抽象畫作品《灰貓之夜》。這幅作品之所以被選為范例,是因為作品以線條、色塊單純的動物形象為主,學生易于模仿創作,而畫面中出現的道具均為日常生活中所常見的器皿。為幫助學生理解,畫作旁的幾排支架上放置了色彩鮮艷的廚房用具,學生可在其啟發下動手組接、拼貼藝術作品。模仿也并非藝術教育的終極目標,最終目的是要啟發學生舉一反三,實現藝術創作的自我激勵。
美國納什維爾市立藝術館附設的“馬丁藝術學習中心”以隔間劃分了不同的藝術主題:“光與影”“色彩”“動畫”“空間中的物體”等主題。如果僅以概念的方式出現,必然是枯燥乏味的。以“抽象主義”模塊為例:主辦方采用了對比式的方法,在幫助學生理解藝術基本概念的基礎上,給出了實踐方案:以配圖展現了茶壺、玻璃瓶、剪刀三樣物品在寫實、簡化、夸張三種不同繪畫手法之下的不同形態。學生可以此為例,變換創作手法,在實踐中理解抽象主義的發展脈絡,并自然地進行藝術創作。
不難看出,美國公共藝術教育平臺擺脫了灌輸思維,和傳統課堂教育相比,更倚重展館的地點、內容優勢,靈活機動地開展教學實踐。
4 中美比較
公共藝術教育在中國是尚未充分開發,但卻是充滿無限活力的領域。《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學校、家庭、社會密切配合,形成體系開放、機制靈活、渠道互通、選擇多樣的人才培養體制。”公共藝術教育代表著教育體系中的“社會”一環,有力銜接學校與家庭,形成教育資源的有機整合與互動,并成為不容忽視的文化藝術教育陣地。21世紀以來,我國城市居民對公共精神產品的需求和關注急劇增加。公共精神產品不僅僅包含各類在公共場所展示的藝術作品和藝術活動,同時也包括公共藝術教育——建立包容性及凝聚力兼備的社會文化場域,培育大眾的藝術審美經驗和創新能力,并承擔區域和民族的文化傳承任務。公共藝術教育作為公共精神產品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體現著社會公平和公共資源的有效配置,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具體實施面。
上海作為國內首屈一指的國際型大都市,起著領頭羊的作用。就本人在上海市嘉定區、普陀區、長寧區的考察發現,上海各區縣的文化館承擔著重要的公共藝術教育產品開發以及輸送功能,由于社會需求量增大,他們也積極采取產品外包的方式運作。近些年來,國內一線城市的公共藝術教育有了長足的進步,各區縣藝術館、文化館場館硬件設施的完善程度和公共藝術教育產品的積極開發層面展現出令人驚異的發展速度。然而,文化館作為國有型事業單位,如何在市場中尋找到愿意把追求商業利益最大化放在第二位,把社會公益放在第一位的民營企業或團體,卻是一個難點。過于依賴政府撥款,這些公共藝術教育機構的競爭意識也尚顯不足,而且在觀念層面還存在過于保守的傳統教育思維。
反觀的美國公共藝術教育,他們在硬件條件上并不具備絕對的優勢力量,換言之,假以時日,我國依托強勁的經濟實力實現彎道超速并非難事。但是在教育觀念更新和教育機制的細節設置環節,我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這恰是美國公共藝術教育的核心競爭力所在。通過對美國公共藝術教育的一番初步探尋,筆者認為美國公共藝術教育理念較為全面地考慮到人文精神價值觀引導,以及對少年兒童人文藝術綜合素養的全面培養。“跨元性”“交互性”以及“實踐性”充分體現了美國公共藝術教育的開放、包容與靈活的機制建設成果,這應當成為中國加以借鑒的部分。
參考文獻:
[1] Henry Fairfield Osborn . Creative Education in School,College,and Museum[M] . New York-London: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7:236-237.
[2] The Barnes Foundation[EB] . https://goo.gl/photos/xEA9caJ5HDzkGdEY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