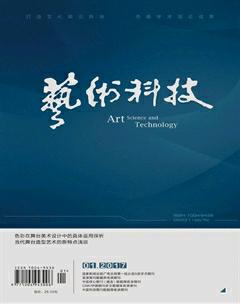淺析動畫電影《瘋狂動物城》:理想中的“烏托邦”
劉璇
摘 要:迪斯尼出品的動畫電影《瘋狂動物城》受到了人們的高度關注和青睞,刷新了中國內地影史上動畫片類型的票房紀錄。這部“全年齡段”受眾的“烏托邦”動畫電影,不論是精致的畫面和反轉的劇情,還是充滿隱喻的故事內核和傳達的正能量價值觀,都值得我們回想及深思。
關鍵詞:“烏托邦”;主題;人物;場景構建
迪斯尼出品的動畫電影《瘋狂動物城》受到了人們的高度關注和青睞,2016年3月12日,《瘋狂動物城》上映的第9天,單日報收1.66億元,打破了《功夫熊貓3》創(chuàng)下的上映首日單日票房1.51億元的紀錄。4月17日,《瘋狂動物城》下架,在內地上映45天,累計票房達到15.3億元,成為中國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動畫片,取得票房、口碑雙豐收。這部影片的英文名為“Zootopia”,Zootopia的詞根topia,譯為“烏托邦”,所以該影片最開始被翻譯為“動物烏托邦”。所以,對于這樣一部這部老少皆宜的動畫片,我們從“烏托邦”說起。
1 反“烏托邦”情結的影片主題
“烏托邦”一詞來源于托馬斯·摩爾在1516年發(fā)表的《關于最完全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書》。希臘字母U為否定前綴;topos表示“地方”,因此“Utopie”(烏托邦)表示“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東西”(有些人認為這個詞的前綴“eu”,是“好”的意思,在這種情況下,“eutopie”是指“好地方”)。對“烏托邦”類似的概念描述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那本著作《理想國》,而之后古今中外都對“烏托邦”理想進行了理論與實踐的嘗試,不過烏托邦主義是社會理論的一種,它試圖借由將若干可引起人們欲念的價值和實踐呈現于一個理想的國家或社會,而促成這些價值和實踐。但烏托邦的作者也并不認為這樣的國家可能實現,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描繪的完美形態(tài)實現。
對于本片來說,影片講述的動物烏托邦是一個只有動物存在的現代文明世界,各種動物以種族混居的形式居住在一座城市里,給我們呈現了一個看似其樂融融、和諧繁華的都市,但其實夾雜著被掩藏在動物內心的種族歧視與固有偏見,以及最后少數人的陰謀被揭穿后,整個城市又回到了像“烏托邦”一樣的和諧世界。影片通過“擬人化”的手法,將可愛的動物們作為城市中的主角,用絢麗壯觀的城市設定以及妙趣橫生的情節(jié)展示給觀眾,從動物之間的體型矛盾、草食肉食矛盾、物種矛盾、棲息地矛盾等影射當今的社會問題,尤其是當今矛盾重重又極具包容性的美國社會,以及看似和平卻波濤洶涌的世界。
在影片的故事情節(jié)上,諷刺了尖銳的社會現實問題:從羊副市長和兔子朱迪的不公待遇身上看到了性別歧視的議題,從狐貍尼克的身上看到的社會偏見,用“樹懶式”的行政機構諷刺現實中行政工作的效率低下問題,以及貫穿影片的線索“午夜嚎叫”毒品等,影片毫不避諱現實中的黑暗,反而堅持正確的政治態(tài)度,揭露在烏托邦外衣下的殘酷現實,所謂的“完美”也不過是一個假象。
影片通過主人公兔子朱迪的“美國夢-紐約夢”的自我實現,以及一宗社會大陰謀兩條線索,其中穿插親情、友情、冒險、懸疑的故事情節(jié),給我們展示出了美好想象與現實世界的差距,傳播和呼喚更多的包容和平等的正能量,雖然我們的理想是要建立一個“烏托邦”式的社會,但事實證明,所謂的“烏托邦”也只能存在于設想之中。
2 “烏托邦”中完美人物塑造
2.1 弱勢群體主角的塑造
電影角色作為一種即時的再現形式,可以成為一種帶有政治意味的代表性聲音。[1]在影片中,我們看到的兩個主人公——兔子朱迪和狐貍尼克,一個是進城追求夢想的小鎮(zhèn)女青年,一個是整天投機倒把的街頭小混混,在動物城中兩位主角無論從身份、地位,還是種族、體型都屬于城市中的弱勢群體、邊緣人物,影片再次向我們講述了“好萊塢式”的經典模式——社會小人物的成長歷程以及最終成為被認可的英雄的故事。這與“美國夢”的解釋是一脈相承的:“一種相信只要在美國經過努力不懈的奮斗便能獲得更好生活的理想,亦即人們必須通過自己的勤奮工作、勇氣、創(chuàng)意和決心邁向繁榮,而非依賴于特定的社會階級和他人的援助。”
在最開始籌劃這部電影時,制作方原本想讓狐貍尼克作為動畫的主角,但最終的版本卻是以朱迪為主角。導演Howard在采訪中也說到,“我們是要講一個關于偏見的故事。如果用尼克這個人物做主線,他不喜歡這座‘動物烏托邦。如果我們想說歧視——這種不論我們承不承認都無所不在的東西——那么主角就必須是像朱迪這樣的:單純,成長于一個積極的環(huán)境,認為所有人都是美好的、值得相處的。然后我們讓尼克——這個已經認識到世界殘酷的真相的角色,開始和朱迪彼此扶持,共同成長。這對我們來說是個巨大的變動,但這個變動讓故事變得更好了”。
朱迪作為主角,在影片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努力、執(zhí)著、勇敢、樂觀的、個性豐滿的兔子,不僅讓電影想要呈現的種族或者階級歧視得以呈現,同時也能讓觀眾更好地認識到性別偏見。她來自偏遠的鄉(xiāng)村,能夠突破種族的束縛,解開家族身上的枷鎖,在眾人的羨慕和驚嘆中,懷揣著自己多年的夢想,獨身前往這個繁華的“大都市”,企圖做出一番成就,這是她對世俗的挑戰(zhàn),也是對個人價值的追求;然而對于如此瘦小的她,在夢想之地小得微不足道,受盡了歧視的目光,從不被上司重視到立功成為英雄,完成了社會對她的認同;與小伙伴的誤解,引咎辭職到彌補過錯,是她完成自我內心蛻變的過程,進而實現了自我認同。影片通過兔子朱迪追求“美國夢”的過程,完成了三次重要的蛻變,實現了她從一個普通兔子到城市交通協警再到人民英雄的完美成長。正如影片中牛局長后來在發(fā)布會上說道:“霍普斯當然不是什么‘吉祥物,而是一名非常讓人欽佩的警探,她幫助了整個城市。”
至于狐貍尼克,他在影片中是心理轉變最大的角色,從一個混跡市井的“老油條”,到和同伴一起并肩作戰(zhàn)獲得成功的人民英雄。刻板印象和形象扭曲的大部分原因是歷史上的某些邊緣群體對控制自我的無能為力。[1]孩童時代的尼克也有過夢想,還是小狐貍的他心中也溫熱天真,幻想成為為大家服務的童子軍,但卻被不信任的小伙伴套上了嘴套,然而帶上的不是簡單的嘴套,而是為了防止食肉動物亂咬的嘴套,是一種無聲的欺凌和侮辱。于是,他在這個充滿動物種族偏見和有色眼鏡籠罩的社會中,選擇漠視這個社會的陰冷,讓他面對“不接受”時可以變得如此堅強,然而在他內心深處卻又如此地渴望“被接受”。直到遇到兔子朱迪,他得以正視幼年的自己,打開自己的內心,直面現實和夢想,最終和朱迪一同幫助了城市和人民,也重新獲得了友情和信任。
2.2 天敵變搭檔的顛覆設定
也許只有在動畫電影中,兔子與狐貍的天敵關系才能得以轉變,甚至達成信任成為朋友。對于兔子與狐貍之間的人物關系設定,首先,符合本片構建的世界觀中食草動物與食肉動物之間的對立關系;其次,符合現實社會中刻板印象的兔子可愛與狐貍狡猾的對比關系;再次,符合真實生活中人們內心的積極樂觀和消極淡漠的人物性格對應關系。在我們看來,這種截然相反的人或動物,是不能在他們人生道路上找到交匯點的,然而影片中卻給我們展現兩位主角之間這樣的關系,這種關系也是隨著整個故事的劇情推動逐漸發(fā)展起來的。第一次,兔子朱迪與狐貍尼克相遇,兔子朱迪太過天真,被狐貍尼克欺騙,朱迪發(fā)現其奸詐的本質后與之理論,卻被教育一番,并且讓兔子朱迪看清了社會的本質;而第二次相遇,兔子朱迪利用錄音筆把柄威脅狐貍尼克一起破案,而后在破案的過程中狐貍尼克敞開心扉,將真實的自己展現給兔子朱迪,但由于兔子朱迪內心根深蒂固的偏見傷害了狐貍尼克,他們分道揚鑣;直到第三次見面,兩人坦誠以待,協力合作,同甘共苦,不僅解決了危機,還成為真正的朋友和工作上的伙伴。
3 “烏托邦”中空間場景構建
在這個“烏托邦”的動物城中,不得不贊嘆是城市的空間場景構建。動物城就像是人類世界的“動物化”變體,童話般五彩絢麗的色彩,高樓大廈林立,飛馳的列車穿梭,車站廣場上熙來攘往、高低胖瘦、大小不一的動物物種,像是童話中的現實想象,又像現實中的童話夢境,井然有序、生機勃勃。
動物城按照氣候和環(huán)境不同,分成了平原區(qū)-大都市(或者叫市中心)、冰原區(qū)-冰川鎮(zhèn)、沙漠區(qū)-撒哈拉廣場、熱帶雨林-森林城四大區(qū)域。然而,在區(qū)域內根據不同種族又打造不同的公共設施和生活區(qū)域,如在城市中心,按照動物體型大小打造不同的生活和居住區(qū),印象深刻的小型嚙齒動物鎮(zhèn)。從兔窩鎮(zhèn)跟隨朱迪的火車,見識了沙漠區(qū)壯觀的地質地貌,零星的野草和仙人掌以及裸露的巖石和沙丘;冰原區(qū)白雪皚皚,銀裝素裹的景色,城區(qū)中特有的浮冰作為動物的交通工具;熱帶雨林區(qū)城市架空的結構,結合植物、藤蔓、多雨的氣候特性和相應的熱氣球交通,除此之外,在市中心的火車站匯聚了各種動物的交通樞紐里。火車門一開,大中小型動物會從大小不同的門分別出站;水生動物(比如河馬)可以從水路上班,到達出口就會有自動吸干裝置使他們穿著干爽的西裝拎著公文包繼續(xù)出行;還有倉鼠通過他們身型大小的特殊的專屬快速通道到達車站,讓觀眾看得目瞪口呆,也大飽眼福,不得不佩服動畫師們的場景設計。動物城就像一座大熔爐、一座獨一無二的現代動物生態(tài)都市,動物們在這里可以和平共處,在這里有無限的可能。
4 結語
電影為觀眾提供了一種錯覺,讓他們可以從當下的現實生活中逃離出來,進入一個理想的環(huán)境。不過有點自相矛盾的是,這個烏托邦世界又和現實有相似之處。[2]迪斯尼的造夢者給我們帶來的《瘋狂動物城》,是一個孩子們可能會被精致的畫面和反轉的劇情吸引,而成人們卻被它充滿隱喻的內核觸動的影片。這不是一部簡單意義上的動畫片,片中的故事內容和情感,讓我們產生共鳴和觸動,讓我們在歡樂中有所思考。影片的最后,兔子朱迪在中央廣場看到動物們可以隨心所欲地享受陽光、享受歡樂,似乎種族歧視與固有偏見已不復存在,食肉動物和食草動物又能信任相處,整個世界又恢復了平靜,這樣的城市就是我們理想中的“烏托邦”。不論影片是想告訴我們真實社會的現實、還是一個“美國夢”的青春勵志故事,不論我們理想中的“烏托邦”是否真實存在,我們都相信朱迪的那句話:“Anyone can be anything”。
參考文獻:
[1] 陳犀禾,等.當代西方電影理論精選[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2.
[2] 麥特白(澳).好萊塢電影[M].吳菁,何建平,劉輝,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