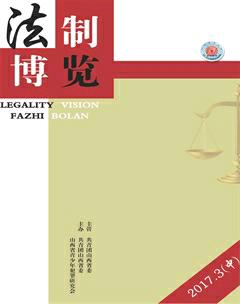刑法因果關系的新視角:危險分配與客觀歸責
摘要:以“條件說”為代表的傳統因果理論始終無法跨越歸因的“鴻溝”而進入歸責領域,因而具有局限性。因果關系本質是一種歸責判斷,須先從存在論的角度肯定行為與結果之間具有事實因果關聯,然后再通過規范評價,得出結果能否歸責于行為的結論。本文借鑒客觀歸責理論中的危險創設原理與規范保護目的概念,試圖為因果關系是司法認定打造一個兼具規范性與可操作性的處理框架。
關鍵詞:因果關系;客觀歸責;危險分配;規范目的
中圖分類號:D9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7)08-0001-05
作者簡介:陳誠(1986-),男,漢族,江蘇南京人,碩士研究生,杭州市人民檢察院案件管理辦公室,副主任科員,主要從事研究:教義刑法學。
一、問題的提出
犯罪的實體是不法和罪責。對于結果犯而言,行為人承擔罪責以實行行為與法益侵害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為前提。然而,刑事司法解決的是靈動與豐富的現實問題,個案中因果關系往往呈現出“多因一果”的特點,法益侵害通常由多個原因力“疊加”所致,還會伴隨著第三因素介入因果流程的現象。因果關系的這種復雜性既為刑法理論研究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與舞臺,也給司法實踐帶來了極大的混亂與困惑。實踐證明,傳統的因果關系理論深受因果性思維方式掣肘,始終未能正確揭示因果關系的本質,因而在具體案件中缺乏清晰的、可操作性的判斷方法和標準。20世紀70年代,德國著名刑法學家羅克辛教授提出了客觀歸責理論,明確區分了事實歸因與客觀歸責,為因果關系的研究開辟了一個全新的視角。正如羅克辛本人所言,只要人們將不法理解為通過不允許的危險的實現所導致的法益侵害,就能同時實現一種從存在論向規范論的轉變。客觀歸責理論甫一提出就成為德國刑法學乃至歐洲刑法學被討論得最頻繁和最熱烈的學理問題。近年來,雖然客觀歸責理論作為“舶來品”在我國刑法理論界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與討論,但并未對實踐產生多大影響——主要是因為研究其理論基礎者、體系定位者如過江之鯽,而探討其實踐操作者、辦案實用者鳳毛麟角。尤其是對居于客觀歸責理論核心地位且對實踐大有裨益的危險判斷模式缺乏必要的研究。鑒于目前國內對“條件說”、“原因說”、“相當因果關系”、“客觀歸責”等德、日等刑法因果理論的研究已經較為豐富與成熟,故本文無意也沒有必要對以上因果理論學說再做詳贅。本文立足司法實踐,結合真實發生的案例,借鑒客觀歸責理論中的危險創設原理與規范保護目的概念,試圖為因果關系是司法認定打造一個兼具規范性與可操作性的處理框架。
二、刑法因果關系本質解析
我國刑法理論由前蘇聯移植而來并被本土化。在因果關系領域長期存在著必然因果關系與偶然因果關系的爭論。必然因果關系說認為,當危害行為中包含著危害結果產生的根據,并合乎規律地產生了危害結果時,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就是必然因果關系,只有這種必然因果關系,才是刑法上的因果關系。①顯然,必然因果關系說排斥因果關系的偶然性,將偶然發生的結果排除在行為的結果之外,因此受到了偶然因果關系說的批判。偶然因果關系說主張,當危害行為造成某種危害結果,這一結果在發展中又與另外的危害行為或事件競合,合乎規律地產生了另一種危害后果,先前的危害行為不是最后結果的決定性因素,最后的結果對于先前的危害行為來說,可能出現,也可能不出現,可能這樣出現,也可能那樣出現。它們之間是偶然因果關系。②
本文認為,“必然因果關系說”、“偶然因果關系說”與德、日刑法中的“條件說”、“原因說”等傳統因果理論如出一轍,僅僅從哲學/自然科學的角度定義了因果關系,③將其視為物理的、實在的關系,未涉及因果關系的本質,因而具有局限性。這種局限性在具體案件中突出地表現為司法人員深受因果性思維方式的影響和制約,機械套用“沒有前者就沒有后者”的判斷公式,審查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存在一種需要刑法規制的客觀聯系,從而完成構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斷。換言之,傳統因果理論將刑法因果關系視為一個“是”與“不是”的命題而停留在歸因的階段,尚未進入歸責的領域將其作為一個“應”與“不應”的問題而展開。盡管德、日刑法學者對傳統因果理論做出了某種修正,提出了“因果中斷”、“禁止溯及”等理論,但是修正后的理論仍然無法跨越歸因的“鴻溝”。事實上,無論是“必然因果關系說”、“偶然因果關系所”,抑或“條件說”、“原因說”,都具有非定型性與非規范性特征,在司法實踐中難以操作,根本無助于揭示刑法因果關系的本質。由此看來,拋開哲學觀念的束縛而另起爐灶,重新架構司法人員對刑法因果關系的認知已是大勢所趨。畢竟,刑法上的“原因性”概念,是一個法律——社會影響上的關系概念,具有本體論和規范性的含義,既不同于自然科學上的因果概念,也不同于哲學上的因果概念。④從這個意義上說,哲學上/自然科學意義上的因果關系只是一個存在論的概念,而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則是一個價值論的概念。兩者的區別就在于:存在論關注的是事實命題,而價值論討論的是價值命題。事實命題只是關于“真”與“假”的認知,而價值命題還包含“善”與“美”、“丑”與“惡”的褒貶。價值不是現實的存在,但卻宣示了現實存在的意義。申言之,如果從存在論的角度解釋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是指實行行為與實害結果之間客觀存在的一種決定與被決定,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如果從價值論的立場來把握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則是一種觀念的、論理的關系,是一個能否將一定的法益侵害結果歸屬于一定的構成要件行為,為犯罪成立提供客觀依據,進而讓行為人承擔不法的價值判斷過程。
在此,不得不指出,以“條件說”為代表的傳統因果理論最大的弊端在于:對于殺人、傷害、故意毀壞財物等實行行為缺乏定型性犯罪的無限溯及擴張了刑法的處罰范圍,因為“條件說”運用“思維排除法”判斷因果關系的前提,是人們必須事先就已經知道究竟條件具備何等的原因力,即知道這些條件如何作為原因力而發生作用,而早期的刑法理論沒有對實行行為做出適當的限制且殺人、傷害、故意毀壞財物的實行行為確實難以具體描述,故而各國刑事立法不約而同地以簡單罪狀的方式規定了上述幾種犯罪的構成要件,實踐中又普遍存在不考慮條件的原因力,濫用條件關系的做法,更是放大了傳統因果理論的缺陷——將一個有重大因果偏離的結果歸屬于行為人,并不利于預防一般人造成這種結果。即便如此,本文認為傳統因果關系理論還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它至少解決了事實歸因的問題,為客觀歸責奠定了基礎。正如新康德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德爾班所言,事實命題所關注的“真”既關系到對事實的認識,也關系到對事實的評價,因而它是事實世界與價值世界之間的橋梁,正是它將這兩個彼此區別的世界聯系起來了。
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刑法的目的和任務是保護法益,保護的方法就是將具有侵害法益危險的行為類型化,并規定差別化的刑罰,交由司法機關去裁判。因此,構成要件都是對違反保護法益目的之生活事實所作的類型性記述,法益侵害的產生必然遵循從“危險結果”(實行行為所造成的法益受威脅的客觀狀態)向“實害結果”的轉化過程,具體而言(以故意殺人為例):制造危險(行為引起了他人死亡的危險性)→危險升高(他人死亡的危險性增加)→危險現實化(死亡結果發生)。問題在于:行為人對危險源或者脆弱法益的支配往往并非造成法益侵害的唯一原因,現實個案中的法益侵害通常系由多個原因“累積”所致。在這種情況下,能否將法益侵害作為行為人的“作品”歸屬于行為人則是刑法因果關系必須完成的任務。然而此時僅僅從事實歸因的層面來判斷行為與結果之間有無因果關系從而為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提供客觀依據是否合理呢?答案是否定的。例如,某天傍晚,甲、乙二名游客在某動物園蛇館旁因瑣事發生爭執,甲將乙打暈后揚長而去,結果當天晚上昏迷中的乙被從動物園蛇館里“越獄”的毒蛇咬死。本案中,倘若僅對甲的毆打行為作形式判斷而將其評價為刑法意義上的傷害行為,盡管在乙死亡的因果流程過程中介入了毒蛇“越獄”這一概率極小的事件,但是根據條件說“若無前者,即無后者”的經典公式,只要甲的毆打行為參與了乙的死亡這一結果現實化的過程,甲的毆打行為與乙的死亡之間就存在因果關系,甲就應當對乙的死亡負責。然而這樣的結論顯然不合理。所以,在“多因一果”的情況下,對因果關系的判斷已經超越事實歸因的范疇,而進入歸責領域,歸責意味著將某一法益侵害歸屬于特定行為而由實施該行為的人承擔不利后果。上述案例中,由于傷害行為缺乏定型性,當法益侵害表現為乙的死亡時,引起該事實的毆打行為是否屬于刑法上傷害行為,就難以下結論。于是,先采取條件說,從存在論的角度肯定與乙死亡結果具有因果關系的毆打行為是傷害行為,再通過規范評價,得出能否將該結果歸屬于甲的行為的結論。這就是歸責的過程。本文認為,甲的毆打行為沒有,也不可能制造乙被毒蛇咬死的危險。因為毒蛇“越獄”后傷害他人的危險不甲的控制與管轄之下。根據社會分工原理與公平責任原則,這種危險應該由動物園管理方控制與承擔,因為動物園作為飼養動物的專業機構,依法負有注意和管理義務,其安全設施、管理制度應充分考慮到特殊情況下游客的安全需要,最大限度杜絕危害后果發生。動物園管理方因此負有防止毒蛇逃離蛇館的義務與責任。毒蛇“越獄”事件發生本身就足以說明動物園安保設施、安全措施存在重大隱患,動物園管理方未盡合理的注意義務。故而既不能將甲的毆打行為認定為刑法上的傷害行為,更不能將乙被毒蛇咬死這一結果歸屬于甲。由此可見,認定因果關系,意味著將現實的法益侵害歸屬于某個實行行為,而實行行為本身就是類型化的法益侵害行為,所以,刑法因果發展流程就是類型化的法益侵害危險現實化的過程,而司法人員的使命就在于規范判斷法益侵害危險應當分配給誰,法益侵害結果應當由誰承擔。當然,這種危險的分配與法益侵害的承擔是以行為與結果之間存在“若無前者,即無后者”的條件關系為前提的。換言之,事實歸因與客觀歸責之間具有位階性,即事實歸因旨在解決行為是否是造成結果的事實上或者具有條件關系的原因;客觀歸責則是進一步探討結果是否作為行為人的作品而讓其負責的問題。
三、危險的分配規則初探
在科學技術欠發達的古代社會,法律是通過一種外在的時間尺度以確定危險的分配,中國古代刑法中的保辜制度即是如此。《唐律》規定:“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毆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支體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外及雖在限內,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毆傷法。”由此可見,辜內死與辜外死,除以他故死外,成為從客觀上區分殺人罪與毆傷罪的界限。殺人和毆傷本來不僅在法益、行為客觀樣態上存在區分,而且在主觀故意的內容上也是具有明顯區別的,但根據《唐律》保辜的規定,主觀區分不再考慮,僅取決于死亡是發生在辜內還是辜外。從這個意義上說,保辜制度是將被害人在辜內死亡的危險分配給了行為人。《唐律》之所以這樣規定,旨在要求不法加害人于法定的期間內積極救助被害人,以期獲得刑罰的優惠而減輕處罰。在醫學不甚發達,難以從醫學上確定死亡結果與傷害行為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的情況下,保辜制度具有合理性。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尤其是醫學的進步,這種推斷式的因果關系規則與制度已經過時。盡管如此,保辜制度所蘊含的樸素的危險分配思想及其所設計的危險分配方案對于因果關系的研究仍然具有借鑒意義。
(一)危險分配
不可否認,危險如何分配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本文初步認為,“法益侵害危險”這一刑法學概念具有地位上的依附性、涉及法益的確定性、判斷標準的經驗性,具有規范內的解釋功能。所以,對危險的分配,一方面須滿足有效保護法益的要求,符合社會分工原理,另一方面又要受到國民預見可能性與價值觀念的影響。如前文所述,既然實行行為本身是具有造成法益侵害結果危險的行為,那么,這種危險并不是偶然的危險,而是類型化的危險,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對實行行為的危險的現實化的判斷,就是為了將行為偶然造成的非類型化的結果,排除在構成要件結果之外。類型化的危險是對實行行為的實質考察——實行行為不再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形式名稱,而是通過“法益侵害危險”獲得了實質的內涵,從而極大地增強了殺人、傷害、毀壞財物等實行行為缺乏定型性的刑法規范的明確性與指引性。類型化的結果則需要根據刑法規范的保護目的原理進行規范判斷。
法益侵害危險之有無的判斷主要涉及判斷基礎和判斷標準兩個方面,前者是指判斷資料之范圍,即應以何種事實作為危險有無之判斷資料。后者是指站在何種立場依據資料判斷危險有無,一般包含經驗法則與科學因果法則。目前,關于危險判斷的爭議焦點在于確定危險有無之資料時是否應當介入行為人的主觀認知?對此,有學者指出:如果將行為人的特別認知和主觀的預見可能性作為危險的判斷資料,我們能夠明顯地感受到主觀要素對客觀要素的強烈滲透與沖擊,以及由此帶來的主客觀范疇之間的相互糾纏與混淆。本文認為上述觀點值得商榷:
第一,行為人的特別認知也許與成立責任故意所必要的事實存在部分重合,因而將行為人的特別認知作為危險有無的判斷資料,可能與責任故意的審查存在某種關聯,但是這僅僅意味著對危險的判斷在一定程度上提前介入了對責任故意認識因素的局部審查,而構成要件具有故意規制機能,責任故意由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共同組成,其成立與否具有獨立的、完整的判斷標準,因而對危險的判斷無法取代對責任故意的整體審查。況且,特別認知必須存在于事前,而對責任故意的審查則是在確立不法之后進行。在過失犯的場合,盡管還存在爭議,但是按照羅克辛教授的觀點,凡是符合客觀構成要件的,就是過失犯。換言之,羅克辛教授認為,過失犯的行為是通過違反構成要件特別規定的特定義務而加以描述的,根本無須考慮行為人的主觀認知。
第二,對危險的判斷是一種價值評判,既然如此,就不得不考慮一般國民的預見可能性和價值觀念。然而,一般國民的預見可能性只是作為確定“危險有無”判斷資料范圍的標準。換言之,一般國民的預見可能性本身并不是判斷資料,而只是決定行為時存在的客觀事實哪部分能夠進入“危險是否存在”的判斷資料的選擇性標準而已。
第三,如果以行為當時存在的全部客觀事實作為危險的判斷資料,則可能與責任主義原理相悖,不利于刑法人權保障機能的實現。因為某些事實,甚至是對危險認定具有重要影響的事實可能是行為人(或社會一般人)無法認識到的,甚至科學理性都無能為力,即沒有預見可能性。具體而言,一方面,預見可能性是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的共通前提,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都要求行為人對符合構成要件的客觀事實具有預見可能性,故而將沒有預見可能性的客觀事實評價為符合構成要件的事實不符合責任主義的要求,而將沒有預見可能性的事實作為危險有無之判斷資料就意味著將其作為構成要件的事實進行刑法評價。顯然,這樣判斷得出的結論并不合理;另一方面,將沒有預見可能性的客觀事實作為危險價值評判的資料亦有可能造成危險分配的不公允,從而加重行為人的負擔。危險如何分配,本質上涉及的是注意義務如何分配的問題,它往往又與危險是否容許的判斷緊密聯系在一起:如果危險被容許,則行為人未被科以刑法上的注意義務,如果危險不被容許,則行為人勢必需要謹慎履行其注意義務,不然就可能要承擔相應的刑罰后果。問題在于,某些行為人無法預見的客觀事實對危險的分配產生重要影響,若此時仍將行為人無法預見到客觀事實作為判斷資料勢必加重行為人的危險防范義務負擔。比如說在深圳就發生過一個案件,加害人和被害人并不認識,一天早上在買早餐的時候,雙方發生爭執產生糾紛,加害人打了被害人一拳,被害人倒地就死了,事后查明,被害人患有嚴重的心臟病。如果將被害人患有心臟病這一客觀事實納入判斷資料,則加害人是可以被客觀歸責的,如果不把被害人患有心臟病這一客觀事實納入判斷資料,則排除客觀歸責。問題是,本案中,被害人患有心臟病,社會一般人無從知曉,加害人因為與之不認識,故也法知曉被害人患有嚴重的心臟病這一客觀事實。如果硬將被害人患有心臟病這一事實納入判斷資料,認為加害人違反不應對心臟病人動粗這一注意義務從而制造被害人因心臟病發作而死亡的危險,最終被客觀歸責,則顯然不能被一般國民接受,有悖于刑法人權保障機能。
由此看來,引入人的認知能力旨在排除行為當時沒有預見可能性的那部分客觀事實。同時本文主張在確定危險有無之判斷資料時,必須根據經驗法則考察“假定事實”發生的蓋然性,將“假定事實”中發生概率較大的那部分事實納入危險有無之判斷資料。例如,如果奪取一只警察手中的裝有子彈的手槍之后再開槍射擊的,盡管警察攜帶的手槍中碰巧并未裝子彈,仍構成殺人罪未遂(“奪警槍殺人案”)。這就是考慮了“假定事實”(執勤警察手槍一直裝有子彈)的高度蓋然性。奪警槍殺人案中,既要查明沒有發生結果的原因,并且要科學地探明在事實屬于何種情況之下可能會發生結果;又要判斷應該導致引起如此結果的(假定的)事實(盡管現實中是不存在的)是否可能存在。“假定事實”由此成為判斷危險有無之核心要素。
(二)結果承擔
眾所周知,空白罪狀是指在刑法分則條文中不直接敘述犯罪的特征,而只是指出該犯罪行為所違反的其他法律、法規。因此,刑法對于空白罪狀多采用“違反……法律、法規,因而造成……結果”的表述方式。由此可見,對于空白罪狀,違反其他的法律、法規是構成某種犯罪的前提,沒有這個前提,該犯罪也就不能成立,法益侵害就是違反某種注意規范危險現實化的產物。在這種情形下,必須考慮行為人所違反的注意規范之保護目的,如果行為人雖然違反了注意規范,但所造成的結果并不是違反注意規范所造成的結果時,不應當將該結果歸屬于行為。即結果雖然發生,也就是風險已經實現,但這一結果并不在注意規范保護范圍之內(行為沒有引起注意規范的保護目的所包含的結果),仍然不具有客觀上的可歸責性。例如,A酒后在封閉的高速公路上駕駛機動車,撞死了突然橫穿公路的B,本案中,A的行為無疑違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條關于禁止酒后駕車的規定,其酒后駕車行為與B的死亡之間存在事實上的因果關系,A的行為在當下的司法實踐中構成交通肇事罪幾乎毫無懸念。然而,禁止酒后駕駛的注意規范,是為了防止因飲酒而喪失或者減弱控制車輛的駕駛能力而造成交通事故。因此,該案的結果并不在禁止酒駕注意規范的保護目的范圍內,也即A的醉酒駕駛行為與B的死亡之間并不具有規范保護目的關聯性。
應當指出,交通法規雖然錯綜林立,但絕大多數交通法規的目的,如禁止超速、闖紅燈,禁止危險駕駛,禁止疲勞駕駛、遵守交通信號等等都是為了避免和減少交通事故,確保交通安全。只不過不同的交通規范的具體保護對象是存在區別的:有的注意規范旨在確保他人安全目的,如禁止超速;有的注意規范側重于保護交通工具駕駛者本人安全目的,如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條關于摩托車駕駛人員應當戴安全頭盔的規定;而有的注意規范僅僅是單純指向交通行政管理目的,如禁止遮擋、污損車牌,這類注意規范對于駕駛人、乘車人以及其他行人、車輛的安全并無保護的意義和作用。規范保護對象的不同,在交通事故案件中的裁判結論就會不同。因此,我國司法實踐中普遍存在的以交通事故責任書直接作為刑法上交通肇事犯罪成立依據的做法是欠妥的。應當運用注意規范保護目的理論,結合案件具體情況分析特定注意規范保護對象,合理限定交通過失犯的成立范圍。特別是,在行為人沒有違反確保交通安全的注意規范保護目的之下,僅僅違反了確保交通行政管理之需的注意規范保護目的,不能成為其成立交通過失犯的理由。概言之,規范是否確實具備有保護目的,應該從具體的個案來著手檢驗,因為只有透過具體案例我們才能確定,規范的遵守是否可以適當地阻止結果發生。⑤
四、余論
從因果理論發展的進程來看,德、日刑法經歷了從條件說、原因說到相當因果關系說,再到客觀歸責這樣一個學說的演進過程。其基本進程是將歸因與歸責加以區隔,在歸因的基礎上再考慮歸責。⑥既然如此,法官在個案中對因果關系的審查與判斷,絕不是僅僅為了查清被告人的行為與結果之間有無哲學/自然科學意義上的因果關聯,而是要規范判斷能否將作為實行行為危險現實化產物的法益侵害公平合理的分配給被告人。因此,一方面要從歸責意義上考察因果關聯,另一方面又要對實行行為與法益侵害結果分別進行獨立的規范考察。唯有如此,才能克服事實命題的因果理論所形成的缺陷,實現從存在論到規范論的類型化判斷。風險分配的復雜化使得對刑法因果關系的認定不可能存在可以適用于所有個案的一般化標準,只可能提供一個統一的處理框架,法益侵害危險分配的規則體系的完善尚待于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的探索實踐。
[注釋]
①高銘喧.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4:129.
②高銘暄主編.刑法專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90.
③哲學上的因果關系是對自然科學意義上因果關聯的總結與升華,二者具有同一性,都以承認因果關系的客觀規律性與時間序列性為必要.
④[德]約翰內斯韋塞爾斯.德國刑法總論[M].李昌珂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94.
⑤[德]Ingeborg Puppe.規范保護目的理論[A].李圣杰譯.國際刑法學會臺灣分會主編.民主·人權·正義——蘇俊雄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C].臺灣:臺灣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105.
⑥陳興良.從歸因到歸責:客觀歸責理論研究[J].法學研究,2006(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