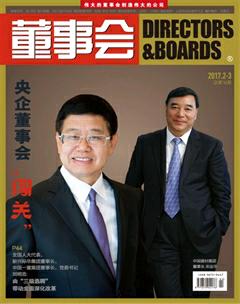熬出來的“隱形冠軍”
陳捷

人活著有多大意義,能做多少事情?只要自己能夠心安理得,暢快,心里不揪著。上不愧天,下不愧人,中不愧己,這就是最好的活法。當有了這種心態,就不會為一時的得失而困擾自己。
早春的石城,陽光明媚。2月9日上午,記者如約來到古平崗18號,紫金智夢創業園區的一處辦公地,由于新年剛剛上班,員工都去內訓了,只見唐紹林一人忙著接客戶電話的身影。
這位準備IPO的新三板公司的董事長,當年從江蘇省建材研究設計院下海創業至今,已跨入第18個年頭,雖過知天命之年,仍然不辭忙碌。“娶了一房媳婦認定就是一輩子的事。”而他眼中的“媳婦”,如今已出落成工業副產石膏資源化循環利用研究與應用行業的技術領跑者。
“硬著頭皮熬了過來”
這究竟是一門什么樣的生意?
所謂工業副產石膏,指的是工業化生產過程中,因化學反應伴生的以硫酸鈣為主要成分的副產品或廢渣。據了解,目前全國已堆存近8億噸,每年還新增約1.8億噸,由于目前利用水平低下(真正循環利用量不足30%),嚴重破壞土壤及水資源環境,加重空氣粉塵污染。這也是當前的行業現狀。一夫股份做了什么?唐紹林說,經過公司一系列特殊技術手段和專有設備綜合處理后,工業副產石膏可百分之百替代天然石膏,既解決相關企業由于廢渣外排、堆存所造成的環境問題,有效保護礦產資源,減少水土流失,同時為企業創造一定的經濟效益。
1999年下海創業的唐紹林,起初并不做這行。作為基礎材料供應商,與房地產行業接觸多年、見慣了招投標等諸多亂象后,他逐漸意識到,作為一個規模較小卻又想做一番事業的民營企業,基礎建材行業沒有太大的出路可走,轉型從來就不是大企業們所獨占的專利。下海第十個年頭,他下決心轉型。當時的思路是,以石膏材料應用為著眼點,從材料基礎研究著手,從原來的石膏粉料在墻板、石膏砂漿中的簡單拌合利用,以及脫硫石膏粉料簡單加工,采用實驗室經濟模式,逐漸朝著節能、環保、新材料的方向走,進而實現一夫的轉型戰略。
做出這個重大決定并不容易。為了穩妥起見,轉型前他到德國考察了大半個月。“在歐洲做一個項目,規劃用八年、十年、十五年的很多,也很正常,而我們國內的企業最大耐心差不多只是3年左右。公司當時如果抱著建材不轉的話,也不會有虧空,不過我們在對各類環境充分分析判斷之后,總感覺不能再那樣發展下去,可以說,轉型是必須的。”
《董事會》:為什么選循環利用這條路,發展空間大嗎?
唐紹林:一年將近兩億噸工業副產石膏外排,破壞土壤,破壞空氣和水源,利用技術手段加工以后,可百分之百替代天然石膏。應用前景好,品位比天然石膏高,可以說是非常好的一個循環再經濟產業。我們規劃得比較長遠,比較系統。做這個行業七年,我們大部分時間在工藝開發上,研究成果的真正目的是為了促進生產力的提高,走向市場,被市場接受,創造價值。
《董事會》:整個轉型花了多長時間?
唐紹林:持續了6年,到2015年才開始見效。
《董事會》:跟你說的“最大耐心”相比,時間上差不多有一倍了。
唐紹林:我充分體會到了什么叫重重困難,什么叫壓力山大。在這個過程中,很多股東、銀行、投資商離我而去,都想追求短平快的效果。他們的邏輯很直接——第一年栽樹,第二年開花,第三年還不結果嗎?
《董事會》:怎么熬過來的?
唐紹林:貸款、借錢,所有東西都抵押了,甚至還要借高息貸款!公司多少次被債務逼到懸崖邊,但我琢磨著,既然認準了對的方向,就要一直往前走,就是要咬緊牙關堅持活下去。可以說是硬著頭皮熬了過來。一夫能夠轉型成功,也讓我感到欣慰,畢竟還有很多企業倒在了轉型的路上。
《董事會》:在這個行業里面,有別的企業嗎?
唐紹林:這一塊在環保細分領域里是個單科,目前在國內只有我們在做。從技術研發到市場開發以及產品應用,我們是這個行業的龍頭,國家相關標準大部分都有一夫股份參與制定。這個行業也是跨國界的,去年全球石膏大會在曼谷召開,我們代表中國參會企業作了大會發言。
《董事會》:是你們提出了“實驗室經濟模式”?
唐紹林:我國今后主要發展方向就是循環經濟,就像“互聯網+”一樣,這是“綠色產業+”“循環產業+”,這是今后主體產業方向。我們選擇的,是以工業固體廢料資源化循環利用為對象,以科技研發為核心,以服務外包為主體的實驗室經濟模式。實驗室經濟模式最早誕生于美國硅谷,國內最早是2008年左右由清華大學魏強教授提出來的,這個模式最核心的內容就是自主創新。我們根據當時自身的情況提出自己的實驗室經濟模式,由原來的建材行業轉型到現在。這種模式在中國企業中目前是比較少見的。
《董事會》:為什么?
唐紹林:因為在中國當下一味追求速度,那么功利不顧一切的大環境下,很少有企業家愿意去承受創造的不確定性而有可能帶來的失敗。這需要一定的戰略眼光和文化底蘊的支撐,更需要在這紛繁復雜的環境中保持清醒的頭腦和正確的價值觀。
“做一個有靈魂的企業”
“你知不知道,有一種愛叫做堅守和忍耐。你知不知道,有一種愛叫做敦厚和寬懷。你知不知道,有一種愛叫做擔當和承載。你知不知道,有一種愛叫做懸崖邊顫抖的徘徊……因為愛,我們共筑平臺,堅韌篤行到現在;因為愛,和諧之花在一夫盛開……”發展戰略決定創新模式,而想要做什么事情,想怎樣去做,則與企業的文化緊密相連,也跟領導者的個性充分關聯。這首歌的詞,就是唐紹林的心聲。
怎么想起來作詞?用唐紹林的話說,一夫企業發展、轉型中的堅持,是有底蘊有支撐的,體現在“敦厚從善,和諧發展”這八個字。
“這不是一個口號,確實是我們歸納總結出來的,是跟我個人價值觀相吻合的企業文化。”他解釋,八個字的意思就是說,做人要敦厚從善,做事要和諧發展。和諧發展代表我們從事的這個事業對環境友好、綠色發展,天地人和諧的寓意,尊重自然,尊重生態。今后所做的事情,所走的方向,都是來源于“敦厚從善,和諧發展”的這個理念。
為什么要倡導?“我們所倡導的這種企業文化,包括做事的方法,是叫好的,是被社會認可的,但往往是不叫座的。給人第一認識就是,這樣做是對的。”他說,然而現在人們的世界觀很多都是比較現實的。由于發展對環境和資源帶來的破壞,是用錢買不回來的。先破壞,再治理,我們走的這條路,是西方19世紀、20世紀就走過的路,對價值觀和對世界觀的破壞,是要一兩代人甚至兩三代人才能慢慢修復過來。“像我們這樣,有一顆正能量的心,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們做企業的方式就是盡量按自己的心路去走。”
采訪中,一個細節引起我們的注意。那是唐紹林背后墻上的“一夫”商標,整體看上去像“天”字,又有“人”字在其中。
“一夫這個商標,是1999年成立公司時,我在工商局門口自己畫的。”他笑著說,“當時就是一個人的意思,有點悲壯!后來發現還可以這樣解讀:綠色代表大地,代表我們從事的產業,商標整體看,像是“天”字,同時突出“人”字,代表天、地、人三才合一,冥冥之中的巧合吧。”
《董事會》:親自寫歌詞,這在企業領導人中不多見。
唐紹林:我記得,自己的性格養成是在十幾歲的時候,那時最潮的是文學青年,耳濡目染接觸了不少朦朧詩、反思文學。后來創業后又系統學習了國學、哲學,寫東西是自己的一點愛好,再者,用這個形式傳遞價值觀,抒發自己的感受比較好,大家容易接受。
《董事會》:塑造價值觀,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唐紹林:一個企業就像一個人一樣,要活的有精神,有文化,有理念,有想法。一夫真正的核心競爭力是企業文化和研發。企業文化是形而上的,形而下的是我們掌握的方法,是創新,創新的基礎是研發。公司大方向有利于社會的發展,與全球的產業方向相對應,既要有技能,又要有思想,這樣才能更長久。我們認為做企業就要做一個有靈魂的企業。
《董事會》:有靈魂的企業?
唐紹林:是的。我認為,做事的過程就是做人的過程,做事是做人的外在表現。不一定賺了多少錢就代表著成功,其實我們每個人從出生最終就是要走向死亡,人活著有多大意義,能做多少事情,只要自己能夠心安理得,暢快,心里不揪著。做到上不愧天,下不愧人,中不愧己,這就是最好的活法。
《董事會》:所以要敢于創新,要善于作為。
唐紹林:造船的目的是要乘風破浪的,停在港灣里最安全,但就失去了船的意義。所以,我們不怕模仿,直面大環境,不斷創新。材料基礎研究是關鍵,一夫股份一直處在不斷向前走領軍者的過程中,一夫的價值絕對不能以常規的方式去發現,普通的價值判斷,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反而對我們是一種誤讀。
對待技術,別人可能是照葫蘆畫瓢,我們是舉一反三,始終站在行業的制高點去規劃。石膏再利用的前景有多大,如果每臺套設備三千萬,就是三千億以上的市場空間,而現在,一夫還處在價值被發現的過程。
《董事會》:在你心里,一夫價值發現,或者說價值創造的目標是什么?
唐紹林:這是一個信息化的時代,時代在變化,就不能固守原有的陳規陋習。至于一夫股份最終達到一個怎樣的目標。認識到更深層次,數字就不是太重要了,重要的是怎樣去做、走什么樣的路,這個過程非常重要,賺錢和財富的多少,在我心里,不代表真正的成功。
《董事會》: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么?
唐紹林: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是渺小的,對財富觀的認識,生命觀的認識導致對價值觀和世界觀的判斷各不同,進而確定怎樣做事,至于做到什么地步,都不是很重要了。當有了這種心態,就不會為一時的得失而困擾自己,在這種大環境中,抱著這種心態做事,要得到別人真正的認可是很不容易的。雖大環境充斥著銅臭味,但是,如果心對了,方向對了,路子走對了,這個過程中,總會有人幫你,等著我們的必將是一個輝煌的未來和無盡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