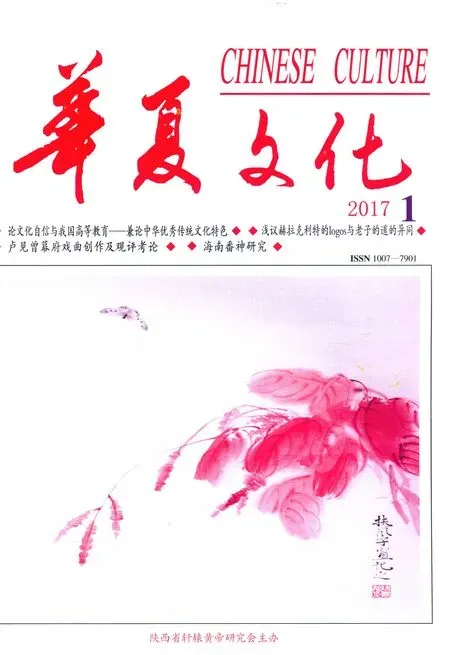論文化自信與我國高等教育
——兼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色
□ 張豈之
論文化自信與我國高等教育
——兼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色
□ 張豈之

一、總書記習近平同志關于文化自信的論述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同志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文化自信作了深刻的理論闡述:“我們說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2016年11月30日,習近平同志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對文化自信作了進一步論述,他說:“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沒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寫出有骨氣、有個性、有神采的作品。”
文化自信是國家興衰的命脈,是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基石。其中包含:1.認同中華文明有5000多年沒有中斷的歷史;2. 認同人類文明的多樣性,世界上不同國家和民族都對人類文明作出了貢獻;3.中華民族創造了博大精深的獨特文明;4.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有了這四個認同,我們才能滿懷信心地走自己的路,在“兩個百年”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總之,習近平總書記論述的文化自信,其中既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又有現實的社會主義文化,同時又擴大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中的核心理念。對此,我們應深入學習,將其精神引導到中國高等教育的理論和實踐中去。
二、論大學的文化素質教育
我國高等學校實施素質教育,1999年,第四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中有明確的論述。
我國高等教育的任務是:培養優秀綜合素質的專門人才。“素質”指人的特質,它是知識與能力的結合,其中有思想道德素質、科學素質、文化素質、身體素質、心理素質等。在大學實施素質教育,這是我國高等教育的特征。
我國大學的文化素質教育和西方大學的通識教育有相同處,也有自身的特色。我作為大學文化素質教育的參與者,曾經研究過西方大學的通識教育。2005年我在《論我國大學文化素質教育的特色》一文中有這樣的話:“西方大學的通識教育并非各種知識的‘拼盤’,而是更加注意貫串其中的關于人的思維方式、價值追求的論述。我國大學借鑒西方大學的通識教育,不能只是著眼于不同知識的傳授,而要求用我們自己的價值觀、思維方式將各種知識融會貫通。這也就是說,評判我國大學所謂‘通識教育’的成效,只看課程的名稱是不夠的,還要進一步研究:在各類知識的傳授中,我們給大學生以怎樣的世界觀、方法論和價值論?”(《中國高教研究》2005年第9期,收于拙著《大學的人文教育》一書的第57—75頁,201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三、我們應深入研究中國智慧和理性思辨
習近平同志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華民族有著深厚文化傳統,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體系,體現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這是我國的獨特優勢。中華文明延續著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也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
1.中華文化的根脈,可從《周易》說起
傳說中華文明起源時期,炎帝發明五弦琴、七弦琴,演八卦為六十四卦,為后來西周禮樂文明作了鋪墊。除此之外,還有伏羲基于陰陽概念畫八卦的傳說。
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西周,由陰陽兩種符號組成八卦,即坤、艮、坎、巽、震、離、兌、乾,它們分別代表八種自然物:地、山、水、風、雷、火、澤、天,這些具有剛或柔的性質。八卦兩兩相重,形成六十四卦,包括三百八十四爻,代表眾多事物。陰、陽是《周易》經文中貫串始終的概念。
陰陽最初作為山的向陽面和背陰面,這在原始社會中先民們已有這樣的樸素認識。經過很長時間,人們才從廣大的物質世界抽象出兩大類或兩大性質的概念,即陰與陽,這從《周易》經文中可以看到。后來儒者研究《周易》,解釋其經文,寫成《易傳》即所謂“十翼”的時候,才有了“一陰一陽之謂道”的理論概括。春秋末期儒學創立者孔子研究《周易》,他不是將此簡單地作為占卜之書,而是要從六十四卦的結構中去找到世界和人生的法則。
戰國末期,儒者研究《周易》,將研究心得寫成《易大傳》,共分十篇,其中《系辭》著重論述《周易》的理論要義。
比如,《易傳·系辭》的作者認為,《周易》主要講萬物、人事變化的道理。“《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這說明自然和人類社會無一不在變化,禮儀刑法也是這樣;變化了就能發展;發展了就能暢通;暢通了就能長久。基于此,《易傳·系辭》的作者用“生生”、“日新”來指稱事物變化的過程,肯定它,贊美它。《系辭》還從歷史角度去說明事物變化之理,如說黃帝、堯舜時期的各種文明創造,為百姓帶來福祉,加以歌頌,就是很好的例證。《易傳·系辭》研究變易之理,認為陰陽、剛柔、動靜、吉兇、禍福、存亡等對立方面相推相摩,引發自然和社會變化,用“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來表述。認識到這個道理,君子們才能達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這個原創在中國歷史文化中被稱為“憂患意識”。
2.關于“憂患意識”
這里要提到北宋時期政治家、思想家范仲淹(989-1052)的一篇名文《岳陽樓記》。此樓唐朝時初建,宋仁宗時重修。范仲淹應友人之邀,著文以記其事。文中首敘岳陽西大湖洞庭景觀,次敘在風雨飄飛的日子里登樓感物而悲,再敘春和景明之際登樓覽物而喜。最后作者問如何才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回答是:“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
范仲淹提出了一個大問題:政治家怎樣才能不因環境變遷而改變自己的志向?不因個人得失而轉移個人的感情?他回答說:在朝廷做官,要情系百姓,不在廟堂之上,仍然要有對于國家的憂患情懷。當天下人都有了快樂和幸福,這個時候才有個人的歡樂愉快。范仲淹把我國古代的憂患意識提升到憂國憂民的高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016年6月,媒體上有一條消息:岳陽樓被一家企業承包經營,引起公眾質疑。如何保護像岳陽樓這樣重要的文化遺產,需要公眾的關心。應當看到,這不僅是一個景觀,而且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標志著中華的憂患意識,需要岳陽樓所在地的政府對此保護好,管理好,不能有絲毫的疏忽大意。
四、中國古代博大精深的文明例舉
習近平同志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古代大量鴻篇巨制中包含著豐富的哲學社會科學內容、治國理政智慧,為古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據,也為中華文明提供了重要內容,為人類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對中華文明進行深入的學術研究,又加以普及性介紹,應當是我國高等院校、特別是其中的人文學科教學與科研單位應當承擔的責任。
1.孔子創立的儒學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魯國昌平陬邑(今山東曲阜)人,他創立了儒家學派。
在孔子看來,一個有道德修養的君子,要有理想;此理想可稱之為“道”。“道”的價值超過人的生命。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當“道”與人的生命相沖突,一個有道德修養的君子應當犧牲個人生命,以維護“道”之尊嚴,這就是孔子所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人之所以有高尚理想,并有為理想而奮斗的精神,就因為人有道德,人能思考,人超越于其他動物。這個道理,孔子用“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這8個字加以理論概括。這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最早的主體意識觀。他追求的不是個人的富貴尊榮,而升華為強烈的歷史使命感。
這種使命感在儒家“人學”的思想中被稱為“正氣”和“操守”。戰國中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提出“浩然之氣”。在他看來,“浩然之氣”是集合了正義行為而生成的一種氣,不是偶爾一次的正義行為所能取得的。孟子認為,人有了這么一種精神,就能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戰國末期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稱此為“德操”,他說:“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荀子·勸學》)總之,人與其他動物的區別,君子與小人的區別,標準就在于有沒有德操。
在孔子看來,人對理想的追求,人的道德完善,要靠后天努力。所以他特別關心教育。他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教育家,其教育理論和教學方法,是我國教育史上的寶貴遺產。
2. 道家的“自然”之學
中華文明不僅研究“人”之所以為人,而且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其最早的杰出成果表述于《老子》(即《道德經》或稱為《道德經五千言》)一書之中。
《道德經》五千言的作者為李耳,春秋末期楚國苦縣(今河南鹿邑)人,曾經在東周管理國家圖書。據司馬遷《老子韓非列傳》記載,老子眼見東周王室衰微,便離開職守,出函谷關,行蹤不詳。
老子明確指出:世界的本原稱之為“道”。《老子》書81章,直接談到“道”的有77章,“道”字出現過74次,反映出老子從不同的層面去闡釋世界的本原——“道”。
老子書稱“道法自然”(第25章),“道”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千變萬化的世界。《老子》第25章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效法于地,地效法于天,天效法于道;天地人都是自然而然地從“道”中產生的。
在老子看來,“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老子》第40章),“道”在運動,不斷向相反的方向前進,最后又回到出發點。由此,老子提出問題:人們怎樣才能防止事物向相反的方向轉化,從而避開災禍?老子說:人們應當懂得“上善若水”的道理:最高的善象水那樣,它是至柔的,因而,它才是真正的無堅不摧。“上善若水”可用來比喻“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老子》第49章)。老子倡導大愛精神,是值得贊美的。
老子是道家學派的開創者,他提出的理論是人本主義的,并非宗教。至于為何兩漢之際老子卻成為道教的始祖?這是因為有人扭曲了他的思想,把他神化了。
3. 中華古代的辯證思維
儒學的“二端”說、“中庸”論以及“和而不同”說都是“有對”之學的顯例。而道家的“自然”之學更加深入地論述了古代辯證思維的要點。老子從社會和自然現象中概括出一系列“有對”之學的范疇,如“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老子》第2章),并指出對立范疇可以轉化,即“物極必反”。對此,《老子》書作出詳細的論述,如“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老子》第22章)。再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同上第58章)。依據事物轉化的道理,在老子看來,要想達到某種既定目的,最好是致力于該目的相反的方面:“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去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第36章)關于轉化的終極原因,還不是老子所能解決的。
值得往意的是,中國古代“有對”之學,并非純哲學理論,它更加著重于運用,即運用于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其成就輝煌卓著。于是,在長期歷史演變發展中逐漸形成這樣的看法:要使事業成功,必須學習和運用中國的“有對”之學。眾所皆知,當今世界上有些國家研究《孫子兵法》十三篇,就是這個道理。《孫子兵法》是“有對”之學運用于軍事和人事的范本。其作者相傳為春秋末年的齊國人孫武。據《史記》載,孫武任吳王闔閭的大將,指揮吳軍戰勝楚國。他的后裔孫臏繼承其軍事思想,曾任齊軍師,擊敗魏國。今本《孫子兵法》帶有戰國時代色彩,可能經過孫臏的整理修改。
《孫子兵法》強調在規定并設計戰略和戰術時,需全面考察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第一篇《計篇》說,須“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而索其情”。所謂“五事”即道、天、地、將、法。對于“道”,孫子是這樣解釋的:“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孫子兵法·計篇》)可見這里說的“道”乃是合乎人民利益的政事。在他看來,戰爭的目的能否“令民與上同意”,是否得到人民支持,這才是決定戰爭勝敗的首要因素。其次要看到決定戰爭勝負的綜合條件。對此,孫子剖析頗細,他說:“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同上《形篇》)這是說,作戰雙方的地形、資源、兵源、兵種等綜合力量的對比,構成勝負的物質基礎。勝負不能單憑哪一條,必須作全面的綜合分析。他的結論是:“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同上《謀攻篇》)這個原理不僅對戰爭適用,對其他任何事情都適用。
孫子不但看到對立面可以轉化,而且看到轉化的某些條件,人們可以創造,以促使事物向好的方面轉化,這是對中國古代“有對”之學的重大貢獻。例如他說:“亂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同上《勢篇》)說明治亂依賴于“數”,勇怯依賴于“勢”,強弱依賴于“形”。人們可以揚己之長而去己之短,以取得事業的成功,因而不能坐等勝利,人的主觀能動性有重要作用。
如果說中國先秦時期是“有對”之學的一個高峰,那么宋明時期又是另一高峰。宋明理學不僅繼承和闡發了以前的“有對”之學,而且吸取并改造了佛學的辯證思維。因此,宋明時期“有對”之學在“分”與“合”關系的理論闡述方面做出了創造性貢獻。如北宋時期邵雍提出“一分為二”,他說:“是故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合之斯為一,衍之斯為萬。”(《觀物外篇》中之上)這是數學上的一分為二,包含有辯證因素,還不能完全等同于辯證的一分為二。
再如北宋思想家張載提出“一物兩體”論,他說:“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二故化。此天地之所以參也。”(《正蒙·參兩》)這里就表述了事物矛盾既對立又統一。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不但論述動與靜、陰與陽、生與死、始與終的對立統一,而且猜測到“對立”的兩方面不是平衡的,其中有一方占主導地位。他說,動與靜互根,然而動卻是主導面。這個觀點后來在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著作中得到發展。
不過,中國古代“有對”之學未能解決何以萬物有對、何以物極必反、何以兩體中有一體占主導地位等問題。盡管如此,“有對”之學毫無疑問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的精華部分。
4. 中華的“會通”之學
中國先秦時期有許多學派,學派間相互爭論又相互吸收,共同發展。不僅如此,中國文化還善于學習和吸收外來文化,例如:從2世紀至8世紀,印度文化及其佛學不斷傳入中國,16世紀末,西方最早的一批傳教士帶來歐洲中世紀的神學和自然科學,也影響了當時中國的思想和文化。
上述狀況,用孔子的話說就是“和而不同”。明代自然科學家徐光啟和清初思想家方以智稱此為“會通”之學,即融合貫通之學。
應當承認,“會通”之學是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特色和優點。這在春秋戰國時期表現得格外明顯。當時學派分布的情況大致是:儒、墨以魯國為中心,而儒學傳播于晉、衛、齊,墨學則傳入楚、秦。道家起源于南方的楚、陳、宋,后來可能是隨著陳國的一些逃亡貴族而傳入齊國。楚人還保留著比較原始的“巫鬼”宗教。在北方的燕國和附近的齊國,方士也很盛行,后來陰陽家就在齊國流行。法家主要源于三晉。如果說春秋時代文化中心偏于鄒、魯,則戰國時代的文化已無此種界限,文化的交流會通日益開展起來。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中國民族的逐漸融合,以及各國間頻繁的交往和聯系,各個學派的思想也相互影響,相互學習吸收,成為“會通”之學。如荀子雖出身于儒家,尊崇孔子的傳統,但正如清初學者傅山所說,其思想“近于法家,近于刑名家”,而且在一些論點上,又有“近于墨家者言”(《荀子評注》)。荀子廣泛吸取了各家的思想精華,同時對各個學派,包括儒家的若干派別在內,都作出了深刻的研究。
再如戰國末期的《呂氏春秋》一書也帶有“會通”之學的特色,它兼采相互矛盾的諸家學說,這即是后人所稱的“雜家”。如《漢書·藝文志》所說,雜家是“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
中華文化善于吸收外來文化,佛學最初傳入中國時,就產生了“格義”之學,用來溝通當時流傳的玄學和佛學原理。在這之后,佛經的傳譯逐漸發展起來。中國形成了許多佛學宗派,它們具有中國特色而不純為印度佛學。佛學被改造而融匯于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對中國古代思想產生了很大影響。
首先,佛學豐富了中國思想范疇。宋明時期中國思想范疇之豐富遠遠超過以往,這是因為佛學的一些范疇(如緣起、因果、慈悲、解脫以及“能”、“所”、“識”、“相”等)被納入中國思想,使它豐富起來。
其次,佛學將中國思想中的主體意識論推進到新的高度。唐代禪宗六祖慧能所謂“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四句偈,已反映出禪學乃是宗教化的主體意識論。它從本體論、認識論、道德論、時空論諸方面闡述了主體意識的作用,但同時也留下了比較豐富的關于生與滅、相對與絕對、整體與分別、暫時與永恒等對立范疇的關系,及其與人的主體意識之聯系等方面的思想資料,豐富了中國哲學的內涵,又引發出新的哲學流派(如陸王心學)。
清初的一批大學者,他們對于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有精湛的研究,他們的思想學說大都可稱之為“會通”之學。他們縱論古今文化遺產,從政教風俗到自然科學,從哲學到歷史、地理,從儒家經典到釋、老之說,無不有所論述。如方以智對諸子百家有許多精辟的見解,同時又對儒、佛、道思想給以批評和改造,既有舍棄,又有“擇善”(方氏用語,指擇取其精華)。王夫之對傳統典籍和諸子之學有精深研究,他對儒家經典并不迷信,而以“六經責我開生面”的態度進行總結,同時又對老、莊之說采取批評改造的態度。他在《老子衍》自序中說:“入其壘,襲其輜,暴其恃而見其瑕”,在《莊子通》自序中表示要“因而通之,可以與心理不背”。同時他對佛學既有批評,也有吸收,在其著作《相宗絡索》中可以看得清楚。王夫之的思想學說可稱之為“會通”之學。
結語:關于北宋時期思想家張載的“四句教”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有一段發揮北宋時關學思想家張載的“四句教”。
關學是北宋時期理學的一個重要學派。河南陜西之間有函谷關,關以西稱為關中,關學由當時的思想家張載(1020-1077)創立。張載祖上為大梁(今河南開封)人,后來到關中郿縣的橫渠鎮,他在這里講學,所以人們又稱他為張橫渠。張載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四句話,被稱為“橫渠四句”或“橫渠四句教”,這不是出自張載的文章,而是來自他的語錄《張子語錄》。
第一句“為天地立心”。張載認為,人有見聞之知,這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感性認識。除此,人們還有德性之知。德性之知來源于戰國中期孟子的“盡心”論,張載稱之為“大心”,認為君子應該發揮“大心”的作用,“大心”和我們今天所講的理性認識有相似之處。
張載認為,人有見聞之知,又有德性之知,重要的是要有德性之知。 “為天地立心”,就是要沿著孟子的思路,用理性認知來思考天地萬物之理。
第二句“為生民立命”。這是孔、孟儒學堅守的優良歷史傳統。孔子說過:為百姓解除各種患難,堯和舜這樣一些圣王也沒有完全做到。張載將儒學的宏大志愿稱之為“為生民立命”,符合儒學的基本信念,也反映了他生活時的北宋情況。當時人們面臨兩大困苦,一是土地兼并,再一是邊患。關于土地兼并,張載在關中的郿縣試圖解決,他把一些田地分給少地的農民,但沒有造成全國影響。總之,“為生命立命”講的是解決百姓的患難和困苦。
第三句“為往圣繼絕學”。張載講的“絕學”指的是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學傳統。在張載看來,孟子以后沒有出現過繼承孔孟思想的學人。唐朝韓愈雖寫了《原道》一文,提出了儒學的道統論,從西周文王、武王,到春秋時孔子一直到戰國時的孟子,這些只是一些文字,缺少圣人之心,即對儒學堅定的信念;從這個意義上講,儒學成為“絕學”(中斷了的學問)。張載認為,他創立的關學才是上接孔孟道統的傳人,要以實際行動實現儒家的思想,以此作為自己的使命。
第四句“為萬世開太平”。這是儒學的大目標,做人、做事,在張載看來,都不能離開它。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說:“自古以來,我國知識分子就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志向和傳統。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應該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積極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
習近平同志的這個期望當然包括在我國高等院校做工作、特別是進行哲學社會科學教學和研究的老師們。
我們應傳承發展中華文明根脈,將我國高等院校哲學社會科學的教學、研究向前推進。
2016年12月17日寫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