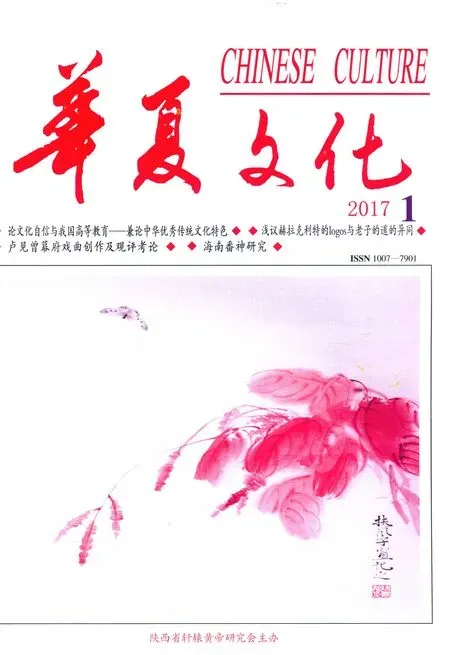淺議赫拉克利特的logos與老子的道的異同
□ 張 昕
淺議赫拉克利特的logos與老子的道的異同
□ 張 昕

老子和赫拉克利特都生活在社會發生巨大變革的時期,兩位哲學家都對萬物的起源和滅亡、產生和消失有著濃厚的興趣,對宇宙本原及其運動提出了相近的看法。“道”和“邏各斯”分別是這兩位哲學家最重要的哲學范疇,代表著兩人對宇宙本原及其運動變化模式的哲學反思。
一、“道”和“logos”的相同之處
1.兩者都是指客觀世界變化發展的普遍規律
老子和赫拉克利特都認為世界是不斷變化的。赫拉克利特把世界的本原歸結為一團永恒的活火,他說:
這個世界對于一切存在物都是同一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創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創造的;它過去、現在和未來永遠是一團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燒,在一定的分寸上熄滅。(《古希臘羅馬哲學》,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三聯書店,1957年,第21頁。下引赫拉克利特言論皆出本書,只標注頁碼)
赫拉克利特強調火的運動變化性質,他認為火最能表達宇宙萬物的變動性,具有能動性和變易性,沒有固定形狀,沒有固定邊界,瞬息萬變。他認為:“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第27頁),世界上沒有什么東西是永恒不變的。但同時,世界上的一切變化都是由規律所制約的,這個規律就是所謂的邏各斯(logos)。所有事物都是按照邏各斯而產生的;邏各斯是一切事物所共有的;邏各斯主宰著事物的運動,使它們“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燒,在一定的分寸上熄滅”(第21頁)。
老子認為道是萬物的本原,也是萬物的本體,無處不存在無時不存在。所以從萬物運動變化的角度來看,它就是萬物運動變化的規律。故老子說: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第25章)
道是“天下母”即是說“道”是萬物的本原,道“周行而不殆”,就是說道是永恒的、變動的。道的永恒性表現在無始無終、無生無滅。莊子繼承了老子的觀點,更明確地指明了道的永恒性。在莊子看來,一切具體的事物都是暫時的相對的,有始有終有生有滅,道則與此相反,“道無終始,物有死生”(《莊子·秋水》)。 莊子說道“自古以固存”(《莊子·大宗師》)、“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莊子·大宗師》),講的都是道的永恒性。
在老子和赫拉克利特看來,運動和變化是宇宙最基本的特征,但是,宇宙的運動和變化并不是盲目的、混亂的,而是有規可循的,一切運動和變化都服從“道”或“logos”的支配。任何具體的事物都不是永恒的,只有支配事物運動和變化的規律(道和logos)才是永恒的。
2.“道”和“logos”都包含著對立和統一
老子認為萬物里都有“陰”“陽”兩種對立的因素,這兩種對立的因素在看不見的“氣”中得到統一。同時,“道”也是“有名”與“無名”、“有”與“無”的統一: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老子》第1章)
這也就是說,有和無謂之玄,玄之又玄就是道,“有”和“無”同出于“道”。陰陽、有無既是對立的,又是互為存在的前提,是統一的。《老子》雖僅有5000多字,但是在其中揭示了事物中大量的矛盾統一現象,如有無、剛柔、智愚、善惡、正反、強弱、損益、得失等等,可以說老子是把對立和矛盾當做思維的最基本的單元(參見張豈之主編《中國思想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4頁)。
赫拉克利特認為,支配事物運動變化的logos也是由既對立又統一的兩種因素構成的。他說:“疾病使健康舒服,壞使好舒服,餓使飽舒服,疲勞使休息舒服”(第29頁);“如果沒有非正義的事情,人們也就不知道正義的名字”(第21頁)。這和老子所說的“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有異曲同工之妙,都認為矛盾是思維的基本單元,只有從對立統一的角度看待世界,才能真正理解世界。赫拉克利特還說:
互相排斥的東西結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調造成最美的和諧;一切都是斗爭所產生的。(第19頁)
自然也追求對立的東西,它是從對立的東西產生出和諧,而不是從相同的東西產生和諧。(第19頁)
生與死、醒與夢、少與老,都始終是同一的東西;后者變化了,就成為前者,前者再變化,又成為后者。(第27頁)
在赫拉克利特看來,各種看似對立的事物其實本質上是相關的,都是同一個單一的、不變的發展過程的不同階段。此外,他還列舉了日與夜、熱與冷、曲與直、始與終、戰爭與和平、善與惡、存在與不存在等來說明對立的普遍性。赫拉克利特認為“變化發展”的根本在于斗爭和沖突,有這種對立和沖突才可能有世界,而這種斗爭統一于“logos”之中。
3.“道”和“logos”所包含的對立雙方又是互相轉化的
老子的“道”不僅揭示了矛盾相互獨立相互依存的關系,而且還揭示了矛盾雙方相互轉化的觀點。他指出:“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老子》第2章)也就是說有無、難易、長短、高下、前后不僅只是相互依存的,也是相互轉化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老子看到了萬事萬物都是向著它的對立面轉化的基本事實,他在揭示這一基本規律的基礎上,又提出了兩種轉化形式:一種是事物由弱小變強大,另一種則是由強大到滅亡。比如“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弱之勝強,柔之勝剛”。老子用“反者道之動”(《老子》第40章)來總結事物向對立面轉化的普遍趨勢和運動模式,甚至道本身的運動也遵循這樣的模式,所以說“有物混成……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老子》第25章)。老子還認為,一切事物的運動變化最終還會重歸于本原,“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老子》第16章)
赫拉克利特也認識到矛盾雙方不但是對立的,也是互相轉化的。他說“冷變熱,熱變冷,濕變干,干變濕”(第30頁);“一切事物都換成火,火也換成一切事物,正像貨物換成黃金,黃金換成貨物一樣。”(第27頁)“對于靈魂來說,死就是變成水;對于水來說,死就是變成土。然而水是從土而來,靈魂是從水而來的。”(第22頁)
和老子一樣,赫拉克利特也認為對立事物的相互轉化根源于宇宙的統一性:“結合物既是整個的,又不是整個的,既是協調的,又不是協調的;既是和諧的,又不是和諧的,從一切產生一,從一產生一切。”(第19頁)赫拉克利特又把宇宙的本原稱為“神”,“神是日又是夜,是冬又是夏,是戰又是和,是不多又是多余;他變換著形相,和火一樣,火混和香料時,便按照各人的口味而得到各種名稱”(第25頁)。
二、道和“logos”的區別
老子和赫拉克利特都認為萬事萬物的變化、運動是有規律的,老子將這個規律稱為“道”,赫拉克利特則稱之為“logos”。兩人都認為,道或“logos”是對立面的統一,它們支配著事物的運動發展,使它們向對立面轉化,而且一切事物最終都會回歸于世界本原。但是,道和“logos”之間也存在著區別。主要有幾下幾點:
首先,老子的“道”不僅是世界萬物變化的普遍規律,還是萬物的本原,而赫拉克利特的“logos”只是萬物變化的普遍規律,火才是世界萬物的本原。老子認為世界的本原是“道”。他把世界運行的規律和世界的本原合為了一個事物。和老子不同,赫拉克利特認為世界萬物是“火”的轉化過程,“logos”是火這個本原轉化過程中的規律。他對世界的本原和萬事萬物的運行規律進行了區分。
其次,“道”在對立統一問題上更注重相互依存和統一,而“logos”更注重斗爭。老子雖然認為事物的永恒運動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但同時認為“虛靜”也是世界的根本特征,萬物最終回歸到道,他稱之為“歸根”,并說“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老子》第16章)。相反,赫拉克利特將斗爭看成是萬物生成、變化的力量和來源。他認為斗爭、對立是和諧的前提,世界上不存在絕對的和諧:
應當知道,戰爭是普遍的,正義就是斗爭,一切都是通過斗爭和必然性而產生的。(第26頁)
互相排斥的東西結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調造成最美的和諧。(第19頁)
雖然和老子一樣認為萬事萬物的矛盾、運動、變化蘊含著根本和諧,但赫拉克利特區分了“看得見的和諧”和“看不見的和諧”,認為潛在于斗爭背后的“看不見的和諧”要優于“看得見的和諧”。相比而言,老子的“道”的辯證法思想只強調對立面之間的相互統一和轉換,忽略了對立面之間的斗爭和排斥,老子的“道”是無為的,是不爭的,是看到了兩個對立面,而避免斗爭,這與赫拉克利特的斗爭思想完全不同。
再次,老子認為“道”是萬事萬物的普遍規律,同時又認為人類社會存在著不同于自然之道的“人之道”,認為“人之道”與宇宙的普遍法則是截然相反的,“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老子》第77章),甚至還說“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老子》第57章),對“人之道”做出極為負面的評價。這當然是針對春秋時期混亂的社會狀況而言的,老子并沒有將“法”看做是“道”在人類社會的體現。明確從“道”引申出“法”的是戰國時期的黃老學派。赫拉克利特則把人類社會的法律與作為宇宙的神圣法律的“logos”聯系起來:“人類的一切法律都因那唯一的神的法律而存在。”(第29頁)從對世界的本質、法律的性質的不同認識出發,老子和赫拉克利特引申出了截然不同的倫理觀和人生觀。老子強調柔弱、不爭:“柔弱勝剛強”(《老子》第36章);“守柔曰強”(《老子》第52章);“天之道,不爭而善勝”(《老子》第73章);“圣人之道,為而不爭”(《老子》第81章)。而赫拉克利特則強調斗爭的價值,說:“人民應當為法律而戰斗,就像為自己的城垣而戰斗一樣”(第23頁)。
三、結語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老子的“道”和赫拉克利特的“logos”由于中西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造成了許多差異,但是所處的相似的時代背景又賦予了他們的思想許多相同之處。最后需要指出,老子和赫拉克利特都認為,關于“道”或“logos”的真理,是不容易為常人所把握的,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言,“自然喜歡躲藏起來”(第30頁),老子認為“正言若反”,就是說它看起來違背人們的日常認識,赫拉克利特也說:“這個logos,雖然永恒地存在著,但是人們在聽見人說到它以前,以及在初次聽見人說到它以后,都不能了解它。”(第18頁)“對于‘邏各斯’,對于他們頃刻不能離的那個東西,對于那個指導一切的東西,他們格格不入;對于每天都要遇到的那些東西,他們顯得很生疏。”(第26頁)
(作者:陜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碩士研究生,郵編71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