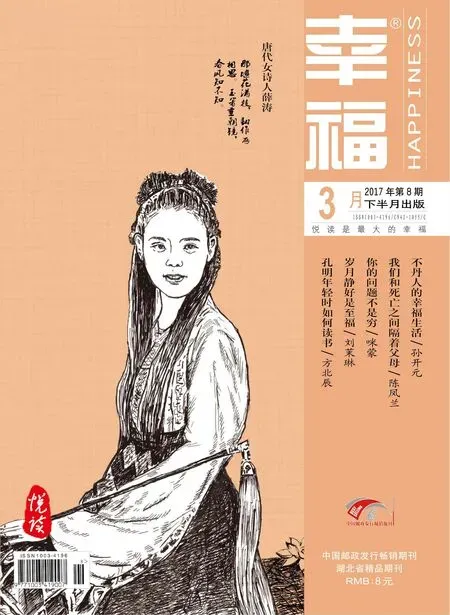我不準(zhǔn)你老去,不準(zhǔn)你離開(kāi)
文/潘云貴
我不準(zhǔn)你老去,不準(zhǔn)你離開(kāi)
文/潘云貴

從高中開(kāi)始寄宿生活以來(lái),我每周五晚上都會(huì)給家里打電話,多半時(shí)候都是我爸接的。等我爸把話筒交給我媽時(shí),我媽就成了啞巴,只是笑著沒(méi)再說(shuō)什么。
后來(lái)我爸和我媽都有了各自的手機(jī)號(hào),但我多數(shù)情況下也只給我爸打,因?yàn)樗奶?hào)碼太好記了。
以實(shí)惠原則來(lái)掂量事物幾乎是每個(gè)持家有道的家庭婦女所應(yīng)具備的日常生活技能,我媽把它發(fā)揮到了極致。她到菜市場(chǎng)買根蔥都可以跟攤主為三毛錢磨磨唧唧半小時(shí),對(duì)方拗不過(guò)她的嘴上功夫,最后還倒貼一棵小白菜給她。我媽像打了勝仗一樣,神氣地提著塑料袋離開(kāi),腳下高跟鞋一路發(fā)出高亢的響聲。
我爸也抱怨過(guò)我媽,兩眼不能緊盯著錢孔,我們家買些油鹽醬醋的錢還是有的。他說(shuō)這句話的時(shí)候常常是看到飯桌上菜肴太過(guò)清淡沒(méi)放多少油水,腹里充足了氣便往我媽臉上噴。我媽也不示弱,義正言辭回道:“你血壓高、脂肪高,我這樣做不都是為你好嗎。”
我媽柳眉鳳眼櫻桃嘴,頭發(fā)黑、皮膚白,平常出門時(shí)穿著都很素淡,表面上看,她是個(gè)艱苦樸素又端莊賢淑的好妻子、好母親。但實(shí)際上,我知道她的很多秘密。
有次暑假我回到家,正好看到她一個(gè)人在客廳里對(duì)著電腦聚精會(huì)神地網(wǎng)購(gòu),山寨皮包、大衣、裙子甚至是胸罩,內(nèi)容超勁爆,我在一旁臉都看紅了。我媽得意地點(diǎn)了一下付款,卻大叫起來(lái),“不是說(shuō)滿200減100嗎?怎么沒(méi)減,這家網(wǎng)店真無(wú)良,我要給差評(píng)!”我這時(shí)說(shuō)話了,“不是賣家無(wú)良,是您老沒(méi)在規(guī)定的專區(qū)里買。”我媽轉(zhuǎn)過(guò)來(lái)看到我站著,瞬間感覺(jué)不好,急忙退出網(wǎng)頁(yè),呵呵笑著,像個(gè)秘密被人發(fā)現(xiàn)的孩子。
我媽特聰明,怕我嘴巴不牢固到七大姑八大姨面前破壞她形象,就帶我上街買衣服,想給點(diǎn)好處堵住我容易漏風(fēng)的嘴。當(dāng)我到專賣店里真挑了幾件價(jià)格還不便宜的衣服時(shí),她卻說(shuō)家里的門忘關(guān)了得先回去,便拉著我往外跑。沒(méi)走多久,在一家少女系列服裝店的櫥窗前,她卻停下來(lái),癡癡看著一件純白色的公主紗裙,許久不動(dòng)。我問(wèn):“家里沒(méi)關(guān)門不怕小偷嗎?”她輕輕回了句:“家里供著財(cái)神爺,怕什么。”
我媽說(shuō)她年輕時(shí)可是鎮(zhèn)上一枝花,可她往往在一句“嫁給你爸后就毀了”后黯然神傷。我爸原先臉就大,身形彪碩,加上平日飯后只坐于沙發(fā)看電視,甚少運(yùn)動(dòng),在時(shí)間的過(guò)道里滾成了球。我媽經(jīng)常跟我念叨:“早十幾二十年如果知道肥胖也是種傳染病的話打死我也不跟你爸過(guò),你瞧瞧他現(xiàn)在把我傳染的。”我搖頭,說(shuō)這不科學(xué)。我媽就咬咬牙用移動(dòng)每月只送的30兆流量在手機(jī)上刷出一條微博來(lái),只見(jiàn)上面寫(xiě)著:“哈佛最新研究表明:近胖者胖……”
跟全天下的中老年婦女一樣,我媽喜歡搓麻將和跳廣場(chǎng)舞。一旦被人提及,她從不心虛,反而理直氣壯,說(shuō)搓麻將可以鍛煉大腦,跳舞則可以活動(dòng)四肢,二者都對(duì)減肥有效。
但我爸十分排斥搓麻將這種腦力勞動(dòng),不僅深夜擾民,更為重要的一點(diǎn)是還傷財(cái)。我爸說(shuō)過(guò)我媽幾回,每次他一見(jiàn)我媽精心打扮好后要出門便攔腰截住她去路。我媽表面上和顏悅色答應(yīng)了,一等我爸不在家或者半夜睡得正酣,她就悄悄溜出門去。
至于跳廣場(chǎng)舞,我爸的態(tài)度是不支持也不反對(duì),在他看來(lái)只要我媽不賭錢不出軌,就能獲得絕對(duì)自由。
有時(shí)廣場(chǎng)上跳的是交際舞,我媽也會(huì)。但她的同伴卻笨手笨腳,經(jīng)常踩到我媽。我媽起初說(shuō)沒(méi)事,兩三次下來(lái)她終于受不了了,四處瞅瞅,見(jiàn)我在,便急忙跟同伴阿姨說(shuō):“我兒子來(lái)叫我回家了,我就先走了。”那阿姨看著我媽說(shuō):“你人真好,下次我還跟你跳。”我媽猶豫地“嗯”了一聲,趕緊拉著我跑了。
每天夜里,我媽經(jīng)常要跟我爸展開(kāi)一場(chǎng)電視遙控器爭(zhēng)奪戰(zhàn)。
我媽是芒果臺(tái)的死粉,特別鐘愛(ài)一檔叫《我是歌手》的欄目。第一屆的時(shí)候,她迷黃綺珊,到了第二屆就超迷鄧紫棋,還說(shuō)鄧紫棋就是女神,有次電話里我問(wèn)她那黃媽不是嗎?她堅(jiān)決說(shuō)不是,理由是她的“胖子傳染病理論”。她說(shuō)跟著瘦子才有未來(lái)。
鄧紫棋在福州開(kāi)演唱會(huì)的那天,我媽騙我爸,說(shuō)自己去大姨家,結(jié)果一個(gè)人跳上大巴去了海峽會(huì)展中心。數(shù)以萬(wàn)計(jì)的粉絲蜂擁而來(lái),我媽在人流中陀螺似地轉(zhuǎn)圈,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通過(guò)團(tuán)購(gòu)買到的靠邊位置,一瞧,前前后后都是一群戴眼鏡的宅男。她剛坐下,一男青年便問(wèn):“大媽你也追星啊?”我媽尷尬地回答:“陪我兒子來(lái)的,陪我兒子來(lái)的,他坐前面……”那天晚上我正在圖書(shū)館上自習(xí),我媽先是發(fā)來(lái)彩信告訴我她正在看鄧紫棋,說(shuō)她跟電視上一樣真的好瘦好漂亮,緊接著她控制不住又給我打電話,我小聲跟她說(shuō)自己在上自習(xí)。人聲鼎沸中喧囂蓋過(guò)一切,她沒(méi)聽(tīng)清我說(shuō)什么,只興奮地一個(gè)勁兒喊著:“你聽(tīng),你聽(tīng)……”手機(jī)隨之被她湊向舞臺(tái),鄧紫棋在唱《喜歡你》。瞬間自習(xí)室里的目光都向我掃射而來(lái)。
我也聽(tīng)過(guò)我媽唱歌,從新中國(guó)的經(jīng)典兒歌到筷子兄弟的《小蘋(píng)果》,她都會(huì)唱,最經(jīng)典的還是《讓我們蕩起雙槳》。說(shuō)起這首歌讓我印象深刻,倒不是因?yàn)槲覌尩穆曇粲卸嗝刺旎[可以返老還童,而是她在唱這首歌時(shí)都會(huì)加上她那個(gè)年代小孩子表演節(jié)目時(shí)的標(biāo)準(zhǔn)動(dòng)作,一手叉著腰,一手前后搖擺,樣子很乖。
我媽常跟我說(shuō)起她年輕時(shí)的事情,參加學(xué)校里的各種比賽,學(xué)當(dāng)時(shí)很紅的張曼玉燙過(guò)卷發(fā),在床頭貼過(guò)周潤(rùn)發(fā)的海報(bào),收集過(guò)小虎隊(duì)的卡帶,喜歡穿淡藍(lán)色的牛仔套裝,還去過(guò)最小清新的鼓浪嶼,按照現(xiàn)在時(shí)髦的話講,也算是個(gè)“文藝女青年”。如果不是因?yàn)橥夤馄旁缭绨阉蘖巳耍崆敖Y(jié)束她美好的少女時(shí)代,她現(xiàn)在說(shuō)不定還能在電視上唱歌或者演某部大齡剩女劇的女主角。她說(shuō)的時(shí)候略帶一些怨懟和遺憾,眼睛眨都不眨一下,仿佛一切都是真的。
我媽不止一次跟人提起這些話,好像要告訴全世界她現(xiàn)在變成一個(gè)庸俗肥胖的家庭婦女都是拜外公外婆所賜。聽(tīng)眾們都跟聽(tīng)祥林嫂的悲慘故事一樣,從最初的表示惋惜到隨后的漸漸習(xí)慣又到最后不得不麻木離開(kāi)。沒(méi)有人跟我媽這位曾經(jīng)有故事的女同學(xué)講話,她就變得很孤獨(dú)。
外公過(guò)世的那天,我媽不像大姨小姨那樣提著錄音機(jī)在靈堂哭,她沒(méi)有眼淚。
晚上,我爸忙著外公的喪事沒(méi)回家,是我媽先帶我回來(lái)的。深夜,起風(fēng)了,屋外的樹(shù)叢猛烈搖晃著,樹(shù)蔭間的縫隙像陰森森的墓穴。我睡了一會(huì)兒,突然被一陣劇烈的哭聲吵醒,隔著墻,我也能聽(tīng)得清,那是我媽在房間里哭。我起身走到她的臥室外頭輕輕敲了敲門,房?jī)?nèi)的哭聲頓時(shí)止住。
我媽開(kāi)了門,面對(duì)她雙眼紅腫、眼袋低垂又有些許皺紋的面頰,我一下子也不知道自己要說(shuō)什么,只問(wèn):“爸爸回來(lái)了嗎,我想爸爸了。”我媽頓時(shí)撲過(guò)來(lái),抱住我,一頭壓在我的肩膀上,悶住哭聲,滅火似的,抽噎著說(shuō):“媽媽也想爸爸,爸爸,爸爸……”之后她哭開(kāi)了,那樣子像極了童年時(shí)迷了路或者丟失了最好玩具的小女孩。
我媽一直都不喜歡或者是不習(xí)慣離別的氛圍。從小到大,把我送進(jìn)幼兒園的是我爸,帶我去小學(xué)報(bào)名的是我爸,目送我離開(kāi)小鎮(zhèn)去城里念高中的還是我爸。記憶中,離別的場(chǎng)景里,我媽從來(lái)都缺席。
但自從外公去世后,再碰到我離開(kāi)家去學(xué)校的時(shí)候,我爸的身旁總會(huì)站著我媽了。她一臉平靜,沒(méi)有演繹電視上那樣催淚的劇情,看我上了車,揮揮手,連再見(jiàn)也不說(shuō)。惟有一次她開(kāi)口了。
在我去重慶北碚念大學(xué)的那年九月,我媽被查出患有神經(jīng)衰落,開(kāi)始過(guò)上一種每日都需靠藥物維持神經(jīng)正常的生活。我好幾次看見(jiàn)忘記吃藥的她站在我面前,樣子傻傻的,像陌生的小孩子,我大聲叫她,喊她,她都聽(tīng)不見(jiàn)。我怕她有天就忘記了這個(gè)世界,也忘記了我。臨行那天,她先是笑著湊到我耳邊,輕輕地說(shuō):“知道你現(xiàn)在已經(jīng)大了,但還是舍不得……”她哽咽住了,后面的話沒(méi)有說(shuō)出,臉上抽搐著又立即被她強(qiáng)壓下去,然后裝作沒(méi)事人一樣朝我揮手,見(jiàn)我上車落座,便趕緊背過(guò)身去。那次到校后,我打電話回家,我爸說(shuō)那天我媽回到家后就一直躲在房間里哭。
繁蕪世間里,我們總是在行走,總是在離別,總是在習(xí)慣身邊的人來(lái)人往、好聚好散,惟只一句“舍不得你”讓人淚流滿面、唏噓不已。
整個(gè)夏天福州跟重慶氣溫都很高,但重慶是在蒸籠里悶著,福州則是在鍋蓋上熱著,不時(shí)有海風(fēng)吹來(lái),碧空如洗,沒(méi)有半點(diǎn)云。
我媽在老家的天臺(tái)上曬衣服,陽(yáng)光明晃晃的,刺到眼睛里,她打了個(gè)噴嚏,突然想起身處?kù)F都的我應(yīng)該沒(méi)見(jiàn)過(guò)這么好的天。我媽不由地便拿起手機(jī)給我打電話,問(wèn)我在重慶過(guò)的好嗎,是不是辣慘了,吃火鍋的時(shí)候有沒(méi)有想到她?我一邊接電話,一邊看著一道道母性的光輝踏過(guò)千山萬(wàn)水正照耀著自己。之后我媽便跟我聊起她最近想學(xué)隔壁陳婆婆那樣買份保險(xiǎn),說(shuō)等哪一天自己離開(kāi)了,起碼還能留下點(diǎn)什么給我和我爸。
我突然間沉默了,發(fā)現(xiàn)我媽真的老了,我的心像被人重重打了一下。
我媽見(jiàn)電話那頭許久沒(méi)有動(dòng)靜,便有些后悔自己剛剛說(shuō)的話,急忙補(bǔ)了一句“我也只是隨口說(shuō)說(shuō),你在學(xué)校好好念書(shū)別多想,啊?”我在電話這頭半晌才應(yīng)了一聲“嗯”,之后沒(méi)說(shuō)一句話,只聽(tīng)見(jiàn)她又在電話里叨叨著:“昨天看天氣預(yù)報(bào),重慶又升溫了,你自己注意防暑,飯多吃點(diǎn),不要怕多花錢,我和你爸……”
媽媽,已經(jīng)二十歲的我特別想像小時(shí)候那樣矯情地喊你一聲。
你是個(gè)大美人。
不準(zhǔn)你老去,不準(zhǔn)你離開(kāi)。摘自《親愛(ài)的,我們都將這樣長(zhǎng)大》
我們歷來(lái)缺少形而上意義上的信仰,只有社會(huì)倫理和社會(huì)政治意義上的信仰,不是尋求人生與某種永恒神圣本體的溝通,而是把人生與一定的社會(huì)理想聯(lián)系起來(lái)。社會(huì)層次上的信仰不但不涉及、而且還限制了對(duì)人生終極根據(jù)的探究,掩蓋了形而上層次上的信仰的欠缺。因此,社會(huì)信仰一旦失去統(tǒng)攝力,形而上信仰的欠缺就暴露出來(lái)了。
現(xiàn)代社會(huì)是一個(gè)娛樂(lè)社會(huì)。隨著工作時(shí)間的縮短和閑暇的增加,現(xiàn)代人把越來(lái)越多的時(shí)間用于娛樂(lè)。所謂娛樂(lè),又無(wú)非是一種用錢買來(lái)、由時(shí)髦產(chǎn)品提供、由廣告逼迫人們享用的東西。如果不包含這些因素,人們便會(huì)覺(jué)得自己不是在娛樂(lè)。在娛樂(lè)中,人們但求無(wú)所用心,徹底放松。花費(fèi)昂貴和無(wú)所用心成了衡量娛樂(lè)之品級(jí)的尺度,進(jìn)而又成了衡量生活質(zhì)量的尺度。如果一個(gè)人把許多時(shí)間耗在豪華的俱樂(lè)部或度假村里,他就會(huì)被承認(rèn)是一個(gè)體面人士。
在閑暇時(shí)間越來(lái)越多、甚至超過(guò)了工作時(shí)間的情況下,一個(gè)人的生活質(zhì)量確實(shí)將越來(lái)越取決于他如何消度閑暇,而教育的目標(biāo)也隨之發(fā)生變化。過(guò)去,教育的目標(biāo)是為職業(yè)作準(zhǔn)備。現(xiàn)在,教育應(yīng)該為人們能夠有意義地利用閑暇時(shí)間作準(zhǔn)備。也就是說(shuō),應(yīng)該使人們有能力在閑暇時(shí)間過(guò)一種有頭腦的生活,而不是無(wú)所用心的生活。用這個(gè)標(biāo)準(zhǔn)衡量,我們發(fā)現(xiàn)上述所謂的體面人士原來(lái)是受教育程度太低的產(chǎn)物。
今天我們最缺的不是偉大的理論,而是普通的常識(shí),不是高超的信仰,而是基本的良知。所以,在我看來(lái),最緊要的事情不是制造理論和奢談信仰,而是恢復(fù)常識(shí)和良知。
一個(gè)人倘若能夠堅(jiān)持常識(shí)和良知,只說(shuō)自己心里真實(shí)的想法,不跟著別人胡說(shuō)八道,也不口是心非,他就可以算是半個(gè)智者了。另外半個(gè),則要看他有沒(méi)有天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