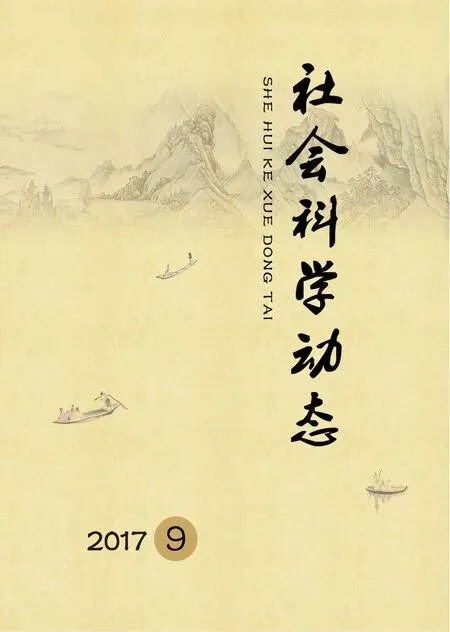談談關于董仲舒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周桂鈿
談談關于董仲舒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周桂鈿
哲學研究方法很多,首先要不迷信權威,不隨眾;其次,要全面掌握資料,對資料要作精當解讀。要了解古人用語習慣,避免用西方觀念誤解和現代觀念曲解古文;復次,要了解人物之間和事件之間的相互聯系,認識人物和事件的發展變化。總之,為了做到實事求是,需要運用唯物的和辯證的方法。
董仲舒;《春秋繁露》;獨尊儒術;方法論
在多年對董仲舒的研究和閱讀研究董仲舒的著作和文章的過程中,我發現了一些值得探討的方法論問題。
一、事實求是地對待史料
《史記·儒林列傳》的最后是董仲舒傳,沒有記載董仲舒生卒之年,需要研究者探討。清代學者蘇輿著有《春秋繁露義證》,有較高水平。因此,蘇輿就被學界視為董仲舒研究權威。其書前有董子年表,將董子生年系于漢文帝元年,卒年在漢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年,董子壽至75。這個權威結論在上個世紀出版的中國哲學史教材中廣泛引用,許多論文也以此為定論。但是,班固說他“親見四世”,從漢文帝到漢武帝只有三世(文、景、武),四世應上推至惠帝。這是簡單的錯誤,因為收集資料不全,以致以訛傳訛,錯誤流傳多年,得不到糾正。
桓譚說董仲舒“年至六十余,不窺園中菜”,這句話對于確定董仲舒生年是極其重要的資料。“不窺園”發生在特殊時期,即董仲舒對策之前的準備階段。按桓譚說法,“年至六十余”,約為61歲,3年埋頭研究,對策時約為64歲。而對策時間,按班固《漢書》的說法在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年。上推64年,即公元前198年,高祖九年,那么,董仲舒在漢惠帝元年時才3歲,能不能說他也“見”了劉邦這一世呢?
董仲舒將《春秋》十二世分為三個階段:“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孔子“見三世”是哀公、定公、昭公,從昭公元年到春秋結束,一共61年,孔子壽至73歲,有12年生活在昭公之前的襄公時代,為什么不能算又見了一世?大概漢人的習慣,小孩不知世事,不算見了世面。孔子12歲之前不算見了世面,董仲舒3歲之前也不能算見世面。桓譚說的“六十余”,即使從61擴大到65,也不會達到見世面的年齡。有的學者不愿意引用桓譚的說法,也不對“三年不窺園”的特殊時期作出探討,甚至還將董子生于公元前179年這種低級錯誤當作一回事。而有的學者則斷章取義以桓譚之說確定董仲舒“壽至六十多歲”。這都不是做學問的嚴謹態度。實事求是,是學術研究的生命線,為了求真,要搜集全面的資料,進行聯系、分析,作出有根據的合理的解釋。不肯下苦功夫,只憑小聰明,是找不到真理的。
二、正確理解古文本意
這里就講一個關于數字的用法。例如三字,有時就有多數的意思,如“再三”就不一定只有三次。董子說孔子“見三世”就是三世。但孔子說自己15歲開始知道學習,以后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隨心所欲不逾矩”,為什么他都在整數的年齡才有一變化呢?怎么會那么湊巧呢?值得懷疑。古代還有“二十曰弱冠”,“七十懸車致仕”的說法,即20歲舉行冠禮,70歲退休。從古代許多記載來看,不是一到70歲就退休的,與董仲舒同時代的公孫弘一直到80歲才死于丞相任上。關于“二十曰弱冠”,班固對自己23歲、27歲,都稱為“弱冠”,如說“弱冠而孤”,其父死時,他23歲成為孤兒。唐代經學家孔穎達說,從20至29通稱弱冠。大概唐代就有人以為20就是整20,所以他才會給予明確糾正。
三、對古代范疇要具體分析
董仲舒講天有十端,包括天、地、陰、陽、金、木、水、火、土、人。前一個天,代表整個宇宙,后一個天,只是與地對應的天,包含日月星辰。在一句話中的兩個“天”,內涵與外延均不相同。漢代有“天有五號”說,也是從不同意義上講天。漢代還有科學研究的物質的天,比如蓋天說的如車蓋的天,渾天說的如雞蛋殼的天。董仲舒講天基本上沒有涉及這類天。
董仲舒講天人感應,從來沒說天有什么具體形象。天也不說話,只是會賞善罰惡,會用自然現象來表達意愿,表明好惡。自然災害,就是天對當政者行為不當的譴告。當政者施行德治,就出現表明吉祥的瑞物,這是天的高興的表達。有的人說,董仲舒講天人感應是為了欺騙老百姓,為鞏固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制度服務。而事實上董仲舒在對策中首先提出天人感應,是由于漢武帝在策問中問到這個問題。董仲舒借此提出上天賞善罰惡,意思是只要堅持行善,就不必擔心,主動權在于自己。這是從政治上考慮,讓漢武帝有敬畏之心,不像秦王那樣無法無天,無所畏懼,折騰人民,導致國破家亡。漢武帝明確表示,對策只有自己一個人看,“朕將親覽焉”,其他官員都看不到,百姓更無從知曉。如果說欺騙,那只騙漢武帝一人。欺騙人民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四、如何理解和評價形而上學?
董仲舒說“天不變道亦不變”。天這個概念很復雜,其中有一意義是指整個宇宙。道也是復雜概念,有一意義相當于現代所謂規律。宇宙是不變的,規律也是不變的。如果這樣理解,這句話并無不妥。
關于形而上學。形而下是具體事物,如一塊石頭、一棵樹,都是變化著的。形而上即抽象的東西,如好與壞、善與惡、一加二等于三,兩條平行線不相交等。這些都是不變的,在日常生活中都是正確的。天與道如果在抽象的意義上說,認為是不變的,也是無可厚非的。西漢時代,董仲舒的辯證法思想是很豐富的,相當杰出的,因為說一句天不變的話就定為形而上學,并且將形而上學列入錯誤范疇,實在不妥。
五、何謂先進文化代表?
多年來,經常講先進生產力代表,先進文化代表,但許多人并不了解其中真諦,只是當作口號、口頭禪加以引用。一種社會制度適合當時當地的社會實際,又能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種社會制度就是先進制度,創立這種制度的階級,就是先進階級,即先進生產力代表。為這種制度,為這個階級服務的文化,就是先進文化代表。
在私有制的條件下,地主階級創造了封建制度,與奴隸制度相比有巨大的進步意義。在封建制度下,農民與地主是被統治與統治的矛盾關系,這個關系是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在封建社會初期、前期,統一大于對立,雙方相互依存的成分更多一些。在地主階級衰落以后,統一性逐漸減少,對立性逐漸增加。農民起來要推翻地主政權時,農民視地主為敵對階級。共產黨革命之初,也表達了這種感情,認為與地主的對立、斗爭是絕對的,統一是相對的。之后在理論上講到農民與地主的矛盾時,連相對的統一也不講了,而且將地主階級歸入從來就是本質上壞透了的一群人。這種說法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幾乎成了社會共識。于是建立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制度的封建地主就是反動階級。西漢當政者就是這種階級,董仲舒學說就是為這種階級服務的,因此就成了反動思想家。但是,如果按馬克思主義理論來分析,在兩千多年前的中國西漢時代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制度,在當時世界上是最先進的制度,當時整個歐洲還都處在奴隸制社會。董學為這樣的制度服務,應該是先進文化的代表。沒有歷史觀念,一切以現代為標準,對歷史都作出否定的評價,這就導致歷史虛無主義。習近平提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發展而來的。中國悠久歷史沒有中斷過,積累了豐富的人生智慧,特別是政治智慧。中國這么大,人口眾多,民族復雜,能維持統一大國的局面,這正是政治智慧的體現。而歐洲只有五億人口,卻分成幾十個國家,統一不起來。歐洲的封建社會只維持了幾百年就崩潰了,中國則維持了數千年,這也是中國政治智慧的高明之處。這一切都有中國古代政治哲學家的貢獻。董仲舒就是其中杰出者。他提出大一統論、天人感應說、獨尊儒術、調均思想都對中華民族延續和發展,起過重要的作用。
六、關于獨尊儒術
董仲舒沒有說過“獨尊儒術”這句話,但在《舉賢良對策》的最后確實講了“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即除了孔子之術都要罷黜,勿使并進。這里當然包含“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意思,因此后代學者稱董子有此建議,并非沒有根據。但是,這個問題最為復雜,需要較大篇幅進行討論。
20世紀,有些學者對此提出各種不同見解。有的說這種理論太偏激,只要儒家,消滅其他各家。實際上,這種理解不合原意,也不符合歷史事實。“獨尊”并非僅存,“罷黜”亦非消滅。“獨尊儒術”之前,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所列六家有名家、墨家、陰陽家、法家、儒家和道家。各家都有合理成分,也都有不足之處,只有道家綜合各家長處,又能應變,所以沒有不足之處。說明漢初“獨尊”道家。經過一百多年“獨尊儒術”以后,到班固撰寫《漢書·藝文志》時,“罷黜”了一百多年的名家、墨家、陰陽家、法家、道家都存在,一個不少,還增加許多家,如縱橫家、農家、兵家、醫方家、雜家、小說家、天文、方技等等。所以可以肯定的是,獨尊儒術并不消滅其他學派。事實上,儒術獨尊了兩千多年,這許多家都存在,而且有很大的發展。任繼愈先生曾告訴我:“獨尊實在太高明了!”我完全同意他的評價。獨尊儒術對于中華民族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各派學說各有優劣,但不是平等的,有高低之分,有尊卑之別。水平雖低,只要有合理性,就不會被消滅,因為社會需要它。例如在用人上,漢武帝不是只用儒家,也用一兩個道家、縱橫家。雖然多為儒家就是獨尊的表現但將“獨尊”作絕對化理解是不適當的。
又有學者根據漢宣帝一句話,即漢成立以來,一直實行“霸王道雜之”(《漢書·元帝紀》),認為漢從劉邦以來,當然包括漢武帝時代都既有儒家的王道,也有法家的霸道,說明并非“獨尊儒術”。然而事實上所謂儒法對立,是文革中講儒法斗爭的遺跡。在春秋戰國時代,百家殊方,儒法當然也有爭鳴,但他們并非勢不兩立、絕對互斥的。管仲、子產都是著名的法家。《論語》記載了孔子對管仲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左傳》中記載子產,孔子說別人再說子產不好,我都不相信。子產認為治國理政要從嚴,孔子也從中得出“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的體會,還稱子產是“古之遺愛”。儒家還認為“圣人不能無法以治國”。孟子明確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只有善良意志做政治是不夠的;只有法,它不能自己去施行,必須有人去施行。這人道德不好,就會貪贓枉法。這說明法律與道德都是治國理政不可或缺的。因此,董仲舒認為德教為主,刑罰為輔才是最合適的。荀子認為,治國最高是王道,其次是霸道。說明霸道不是法家的專利,儒家在一些情況下,做不到王道,可以求其次,行霸道。
《史記》分紀、世家、傳三級,天子上本紀,諸侯屬世家,其它官員入列傳。孔子不是諸侯,卻有《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入《列傳》,孔子后學還有一個專門的《儒林列傳》,只有儒家有此特殊情況,老子沒有入世家,墨子弟子沒有列傳,也沒《道林列傳》 《墨林列傳》。如果不是獨尊儒術,司馬遷就不會這樣處理了。
七、關于董仲舒的歷史地位
董仲舒在西漢有特殊地位。班固說他“為群儒首”,“為儒者宗”。王充說:“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漢武帝經過董仲舒墓前,下馬步行,那里后世稱為“下馬陵”。可見漢武帝對于董仲舒的尊崇。
有人根據董仲舒對策以后,漢武帝留公孫弘在身邊,直至80歲死于任上,而沒有留董仲舒在身邊,反使其遠離京師,任江都相,后又任膠西相,認為董子沒有像公孫弘那樣得到漢武帝的親近。但從后來的事實來看,先是遭主父偃陷害,董子入獄得到漢武帝赦免;退休后漢武帝又派人請教祭祀的事;最后,又有下馬陵之傳說。相比之下,公孫弘當時很紅,成為士人楷模,死以后影響卻不及董子。這是什么原因呢?值得探討。
公孫弘在朝廷上很適應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當皇帝遇到難題,召集群臣議論時,公孫弘總是會想出幾種對策,又能詳細分析各種方案的利與弊,由皇帝權衡選擇。漢武帝對這樣的大臣很感興趣,留在身邊,好相處。公孫弘也因此得到寵幸,受到封侯,成為士大夫的楷模。董仲舒則不同,發表的言論,都是自己深思熟慮的觀點,不照辦就違反儒道,讓皇帝沒有自主選擇的余地。董仲舒在身邊,皇帝有不自由、不自在的感覺,因而還是“敬而遠之”好些。兩人作風不同,而有生前榮耀和死后流芳的差別。
還有人提出,董仲舒沒有參加對策,理由是《史記》沒有記載,《漢書》中所記,都是班固編的。如果對策不存在,當然,董仲舒建議“獨尊儒術”和漢武帝實行“獨尊儒術”也就成為子虛烏有了。有人就將“獨尊儒術”的時間往后推遲幾十年。于是,文、景、武時代的盛世就與儒學無關。漢元帝才開始“獨尊儒術”,而西漢開始走向衰敗。這樣一來,儒學在盛世無功,衰世有罪的結論就可以成立了,批孔批儒就可以理直氣壯了。
沙灘雖然可以建起高塔,但不穩固。歷史問題即使有嚴密的推論,作為根據的史料如果不確實,就不可能有穩固的結論。關于董仲舒的資料,在《史記》中只有《儒林列傳》的最后,記了數百字。而在《漢書》中則單獨立傳,糾正了董仲舒弟子名字的錯誤,抄錄了正確的內容,最大差別是全文錄入了漢武帝三個策問與董仲舒的三個對策,使董仲舒傳從數百字擴大為數千字。如果董仲舒對策是班固編的,那么,漢武帝的策問也是編的。但班固曾因私撰史書差點殺頭,他怎么敢胡編漢武帝的策問?中國寫史,特別重視真實性,尤其有關皇帝的史實,怎敢亂寫?司馬遷對董仲舒思想的認識受到時代的局限,只知道他對《春秋》的解讀最高明。而經過一百多年的考驗,董學的影響巨大。因此,班固將三策全文錄入《漢書》。當時也存在厚古薄今的問題,對司馬遷來說,董子為同時代的今人,對班固來說,董子已是一百多年前的古人。在其弟子、后學的努力下,董子影響日增。在《鹽鐵論》中,在許慎《說文解字》中,在讖緯中都出現董仲舒的名字,都能說明問題。“為群儒首”、“為儒者宗”正確反映了他的社會影響。
八、關于董仲舒著作的真偽
在疑古盛行的時代,似乎懷疑一本古籍的真實性就是重大學術成果。至今還盛行的偽古文尚書,偽《列子》就是顯例。疑古風也刮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理由很簡單,漢代并沒有《春秋繁露》這本書名。在《漢書·藝文志》中只有《董仲舒書》。同樣情況,漢代沒有司馬遷《史記》這本書名,(有一《史記》是魯國史書,是孔子寫《春秋》的底本,也叫未改《春秋》。) 只有《太史公書》。如果不能否定《史記》是司馬遷的著作,當然也不好否定《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著作。
《史記》稱董仲舒重點研究《春秋》,《漢書》列董仲舒著作的篇名有《蕃露》 《玉杯》 《聞舉》《清明》 《竹林》等。可能有這種情況:全書解說《春秋》之得失,因以《春秋》為篇名,第一篇為《蕃露》,后人以為書名為《春秋蕃露》,這樣第一篇有內容無篇名,就取篇首“楚莊王”為篇名。這只是假設,未成定論,不敢徑改。
有人提出《春秋繁露》中有九篇題“五行”的篇目,后七篇與前二篇思想不一致,因此認為后七篇是后人偽造的。前二篇與后七篇為什么不聯在一起,可能由于寫作的時間有前后不同,而且相隔較久。如果這個假設成立,那么,因為相隔時間長,思想有了變化,文字不那么一致,就是很自然的事。以前有一些學者對一些古籍發現不一致現象,就以為有假,結果多有誤判。如胡適讀《論衡》就有這類誤判。古代許多人一輩子只寫一本書,幾十年中思想會有許多變化,各種說法可能與當時語境還有關系,怎么能完全一致?
我以為,對于古籍要特別尊重,沒有充分的根據,輕易不能改動,對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我認為都是可信的研究資料,采取懷疑、改動,都是沒有充分根據的。
(責任編輯 胡 靜)
B234.5
A
1003-854X(2017)09-0021-04
周桂鈿,北京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