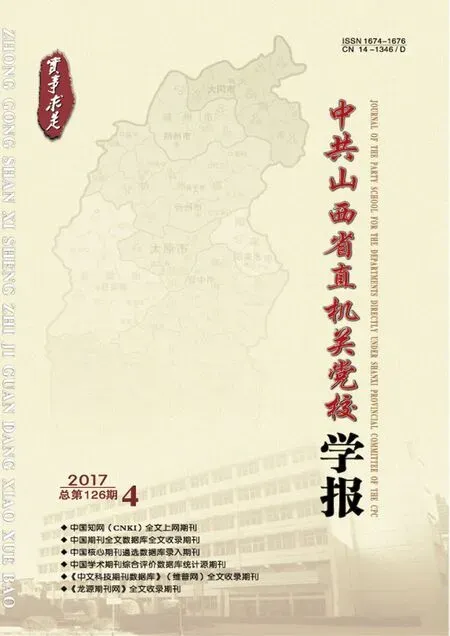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開展反腐敗斗爭的歷史經驗
劉清華 熊玉先
(中央財經大學,北京 100081)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開展反腐敗斗爭的歷史經驗
劉清華 熊玉先
(中央財經大學,北京 100081)
新中國建立之初,由于封建思想的歷史慣性、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以及一些黨員領導干部角色轉變不及時等原因,中國共產黨內部出現了一些消極腐敗現象。但剛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迅速采取了有力的應對措施,并積累了一些反腐經驗:黨中央旗幟鮮明高壓反腐,對腐敗分子形成震懾;充分發揮各種監督主體的合力作用,讓腐敗分子無處藏身;加強思想道德教育,提高領導干部拒腐防變能力,從而為執政黨建設和現代化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反腐敗;領導干部;建國初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剛剛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一方面面臨著國民黨留下的千瘡百孔的國家混亂局面需要建設,同時還面臨著共產黨內部一些領導干部的貪污腐敗問題。當時出現這些貪污腐敗問題的主要根源包括:黨員領導干部角色轉變不及時,“許多地下干部來不及思想準備與政策教育,來不及糾正嚴重的無組織無紀律的脫離群眾的游擊作風”;[1]黨員人數激增,教育不及時造成良莠不齊;社會意識的滯后性,封建腐朽思想依然在起作用;官僚主義的興起和資產階級的侵蝕。中國共產黨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加以應對,為此后的執政黨建設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一、黨中央旗幟鮮明高壓反腐,對腐敗分子形成震懾
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是取得反腐敗勝利的可靠保障。在建國初期,毛澤東堅持強硬反腐的態度促進反腐敗工作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他指出:一切貪污行為必須揭發,按其情節輕重,給以程度不等的處理,從警告、調職、撤職、開除黨籍、判處各種徒刑,直至槍決。典型的貪污犯,必須動員群眾進行公審,依法治罪。[2]據薄一波回憶,毛澤東“不僅提出方針,而且親自督辦;不僅提出任務,而且交代辦法。在‘三反’運動緊張的日子里,他幾乎每天晚上都要聽取我的匯報,甚至經常坐鎮中紀委,參加辦公室會議,親自指點。有毛主席的親自直接指導、督促和撐腰,我們的工作也就好做了,而且做得很起勁。”[3]反腐的堅定立場不僅昭示著中國共產黨反腐敗的決心,更在全國范圍內起到了很好的教育警示作用,贏得了民心,鞏固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一)嚴懲劉青山、張子善,對高干腐敗絕不姑息
中共中央高度重視黨員隊伍中的腐敗問題。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兩個務必”的重要思想。他告誡即將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千里之堤,潰于蟻穴。如果不及時清除黨內的“蛀蟲”,那么革命先輩用血和生命鑄就的偉大基業很可能一朝崩潰,甚至有亡黨亡國的危險。他明確指出:“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4]但是偏偏有那么一些人,自恃有功,認為完成了革命任務就應享福,他們禁不住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以及來自方方面面的誘惑,淪為國家的罪人。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劉青山、張子善的貪污大案。面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少有的大貪污案件,黨和國家并沒有不知所措,更沒有包庇縱容。1951年12月下旬,華北局通過河北省委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屬部門對劉、張兩犯量刑的意見。結果是:絕大多數人同意判處劉、張二人死刑。黨中央、毛澤東看到上述材料,決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議,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對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處以死刑,立即執行。[3]時任天津市委書記的黃敬,考慮到劉、張二人在戰爭年代確實做出過突出的貢獻,遂向毛澤東求情,希望網開一面。毛澤東的回復耐人尋味,同時又值得深思:“正是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3]面對這些高級干部的腐敗問題,黨和國家并沒有將他們的功勞拿來“做交易”。功是功,過是過。功不能代替過,功當然也不能抵過。任何黨員干部,只要觸犯法律法規,損害人民利益,就要受到相應的制裁。中央下決心槍決劉、張二人的目的,就是對腐敗的高級干部殺一儆百,避免其他黨員干部犯類似的錯誤。
(二)反腐全面展開,成效顯著
劉青山、張子善貪污案件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毛澤東明確指出:必須嚴重地注意干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并須當作一場大斗爭來處理。[5]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轉批了華北局關于劉青山、張子善大貪污案調查處理情況的報告。次日,中共中央就頒布了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此后,反貪污成為中央開展的“三反”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1951年12月8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了《關于三反斗爭必需大張旗鼓進行的電報》,指出“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斗爭一樣的重要”。[2]1952年1月4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了《關于立即抓緊三反斗爭的指示》,指出:“大貪污犯是人民的敵人,他們已經不是我們的同志或朋友,故應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將他們肅清,而不應有絲毫的留戀和同情。”[2]可以說黨和國家解決腐敗問題的措施是及時的、有效的。據統計,全國縣以上黨政機關參加“三反”運動的總人數為383萬多人(為包括軍隊的數字)。經核實,貪污1000萬元(舊幣1萬元等于新幣1元,下同)以上的共10萬余人,貪污的總金額達6萬億元。對有嚴重貪污行為的罪犯,判處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處無期徒刑的67人,判處死刑的42人,判處死緩的9人。[3]
(三)既打“老虎”,也拍“蒼蠅”
中共中央不僅對貪污的“大老虎”進行打擊懲治,形成震懾,而且還對基層存在的“蒼蠅”進行整治,因為基層干部是與人民群眾接觸最多,涉及到群眾直接利益。基層黨員干部行為的好壞直接影響著黨在群眾心目中的形象。“拍蠅”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全國縣級(只含部分縣級)以上單位(不包括軍隊)參加三反運動的總人數約為383.6萬人,共查處貪污分子和犯貪污錯誤的120.3萬人,占參加運動人數的31.4%。其中共產黨員約為19.6萬人,占貪污分子和犯貪污錯誤總人數的16.3%。”[6]
經過黨和國家的不斷努力,建國初期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不減,促使黨的領導干部時刻提醒自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能忘,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不能丟,人民賦予的權力不能濫用,黨在人民心中的光輝形象不能抹黑。
二、發揮多種監督主體的合力,讓腐敗分子無處藏身
監督是防止腐敗和反對腐敗的有效武器。在我國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貪污、浪費、官僚主義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因此,反腐敗必須將全社會的力量動員起來。1956年9月,黨的八大強調,對權力的監督應來自多方面,既要有來自權力主體內部不同層次的監督,又要有來自權力外部的監督。[7]這種全方位的監督理念,在黨的民主監督發展歷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建立專門機構開展黨內監督
建國初期,黨中央已經意識中共執政后某些黨員干部可能出現貪圖享樂不思進取等觀念,因此開始進行防腐敗制度建設,在黨內設立專門機構進行監督。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做出了《關于成立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決定》,成立了以朱德為書記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以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職權是檢查黨的組織、干部黨員是否違反黨紀、黨性,審查并決定其違犯紀律的處分。到1950年底,全國大部分縣以上黨委都建立了紀律檢查委員會。1952年10月,全國專職紀委干部有2800人,到1954年底,發展到7200多人。[8]1955年3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于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的決定》,各級黨委又相繼成立了監察委員會。1956年9月,黨的八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對監察機構的設置、任務、職權和領導體制等都作了明確的規定:黨的各級委員會都設立監察委員會。黨的監察委員會實際上取代了1949年設立的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職能。
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或監察委員會不斷清除藏匿在黨內的變質腐化分子,在“三反”運動中的作用尤為明顯:揭露出大量違反黨規黨紀的案件。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于全黨紀律檢查工作的總結報告中指出,“華北、東北、西南、西北等地區參加‘三反’運動干部及工作人員共3122437人,揭發出貪污分子和有貪污行為者1226984人,……在貪污分子總數中,有黨員202683人,占貪污總人數的16.5%。地方縣委以上干部犯有嚴重錯誤受到行政上撤職、撤職查辦、逮捕法辦的處分者共4029人。從職務上看,其中有省委或相當于省委者25人,占0.62%;地委或相當于地委者576人,占14.3%;縣委或相當于縣委者3428人,占85%”。[9]各級紀委或監察委員會在反腐敗斗爭中的舉措,清除了存在黨員干部中的“蛀蟲”,純潔了黨員干部隊伍,教育了黨員干部,為國家的建設和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二)發揮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
在我國,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各民主黨派是參政黨。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之間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關系。早在1941年,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參政會的演說中就指出:《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上有一條:共產黨員應當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共產黨員必須傾聽黨外人士的意見,給別人以說話的機會”。[10]這樣才可能達到集思廣益、共同協商、不斷進步的目的。各民主黨派可以通過審議人大的提案等對共產黨的工作進行監督,確保國家制定的各項規章政策是真正有利于國家、有利于人民的。鄧小平也主張各黨派的互相監督。1957年,他指出:“有監督比沒有監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共產黨總是從一個角度看問題,民主黨派就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出主意。這樣,反映的問題更多,處理問題會更全面,對下決心會更有利,制定的方針政策會比較恰當,即使發生了問題也比較容易糾正。”[11]中共黨員在全國來說還算是少數的,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還是有一定局限的,必須聯合各民主黨派,充分發揮一切可以發揮的力量,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三)開展廣泛的群眾監督
1945年9月,毛澤東在延安著名的“窯洞對”中回答了黃炎培先生關于如何打破歷史周期率的提問,他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12]領導干部的權力是人民群眾賦予的,是要為人民群眾全心全意服務的,理應受到人民群眾的監督,這是不容置疑的。面對建國初期的腐敗問題,毛澤東指出:“必須開展一個群眾性的民主運動,才能收到最大的效果。”[5]鄧小平也表示:“讓群眾來監督批評,只有好處,沒有壞處。”[11]
建國初期建立的人民檢察通訊員和人民檢舉接待室制度為群眾監督提供了制度保障。1951年9月,政務院發布《各級人民政府人民監察委員會設置監察通訊員試行通則》,各地相繼設置通訊員,接受群眾的監督和意見、建議。1952年8月,政務院發布《關于加強人民監察通訊員和人民檢舉接待室的指示》,將群眾的監督行為制度化。1954年中央紀委通過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于處理控告、申訴案件的若干規定》明確規定了黨員或群眾向黨控告申訴案件的范圍、原則及結案的手續等問題,確保了廣大人民群眾對黨員干部進行監督的合法性,提高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對反腐敗斗爭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據原松江省(1954年后并入黑龍江)調查,1953年共接受人民來信來訪1251件,較1952年增加了6倍多。僅從1951年12月至1952年1月,據政府系統18個單位初步統計,就有823人參加檢舉;被檢舉的人數,根據20個單位不完全統計,有322人。又據軍委后勤系統的初步統計,參加檢舉者566人,被檢舉者37人。[13]當然,人民群眾反對貪污腐敗的運動必須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就是“要把群眾運動約束于政府法令之內,亦即約束于統一戰線范圍之內”[11]。
此外,建國初期還采用了人大監督和輿論監督等不同的監督形式。人大和輿論的監督對當時正在進行的反腐敗斗爭,也起到了很好的協調和輔助作用。
三、加強思想道德教育以提高黨員干部拒腐防變能力
思想道德制約權力能夠從源頭上遏制腐敗。從行為邏輯看,一切腐敗行為都是從背離道德開始的,道德腐化是權力主體走向腐敗深淵的第一步。[14]道德制約權力的要義就在于,“培養政府官員內心的道德力量,增強他們抵御外部不良誘惑的能力,從而減少濫用權力的可能性,即通過制約靈魂而制約行動”。[15]毛澤東黨建思想的突出特點就是特別重視思想道德教育。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依靠思想道德教育將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共產黨改造成為具有共產主義信仰的無私的先進政黨。建國以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執政黨建設中依然重視對黨員群眾的思想道德教育,為抵御各種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腐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一)通過思想道德教育,不斷提高領導干部的黨性修養
黨性是共產黨員的立身之本,沒有黨性的人是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的。黨員要不斷加強黨性修養,這是黨保持先進性、不斷走向成功的重要歷史經驗。這個經驗我們必須堅持。針對部分黨員干部的黨性缺失現象,要通過加強黨性教育和道德修養,不斷提高黨員干部的思想道德覺悟,抵制腐化思想的侵蝕。1939年7月,劉少奇在延安所做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報告中指出:“共產黨員應該具有人類最偉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確堅定的黨的、無產階級的立場(即黨性、階級性)。”[16]也就是說,共產黨員要做到真正大公無私,沒有離開黨而獨立的個人目的和私人打算。1941年11月,毛澤東指出:“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10]1957年,毛澤東在濟南黨員干部會議上指出,共產黨“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17]要不斷強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黨員干部尤其是黨的高級領導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視、愈要身體力行共產主義道德。要見賢思齊,學習白求恩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張思德為人民服務的奉獻精神等。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黨員干部要主動進行自我教育,不斷提高自身的道德素養,用自己的言行去影響和教化別人。
(二)開展反腐倡廉教育,治病救人
中國共產黨在嚴懲劉青山、張子善等貪污犯的同時,也注意通過開展反腐倡廉教育活動向其他黨員干部敲響警鐘。黨的八大指出:“對于犯錯誤的同志給以嚴厲的處罰,以至把他們驅逐出黨,這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沒有解決為什么造成錯誤的思想問題,那末,嚴厲的處罰不但不能保證不再重犯同樣的錯誤,甚至還會造成更大的錯誤”。[18]因此,一定要弄明白、搞清楚出現貪污腐敗的思想原因,在此基礎上,加大對黨員干部的反腐警示教育。北京人民廣播電臺播放了河北省人民法院公審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大會實況錄音,對一些思想意識不堅定的黨員干部起了警示教育作用,挽救了一批黨員干部。1986年,鄧小平曾對此次通過“殺一儆百”教育廣大干部群眾的做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說:“一九五二年殺了兩個人,一個是劉青山,一個是張子善,起了很大的作用”。[19]此后半個多世紀,人們只要提起殺劉青山、張子善這件事,依然記憶猶新,引以為戒。
要把反腐倡廉教育活動納入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活動中去,面向全黨全社會進行反腐倡廉教育,擴大其影響力,增強教育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使教育內容貼近黨員干部的思想和實際,將反腐倡廉教育同職業道德、社會公德等教育相結合,增強反腐倡廉的自覺性,讓貪污腐化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于心中。教育的訓導性質,使它成為控制腐敗的一個重要手段,教育可以在官員內心深處形成約束自身行為的內在力量。[20]同時,只有建立起反腐倡廉教育的長效機制,才能筑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道德防線,才能真正從不敢腐、不能腐發展為不想腐的良好政治生態環境。
(三)時刻不忘艱苦奮斗的政治本色
無論在戰爭年代還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為了抵制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防止黨員干部的貪污腐化,毛澤東都特別強調黨員干部要時刻謹記艱苦奮斗的作風。他認為,黨員干部要時刻銘記艱苦奮斗的政治本色,不要因為權力變大,生活水平提高,就忘記艱苦奮斗的歷史,就開始放任自己貪污腐化。1929年,毛澤東針對紅軍內出現的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進行了嚴厲地批評,指出紅軍中存在一些不愿意在艱難環境中吃苦奮斗的人,“他們總是希望隊伍開到大城市去。他們要到大城市不是為了去工作,而是為了享樂。”[21]“艱難困苦,玉汝于成”,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不斷壯大,不斷取得勝利,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一個沒有艱苦奮斗精神作支撐的政黨,是難以興旺發達的。[22]1949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明確提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4]在黨員干部的教育活動中,要不斷加強有關艱苦奮斗方面的教育,不要忘卻革命先烈奮斗的血淚史,更不能忘懷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他們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作為黨員干部不應該用貪污腐化的形式踐踏前人的勝利果實,這是要被人民所唾棄,被后人所不恥的。
總之,從黨的建設和國家建設的角度看,建國初期的中國正處于社會發展的轉型時期,當時出現了各種貪污腐敗現象。當今中國也處于社會轉型期。在“社會轉型時期要更加注意腐敗現象的滋生和蔓延”。[23]反腐敗斗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一環,它的成功與否直接關系著我國是否出現政治領域的“山清水秀”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建國初期黨采取的種種反腐敗措施取得了明顯的效果,這些反腐經驗對于今天正在進行的反腐敗斗爭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毛澤東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4]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6]孫瑞鳶.三反五反運動[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1.
[7]張晞海.民主監督——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6.
[8]黃寶玖.新中國反腐倡廉建設歷程[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
[9]李雪勤.探索與輝煌: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工作及其基本經驗[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
[10]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鄧小平文選: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黃炎培.八十年來[M].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
[13]黃寶玖.新中國反腐倡廉建設歷程[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
[14]陳國權,等.權力制約監督論[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
[15]侯建.三種權力制約機制及其比較[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3).
[16]劉少奇選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7]毛澤東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8]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19]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0]馬海軍.轉型期中國腐敗問題比較研究[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7.
[21]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2]張希賢.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研究[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23]王順生,李軍.“三反”運動研究[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
責任編輯:張明明
K27
A
1674-1676(2017)04-0104-05
北京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民主集中制重要論述和實踐要求研究”(16KDA007)。
劉清華(1989-),河北保定市人,中央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黨內監督問題研究。
熊玉先(1979-),男,貴州黃平人,中央財經大學在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黨內民主問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