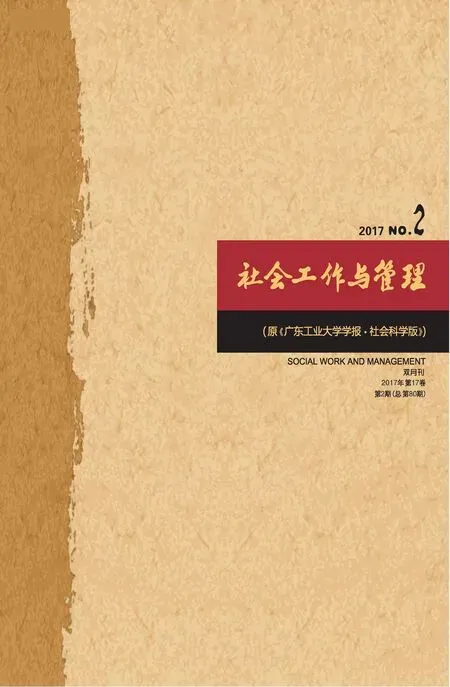化解社區治理中個體化困境的有效途徑
李 斌,王鎰霏
(中南大學社會學系,湖南 長沙,410083)
化解社區治理中個體化困境的有效途徑
李 斌,王鎰霏
(中南大學社會學系,湖南 長沙,410083)
隨著新型城鎮化的加速,居民的流動性加快,城鄉社區居住空間變動迅速。社區內部居民之間的陌生感難以化解,居民個體化引發的困境日益突出。現有的社區組織(如居委會、社會組織、社會工作機構)大多沒有認識到以居民之間團結互助為基礎的組織化過程的重要性。為化解個體化困境,有效應對即將來臨的高齡化浪潮,社區社會組織機構需要著力實施社區居民組織化工程,構建以“助人助他”為理念,組織形式上類似于銀行“存儲—支付”體系的“跨時空服務提供—跨時空服務提取式的服務傳導”式的服務組織體系。在這一組織化建設過程中,社會工作尤其需要在既有提供專業社會服務與角色的基礎上,成為建構跨時空服務傳遞網絡系統的主體。
個體化困境;助人助他;組織化;社會工作;服務銀行
一、社區治理面臨組織化不足困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社區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首先,城市社區的地理形態發生大規模變遷。因城市宏大規劃而引發的社區重組、更生、消失的現象幾乎每天都在發生。其次,從社區性質上分析,絕大多數單位制社區已逐步演變為商品房社區。經濟邏輯已經成為社區內居民普遍認同的行為邏輯。再次,從社會分層維度看,居住空間階層化趨勢明顯,即同一階層的居民居住在同一社區,不同階層的居民居住在不同社區。[1]最后,社區內居民的流動性增加,住房易手頻率加快,鄰居之間的穩定性減少。于是,社區內住房與“人”的關系變得復雜:有人居住自己的房子(獨立產權、小產權、集體產權),有人承租他人的住房(直接承租、間接承租)。上述現象從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共同加速社區內居民的原子化與碎片化,削減或肢解社區內居民之間的直接聯系與時間上的持續性關系。
化解上述困境的有效手段是構建以社區居民為主體的現代社會組織,讓社區組織的持久性存在給社區居民以期待與信心。因為社區組織可以“聚合社區資源,是提高社區治理的手段,增進社區社會資本的基本途徑,是包容性城市建設的起點”。[2]城鄉基層社區一直或多或少有一些組織:有正式的社區組織,如居委會;也有滿足居民相關利益需求的社會組織,如業主委員會;還有發揮居民業余興趣愛好的群眾性團體,如老年協會、婦女廣場舞協會。近年來,應社會管理創新要求,社會工作機構也逐步進入社區,為社區居民提供專業支持。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上述組織機構以及群眾團體似乎很難抑制居民原子化、碎片化趨勢。原因有三點。
1. 居委會未承擔居民群體化、組織化的職責與任務
作為社區組織機構的居委會,其工作范圍主要設定在執行黨和政府的各項法規政令指示、社區黨支部工作、衛生、綠化工作、治安保衛工作、計劃生育工作、民政工作、司法調解工作、統戰工作、婦聯工作、少兒教育工作等。上述這些工作基本沒有設置“居民組織化”任務。與滕尼斯意義上的社區包含眾多內容尤其強調社會關系及其建構不同[3],在中國城市的行政層面,社區“被設定為我國城市政府為了實現城市區域小型化、管理對象清晰化的目標做出的管理體制選擇”[4]。社區成為城市最小行政區劃,最小“網格”①。這樣的網格管理機構沒有被賦予相應職責關注社區居民之間的聯系,以及居民之間友好關系的建設,更談不上承擔居民組織化職責了。這可以從社區的《社區自治章程》關于社區機構設置職責的規定中得到說明②。在實地調查中筆者發現,各居委會或社區組織工作人員的工作任務大致包括3點:(1)下達上級政府的相關指令,完成政府要求的各項惠民政策,上傳本社區政府需要的相關信息;(2)完善本社區物理空間。如解決社區混亂,基礎設施不配套,專業物業管理要么欠缺要么變動太快,公共活動場所缺乏,環境惡化等問題;(3)應對逐步顯現的難題。如社區居民流動快,人員構成復雜,社會治安差,老年人增加迅速,下崗人員多,困難人員多等難題。
2. 社會組織不承擔組織社區居民的職責
在中國行政語境中,社會組織是指在不同級別的民政部門登記注冊的非營利組織。法理上,社會組織并不承擔組織社區居民的職責。在走訪民政部門發現,類似于志愿者服務、文化傳播、殘疾人服務、青少年培訓等方面的組織比較容易獲得注冊,注冊了的社會組織在社區建設方面發揮了一些作用,如調解糾紛、社區巡邏、構建文化、居民自治、和諧督導(拍攝一些不文明行為),發動居民參與社區活動(舞蹈隊),使一些癌癥病患者娛樂身心,把病人從床上拉起來,把居民從麻將桌上拉下來,參加有意義的社區活動等。社區之間在社會組織建設與發育上存在極大差異:有些社區有多個社會組織。如長沙市雨花區L社區目前有備案的社會組織7個,其中的“H家園”組織相對突出些,他們走家串戶,給社區居民經濟物質上幫助,開展安撫活動,減少社區居民的失落感。DX社區有登記備案的社會組織8個,他們的服務涉及紅白事幫協、居家養老、紅袖章志愿者、幸福港灣、老人沙龍、舞蹈隊、“四點半課堂”“幫幫團”等。③盡管2000年以后,社會組織發展比較迅速,不過目前還很少有社會組織有意識地將“分散的社區個體重新積聚起來”作為社會組織的主要目標。盡管如此,社區只要有社會組織并且還經常開展活動,其社區粘性度④通常就比較高,居民的滿意度也高。在社會科學語境中,社會組織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社會組織是指人們從事共同活動的所有群體形式,包括氏族、家庭、企業、政府、學校、醫院、社會團體等形式。狹義的社區社會組織是“伴隨著社區功能逐步完善而發展起來的一種新型群眾組織形式,是以社區居民為成員,以社區地域為活動范圍,以滿足社區居民的不同需求為目的,由社區成員自發成立或參與,介于社區個體組織(社區黨組織和社區居委會)和居民個體之間的組織”,[5]因此需要將行政語境的社會組織與社會科學語境的社會組織關聯起來,使其既具有合法性又能夠承擔起組織社區居民的任務。
3. 社會工作尚處于起步階段,不足以承擔組織社區居民的職責
截至2015年底,湖南全省社會工作注冊機構還不足200家,絕大多數偏僻區縣還沒有社工機構。[6]盡管一些接受“三區項目”的縣已經成立有社工機構,不過其專業化程度仍然不高,他們的運行經費來源方式、從業人員結構、業務范圍、工作方法、工作目標都還在摸索之中。⑤與此同時,社會工作專業在大學還沒有成為大學生心儀的專業。目前全國民政部門還是采用權宜之計,依靠轉化本土人才的方式,即督促社區相關工作人員通過考取社會工作資格證的辦法,推進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在湖南省長沙市調查的社區工作人員中,已經有63.1%的人員參加過社會工作資格證考試,其中有21%的人員取得了助理社會工作師(初級)資格,有12.6%的人員取得社會工作師(中級)資格證。⑥另外,就調查所得以及整理現有文獻發現,還沒有一個社會工作項目涉及社區居民組織化,即將社區居民組織起來作為社會工作項目在執行。
綜上所述,目前基層社區建設的“三社”(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力量自身均不夠強大與成熟,其能量還在培育之中。這也許正是“三社”需要聯動的原因。[6-8]因此,要提升社區治理水平需要提升社區組織機構之間以及社區居民之間的聯動水平與組織化程度。
二、社區治理需要以居民互助為組織化邏輯
為了解決城市社區個體化過度而出現的社區居民原子化問題,以社區居民之間的互助性、團結性為核心的“朋友圈”“興趣群”、志愿者、社會組織等群體形式日益被學界重視,一系列相關研究逐步衍生,如形成“社區效力”“社區能力”“社區粘性”等概念,并迅速成為社區治理研究領域的熱詞。盡管這些概念均指向積極的社區治理,不過其內涵有各自的獨特性。“社區能力”可以綜合反映社區居民之間的組織性程度。[9]它由“利益相關者參與社區的能力、評估問題的能力、培育社區領袖的能力、建立或改進組織結構的能力、調動資源的能力、與其他組織和居民建立關系的能力、批判性自省能力、項目戰略管理能力以及聯結外部機構的能力”構成。[10]“社區粘性”則是指社區居民對所在的社區有歸屬感、依戀感,社區對居民有吸引力,居民以居住為核心的相關權益能夠在社區層面得到保護,權利得到尊重與滿足,居民的困境在社區層面可以有效解決,如居民的就醫、兒童照看、高齡照護、殘疾幫扶等需求能夠在社區層面解決。很自然,社區能力、社區效力或社區粘性等的提升是一個綜合性工程,不僅需要現有的基層社區組織、社區社會組織以及快速發展的社會工作機構參與,更需要社區居民的主動參與和付出。因此,社區層面的多方聯動(或稱“四社聯動”)可能是社區層面服務提供與獲得的組織性維持的有效策略。多位學者的社區組織化建設實驗,比如李強的北京清河實驗、沈原的北京大柵欄實驗、羅家德的上海嘉定實驗、王春光的江蘇太倉實驗、楊團的山西寨子村實驗、蔡禾的廣東西部鄉賢會實驗、李向前的成都金牛區實驗、李斌在長沙梅溪湖街道的實驗等,正在從多方面探究基層社區的服務組織邏輯以及社區居民的組織化。⑦不過,目前這些實驗碰到的共同問題是城市社區居民的組織化建設非常困難,群體性連結很不容易。居民個體化困境所面臨的嚴重后果還沒有廣泛被社區居民所知曉、理解與警示。于是,以社區居民為主體的服務型組織體系的建構就面臨更多的問題。更為嚴重的是,不少社區還廣泛存在政府不支持甚至不允許社會組織建設,絕大多數社區居民參與服務性組織的積極性不高,已經組建起來的社會組織面臨資源稀少,居民參與群體活動的興趣不高,社區能力的重要性被漠視等問題。大多數居民對即將來臨的困難不做任何準備,抱著“到哪座山,唱哪支歌”的心態。
正因為社會工作以緩解困難、助人自助為己任,加之所踐行的專業化服務,才逐步成為中國政府加強社區治理的有效手段。那么,運用社會工作策略解決社區居民的碎片化問題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其他問題,是依靠培養足夠多的社會工作力量分別單個地為每個社區居民提供個案社會工作服務,還是發動社區居民一起參與到形色各異的社會服務中去,以實現他們內部有組織有計劃地互助以形成“組織”,進而運用他們自己的力量解決問題,構建溫馨的社區呢?我們認為,上述兩方面的工作需要共同推進才會有成效。也就是說,社會工作既要承擔起既有的專業化服務,又要承擔起組織化居民的重任。首先,高校要拓展社會工作人才培養途徑,加大人才培養力度;政府要通過社會工作資格證考試,社會工作實務培訓等形式加速現有相關人才向社會工作轉軌。類似的努力能夠增加社會工作服務量的有效供給。然而完成更多的社會工作服務量,仍然難以抑制因為個體化趨勢而增加的個體“無力”與“無助”感。其次,社會工作需要積極推進另一方面的工作:即提升社區居民的組織性程度,讓每個社區居民隸屬于某個社區互助組織,貢獻自己的資源,同時能夠在自己需要的時候通過社區內互助組織獲取幫助。
社會工作有兩種導向:一是所謂“注重個人困境消除與個人發展”的微觀導向,二為“注重社群團結”的宏觀導向。[11]中國港臺地區及西方國家的主流社會工作以“個人困境免除”導向為主。鑒于中國大陸特定的人文歷史環境與現實要求,有學者主張將上述兩種存在一定張力的導向結合起來,“社會工作必須在實踐中既突出個體位置,又要將塑造個體性作為重建共同體的基礎”。[12]如何既凸顯個體性以符合市場化工具理性邏輯,又能夠構建起有行動能力的社區共同性以抑制孤獨無力感,似乎在理論與現實層面都構成了難題。在社區操作層面,希望達成的狀態是,社區居民的個體私密空間能夠得到尊重與保護,公共空間經由哈貝馬斯式的理性討論[13]后,可以通過居民互助組織建設得到有效構建,進而居民的困難最大程度地在社區層面通過互助組織得以解決。我們認為如果社區社會工作項目圍繞上述目標設計、開發與執行,社會工作就需要以社區的組織化為基準,以將社區居民組織起來形成形色各異的互助組織為工作內容。于是,社會工作機構在建設社區居民互助組織的道路上,就需要在三個方面著力。
第一,踐行“助人助他”的組織化理念。社會工作“助人自助”理念能夠幫助社會工作者在助人的過程“造血”“鏈接與整合資源”,使受助者能夠自力更生,但是它卻局限了社會工作的對象范圍,容易只注意到困難中的個體;另外還在主觀上忽略了案主本身的生產能力,置案主于被動接受的角色。而“助人助他”理念的核心是協助案主提升幫助他人的能力,即社工幫助案主的目的是使案主最終能夠再幫助其他的人,置案主于主動角色地位。換言之,社工A(或社區居民A1)幫助B,當B解除困境后再幫助C,C再幫助D,形成助人鏈條體系,進而實現組織運作,形成人與人之間良好互助關系,建構幸福社會。
第二,實施“跨時空的服務提供與服務提取式傳遞鏈條”的組織形式。與學雷鋒、志愿服務不同,“跨時空服務提供與服務提取式鏈條”這一概念借助中國家庭代際反哺“養兒防老”式服務傳遞關系,即服務提供者不在提供服務后立即獲得回報,而是在若干年以后,或到自己年老后的某個時間段才提取自己所需要的“養老照顧”服務量。為了鼓勵有能力、有時間提供服務的人提供盡可能多的服務,依據等量傳遞服務原則設計,即自己為他人提供的服務越多,自己在步入困境或年老時可以提取的服務也就越多。“純”服務量的傳遞,可以免除貨幣⑧結算過程中因時間遷移出現的通貨膨脹進而導致購買力下降問題,讓復雜社會實現實現簡單應對,讓“以物易物,以服務易服務”成為社區居民組織化的主要邏輯,讓不同時段與空間的服務量可以實現等值交換。⑨
第三,構建“銀行網絡體系”式的社區社工組織體系。為了使“跨時空服務提供與服務提取式鏈條”這一規劃得以廣泛實施,需要組建一個類似于銀行的網絡組織體系。各社區類似的社工服務銀行構建起全國性的服務銀行體系,服務可以在各銀行之間實現轉移,以應對流動性社會帶來的服務流動的時空問題。讓跨時空服務傳遞的運作方式類似于銀行的資金存儲與提取形式得以實現組織化運作。社區居民提供服務及其數量需要在專業社工的培訓、規劃、計劃、檢查與評估過程中精細地進行,社工將符合要求的服務及服務量記入“服務銀行”,[14]并安排相關服務給需要服務的接受者(案主)。對于提供服務的居民來說,其存儲與提取是跨時空的;而對于服務銀行來說,服務的存儲與提取則是同時進行的,作為在服務銀行工作的社會工作者來說,匹配服務的存儲與提取是其主要的工作。具體的操作規則設計會比較復雜,需要另做大量專題研究。舉例說明,如要應對諸如老齡化浪潮帶來的高齡長期照顧問題,可以動員60歲至70歲的低齡老年人為80歲以上的高齡老年人,或為行動不方便的人提供服務,社會工作者記錄其服務量。給服務提供者的回報就是讓他們相信并獲得組織保障,當他們步入高齡或行動不方便時,可以到社會工作系統建設好的分布全國的“服務銀行”提取他們曾經付出過的等量的服務或照顧。服務銀行的運轉經費由國家投入解決。一旦出現在服務量的提供與服務量的提取之間存在不對等情況時,可以動用老年人的資金儲蓄或財產作為補充支出。
上述互助組織的建設與完善,能夠讓服務量在時間的流變過程中保持恒定。這一體系能夠加強居民之間的團結,增加居民的道德行為,有利于社會信任制度的建設,也能夠積極化解個體化困境,增加社區服務所需的人力資源,為應對高齡化社會來臨后的養老及照護等一系列問題開辟新路。
三、結語
現代社會尤其是城市社會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社會。傳統社會的團結方式依賴于長期穩定形成的血緣、地緣關系,人與人之間形成的是“整體性”關系;現代社會以“個體”為特征,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主要通過“交換”或者科層制理性規定而形成,建構的更多是“碎片化”的局部關系。法國社會學家滕尼斯稱前者為“機械團結”,后者為“有機團結”。[15]針對人際關系碎片化變換,現代國家通過諸如行政體系、市場體系、貨幣體系、教育體系、就業體系、安全體系、保障體系等現代社會設置,讓個人從整體意義上脫離于特定群體,游離于差異化明顯的組織、群體,而逐漸淪落成“碎片化漂游”的無力感個體。當空間回歸到“人的‘存在’,一種基于經驗事實的體驗,一種身份認同與情感歸依的生成領域以及實現身份認同、產生自我歸屬感、獲取情感歸依和本體性安全的場所,一種回歸到空間主體的生存的本質性的關注”[16]時,個體的“孤獨”與“無力”感可能會朝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要么迅速演變為群體意識,成為群體性體驗,突然來臨的群體性會使國家結構與社會秩序面臨挑戰;要么個體走向否定自我之路。布魯姆曾指出,“正在發生的無數的聯合行動……這種聯合行動的參與者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處于系統的需要,而是為了參與者的目的”。[17]這意味著,如果整體意義上的社會或社區任由個體性肢解并走向了原子化極端狀態,最終無論哪種進路都會形成毀壞性要素。暫時性空間始終時隱時現:有時真實存在,有時虛無縹緲;有時充滿游戲和競爭,強者意圖維護或強化既有空間秩序,弱者則企圖運用“弱者的武器”盡力變動空間秩序,各種策略和行動不斷被“創造”,而恒久抵御暫時性、個體性困境則需要走組織化途徑。因此,要抑制社區居民的原子化傾向,社區治理就必須以社區居民的組織化為導向,孵化居民互助組織,將居民組織起來,組織居民互相提供服務,用他們自身的力量解決他們自身面臨的困境。服務銀行網絡體系的建構及其內在存儲與支付邏輯就是為了回應上述挑戰而設置的組織化體系。
馬克思和一些當代主流經濟學家大多承認“貨幣是一種社會關系”,是凝匯著人們“集體意向性”的一種制度實在,“一切價值的公分母”“價值的現金化”。然而,正如杰文斯、門格爾、克拉克、馬歇爾等經濟學家所指出的,貨幣值僅僅只指某一時點上以某一時刻所認定的“貨幣標量”為多少,它既不是指那一幣值、財富或經濟總量包含多少“抽象勞動”,也不是指那一幣值、財富和經濟總量代表多少“邊際效用”。[18]于是,善于思考的人們就會發現,如果僅僅以貨幣量(如居民儲蓄、各種保險)作為人們養老的支付管道,大量中下階層居民步入老年前的貨幣積蓄基本不能支付其年老后的所需服務的貨幣量。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貨幣總量都是隨著時間推移而迅速增加⑩,這使得居民養老儲蓄加養老保險金之和在購買后期服務的能力越來越低。面對這一困境,不少人開始自發地創新養老方式,甚至回歸原初社會“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近年來興起的“抱團養老”■就有純服務交換的含義。這說明,在老年服務領域,需要非貨幣化的服務供需途徑,實現以“服務時間A”交易“服務時間B”的方式。因此,“服務”的存取既是社區社會組織化的基本需要,也是構建組織化網絡的核心。于是乎,社會工作不僅僅要提供“助人自助”“助人助他”式的服務,還需要激勵盡可能多的人為了未來所需要的服務量,在現在有時間有精力時貢獻自己的服務。精準安排、專業認定與記錄居民提供的服務并有效匹配服務者與服務對象也就成為社區治理過程中,社會工作者與社工機構另一個重要任務。這一重大任務不僅需要社會工作機構自身的組織網絡化,以形成“銀行網絡體系”式的社區組織體系,同時更需要組織所有社區居民參與到社會服務的交換當中去。以服務交換為目的的組織化過程自然也就化解了目前社區治理中廣泛存在的個體化、原子化困境。
注釋
①所謂網格,就是將城區行政性地劃分為一個個的“網格”,使這些網格成為政府管理基層社會的單元。如長沙市各個區均設置有網格化管理系統。
②筆者在2016年實地調研中,從所調研社區取得的《社區自治章程》中規定:社區職責是宣傳組織引導居民學習遵守法律,維護社區居民的合法權益,履行義務,美化、凈化社區環境,做好社區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為社區特殊群體提供社會福利性服務,常住、暫住人員的登記管理工作,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和生活秩序,調節民間糾紛,促進居民家庭和睦,鄰里團結。
③⑥筆者在2016年實地調研中,從所調研社區取得相關數據。
④“粘性”原本屬于物理學概念,是指“施加于流體的應力和由此產生的變形速率以一定的關系聯系起來的流體的一種宏觀屬性,表現為流體的內摩擦”。后來被運用于網絡,“網絡粘性”一詞“一方面指網站吸引網絡用戶返回并使之停留在該網站的一種特性,另一方面又是指用戶愿意再次訪問某網站并延長其停留時間,且愿意有意無意地在該網站持續瀏覽的一種心理狀態”。社區內的“朋友圈”興趣群體以及各種由居民自己組成的社會組織是衡量社區粘性的基本緯度。(詳見巴晶、胡麗娜在《現代管理科學》2012年第5期發表的“虛擬社區粘性對網民參與行為的影響實證研究”一文中的論述。)
⑤數據出自筆者從湖南省民政廳社會工作處獲得的內部資料《2015年湖南省社會工作發展總結報告》。社會工作“三區項目”,即在邊遠貧困地區、邊疆民族地區和革命老區開展社會工作人才支持計劃的項目。
⑦2016年3月19日至21日參加在清華大學知行樓109舉行的第一屆“行動—干預社會學(主題:社區實驗)”研討會,獲得相關資料。
⑧塞爾哲學式的理解:貨幣是人類經濟活動和交往中一種凝匯著人們集體意向性和“意見約同性”的制度實在。我們最終把貨幣視作商品與勞務交換、市場運行、經濟增長、資源配置和人們生活游戲中體現著人們集體意向性的一種制度建構(a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human intentionality)。(詳見韋森在2003年版《經濟學如詩》第57~74頁中的論述。)
⑧不同時段、空間服務傳遞在具體精算技術上還需要更復雜的研究、設計、測量與制度設計。
⑨中國貨幣發行量增長迅速:1952至1957年的增長速度大致在10%左右,1981年至1983年貨幣增長速度為22%,1994至1998年貨幣年均增長速度為39%,2002年以后,每年新增貨幣3萬億以上(詳見《中國建國以來貨幣發行量》中的論述,http://www.360doc.com/ content/10/1117/22/1133289_70280494.shtml)。
⑨“抱團養老”這一概念最先出現在2011年8月14日《人民日報》第7版刊載的李增輝《抱團養老就地享福》一文中,是指有一定關聯的老年人集中到一個合適的地點,就養老活動分工合作,各自承擔責任與義務,互相服務互相照顧等養老形式。不少媒體判斷,“抱團養老”已成新趨勢。
[1]李斌.中國城市居住空間階層化研究[M]. 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3: 5-10.
[2]李雪萍,陳艾. 社區組織化:增強社區參與達致社區發展[J]. 貴州社會科學,2013(5):150-155.
[3]TENNIES F. Community and civil socie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7.
[4]王巍. 社區治理精細化轉型的實現條件及政策建議[J]. 學術研究,2012(7):51-55.
[5]王名. 社會組織論綱[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7.
[6]何立軍. 深入推進“三社聯動”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民政部召開全國社區社會工作暨“三社聯動”推進會[J].中國民政,2015(20):30-31.
[7]葉南客,陳金城. 我國“三社聯動”的模式選擇與策略研究[J]. 南京社會科學,2010(12):75-80.
[8]鄒鷹, 程激清,陳建平. “三社聯動”社會工作專業主體性建構研究——基于江西的經驗[J]. 社會工作,2015(6):99-115.
[9]徐延輝,蘭林火. 社區能力、社區效能感與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社區社會工作介入的可能路徑研究[J].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4(6):131-142.
[10]LABONTE R, LAVERACK G. Capacity building in health promotion, part 1: for whom and for what purpose[J]. Critical public health, 2001, 11 (2): 111-127.
[11]錢寧. 工業社會工作[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24.
[12]江立華,王斌. 個體化時代與我國社會工作的新定位[J]. 社會科學研究,2015(2):124-129.
[13]哈貝馬斯. 交往行為理論:行為合理性與社會合理化[M]. 曹衛東,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36.
[14]李斌,王鎰霏. 組織化與專業化:中國社會工作的雙重演進[J].社會工作,2014(6):3-8.
[15]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58-145.
[16]潘澤泉. 社會、主體性與秩序:農民工研究的空間轉向[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38-40.
[17]BLUMER H.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1969: 74-75.
[18]韋森. 貨幣、貨幣哲學與貨幣數量論[J]. 中國社會科學,2004 (4):61-67.
(文字編輯:徐朝科 責任校對:賈俊蘭)
An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Individualizatio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China
LI Bin, WANG Yifei
(Sociology Department,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 China)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spaces have been greatly changed with the New Urbanization Plan in China. Residents are migrating faster than ever, and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are fast becoming unfamiliar. These reasons are deteriorating residents’ individual dilemmas. Th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such as residents' committee,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work institutions are not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organizing the residents to help each other when they are in predicaments. In order to solve the individual dilemma and prepare for the coming aging wave, community social workers must organize the dwellers, and develop a kind of institution in which dwellers can help each other, with the ideas of “helping the weak and enabling them to help others”. The logic of the institution should be like the system of bank, but in which the services are deposited and withdrawn instead of money.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s need provide professional service in one hand, and build a network system which the human service can inter-exchange across time and space on the other hand.
individual dilemma; helping the weak and enabling them to help others; systematization; social work; service bank
C916
A
1671–623X(2017)02-0052-06
2016-12-08
■ 基金課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課題“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城鄉關系研究”(15ZDA044);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課題“居住空間結構化與人口城鎮化路徑及策略研究”(15ASH007);湖南省智庫專項課題“湖南城市化背景下的城鄉社區發展研究”(16ZWC24)。
李斌(1963— ),男,漢族,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社會政策,城鄉社區發展。
李斌,王鎰霏. 化解社區治理中個體化困境的有效途徑[J].社會工作與管理,2017,17(2):5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