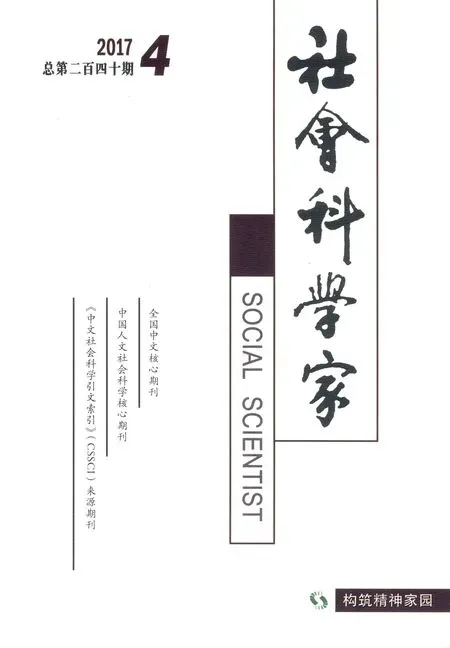建構地域文化自信:《新安文獻志》的范式意義
張小明
(黃山學院 文學院,安徽 黃山245041)
建構地域文化自信:《新安文獻志》的范式意義
張小明
(黃山學院 文學院,安徽 黃山245041)
明中葉徽州學者程敏政(1444-1499)通過蒐集、編纂大型地域文化圖書《新安文獻志》,弘揚鄉邦先哲嘉言懿行,傳承儒文化學脈,始終以朱子之學為歸依,有意統一徽州學術文化理念,同時以文獻作為徽州地域文化的媒介,實現文化立邦的意圖。《新安文獻志》不僅有效地保存了徽州地域圖書文獻,同時為建構地域文化自信提供范式意義。
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徽州;文化自信;范式意義
地域文化自信的建構源于特定地域人們對自身文化傳統的強烈認同,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場域,且對外有著較強的輻射性。明中葉,徽州杰出學者程敏政以其國史之才,蒐集、編纂大型地域文化文獻《新安文獻志》。該書共一百卷一百二十多萬字,為程氏積三十年之功編纂而成,為第一部徽州圖書文獻匯編。《新安文獻志》的編撰不僅體現了程氏整理地域文化的高度自覺,還為地域文化自信的建構提供了一個成功范式:即以總結地方文獻入手,通過取舍排比,誦法先賢,統一文化觀念,強調文化立邦,從而彰顯地域文化自信。
一、誦法先賢:明確的編纂主旨
程敏政于書無所不讀,文章為一代宗匠。《四庫全書總目·篁墩文集提要》稱:“明之中葉,士大夫侈談性命,其病日流于空疏。敏政獨以博學雄才,高視闊步,其考證精當者亦多有可取,要為一時之冠冕,未可盡以繁蕪廢也。”徽州號稱“程朱闕里”,自宋以來就是文獻之鄉。程敏政編纂的《新安文獻志》,其中辭命68篇、奏疏40篇、書40篇、記71篇、序52篇、題跋61篇、議4篇、謚議2篇、論26篇、辨8篇、說9篇、原4篇、考8篇、雜著36篇、問對4篇、策問6篇、策2篇、講義4篇、道5篇、檄19篇、表箋奏附17篇、啟44篇、碑13篇、祭文20篇、銘13篇、箴8篇、贊14篇、頌3篇、賦11篇、行實360篇,另有詩詞曲1000多首。該志所收或取自正史本傳,或取自地方志譜乘,或取自墓志銘、行狀、神道碑,或取自別集、筆記和信函,幾乎囊括徽州文獻的各個方面。程氏“廣搜博集,多方補充,材料豐富,薈萃賅備”[1],可補方志之未備。
程敏政為何要、又如何能憑個人之力去蒐集圖書文獻,編纂《新安文獻志》呢?首先,徽州文化經歷從“崇武”到“尚文”的轉變。古徽州本屬山越之地,崇武之風由來已久。魏晉以來,由于中原世家大族的遷入,又因為北宋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為徽州,更因為公元1132年南宋王朝南遷臨安,徽州作為臨安西北門戶,成為畿輔要地。徽州文化由此蓬勃發展起來,開始以“文獻之邦”、“東南鄒魯”之名聞名于世。為使大量圖書文獻不湮滅失傳,深受徽州文化沾溉而成長起來的學者程敏政,自覺意識到有承擔蒐集編纂徽州地域圖書文獻的責任,故其明確宣稱:“宣子聘魯,而嘉周公典籍之大備;孔子說二代之禮,而嘆杞宋之難征。則生于其地,而弗究心于一鄉之文獻,非大闕與?”[1]
其次,有計劃地搜集鄉邦先賢的著作。程敏政出身世代文化世家,家中藏書頗豐。據明末姜紹書《韻石齋筆談》所記“昭代藏書之家”,程敏政亦是與宋濂、劉基、李東陽、王守仁、楊慎、王世貞、袁宏道、湯顯祖、李贄等有明一代著名的文人學士齊名的藏書家。在姜紹書看來,這些學人著述宏富,名重當時,“翱翔藝苑,含英咀華,尚論千古”,所收藏的文獻典籍必然豐富,“縱未必有張茂先之三十乘、金樓子之八萬卷”,但從他們廣博的學識來看,“亦可見其插架(藏書)之多”[2]。程氏自己則說:“發先世之所藏,搜別集之所錄。而友人汪英、黃莆、王琮植暨宗侄隱充,亦各以其所有者來饋;參伍相乘,詮擇考訂,為甲集六十卷,以載其言,乙集四十卷,以列其行。蓋積之三十年始克成也。”[1]《新安文獻志》是程敏政花費30年的時間,有計劃地搜集鄉邦先賢遺著,并在此基礎上編撰的徽州文獻總集。
程敏政編纂《新安文獻志》非為自己揚名立萬,而是為了誦法先賢,從而使徽州文化得以名揚天下,垂范后世。其《新安文獻志序》云:“凡吾黨之士,撫先正之嘉言懿行萃于此,發高山景行之思,而日從事乎身心,由一家以達四海,使言與行符,華與實稱,文章德業,無愧前聞;又進而誦法程朱氏,以上窺鄒魯,庶幾新安之山川,所以炳靈毓秀者,不徒重一鄉,將可以名天下;不徒榮一時,或可以垂后世,而此編亦不為無用之空言也哉。”[1]明人治學,素遭后人“空疏”之譏。程敏政非不善理學,其《道一編》和合朱陸,頗見思辨功力。然《新安文獻志》不作無用之空言,不僅爬梳博采,薈萃賅備,而且辨證排比,嚴加分類,主題突出,平正醇粹。
程氏所選之文,或表彰雄才大略、安邦定國之重臣、將軍,如《宋端明殿大學士程公珌行狀》、《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蔣公貴神道碑》;或稱頌興利除害、為民請命的直臣良吏,如《方吏部岳傳》、《松江府知事俞公師魯行狀》;或贊揚樂善好施、扶貧濟困的富商大賈,如《記外大父祝公確事》;或謳歌相夫教子、睦鄰和族的賢妻良母,如《孺人陳氏墓志銘》、《程給事中母宜人胡氏墓志銘》。此外,弘揚正氣,敢于與黑暗勢力斗爭的諍臣義士;標新立異,不為陳規陋俗所禁錮的奇才異士;醫德高尚,醫術精湛的良醫術士等,皆在程氏表彰之列。
徽州專志的編修較多,流傳下來且較有影響的有梁蕭幾《新安山水記》、王篤《新安記》、唐代的《歙州圖經》、宋代李宗諤《州郡圖經》、羅愿《新安志》、傅巖的《歙紀》、程曈的《新安學系錄》、趙滂的《程朱闕里志》等。其中羅愿《新安志》在傳統的地記、圖經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并對之進行了揚棄,從而使古代方志走向成熟。《新安名族志》則是由程尚寬根據戴廷明的《新安大族志》續補而成的徽州重要宗族史著。《新安學系錄》則是第一部新安理學的“學案”性著作,該書收錄了105位著名新安學者的傳記資料以及言行、遺事,對徽州人物的研究和徽州文獻的保存均有重要意義。至于《程朱闕里志》這部篁墩村志,則在考證朱熹、程顥、程頤三人出自徽州這一問題上具有文獻價值。程氏《新安文獻志》雖與諸家一樣,同為專志,但別具一格。其以文獻為中心,又不僅僅以文獻保存、傳承為目的,而志在表彰先賢精神品格,凝練徽州地域文化的基本要旨,凸顯地域文化自信所依賴的合理基礎。
二、彰顯朱學:統一的文化觀念
錢謙益曾對程敏政高度贊許,“克勤修眉長髯,風神清茂,考證古今,精詳博洽,追配其先龍圖大昌,近儒莫及也……他所撰輯《宋紀受終考》、《遺民錄》、《新安文獻志》,皆可觀。”[3]錢謙益指出程敏政有南宋徽州大儒程大昌之遺風,反映出程敏政特別重視向徽州鄉賢學習,其《新安文獻志》就是欲集成徽州鄉賢之文獻。當然,程敏政編纂《新安文獻志》并非意圖匯編一部徽州文獻大全,故其不曾竭澤而漁,將徽州文獻一網打盡。其目的在于表彰鄉邦“先正之嘉言懿行”否則,“雖膾炙人口,不在錄也”。為了達成這一目的,在中國歷史留下深刻影響的徽州大儒朱熹就必須得到重視。事實上,少年程敏政就曾寫出《蘇氏梼杌》,其中多萃取朱熹黜蘇軾之言。《蘇氏梼杌》在《四庫全書總目》中未見著錄,但據《篁墩文集·拾遺·蘇氏梼杌序》可見程敏政的主張,該序中云:“……今去子朱子之后益遠,而為蘇學者益盛,竊不自揆,謹取子朱子平日所黜蘇氏之言,萃為一編;凡近世諸賢,其議論有合于此者,悉附其后,題曰《蘇氏梼杌》,以寓除惡務本之義。”[4]錢謙益在高度評價程敏政的同時,也指出其“惟著《蘇氏梼杌》,力詆眉山,以報洛、蜀九世之仇,則腐而近愚,且比于妄矣”[3]。據《蘇氏梼杌序》,該書成于天順五年(1461),當時程敏政才16歲,書中所言自有少年意氣失之偏頗之處,但也較早地奠定其尊崇朱熹的思想基礎。
在程敏政的時代,由于朱熹、陸九淵治學方法不同而引發的“朱、陸異同”之爭,這已成宋明學術史上的熱點。朱熹強調“道問學”,認為為學先要泛觀博覽,反對粗心浮氣,失之太簡;陸九淵則強調“尊德行”,認為為學先要發明本心,反對支離煩瑣,欠缺涵養本原。到明中葉,隨著陸九淵心學思想流布漸廣,甚至滲透到素有“程朱闕里”之稱的徽州,朱熹的地位受到空前的挑戰。當時的學人紛紛棄朱而從陸,二派之間紛爭不斷,學術文化爭辯之風極為激烈。在這種背景之下,程敏政專門撰述《道一編》提出朱、陸“早異晚同”之說,希冀平息朱、陸紛爭。《道一編》在其中所選的一篇《朱子答呂子約書》后云:
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后篤行”之旨。
對此,程敏政作了按語:
此書朱子未與陸子相見時語,所謂脫略文字,直趨本根,與《中庸》先“學問思辨而后篤行”之說,乃朱陸最異處。今考陸子與其門人書,亦孜孜以講學為務,而獨切切以空言為戒,疑所謂空言者,指朱子也。朱子豈倡為空言哉?其說可謂大不審矣![5]
程敏政承認朱、陸早期有異同,同時又積極維護朱子。程敏政在《道一編》選錄《朱子答呂子約書》《朱子答蔡季通書》后云:
以上二書,朱子始謂陸子全是禪學,且嘆其深誤后生之好資質者。今考象山之書,往往以異端為憂,其于儒釋之辨亦嚴。蓋朱子直以其主尊德性之說太過,而疑其為禪耳。然陸子與朱子書,則又譏其為葛藤末說,不知縈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殆其言皆出于早年氣盛語健之時,學者未可執以為定論也。[5]
程敏政認為朱、陸分歧主要是由于早年年輕氣盛,學者不能以此為定論,應以各自晚年思想為依據。程敏政著《道一編》宣揚朱、陸“早異晚同”,曾招致當時及后人的非議,認為其“抑朱扶陸”、“辱朱榮陸”,這其實并沒有完全理解程敏政的本意。[6]程敏政曾明確表明“求孔子之道,必自程朱”[7]的立場,其和合朱、陸的目的,正式為了維護受到陸學沖擊的朱子之學的地位和影響。
《道一編》成書于弘治二年(1489),《新安文獻志》成書于弘治三年(1490),這時程敏政年近五十,是其思想成熟的時期。為維護朱熹的地位和影響,程敏政在《新安文獻志序》中開宗明義:“婺源之朱南徙閩,而得文公,嗣孔孟之統,而開絕學于無窮。”[1]就《新安文獻志》選錄內容而言,程氏廣搜朱熹與新安相關的材料,詳加錄入。其于《凡例》云:“朱子詩文錄有關于新安者,及本集所遺闕者,及嘗流傳故鄉而刻石鋟梓者。”[1]皆一一錄入。就《新安文獻志序》編纂體例而言,其甲集悉遵真德秀《文章正宗》體例,而實際在構建全書的過程中,一方面遵從朱熹注書之例,“朱子注書,例凡先達稱官,如云范太史;稱爵,如云司馬溫公;稱謚,如云范文正公;否則稱字,如云呂伯恭;或兼以號舉,如云張南軒,今悉遵此例,不敢稱名,亦景仰忠厚之一端也”[1]。另一方面,“行實中有文字冗長或牽書者,遵朱子《伊洛淵源》例,略加刪節……”[1]就材料取舍而言,程氏特別指出:“先達時文,多有晚年手自竄定之本,致與刊本、石本異者,又有經后賢所刪潤者,今參伍相校,務從善本。”[1]可見,程敏政特別看重作者晚年手自竄定之本,其用意不僅是保證文獻的可信度,同時也有其良苦用心,那就是針對一些人以朱子早年與晚年自相矛盾的一些觀點批駁朱子的學術局面的一種匡正。
地域文化的形成絕非一日之功,而是在長期的傳承和積淀的過程形成固有傳統,而這種傳統有可被感知的、異于其他地域的文化特征。地域文化以一定的觀念作為核心,然后滲透到物質層面和其他文化元素之中。因此,地域文化自信的建構同樣需要確立主流的核心價值觀。[8]徽州是朱熹的祖籍,由于歷代封建統治者的倡導、科舉的引導,更因為徽州歷代學人對朱子理學的維護和固守,朱子理學是宋明以來徽州地域文化最具主導性的意識形態。程敏政在朱子理學在徽州經典化的建構進程中,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新安文獻志》作為徽州地方文獻的總集,程敏政有意識地以朱子理學作為統一的文化理念,以此來揭示徽州文化的核心價值。程敏政在《新安文獻志》中除古詩以外,選錄了朱熹46篇文章,意在突出朱熹在徽州文化中的地位和影響,其有意識地標榜朱子之學,企圖以之為徽州樹立一個統一的學術文化理念。《新安文獻志》以朱子為最高典范,在朱子之學普遍遭受懷疑的學術背景下,其統一徽州學術文化理念的意義自不待多言。實際上,程氏之前的元代有朱子后學胡一桂、胡炳文、陳櫟等篤遵朱子學的基本原則進行教授、講習和著述,使得朱熹逐漸在徽州取得文化宗主地位。明初在新安理學三大家朱升、鄭玉、趙汸的引領下,朱熹在徽州的地位進一步得到鞏固和發展。稍后于程敏政的程曈(1480-1560)更是結撰出一部《新安學系錄》來維護朱子學統,其明確提出北宋二程和南宋朱熹是新安學派的宗師。雖然程敏政、程曈兩人的具體觀點有不同之處,但在維護朱子學脈、弘揚朱子正統地位上,顯然并無二致。
三、文化立邦:高度的自覺自信
梁啟超先生在《近代學風之地理分布》一文中指出:“氣候山川之特征,影響于住民之性質;性質累代之蓄積發揮,衍為遺傳。此特征又影響于對外交通及其他一切物質上生活;物質上生活還直接間接影響于習慣及思想。故同在一國,同在一時,而文化之度相去懸絕,或其度不甚相遠,其質及其類不相蒙,則環境之分限使然也。”[9]的確,地域文化是指一定地域的空間特征及其區域文化現象的組合,地域空間地理環境是地域文化的發展基礎。空間地理環境通過人的活動,影響地域文化的氣質和特征。文化又會影響人的生活、思維,文化的傳承又強化空間環境的自我特征,確立空間環境的品位及影響力。
唯有文化才能立邦,這是歷史的經驗與現實的表現。程敏政以地域文獻作為徽州地域文化的顯性符號,實際上抓住徽州文化的主要標志。毫無疑問,地域文獻與地方文化之間有著同構的關系。地域文獻是地域文化建構的重要載體,代表地域文化的重要層面和豐富內涵;地域文化的培育進程中又在不斷地進行文化的積累,顯示出崇尚文化的傳統,激發地域文獻創作與集聚的動能。
文化立邦的實現當然也需要優秀的文化傳播手段。程敏政以地域文獻的蒐集、編纂作為文化傳播與展示的重要手段,他以朱子之學為統領,從“人杰”和“地靈”兩個方面對徽州文獻進行有效的匯集,集中顯現徽州地域文化的影響力。《新安文獻志》表彰家鄉先哲,即宣揚徽州“人杰”,這在前文已述及;與此同時,《新安文獻志》還收集整理了大量宣揚徽州“地靈”的文獻,彰顯出無與倫比的地域文化自信。
從空間地理看,徽州位于皖南,境內有黃山、齊云山、新安江等秀美的自然資源。徽州山水之美,天下共賞。程敏政對家鄉徽州的山水極富感情,《新安文獻志》輯錄有大量有關徽州山水的文獻。其中有的反映了如何發現徽州的青山秀水;有的反映了徽州人如何因地制宜,巧奪天工,開發山水自然資源;有的則反映出徽州人重視宜居,把審美與實用互相融合,將徽州山水的利用發揮到極致。
以選編山水游記為中心,《新安文獻志》編入了大量反映徽州大好河山的文獻。此類文章有《三潭記》、《游黃山記》、《游問政山記》等。如張正甫《歙州披云亭記》記披云嶺云:“回廊翼旋,飛閣云褰,萬家井邑在我宇下,實一方之勝概也。”“峨峨絕頂,一上千仞,未幾營之屹而冠焉。”“憑九霄以高視,罔八極而暇觀。塊如眾山,杯分百川,籠吳楚之封境,領江湖之氣象,有足廓虛懷而攄曠抱矣。”[1]汪炎昶《游龍潭記》描繪出婺源城東龍潭云:“石掬兩股為崖瀑,自其后,秉高怒噴,直下數十尺,遠望如出穴中,雹狂雨狠,淙淙不絕,而其細者,空濛霏微如薄霧。”[1]汪古逸《游雪矼記》摹寫江伯幾居所陽昕山之南的層崖飛瀑云:“噴薄懸激而下數十百尺,聲潀然,色如縞雪,崖上聳焉。孱顏呀然空硿,乃迴為平矼,貯澗瀑,矼與瀑相輔為奇。”[1]《新安文獻志》還以亭臺樓閣為中心,編入了大量反映徽州人文景觀的文獻。如《歙州披云亭記》、《浯溪三絕堂記》、《飽山閣記》、《相公橋記》等。
程敏政從人杰和地靈兩個方面宣揚徽州,彰顯出無可比擬的文化自信。整部《新安文獻志》的選編,不僅突出強調徽州為“文獻之邦”、“東南鄒魯”,且將自己究心于鄉邦文獻與宣子聘魯之嘉美、孔子說禮之感嘆相比照。其表彰鄉邦先哲嘉言懿行,又特別突出徽州文化是在朱熹培育和影響下產生的。如此等等,皆在有意識地確立文化立邦的理念,建構徽州地域文化品牌。程氏的舉措,對今天的地域文化建設不無借鑒意義,尤其是程氏選編大量關于徽州大好河山的發現、開發和利用的文獻,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有助于確立徽州人的地域空間認同與地域文化自信。
值得注意的是,徽人在證實徽州為“東南鄒魯”的過程中,時有不惜牽強附會,如將二程納入徽人,前舉程曈《新安學系錄》、趙滂《程朱闕里志》皆是如此。程敏政卻能跳出地域和姓氏偏見,不強將二程定為徽州人。故即如許承堯雖嚴厲批評程敏政,亦承認敏政“其有遷居已久,不歸故籍,如河南二程氏者,志不牽引,亦自有見。”[10]程氏這種客觀公正的治學態度頗值我們借鑒。我們在加強建構文化自信的進程中,應自覺堅持文化自信精神,但也必須拋棄褊狹與自大,而應秉持更科學、更開放、更全面的眼光。
四、結語
在程敏政《新安文獻志》以前,我們鮮見以地域為中心的大型地方文獻總集。在《新安文獻志》以后,明代李堂編纂的《四明文獻志》、管一德《皇明常熟文獻志》、徐世昌《固安文獻志》等,清代夏骃編纂的《南潯文獻志》、蘇源生《鄢陵文獻志》等類似典籍紛紛出現。因此,《新安文獻志》具有重要的開創意義和歷史價值。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其評價:“凡徽州一郡之典故匯萃極為賅備,遺文軼事,咸得藉以考見大凡。故自明以來,推為巨制。”
程敏政秉承孔子以來以述為作的傳統,以徽州地域文獻為媒介,傳承儒家文化學脈,始終以朱子之學為歸依,有意統一徽州學術文化理念。程敏政在文集、方志、族譜等之外,突破各種藝文志收錄較窄的缺陷,以地域為中心,蒐集、編纂、保存相對集中完整的徽州地方文獻,體現出為徽州地方文獻進行總結、集成和發揚光大的編纂思想。文化是一個不斷創造和積累的過程,任何民族和個人,總是在文化的不斷傳承和創新中成長。《新安文獻志》作為地方文獻總集整理的一大創獲,不唯搜羅宏富,集明前徽州文獻之大成,更堪稱徽州文化之淵藪,澤惠后人,遠非一代。程敏政在編纂中所表現的積極有為和文化自信,也為當下日益繁榮的文化建設樹立了一個良好范式。
[1]程敏政.新安文獻志[M].合肥:黃山書社,2004.10;1-2;1;2;1;3;4;4;3-4;310-311;361;359.
[2]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卷上)[A].筆記小說大觀[C].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148.
[3]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冊)[M].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276;277.
[4]江枰.明代蘇文研究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45.
[5]程敏政,程疃.道一編·閑辟錄[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30;32.
[6]周曉光.新安理學[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185.
[7]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十四)休寧縣儒學先圣廟重修記[M].
[8]朱萬曙.地域文化與中國文學——以徽州文化為例[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4(4):25-32.
[9]梁啟超.梁啟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259.
[10]許承堯.歙事閑譚[M].合肥:黃山書社,2001.8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3240(2017)04-0156-05
2017-01-17
張小明(1974-),安徽歙縣人,黃山學院文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與文獻。
[責任編校:趙立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