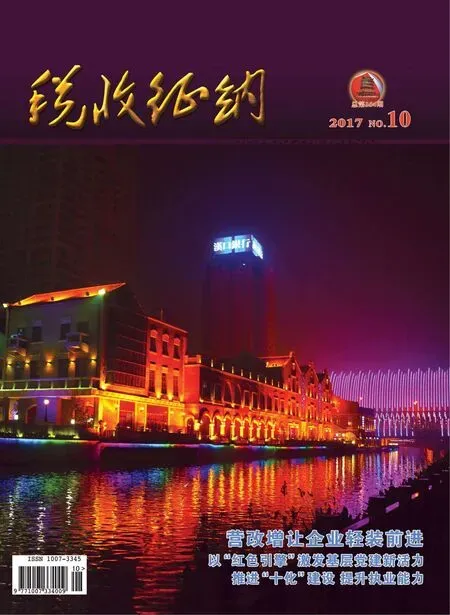人生的況味
汪 文
人生的況味
汪 文
人過五旬,上有老下有小是常態。但是有時生活的大車一旦出現顛簸甚至傾覆狀態,如何面對、如何爬起,還真不容易。這個時候的人生況味,往往有些無以言表。
今年夏季來臨時,西安的房價噌噌地往上漲。我幾近失去了到西北大學領取終南山文學獎的心情,按照兒子的吩咐,便在西安城里看看樓盤。
不看不知道,看了嚇一跳。我所處的小城3000元左右一平方米隨便挑。可西安高新區這地方9000元左右一平方米竟然沒房源。沒過多久,如今竟然漲到16000元一平米。
遠在蘇州工作的兒子欲回陜西,說他那點工資根本招架不住房價增長的速度,說他見證過蘇州去年房價大幅上漲的可怕情形。急得甚至一個月內為此來回高鐵奔波三次。
兒子的話沒有錯,我動作遲疑了一個月,房價每平方米就上漲了1000元,多掏10萬元自作自受。兒子他媽天天抱怨不休。
好不容易將攢下的錢給兒子交了首付,一顆心落地了,但這顆心也感覺徹底被掏空了。突然,有一種感覺,人成了房子的奴役。前半生,自己的積蓄花在自己購房上,后半生還要操心給兒子還房貸以補貼。怎么感覺人生與房子成了一種解不開逃不脫的關系!
人過五旬,人的心幾乎分成了幾半,有一半是在孩子身上,其余一半則操心在其他親人身上。
我年邁的父母遠在千里之外的陜北子洲。父親前年患了腦梗,雖能住著拐棍走路,但是生活已經只能是這樣的狀態。母親75歲,每天早上4點多起床上山勞作,為了這一年2000--3000元左右的收入,一個人種地,一個人施肥,一個人除草,在彎彎曲曲的山路上奔波。
此刻,我的心懸在病父上,掛在操勞的母親上。我都不忍心寫母親的操勞,一想起這些細節,眼淚就止不住地流出來了。母親既要上山種地,又要每天一日三餐用柴火做飯,很是辛苦。我勸老母親不要這樣操勞了,她老人家總是這樣說:“誰有都不如自己有,我能勞動為什么要閑在家里呢?全當鍛煉身體啊!”我說:“你出了岔子么辦?”她說:“什么時候出岔子了?”我們母子永遠在這樣無解地爭執著。
我是家中的長子。去年10月份,一場意外災禍降臨到了我的農民二弟身上。他在操作壓面機時,不慎將右手卷入壓面機。
災禍降臨后,第一次手術保住了他右手的全部手指頭。第二次手術修補了幾乎成半個空洞的右手背。弟弟賺錢實在不易,甚至糊涂到寧可不要手也惜錢的地步,僅這兩次手術的時間是整整9個小時。從手術成功到北京康復至后續3個月的專門醫院手功能恢復,每前進一步,我都要心到言到甚至行到。
親兄弟遭難了,不流淚不由人,不操心不可能。我為此每每想到這里淚水就流出來了,走在路上淚水止不住地滾下了臉龐。
弟弟養活著一家人,靠苦力謀生。遭遇這場事故,勞動能力基本喪失了。一家人怎么生活?我試著找了市縣慈善機構,沒有收獲。弟弟綁著病手在當地的民政、殘聯奔波一周,沒有什么進展,每次回家右手疼得大汗淋漓,無可奈何地說:“這救濟不好要,我不要了!”
我是他的親哥,在家中是唯一一個在稅務機關工作的人員。我不操心能行嗎?但是我遠在千里之外,我怎么管?我除了力所能及地給予弟弟一家以經濟上的接濟,我還能做點什么?
弟弟已經成了殘疾人,成了社會的弱勢群體。我有責任有義務將他的困難向有關方面報告。我為此通過網絡報告給了弟弟所在的市縣相關領導。但我幾乎不敢有什么實質性的期望。
在兩次失敗之后,第三次終于有了實質性的進展。當地領導見信后,指示民政部門給救濟了1000元,同時,鎮村兩級領導從實際出發,不僅將弟弟列入貧困戶,而且列入低保戶。當弟媳婦與我在手機通話中告訴這個消息時,我分明感受到了她的激動。為此,我也甚感欣慰。
這兩年,我的人生之舟確實顛簸得十分辛苦。2015年大年三十我才忙完公務,繞道西安坐火車回陜北探望我的父母。2016年大年三十晚上我還在單位值班。2017年大年初一早上5點我急著坐汽車,趕火車再回陜北,正月初二早上跑到榆林醫院探望兩次手術后的弟弟。
也許有人會說,你怎么和大領導一樣忙呢?不是這樣的。其實,在職一天,就要盡責一天,與級別大小職位高低應該沒有關系。我的母親一年四季四點多起床或上山勞作,或在家經營。我做不到她這一點,但我做到在職一天,盡職一天總是可以的吧。
過了五旬的人生,有時候猶如逆水行舟暗礁布道,確實很艱辛,稍不慎,就會船傾楫摧。最難的時候你不流眼淚都不由你。但是,其實,只要我們自己內心真正強大了,只要我們靈魂中有了進取與堅韌的基因,只要我們能咽下淚水克服困難自強不息,只要我們相信智慧與雙手能創造美好,那么再難的再大的風雨也會過去的。
這個時候,人生的況味確實苦,有時苦中沾淚,但是走出這段人生的泥沼,這滋味也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