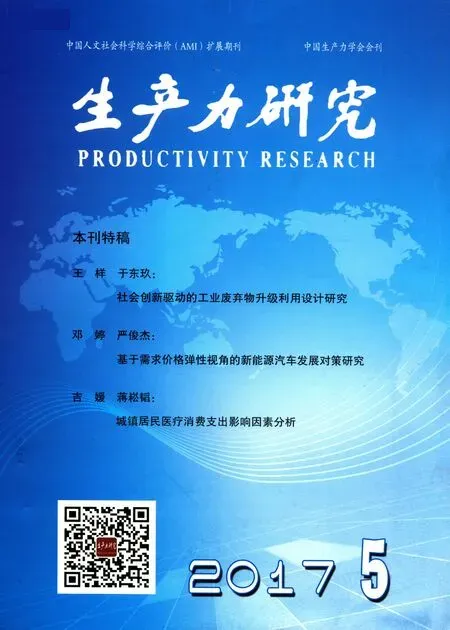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產業空間關系綜述與展望
李 寧,韓同銀
(1.河北工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天津 300401;2.天津商業大學 經濟研究所,天津 300134)
學術動態綜述
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產業空間關系綜述與展望
李 寧1,2,韓同銀1
(1.河北工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天津 300401;2.天津商業大學 經濟研究所,天津 300134)
文章系統闡述了生產性服務業的內涵與分類,在此基礎上,基于產業視角,從互動需求、分工與價值鏈和產業關聯三個層面,綜述了二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和互動機理。基于空間視角,從產業集聚、協同定位等層面,分析二者之間的協同集聚關系。基于創新視角,從價值鏈延伸以及產業層面的知識互動,綜述知識密集型服務業與制造業的交互創新。基于生態學視角,綜述了二者之間的共生關系。最后,闡述了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研究的未來方向及趨勢。
生產性服務業;制造業;互動;協同;創新
一、引言
國內外學者對服務業的研究始于“克拉克定理”,國外學者起初從產業經濟學的視角,研究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互動關系。隨著信息技術和互聯網技術被應用于產業發展,在應用中不斷創新,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在空間上的臨近屬性被逐漸削弱。國內外學者更多地從空間區位特征研究,形成了在區位上分離和在區位上集聚的觀點。在京津冀協同發展背景下,“協調發展”或“協同發展”概念被廣泛提及,越來越多的學者從空間的層面研究,認為二者在空間上存在共同集聚與協同定位關系。《中國制造2025》規劃中明確提出,推進與制造業緊密相關服務業水平提升,才能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制造業。需要指出的是,制造企業競爭力的提升,需要與生產性服務業中的高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交互創新。因此,本文基于產業經濟學、區域經濟學、新經濟地理學、產業集群理論、社會網絡等學科,從產業視角、空間視角、創新視角、生態學視角,對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之間關系的相關文獻進行全面綜述。
二、生產性服務業內涵與分類
(一)生產性服務業內涵
生產性服務業的內涵可以從投入屬性、面向對象以及產出屬性等方面來界定。國外學者Greenfield[1]認為生產性服務業就是向生產者提供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而不是向最終消費者提供服務產品和勞動的服務業。Gruble和Walker(1989)[2]進一步從全要素生產率的角度,認為生產性服務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水平;主要通過提高資本投入和強化知識來促進制造業的專業化。Hansen(1990,1994)[3]從產業鏈的角度將中間投入分為上游研發的活動和下游市場的活動。鄭吉昌、夏晴(2005)[4]從面向對象的角度,生產性服務業是面向生產的各個階段,是作為中間投入部分參與到其他產品或服務的生產。本文將生產性服務業界定為市場化的非最終消費服務,即作為其他產品或服務生產的中間投入的服務;生產性服務業又稱中間投入服務業,是介于生產和消費之間并從制造業中剝離演進而來的[5]。
(二)生產性服務業分類
國外學者將生產性服務業一般分為:金融業、保險業、不動產(即房地產業)、商務服務業。Marshall(1987)、Hansen(1990)、daniels(1993)都認為生產性服務業包括信息加工服務、與商品有關的服務和人員支持服務三類。Coffey(2000)[6]認為生產性服務包括商務服務、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我國學者閻小培(1999)、李江帆(2005)、曹毅(2009)、劉書瀚(2010)、高覺民(2011)等,認為生產性服務業主要指金融保險業、房地產業、信息咨詢服務業、計算機應用服務業、科學研究及綜合技術服務業等。
三、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互動關系——產業視角
關于兩者的關聯性,理論界基本上形成了一個較為統一的認識:二者間的互動關系是隨著社會生產分工深化而建立起來,生產性服務部門從制造業中分離出來,通過專業化提升整體水平,而后被越來越多地“嵌入”到制造業的生產環節。生產性服務業提升了制造業效率,促進其轉型發展及升級改造。制造業的升級和轉型又對生產性服務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促進其技術和知識引入,提升其整體服務水平。因此,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互動關系在相互作用及彼此依賴中表現出來。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互動關系研究大多是基于產業和區域兩個層面展開,既有理論方面又有實證方面。理論方面的研究是以古典經濟學的分工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成本理論、社會網絡理論為基礎,后來又從價值鏈理論、共生理論探討二者的互動關系。實證方面主要從定量的角度測度二者產業的關聯度以及投入產出分析等。
(一)互動需求
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互動關系研究引起學界廣泛的關注,國內外學者在研究二者關系方面,提出:“需求遵從論”、“供給主導論”、“互動融合論”等理論觀點,支持“需求遵從論”觀點的學者有Cohen,Zysman(1987)、Guerrieri,Meliciani(2003)、張世賢(2000)、江小娟和李輝(2004)等,他們認為制造業服務功能的外部化,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是對制造業的一種需求遵從和附屬。支持“供給主導論”觀點的學者有 Markusen(1997)、Gmbel和 Walker(1998)、Eswarran,Kotwal(2001)、Francois 和 Woerz(2007)等,他們認為生產性服務業高度發展促進了制造業生產效率的提高。支持“互動融合論”觀點的學者有呂政(2006)、江靜(2007)、李江帆(2008)等,認為隨著信息技術廣泛應用,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之間彼此互動和融合。
(二)分工與價值鏈
Markusen(1989)[7]和 Francois(1990)[8]認 為 隨著社會分工的深入和生產的專業化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和制造業互動關系逐漸形成。Porter(1998)[9]從社會分工和社會化生產角度解釋了生產性服務的剝離和獨立發展過程。陳憲(2004)[10]認為分工越細,交易費用越高,就越需要中介組織,生產性服務業的不斷深化社會分工,促使制造業的交易成本降低。從價值鏈角度探討二者互動機理的主要學者是Porter(1998)[11],他認為產業價值鏈大致包括上游供應商、中游制造商、下游分銷商、消費者,上游、下游這兩個環節集中的基本上都屬于生產性服務。高峰(2007)[12]認為應把制造業生產過程的生產性服務環節占有資源釋放出來交由專業化的生產性服務企業完成。價值鏈的鏈接是產生共生關系的內因,內因是成本降低價值增值,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之間正是建立了這種對雙方獲益的互利關系,就形成了共生關系。
(三)產業關聯
曹毅等(2009)[13]運用投入產出表分析天津市二者的產業關聯,研究得出生產性服務與制造業間存在較好的產業關聯,但是,生產性服務業水平尚不能支撐向高端制造業的升級。高覺民、李曉慧(2011)[14]通過構建協同互動模型,研究得出二者間的內部各部門呈現出產業關聯特征。張曉濤、李芳芳(2012)[15]采用向量自回歸模型(MS-VAR)對我國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相互關系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對制造業的影響要大于制造業對生產性服務業的影響。王成東(2015)[16]以SFA和C-D生產函數為基礎構建了產業融合驅動因素驅動強度測度模型,基于效率視角,通過對中國內地30個區域兩大產業融合動因驅動強度及融合動因驅動效率,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二者融合互動的動因。唐曉華、張欣鈺(2016)[17]通過構建灰色網格關聯度模型,對我國2003—2013年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不同子行業的關聯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兩產業在時間演化趨勢上總體呈現M型的波動形態,兩者的關聯度存在階段性變化,整體關聯度不高,各細分子行業間內部關聯發展存在差異性。
四、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空間視角
隨著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從空間層面研究二者間的協同集聚問題,認為二者在空間上存在共同集聚與協同定位關系。國外學者Andersson(2004)[18]主要是從空間布局和地理位置的角度,說明二者互為函數,存在協同效應。王碩(2013)[19]運用面板數據,驗證了長三角地區27個地級以上城市兩個產業在空間分布上呈現出協同集聚特點,在此研究基礎上,提出不同規模城市的產業發展順序。吉亞輝、段榮榮(2014)[20]通過研究得出,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之間在空間集聚方面存在協同和相互促進效應,相互之間彼此促進,形成具有空間關聯的集聚效應。程中華(2016)[21]運用空間聯立方程研究方法,研究了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空間關聯與協同定位,結果表明二者在空間分布上存在著協同定位效應,并進一步指出成本和城鎮化率是兩個影響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空間分布和協同定位的重要因素。
五、知識密集型服務業(KIBS)與制造業的交互創新——創新視角
生產性服務業中KIBS是參與創新的主體,國外學者對KIBS與制造業知識流動進行研究,認為由此產生交互創新。Hauknes等(2008)[22]認為高技術制造業與其他產業的集群中,高技術服務業起著協調和橋梁的角色,對制造業的創新起到了催化作用。國內學者朱海燕等(2008)[23]從產業層面,指出KIBS與制造業的互動創新機制。呂民樂等(2015)[24]從專業化效應、知識轉移效應和創新嵌入效應三個角度研究了KIBS與制造業互動創新的機制。從價值鏈延伸的層面,聞乃荻等(2016)[25]提出知識密集型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互動的三個階段:初步互動階段、深度合作階段和全面融合階段;并從企業競爭力提升的角度探討了二者互動融合的影響因素。
六、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共生關系——生態學視角
從共生視角研究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關系是近幾年學界關注的焦點,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作為兩個共生單元,在一定的生態環境中,按照某種共生模式形成一定的相互關系。龐博慧(2010)[26]認為對稱性互惠共生是基于生態學視角,揭示二者間共生行為的演化。唐強榮(2009)[27]認為資源、技術和制度等環境因素制約兩個種群數量,并構建了二者共生發展模型,對中國產業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胡曉鵬(2009)[28]從產業共生的視角,提出融合性、互動性、協調性是產業共生的三個基本特征;并運用投入產出表對蘇、浙、滬三地融合性、互動性、協調性進行比較,通過動態比較,揭示了三地產業共生的基本特征。苗林棟(2014)[29]引用投入產出表,對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環渤海地區三大增長極的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共生關系進行比較,結果表明三地兩產處于非均衡內生狀態,環渤海地區兩產的內生狀態優于其他兩地。
七、述評與展望
(一)述評
從以上綜述來看,關于二者之間的關系主要是以產業經濟學、區域經濟學、新經濟地理學、貿易經濟學為理論依據,研究方法主要運用投入產出法、灰色關聯法、協整分析、面板模型、空間計量等方法,已有研究成果從宏觀層面對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很好的解釋。但是從中觀層面對生產性服務業細分行業與制造業的互動機理很難找到很好的理論剖析;針對微觀層面,缺乏結合實地調研企業的實證研究。從目前的“供給側改革”、“京津冀協同發展”、“中國制造2025”宏觀經濟背景下,研究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在產業、空間的關系具有現實意義,并對今后的研究做進一步的展望。
(二)展望
第一,空間視角下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跨地區產業協同發展問題。從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對于區位選擇與協同定位問題,主要集中在某一地區,兩個部門之間協同的原因和機理;實證研究也是以單一地區數據建立模型,驗證二者協同關系居多。但是針對跨地區,兩個產業以及細分產業之間協同問題是個盲點,因此探究跨地區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協同定位過程及協調效果將是我們研究的方向。
第二,創新視角下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企業信息化、網絡化問題。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互動融合外在表現形式是生產性服務外部化和制造業服務化。
生產性服務外部化的理論基礎、發生機制以及協調效果已有文獻講述;但是制造業服務化關鍵是分析企業如何從本地網絡獲取資源,社會網絡的存在成為制造企業實現服務化、創新化的途徑和媒介。因此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兩種企業在信息化、網絡化吸取資源,探究制造業服務化實現路徑將是我們研究的方向。
[1]Greenfield H.Manpower and the Growth of Producer Service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6:37-47.
[2]赫伯特.C.格魯伯,邁克爾.A.沃克.服務業的增長:原因與影響(中譯本)[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3.
[3]Hansen,N.The Strategic Role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J].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1994(1).
[4]鄭吉昌,夏晴,2005.論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與分工的深化[J].科技進步與對策(2).
[5]李寧,韋顏秋.天津市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研究[J].地域研究與開發,2016,35(6):12-16.
[6]Coffey W.J.The geography of producer services[J].Urban Geography,2000,21(2):170-183.
[7]Markusen J.Trade in Producer Services and in Other Specialized Intermediate Input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9,236(1):81-89.
[8]Francois J.Producer Services,Scale,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J].Oxford Economic Papers,1990,318(4):101-108.
[9]Porter M E.Clusters and New Economics of Competetion[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297(11):77-91.
[10]陳憲,黃建鋒,2004.分工,互動與融合:服務業與制造業關系演進的實證研究[J].中國軟科學(10):65-71.
[11]Porter M E.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76(6):77-90.
[12]高峰,2007.全球價值鏈視角下制造業與服務業的互動[J].現代管理科學(1):43-45.
[13]曹毅,申玉銘,邱靈.天津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產業關聯分析[J].經濟地理,2009,29(5):771-776.
[14]高覺民,李曉慧,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互動機理:理論與實證[J].中國工業經濟,2011,279(6):151-160.
[15]張曉濤,李芳芳.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互動關系研究——基于MS-VAR模型的動態分析[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2,52(3):100-106.
[16]王成東.裝備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融合動因驅動強度測度研究——基于效率視角的實證分析[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5,32(3):60-64.
[17]唐曉華,張欣鈺,2016.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聯動發展行業差異性分析[J].經濟與管理研究(7):83-92.
[18]Andersson,Co-locat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er services:A simultaneous equationapproach,working paper,2004.
[19]王碩,2013.生產性服務業區位與制造業區位的協同定位效應——基于長三角27個城市的面板數據[J].上海經濟研究(3):117-124.
[20]吉亞輝,段榮榮,2014.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的空間計量分析:基于新經濟地理學視角[J].中國科技論壇(2):79-84.
[21]程中華,2016.城市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空間關聯與協同定位[J].中國科技論壇(5).
[22]Hauknes J K M.2008.Embodied knowledge and sector lingkages:an input-output approach to the interaction of high-and low-tech industries.Research policy,RESPOL-2232:1-11.
[23]朱海燕,魏江,周泯非,2008.知識密集型服務業與制造業交互創新機理研究[J].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1-7.
[24]呂民樂,安同良,2015.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對制造業創新的影響研究[J].華東經濟管理(12):134-138.
[25]聞乃荻,綦良群,2016.知識密集型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互動融合過程及影響因素研究[J].科技與管理(2):7-14.
[26]龐博慧,郭振,2010.生產性服務業和制造業共生演化模型研究[J].經濟管理(9):28-35.
[27]唐強榮,徐學軍,何自力,2009.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共生發展模型及實證研究[J].南開管理評論(3):20-26.
[28]胡曉鵬,李慶科,2009.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共生關系研究——對蘇、浙、滬投入產出表的動態比較[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33-45.
[29]苗林棟,潘文卿,2014.中國三大增長極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共生關系比較[J].技術經濟(11):36-43.
(責任編輯:C 校對:L)
F062.9
A
1004-2768(2017)05-0153-04
2017-03-13
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課題,首都流通業研究基地開放課題“推進互聯網+改造,優化京津冀流通業產業布局”(JD-KFKT-2016-04);天津市哲學社會規劃項目(TJYY16-024)
李寧(1983-),女,河北蠡縣人,河北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天津商業大學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產業經濟學;韓同銀(1962-),男,山東菏澤人,河北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建筑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