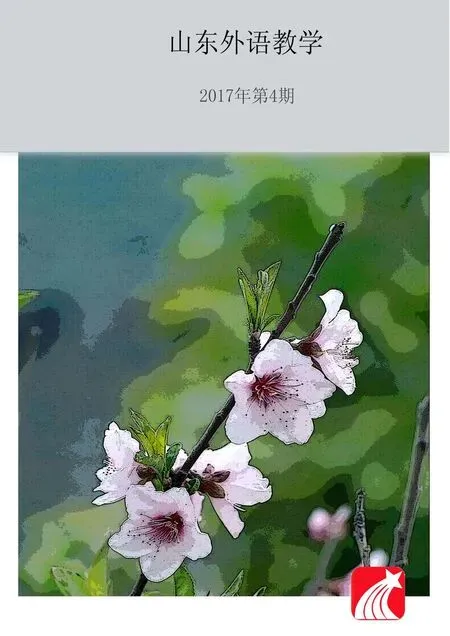西方浪漫主義與五四時期現代自我的生成
——以《沉淪》為例
尚曉進
(上海大學 外國語學院, 上海 200444)
比較文學研究
西方浪漫主義與五四時期現代自我的生成
——以《沉淪》為例
尚曉進
(上海大學 外國語學院, 上海 200444)
西方浪漫主義與中國現代自我的生成密切相關。郁達夫的《沉淪》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五四一代基于浪漫主義話語的主體構建模式,對《沉淪》做癥候式閱讀,可辨析這一主體生成的內在機制及隱含的歷史疑難。在展開浪漫主義“自我確立”的意識形態主題后,文本隨即顯示出自我解構的征兆。主人公以西方浪漫主義話語為資源,將個體確立為具有鮮明主體意識的現代自我,但不同于啟蒙傳統中具有行動力的理性主體,這一現代自我屬于感傷式的主體類型。主人公自我確立以壓抑歷史力量為代價,但歷史之力終究撕破文本光滑的表面,凌空蹈虛的主體建構工程也遭遇潰敗。作為郁達夫筆下“零余人”的代表,主人公折射了一代知識分子遭遇的歷史疑難,這使得作品富于國族寓言的意味。
浪漫主義;現代自我;《沉淪》;癥候式閱讀;歷史疑難
1.0 引言
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浪漫主義傳統是“十九世紀歐洲浪漫主義運動在亞洲的遲緩的迥響” (馮奇,1990: 170),從一開始就與啟蒙現代性糾纏在一起,是在“一種總體的啟蒙背景中實現自身的運動和發展的”(馮奇,2001:34)。浪漫主義尚情、尊主觀、個人主義的傳統呼應五四一代主體覺醒、個性解放的要求,為一代青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啟蒙資源。受浪漫主義影響,五四新文學中出現了一類新型人物形象,他們情感張揚,具鮮明的個性和主體意識,通常被視為現代自我的代表。作為浪漫主義文學的代表作,郁達夫的《沉淪》(1921)以對情感、欲望和自我意識的書寫確立了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但它留有西方浪漫主義的明顯烙印,體現出雜糅的品質,其文本癥候極為顯露,因此,也獨具思想史的意義。以《沉淪》為案例研究,可具體辨析基于西方浪漫主義話語的現代自我的生成機制,也可更好地觀照異質話語與本土語境之間的裂隙。
2.0 《沉淪》與文本的癥候
在《沉淪》中,郁達夫塑造了一位感傷式的浪漫主義人物形象,主人公“他”為20歲左右的留日學生,敏感、孱弱、內省,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沉醉于自然美景,為愛欲折磨,從偷窺發展到買春,最終愧對自己的沉淪而欲投海自盡。有意味的是小說的結尾。評論家普遍認為,主人公意欲投海自殺前的一番聯想和愛國主義的表白極為突兀,巴金曾評議道,“結尾有些‘江湖氣’,頗象元二年的新劇動不動把手槍做結束”(雁冰,2010:304)。但研究者對這種突兀性做深究的并不多。傳統上,解讀大多沿現代主體性和民族國家意識兩個方向展開,兩條思路似乎并行不悖,被整合在啟蒙救亡之宏大主題下。1927年,鄭伯奇在論及郁達夫的創作脈絡時,提出,“作者的主觀,既然由狹隘的自我,擴張到自己的身邊,自己的周圍,自己所處的社會和時代;因而,當然的結果,他的感傷的情緒,也由個人,逐漸擴大到社會人類……”(1985:19)這一論斷認為,《沉淪》的結尾預示了作家主題發展的線索,五四啟蒙運動催生的個體意識,必然走向與集體和民族國家結構的聯結。這一觀點貫穿了《沉淪》的批評傳統,錢理群等史家對此做了精要概括:“郁達夫筆下病態人物的命運,又是與祖國民族的命運相聯的,祖國的貧病也是造成青年‘時代病’的重要原因”(1998:75)。這一診斷無疑是準確的,但在個體與國家必然關聯的總體性視野下,文本隱含的斷裂被方便地抹平,文本裂痕似乎不再具有細究的必要,但從文學生產的角度來看,這點恰恰具有闡釋學的意味。
較之中國學者,西方學者更重視這一問題的闡釋。一個原因在于,西方批評話語并未自動合法化個體與社會和國家的內在關聯,尤其對浪漫主義傳統而言,兩者更多是沖突和對峙的緊張關系。研究者伊根認為,“試圖在一個探析病態人格的故事里,放進民族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議題,必須將之視為一種失敗。從故事內部的證據來看,民族主義和反帝國主義對主人公的心理崩潰并未產生影響,這些仿佛是事后添加上去的,與故事的發展不相干”(Egan,1977:320-321)。西方學者多受新批評影響,傾向于將作品視為和諧統一的有機體,力求以某種解釋性的框架,消解結尾的突兀感,使作品呈現出內在的統一。這一闡釋預設促使伊根以反諷視角觀照主人公的激烈情緒,由此消解結尾的民族主義意味。但另一些研究者并不回避作品的民族主義主題,比如,登頓就提出,“《沉淪》主人公折射了五四自我悖論的焦慮感與復雜性”(Denton,1992:120),現代自我范式的建立以五四反傳統為代價,卻無法使自我抵達社會和民族新生的可能,這使中國知識分子陷入傳統與現代的兩難境地。登頓的詮釋充滿洞見,但囿于傳統批評范式,他從文化歷史層面尋求一種融通的解釋,以儒家傳統、文化民族主義的概念置換了民族國家的政治訴求。這些研究表明,《沉淪》突兀的結尾值得深究,不可簡單地視為技術缺陷,也不能以啟蒙救亡的整體性敘事自動將它縫合,或者,以合理化的闡釋強行賦予文本內在的整一性。
本文從文學生產理論的視角出發,明確將《沉淪》的突兀結尾指認為文本的“癥候”。主人公最后發出這樣的吶喊:“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罷!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里受苦呢!”(郁達夫,1992:75)①作品在風格和形式上明顯出現斷裂,貫穿全篇的感傷風格突轉為民族主義的激昂論調,浪漫主義的自我確認變成愛國主義的訴求,孤獨的“他”不可思議地成了心系家國的熱血青年。不僅如此,主人公還突兀地將自己的沉淪歸咎于祖國的積弱,這一責難在邏輯上頗為牽強,并無相應的敘事支撐。突兀感恰恰暗示某種沉默或敘事的盲區,但它并非可以填補的空缺或可彌補的缺陷,這正是阿爾都塞和馬歇雷等人所言的文本癥候。在這些理論家看來,一切文本都是未完成、非統一、存在裂痕的,是文本不可避免的他者性的顯露,在對意識形態素材進行加工時,“幾層意義并置沖突,形成一種形塑文本的尖銳的他者性:這種沖突無法解決或消除,只能呈現”(Macherey,1978:91)。相對于一般文本來說,《沉淪》的裂痕更為外露,這與它賴以生成的文化或意識形態系統密切相關。它本身就是東西交流和碰撞的產物,作為其生產素材的意識形態系統本身就是雜糅的、臨時屬性的,而非封閉的、總體性的。《沉淪》的文本癥候暴露了其意識形態素材內部的裂痕和沖突,也呈現出五四時期現代自我生成的復雜狀況。
3.0 浪漫主義話語與現代自我的建構
作為意識形態素材內容的西方浪漫主義為《沉淪》提供了“自我定義”和“自我確立”這一主題,亦即馬歇雷所言的“意識形態主題”(the ideological theme)。“自我確立”是《沉淪》統攝全篇的總體意向,《沉淪》在現代文學史上的意義也正在于此:“從思想史的角度,‘自我’的發現,進而確立自我作為世界的中心,無疑是這一時期浪漫主義文學的重點所在。其中典型代表非郁達夫莫屬”(陳周旺,2007:81)。郁達夫僅以“他”來指涉主人公是有深意的,這個“他”是清末民初一代青年的代表,其自我確立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映射這一代青年的集體經驗。
成為自我,首先需要從嵌入其中的整體性結構上分離出來,成為個體,即一種原子式的存在。故事開始時,主人公去國離家,已將自己置于一種近乎人際真空的境地中,為接下來的自我確立鋪平了道路,也為這一浪漫主義神話提供一個完美的實踐范本。對浪漫主義者而言,“自我”并非是自然而然的存在,個體必須確立自我的存在,將個性(individuality)轉化為“自覺的自我”,并以反思能力外化自我的內核,使之成為可表達和表征的對象。同西方浪漫原型人物一樣,主人公圍繞自然和愛情兩個母題展開自我確立的歷程。一方面,“他”疏離人群,獨自漫游鄉間,這原本就是一種疏離社會、反抗權威和自我確立的姿態,直觀地顯示出,“個體已從宗教和社會的傳統束縛中解脫出來,感知到自我深不可測的靈魂”(Schneider, 2007:92)。另一方面,他渴望異性的愛戀,追尋一個“安慰我體諒我的‘心’”(P47)。對浪漫主義者而言,愛既是有意味的人際聯結方式,也是感受自我和確立個體存在的途徑,“愛情的力量在于它以愛人的特異性為放大鏡,透過它來體驗世界和自我”。(Breithaupt,2005:557)
不同于西方浪漫原型的是,主人公的自我建構依托于他的閱讀經驗,具有明顯的衍生性和模仿性,與其說“他”是一個浪漫主義人物,莫若說他有意識模仿浪漫主義經典人物形象。細究《沉淪》中的一些典型場景,可以看到,意識、文本與主體呈現出一種奇妙的同構關系。“他”的特定體驗喚起閱讀記憶,文本意象反過來印證主體經驗,書本成為主人公感覺自我、確認生命存在的重要媒介,自我建構以“主體—文本—主體”循環投射模式展開。這在開篇場景中即有體現:“他”捧著華茲華斯的詩集,漫步鄉間,沉醉于秋日的美景,時而吟誦華茲華斯的《孤獨的刈麥女》(TheSolitaryReaper),又將詩歌翻譯成中文,原詩和主人公的譯文大段穿插在小說文本中。看似突兀的大段引文恰恰暗示閱讀和文本對于主人公自我確認的關鍵作用,這不僅是笛卡爾“我思故我在”式的自我存在的確認,更是一種“我讀故我在”的主體建構經驗,無論是其情感方式,還是漫步鄉間的姿態都有浪漫主義藍本可依,主人公的經驗實質上折射了五四一代融合西學資源的自我構建進程。
確切而言,主人公以挪用浪漫主義話語的方式將自我確立為一種感傷式的現代主體,研究者認為,“他”尤其明顯地投射了維特的影子,“郁達夫在探尋自我的影像時,維特式人物原型似乎總是浮現在他的腦海中”(Lee,1973:280)。作家并未直接提及《少年維特的煩惱》,但它構成《沉淪》重要的潛文本,這一互文關系提示我們,需要關注感傷主義對于現代自我的生成作用。②泰勒認為,現代自我的觀念與一種內在感(inwardness)聯系在一起,成為自我必然伴隨著內在化(internalization)的過程,而18世紀末興起的浪漫主義提供了一種新的內在化路徑。他稱之為“以本性為根源”(nature assource)的觀念,即從“我們的內部,尤其是在情感中尋求真理的觀念”(Taylor,1989:367-9)。作為浪漫主義的先聲,感傷主義不僅預示情感的轉向,也標志著一種新型的主體認同路徑,“感性自我在此取代理性成為人類本真的、標準的內在自我的代表”(Brodey,2005:16)。維特無疑是感性文化孕育的新型自我類型,《沉淪》主人公復制了這種內在化模式,向內或本性敞開,以感性和意識確認個體的存在,并從內在性中尋求道德依據。然而,這種內在化也意味著激進的主觀主義,感性自我往往會陷入病態的自我意識,甚至滑入唯我論的泥淖。和維特一樣,主人公為過于發達的內省意識所困擾,他偶遇日本女學生時的一番心理活動足以說明問題。他為少女所吸引,但太過自卑不敢打招呼,事后左思右想,責難道:“你既然怕羞,何以又要后悔?既要后悔,何以當時你又沒有那樣的膽量?不同她們去講一句話”(46)。第二人稱“你”別有意味,暗示他不斷反觀自我,審視和評判自我的傾向,而這最終將他推向自我分裂的境地,關于這點,后文將作進一步分析。
概言之,《沉淪》主人公在異域相對孤立的空間內,首先成為獨立個體,再以浪漫主義話語為資源,展開自我定義,將自己確立為一個具有感傷色彩的現代自我。不同于啟蒙理性主義孕育的現代個體,這個“他”以毫不節制的情感、欲望和自我意識張揚主體性,確立自我、個體在文化史上的鮮明存在。同時,“他”也是內省的,易感的,耽于思考,而怯于行動,為過度發達的自我意識所困擾。在一定意義上,《沉淪》主人公的自我確立映射了五四時期基于浪漫主義資源的現代自我生成模式。
4.0 文本的自我解構
馬歇雷指出,“在所有文學作品中,都可發現內部斷裂、離心的傾向以及它依賴特定條件生成的證據……作品絕不是連貫的統一整體,只是看似如此而已”(Macherey,1978:41)。《沉淪》的文本癥候非常明顯,對之做癥候式解讀的目的不在于暴露文本癥候,而是為了“揭示文本無力了解自己之處,是顯明文本生產的那些條件(它們銘刻在文字內)”(Eagleton,1976:43)。文本在展開“自我確立”的意識形態主題后,隨即顯示出自我解構的征兆,以癥候式閱讀策略來剖析文本中的細微裂痕,可辨析出被壓抑到文本潛意識的潛隱內容。
前文指出,主人公的自我確立圍繞兩個母題展開,一是追尋自然,與自然融合;二是追求愛情,在與他人的聯系中確認個體本真而獨特的存在。在剖析主人公與自然融合的姿態之前,先看歌德在《少年維特的煩惱》中展現的經典場景。在5月10日的信件中,維特描述沉醉于自然的狂喜,感覺草木昆蟲都“離我的心更近了”,在神性灌注的瞬間,他直覺到神的存在,“我感受到按自身模樣創造我們的全能上帝的存在,感受到將我們托付于永恒歡樂海洋之中的博愛天父的噓息”(1997:3)。對浪漫主義者而言,自然代表著自我異化和分裂前的原初狀態,追尋自然是對原初整體性和同一性的追尋,也是對現代社會一系列對立和分裂的美學克服。歌德的這段描寫體現的正是異化自我尋求同一性的詩性努力,具有明確的宗教性和超越維度。在維特這里,自然不僅是浪漫個體展開自我定義的舞臺,更是心靈與普遍的精神、至高的存在或普遍的自我展開對話的劇場。
《沉淪》主人公同樣沉醉于自然美景,隨之而來的也是一個詩意盎然的瞬間:
在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里,在這澄清透明的以太中,他的身體覺得同陶醉似的酥軟起來。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懷里的樣子。他好像是夢到了桃花源里的樣子。他好像是在南歐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里貪午睡的樣子。(40)
主人公融入自然的懷抱,西化的表述召喚出浪漫主義的經典情境,初讀之下,很像愛默生以“透明的眼球”隱喻的人與自然合一的神秘體驗:個體的邊界消融,自然的輪廓變得透明,宇宙化作透明的以太,或一種澄明的精神性物質。然而,細加比較,可發現兩者微妙的差異。《沉淪》的這個瞬間似是而非,敘事裂痕隱現于文本細節。主人公以“母親”和“情人”來比喻自然,無意中泄露了其潛意識的渴望,身在異域,他渴望的是親情和愛情,而非自然的精神屬性。語言和意象在此背叛文本的意圖。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其中的地理名詞。主人公仿佛夢到桃花源,又恍惚去了南歐的海岸。桃花源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是世外桃源和烏托邦的代名詞,在時空之外,隔絕歷史和政治的暴力,“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南歐是一個模糊國家疆界的地理名詞,主人公從中國來到日本,此時遙想南歐,透露的是一種跨國的、世界主義的情懷。人與自然融合觸發的并非個體意識與宇宙精神的合一,而是跨時空、跨國界的自由聯想。自然成了超越國族身份的庇護所,自我建構蛻變為對歷史的逃避。無怪乎華茲華斯的詩歌并未觸發人物的哲性沉思,只是激起一片模糊的感傷。主人公的浪漫主義姿態失去原初話語的意指功能,敘事暗中偏離“自我確立”的意識形態主題。
主人公自我建構的另一維度是對愛的追求,但這直接導致文本的自我解構。在休姆、斯密、盧梭等哲人看來,感性、愛和同情這些品質具有締結人際紐帶、構筑倫理根基的力量。主人公深諳這套話語,渴求一個能安慰他、體諒他的‘心’,祈求蒼天賜他“一個伊甸園內的‘伊扶’”(40)。“伊扶”即夏娃,以伊甸園的夏娃指稱理想愛人有耐人尋味的深意。他自卑于“支那人”的身份,為日本女同學所吸引,卻無法和她們交往,只能將愛的對象虛幻化,抹去現實愛人必然牽涉的民族國家壁壘。在主人公以高蹈的浪漫主義姿態漫游自然時,愛欲將他猛然拉回民族國家的歷史時空。他尖銳地意識到自己國族他者的身份,也看到身為弱國子民的悲愴處境,普遍主義的心靈、同情和愛突然變得無比空洞。由此,主人公身在異國的境況構成一種奇異的悖論,一方面,“他”離群索居,得以在相對孤立的空間里建構自身的主體性,另一方面,在與異國“他者”的對立中,其支那人身份愈發清晰。主人公深覺“我”是孱弱、落后、被征服的劣等國民,無法擺脫的國族身份危機實際上消解了浪漫主義自我定義的神話。
在《<沉淪>自序》中,郁達夫提到作品“有幾處說及日本的國家主義對于我們中國留學生的壓迫的地方,但是怕被人看作了宣傳的小說,所以描寫的時候,不敢用力,不過烘云托月的點綴了幾筆”(1992:18)。癥候式閱讀的結果顯示,縱使沒有這烘云托月的幾筆,文本仍會現出裂痕。《沉淪》主人公的自我確立以對歷史的壓抑為前提,浪漫自我實為歷史之我的逃遁,無法書寫的內容被推入文本潛意識,然而,被壓制的潛隱主題必然從裂痕處綻出,撕裂貌似嚴絲合縫的文本表面,烘云托月的幾筆并非點綴,而是混沌歷史之力沖破壓抑后的總體爆發。
5.0 現代自我的歷史疑難
浪漫主義的自我確立與西方社會的歷史轉型密切相關,傳統農耕社會解體為個體提供了自我確立的空間,同時,也成為歷史的迫切需要。對20世紀初的中國而言,現代自我的生成同樣為時勢所促成。郁達夫追溯了這位浪漫主人公的“前史”:“他”出身士紳家庭,成長于劇烈變動的大時代,舊制度崩潰,新秩序遠未形成,社會對個體失去原有的控制力,在造成動蕩的同時,也給青年一代更多自由的空間。主人公個案的典型意義在于,它折射了現代中國轉型之際,個體從社會結構上剝離出來的境況,舊的家族、宗法和皇權體系已經碎片化,另一方面,內憂外患中的國家未能形成強有力的新型結構,將個體妥帖地納入社會的鏈條中。郁達夫筆下的“零余人”形象敏銳地折射了一代青年人的飄零感。需要深思的是,這一現代自我的生成為何顯得疑難重重,以主體崩潰的悲劇結果告終?
自我性(selfhood)是與善糾纏在一起的主題,我是誰的問題必然牽涉道德的維度(Taylor,1989)。浪漫主義的內在化認同將道德依據置于本性之中,感性被賦予倫理的維度,敏感的靈魂對他人苦難感同身受,移情和同情能力促成德性行為,但過度發達的感性也隱含自我分裂的可能。斯密在《道德情操論》里具體辨析了感性的倫理作用機制,他提出,社會道德評價可憑借感性力量內化為一種自我評判的機制:“當我努力考察自己的行為時,當我努力對自己做出判斷并對此表示贊許或譴責時,在一切此類場合,我分成兩個人”(2003:140)。斯密敏銳地看到,這種“占主導地位的主體類型”出現于18世紀末,“自我身份分裂或衍生為‘旁觀者’和‘行為者’,自我意識存在于這種雙重關系中、并借助這種關系展開”(Rowland,2008:195)。他以鏡子的看與被看比喻感性的倫理作用機制,但問題是,鏡子結構嵌入自我意識后,并不必然導向社會性的倫理行為,對孤獨個體而言,內置的鏡子更可能導致自我毀滅的悲劇。《沉淪》主人公向內求索,窺見的是情欲的黑暗深淵,然而,內置的鏡子只是將他囚禁于病態的自我意識之中。浪漫主義的內在化路徑原本有其自身的缺陷,《沉淪》主人公特定的歷史情境決定,基于浪漫主義的主體建構工程必然將他推入深刻的主體危機。
主人公一開始就表現出內在分裂的傾向,情欲則將他推入深刻的心理危機中。對處于孤絕之境的主人公而言,愛欲“只能以反社會、自我毀滅的方式表達出來:一是自慰,將欲望的對象轉到自我身上;另一種就是偷窺,欲望主體與客體保持距離,從中獲得快感”(Denton,1992:112)。主人公有發達的自我意識,也有敏感的道德意識,性觀念受傳統倫理規約,自慰和偷窺令他倍感羞愧。郁達夫對主人公的欲望和罪惡感描寫得細致入微,“他本來是一個非常愛高尚愛潔凈的人”(55),但一到邪念發生的時候,智力和良心都不管用,犯了罪之后又深感痛悔。另一方面,近代醫學將自慰定義為一種需要矯正的疾病,傳統倫理令他自責,以科學為名的知識則令他恐懼。病態自我意識將他置于無休止的自我審視之中,內置的鏡子損害了其身心健康。
自慰將主體轉化為欲望的對象,在主體與客體間形成閉合的環路;偷窺(voyeurism)則呈現了欲望的挫敗、人際溝通的不可能。第一次偷窺的對象是旅店主人家的女兒,他窺見“雪樣的乳峰”、“肥白的大腿”和“全身的曲線”,女子在他眼里成為“赤裸裸的‘伊扶’”(59)的化身。基于弗洛伊德理論的分析一般將偷窺看作父權制性秩序的若干驅動力之一,因為偷窺首先意味著對他人的對象化:“看的同時,卻要避免被看,對客體施加權力,但要避免被對方控制,主體意欲擺脫對其他主體的依賴,偷窺滿足了這一心理需要”(Charnon,1989:93)。但《沉淪》呈現的是全然不同的心理機制,在主人公的凝視下,店主女兒的裸體成為純粹的、未被文化秩序編碼的自然,只有幻覺中的“伊扶”才可能成為他欲望投射的對象。另一次偷窺實則為偷聽,他偷聽到一對戀人的偷情。偷窺總是與目光和凝視相關,那么如何理解這里的偷聽?拉康關于凝視的分析在此很有啟發意義,他引述薩特的分析,指出凝視效應不一定依賴于視覺物體,諸如樹枝的沙沙聲、窗簾的輕微晃動都可產生這一效應,凝視呈現出他者之場域,“在窺陰癖者的活動中,凝視讓他不安,壓倒他,使他羞愧得無地自容”(Lacan,1998:84)。偷窺者投射出的目光反射回來,指向外部世界的有意識的觀看變成一種評判自我的倫理意識,“他”對自我的觀看使之成為被看者。這一分析與斯密喻說的內嵌鏡子結構是一致的,自我內部“旁觀者”與“行動者”的分裂在偷窺場景進一步加深,偷窺向外投射的目光折射成強力的自我凝視,旁觀者看見行動者的偷窺。凝視直接將主體拋入危機,他看見他成了卑賤的偷窺者,而非他自以為的高蹈的浪漫自我,主人公的自我建構工程頃刻間土崩瓦解。至此,文本徹底解構預設的意識形態主題,沿另一條邏輯推進:“他”從山頂走下,去妓院買春,在羞辱感中,再次爆發出祖國富強的呼喊,文本被壓制的歷史力量破堤而出。《沉淪》主人公的悲劇是自我放逐的結果,更是特定歷史情勢的必然,生命能量只能以自我毀滅的方式向內釋放,其個體悲劇也不具備維特之死所隱含的現代性批判的意味。歸根結底,《沉淪》講述的是一則關于絕對自我之不可能的政治寓言。
6.0 結語
如詹姆遜所言,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都可被當作民族寓言來閱讀,即便是“那些看似私人性的、被賦予利比多趨力的文本,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出政治的維度”(Jameson,1986:69)。《沉淪》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私欲的、力比多的文本,它講述的是一個青年人性的苦悶,是被壓抑的、無法以正常方式釋放的力比多,但投射的卻是一則關于現代自我生成的國族寓言:個體從舊的、崩潰的體系上剝離出來,以西方浪漫主義為思想資源,將自我確立為具反思式自我意識的現代主體,但這一過程以對歷史的壓抑為代價。另一方面,若不被納入社會的和國家的結構之中,這一現代自我無法將生命能量轉化為有意義的、社會性的行動,必然成為深具漂零感和無力感的“零余人”。《沉淪》思想史的意義在于提醒我們,需要進一步厘清浪漫主義對于中國現代性轉折的復雜意味,而不是在啟蒙的總體視野下闡釋它。
注釋:
① 出自《沉淪》的引文后面只在括號內標注頁碼。
② 《少年維特的煩惱》是德國狂飆突進運動中的重要作品,也被視為一部典型的感傷小說。歌德在小說中塑造了一位浪漫主義主人公的原型形象,少年維特內心敏感、情感熱烈,對自然有著特殊的敏感,與世界和自我格格不入,因無望的愛和厭世情緒而最終自殺。感傷主義是浪漫主義的先聲,流行于18世紀后半葉,直接得益于虔敬主義的滋養。虔敬主義為新教路德宗教會中的一派,強調內在生活和自我反省,認為這是抵達神性的真正路徑,虔敬主義通過教育和辦學等途徑有力推動了18世紀感傷文化的興起。
[1] Brodey, I. S. B. On Pre-Romanticism or Sensibility: Defining Ambivalences[A]. In Michael Ferber (ed.).ACompaniontoEuropeanRomanticism[C].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10-28.
[2] Breithaupt, F. Romanticism, Individualism and Ideas of the Self[A]. In Gregory Claeys (ed.).EncyclopediaofNineteenth-CenturyThought[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Ltd, 2005.554-563.
[3] Charnon, L. D. Voyeurism, Pornography and “La Regenta”[J].ModernLanguageStudies, 1989,19(4):93-101.
[4] Denton, K. A. The Distant Shore: Nationalism in Yu Dafu’s “Sinking”[J].Chinese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 Vol. 14 (Dec., 1992): 107-123.
[5] Eagleton, T.CriticismandIdeology:AStudyinMarxistLiteraryTheory[M]. Norfolk: Lowe & Brydone Printers Limited, 1976.
[6] Egan, M. Yu Dafu and the Transit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A]. In Merle Goldman (ed.).ModernChineseLiteratureintheMayFourthEra[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309-324.
[7] Jameson, F.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J].SocialText, No. 15 (Autumn, 1986): 65-88.
[8] Lacan, J.TheFourFundamentalConceptsofPsychoanalysis[M].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8.
[9] Lee, O. L.TheRomanticGenerationofModernChineseWriter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10] Macherey, P.ATheoryofLiteraryProduction[M]. Trans. Geoffrey Wal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11] Rowland, A. W. Sentimental Fiction[A]. In Richard Maxwell (ed.).TheCambridgeCompaniontoFictionintheRomanticPeriod[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191-206.
[12] Schneider, H. J. Nature[A]. In Marshall Brown (ed.).TheCambridgeHistoryofLiteraryCriticism(Vol.5)[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92-114.
[13] Taylor, C.SourcesoftheSelf:TheMakingofModernIdentity[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4] 陳周旺. 從啟蒙到革命:中國浪漫主義的嬗變[J]. 文史哲,2007,(6):81-86.
[15] 歌德. 歌德文集[M]. 楊武能 等譯.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
[16] 馮奇. 郭沫若與郁達夫的浪漫世界之比較[J].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0,(2):170-186.
[17] 馮奇. 現代性語境中的中國浪漫主義運動[J]. 文學批評,2001,(1):33-41.
[18]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9] 亞當·斯密. 道德情操論[M]. 蔣自強 等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20] 雁冰. 通信(摘錄)[A]. 王自立,陳子善 編. 郁達夫研究資料(下)[C].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304.
[21] 郁達夫. 沉淪[A]. 郁達夫全集(第一卷)[C]. 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39-75.
[22] 郁達夫. 《沉淪》自序[C]. 郁達夫全集(第十卷)[C]. 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18-19.
[23] 鄭伯奇.《寒灰集》批評[C]. 陳子善,王自立 編. 郁達夫研究資料(下)[C]. 廣州:花城出版社,1985.12-22.
(責任編輯:任愛紅)
Western Romanticism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Self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A Symptomatic Reading ofSinking
SHANG Xiao-j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Western Romanticism functions as an important shaping force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self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Sinkingby Yu Dafu, to a certain extent, mirrors the self-conscious efforts of the generation of young intellectuals who strive for self-assertion and self-definition by appropriating romantic discourses. A symptomatic reading of the text reveals how it defeats its own ideological project. Unlike the free and rational self nurtured by the Enlightenment tradition, the modern self thus fashioned is sentimental, introspective and intensely self-conscious and can only exist by repressing the historical. The protagonist’s failed efforts at self-definition shed light on the historical predicament of the group of intellectuals who felt disconnected and disorientated in a time of political turmoil and radical changes. Viewed in this light, the text might be read as an example of what Fredric Jameson calls national allegory.
Romanticism; the modern self;Sinking; a symptomatic reading, predicament
10.16482/j.sdwy37-1026.2017-04-007
2017-04-13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西方浪漫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民族國家認同研究”(項目編號:17BWW023)的階段性成果。
尚曉進(1972-),女,漢族,安徽岳西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學,比較文學。
I106
A
1002-2643(2017)04-005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