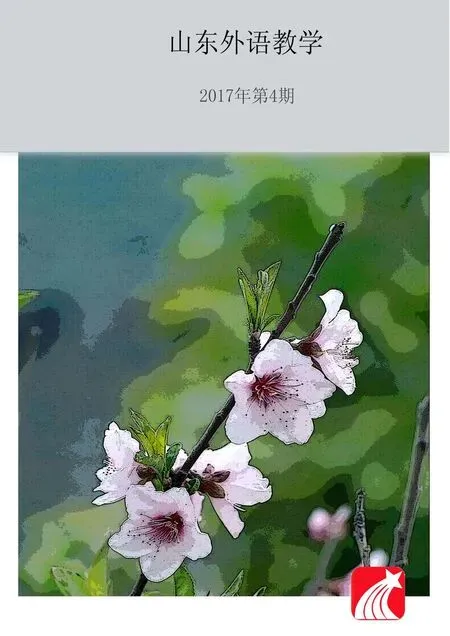基于項目學習的大學英語中華文化教學探索
——以“中國地方文化英語教學”課程為例
顧衛星 葉建敏
(蘇州大學 外國語學院,江蘇 蘇州 215006)
外語教學本土化研究
基于項目學習的大學英語中華文化教學探索
——以“中國地方文化英語教學”課程為例
顧衛星 葉建敏
(蘇州大學 外國語學院,江蘇 蘇州 215006)
“中國地方文化英語教學”按照文化主題設計單元教學任務,依托多樣性、交互性課程學習網絡資源平臺,開展基于項目學習的課堂文化教學與課外文化體驗,積極探索大學英語課程教學新思路,著力培養大學英語學習者的自主學習能力、團隊合作精神、以及傳播中華文化的英語應用能力。
項目教學法;合作性學習;文化傳播;英語應用能力
1.0 引言
中華文化內涵極其豐富,既包括燦爛輝煌的民族文化,又涵蓋特色鮮明的地方文化。在中華文化全面走向世界的背景下,在大學英語課程教授中華文化已勢在必然,因為這既是幫助大學英語學習者“有效傳播中華文化”的必然環節,也是“增強國家語言實力”和“提升國家軟實力”(《大學英語教學指南》,2015)的時代要求。
教學內容和教學模式是課程教學的兩個重要環節。“中國地方文化英語教學”課程顧名思義是以特色地方文化作為大學英語教學內容,旨在增強教學內涵及語篇的真實性和可理解性。但教學模式的選擇卻是需要認真探索的實踐課題,因為教學模式是提高教學效果、實現培養傳播中華文化英語應用能力這一重要教學目標的關鍵所在。
2.0 項目學習
2.1 項目學習的內涵
項目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PBL),也稱項目教學,源于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所倡導的“問題教學法”(武和平、張維民,2011:64)。它以發展學習者的思維品質和創造能力為宗旨,強調學習者在自主探究、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中進行有效的學習。
項目學習以建構主義和社會互動論等教育學理論為基礎,以一系列既定的教學項目和設定的具體學習任務為平臺,以學習者為中心,以過程性學習為特征,以交互性合作學習為媒介,“借助他人的幫助,利用必要的學習資源,解決現實中的問題”(高艷,2010:42)。在實現學習目標和完成學習任務的同時,掌握和發展必備的理論知識和實踐技能 (Beckett & Slater,2005),培養進一步學習的品質和能力。
2.2 項目學習的實施
項目學習是一項系統工程,是一個實踐的過程,其實施一般包括項目前階段、項目實施階段和項目后階段3個部分(李立、杜潔敏,2014)。項目前階段是項目的計劃和準備階段,具體包括人員分組和成員分工、學習任務界定(Grant,2002)、學習項目選定和學習計劃制訂(瞿少成等,2012)等具體步驟,是項目學習的基礎階段。
項目實施階段是一個解決問題的動態過程。項目成員在教師的導引和指導下,在項目同伴的配合和協助下,根據不同的任務分工,開展實踐調查、文獻梳理、數據收集、資料分析、學習總結、報告撰寫等實踐活動(張文忠,2015),以完成項目成員和項目團隊的學習任務,是項目學習的核心階段。
項目后階段是對項目學習過程進行系統梳理,對項目學習成果進行系統總結的階段,具體包括匯報學習發現、展示學習成果、反思學習過程、評價學習效果以及提升學習理念等環節,是項目學習的內化階段。
2.3 項目學習的特征
項目學習運用特定的學習情境、合作學習方式、多種認知和信息資源(高艷,2010),培養和發展學習者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具有開放性和合作性、實踐性和研究性等顯著特征(Alan & Stoller,2005),在學習內容的具體性、學習過程的實踐性等方面與傳統教學方法相比有其顯而易見的優勢。
首先,項目學習改變了以教師為中心、以灌輸知識為主體的傳統教學模式。項目成員自主建構學習共同體,以交互合作為學習媒介,主動獲取學習資源、積極建構學習過程、自主設計學習模式,在自主建構知識和發展能力的過程中,促進自己、他人以及團隊學習效果的最大化,在實現共同學習目標和完成共同學習任務的同時,培養項目成員的集體觀念和團隊合作精神(丁言仁、劉海平,2011)。
其次,項目學習以一系列既定的實踐項目和學習任務為平臺,努力提高和發展項目成員運用所學理論、知識和技能,發現、分析、研究和解決實際問題的實踐能力(劉和林、吳慶華,2016),培養項目成員的創新意識、思辨能力(張文忠,2012)和學習品質。
再次,項目學習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通過創設和提供真實、新穎的學習和實踐環境,激勵項目成員積極主動參與項目過程,充分發揮主人翁學習意識和學習的主觀能動性(李麗君,2009),以項目學習所取得的成就提升自我滿意度和自信心(Fried-Booth,2002),有效激發和維系學習動機(高艷,2010;王勃然,2013),促進學習的可持續發展。
3.0 基于項目學習的“中國地方文化英語教學”①
“中國地方文化英語教學”以內涵豐富的特色文化為教學內容,發揮基于文化主題設計的學程優勢,依托多樣性課程學習網絡資源平臺,開展基于項目學習的課堂文化教學和課外文化體驗。
3.1 課程教學保障
“中國地方文化英語教學”的文化主題和學習任務設計、配套學習資源建設、網站依托支撐等為開展基于項目學習的課程教學提供了便利和保障。
3.1.1 學程設計
“中國地方文化英語教學”的內容涉及“地理”、“歷史”、“語言”、“教育”、“科技”、“哲學”、“建筑”、“節日”、“民俗”和“藝術”等10個文化主題,每個文化主題包括民族精華概覽和地方特色闡釋兩大部分,設計了“主題理解”、“知識填空”、“信息匹配”、“段落翻譯”、“創新思辨”、“信息陳述”、“聽力訓練”、“口語操練”以及“論文寫作”9項學習任務。
3.1.2 配套資源
“中國地方文化英語教學”建設了開放、共享、易用的學習資源,包括“反映課程教學思想、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過程的核心資源”,如目標定位、知識模塊、難點重點、教學大綱、教學進度、課程教案、教學課件、方法手段、題庫建設、管理評估、問題思考、參考文獻等,以及“應用于各教學與學習環節,支持課程教學和學習過程,較為成熟的多樣性、交互性輔助資源”(教育部辦公廳,2012),如課堂教學活動實錄、課外文化體驗和對外宣傳活動等視聽作品和整理、翻譯出版的特色文化多媒體資源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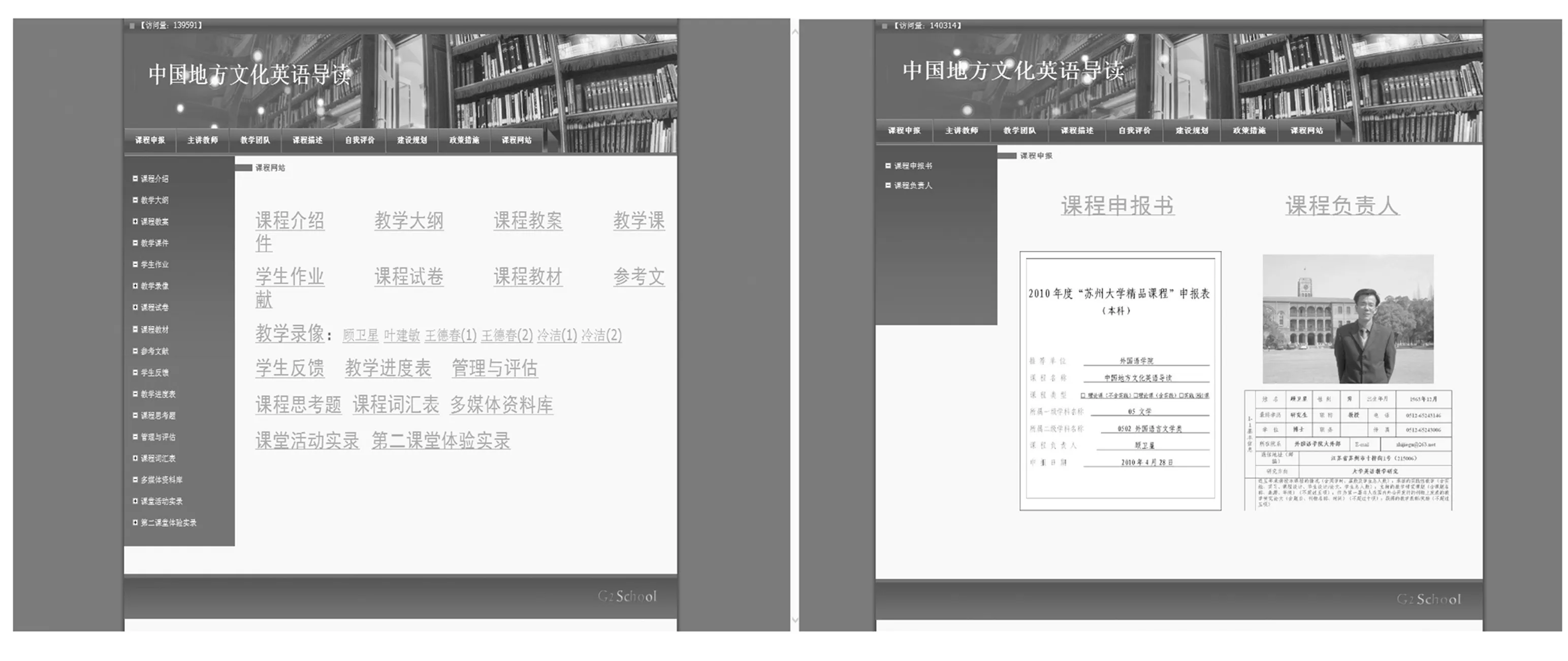
3.1.3 網站依托
“中國地方文化英語教學”建設了校級精品課程網站(2010年),并依托“大學英語應用類課程”國家精品資源共享課網站(201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愛課程”網站(2016年)等。為便于學習者方便、快捷地提取所需學習資源,“中國地方文化英語教學”還為課程教學升級搭建了針對PC端的Abook資源服務平臺,創建了針對移動端瀏覽的二維碼微學環境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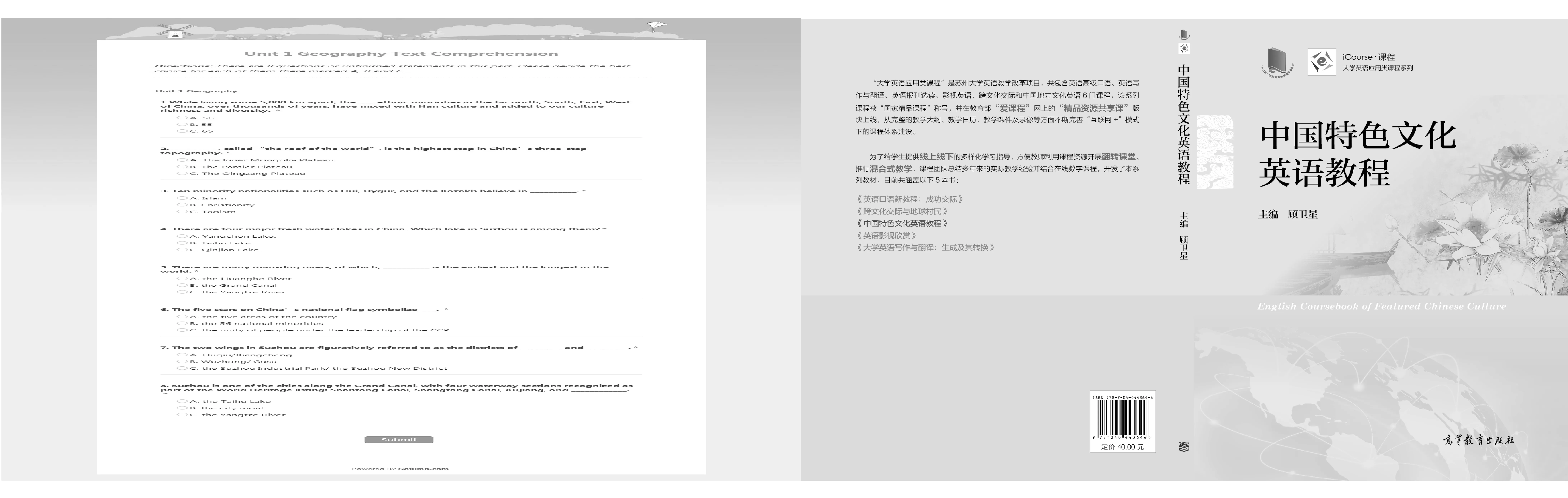
3.2 課堂文化教學
基于項目學習的課堂文化教學從10個文化主題中選擇8個用于項目學習,另外2個文化主題用于學生課外自主學習。課堂文化教學平均4課時(2周)完成1個文化主題教學,其流程如下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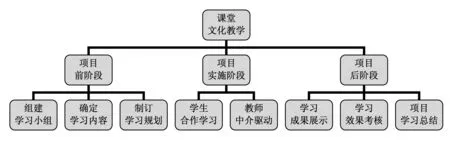
3.2.1 項目前階段
每個文化主題課堂教學的第1課時(50分鐘)為項目前階段,除進行相關文化主題知識介紹和英語表達技能訓練外,主要用于開展項目學習的相關準備。
3.2.1.1 組建學習小組
每個班級一般分為6-8個項目學習小組,每組4-5人。項目學習分組貫徹“同組異質”的原則,以學生自愿組合為主,教師調節為輔,以期通過學生間的親近度、熟悉度,營造和諧、融洽的學習氛圍,最大限度地降低學習過程中的壓力,因為“沒有精神壓力的學習狀態是成功語言學習的先決條件”(Richards & Rodgers,2001:91)。
3.2.1.2 確定學習內容
項目學習小組在每個文化主題的9項學習任務中自主選擇2項進行項目學習,書面陳述和口語表達二者相結合。同一項目學習小組對不同文化主題學習任務的選擇呈現差異性。
3.2.1.3 制訂學習規劃
項目學習小組選定學習任務后,自行制訂學習計劃、協商角色分工、規劃學習過程、確定學習成果展示形式等。信息收集、資料整理、過程記錄、成果展示和作品交流等具體任務分配體現成員角色分工的多元性、學習過程的新穎性以及成果展示方式的多樣性。
3.2.2 項目實施階段
每個文化主題課堂教學的第2課時及隨后的課外時間是項目實施階段,是一個動態的實踐過程。
3.2.2.1 學生合作學習
項目學習小組根據選定的學習內容和制訂的學習規劃,將課堂學習自然延伸和拓展到課外,采用共學式(Learning Together)、學術辯論(Academic Controversy)、合作綜合閱讀(Cooperative Integrated Reading)、小組成績分享(Team Achievement Division)、團隊協助個性化學習(Team-Assisted Individualization)等合作性學習常用方法(Johnson et al,2000),進行主題單元深度閱讀、資源庫個案研習、多元化拓展識讀、收集資料、實踐調查、成果制作等,實現共同學習目標和完成共同學習任務。
3.2.2.2 教師中介驅動
在小組項目學習中,教師努力培養學生自主和合作學習的能力,扮演學習活動的參與者、學習過程的促進者、知識建構和能力發展的中介者等角色。一方面,與項目學習小組共同“創造有利于主動建構與發展的語言環境”(高艷,2008:94),幫助項目學習小組成員在彼此接近、交流、合作等過程中促進相互認可(Johnson & Johnson,1989),在交流情感、增進信任中降低學習焦慮(Richards,1994),建構知識,發展能力,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另一方面,與項目學習小組積極協商具體問題的解決方案,通過引導和支架等中介和驅動,推動項目學習的順利開展,促成包括學習內容、語言形式和話語結構等在內的有效產出(文秋芳,2015)。
3.2.3 項目后階段
每個文化主題課堂教學的第3和第4課時為項目后階段,主要用于展示和交流學習成果、考核學習效果、總結項目學習等。
3.2.3.1學習成果展示
項目完成后,每個項目學習小組有5-8分鐘的時間展示與交流其學習成果,具體內容包括成員分工概況、學習過程介紹、主要學習發現、以及任務完成情況等。學習成果展示與交流在方式上根據不同的學習任務體現出多樣性,既可以是陳述、辯論、演講、對話,也可以是文本或PPT演示,甚至是說課。
3.2.3.2 學習效果考核
項目學習效果考核改變了以課程“測試成績和等級作為衡量學生能力水平標志”(Knight,2002:276)的做法,既考核文化知識和信息收集整理的完整性、英語表達和陳述的正確性,以及相關文化主題的思辨性等項目學習成果,又考察基于表現的學習過程,包括小組任務分工、成員參與程度、學習進程和學習記錄等,以及現場問題回答、觀點交流等即時性學習表現。學習效果考核由各小組推選代表組成的考核小組負責,采用10分制形式(見下表),其中學習過程3分,學習成果5分,現場回答和互動交流2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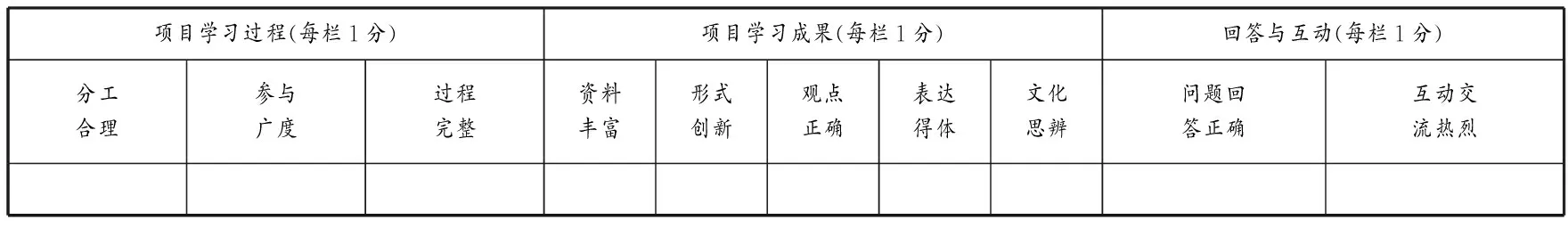
項目學習過程(每欄1分)項目學習成果(每欄1分)回答與互動(每欄1分)分工合理參與廣度過程完整資料豐富形式創新觀點正確表達得體文化思辨問題回答正確互動交流熱烈
3.2.3.3 項目學習總結
任課教師根據學習成果展示與交流的實際情況對項目學習進行總結,其目的不在于評價項目學習小組在某一文化主題學習效果考核成績的高低,而在于了解和聽取學生在項目學習過程中遇到的實際困難和動態需求。一方面幫助項目學習小組共同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案,另一方面以此作為安排下一步教學活動的參考(Black & William,2009),不斷協調、平衡與已有計劃之間的關系(楊華、文秋芳,2013),改進基于項目學習的課堂文化教學。
3.3 課外文化體驗
基于項目學習的課外文化體驗是“中國地方文化英語教學”的重要特色,是課堂文化教學的課外延伸和自然拓展,其實施過程如下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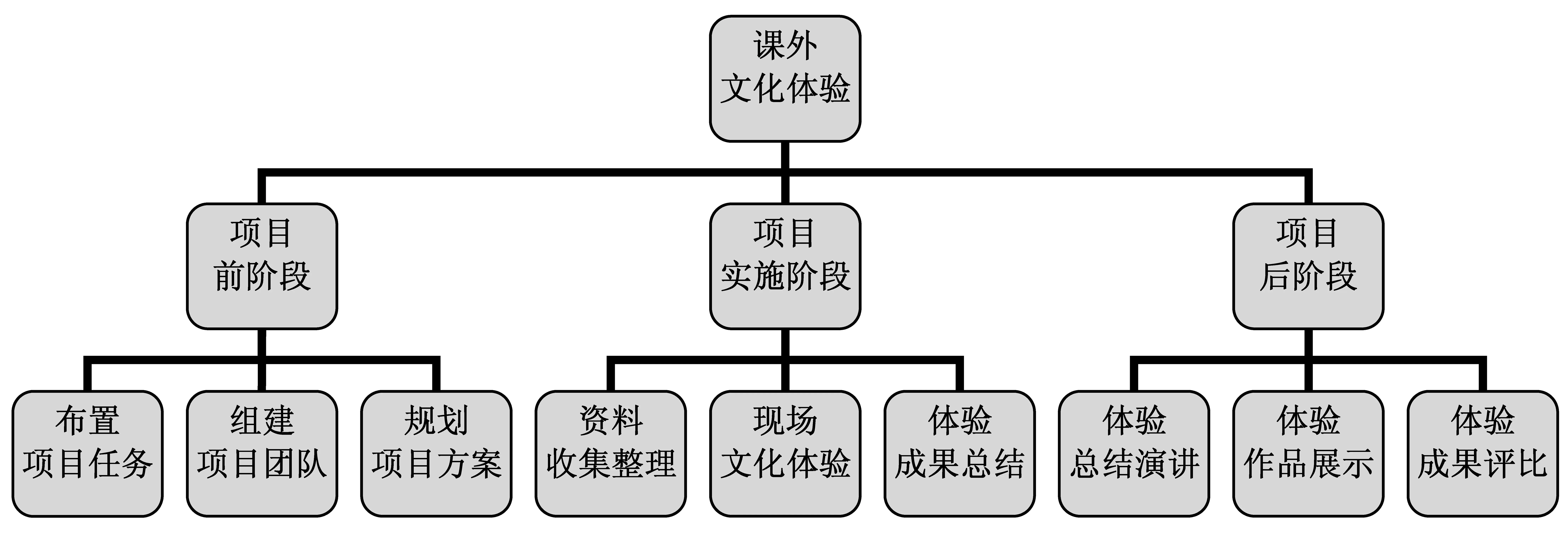
3.3.1 項目前階段
3.3.1.1布置項目任務
學期一開始,任課教師就布置學期文化體驗項目,明確完成項目的具體要求:1)項目的內容;2)項目團隊組建的原則;3)項目完成的時間;4)項目實施的過程方案;5)項目成果的呈現形式;6)項目總結報告等。
3.3.1.2 組建項目團隊
項目團隊組建根據文化體驗的具體內容和規模由學生自行確定,學生既可以按照學習興趣、學習能力、專業類別組建項目團隊,也可以按宿舍、生源地域組建項目團隊。項目團隊成員最少2人,最多不可超過5人。鼓勵邀請其他志愿者和外國留學生參加項目團隊。
3.3.1.3 規劃項目方案
項目團隊在組建后的2周內,完成項目實施方案的初稿設計,具體內容包括:項目實施的總體目標、團隊成員的構成情況及團隊成員的具體分工、項目實施的時間安排和過程分解、項目實施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困難、項目成果擬呈現的形式等等。任課教師在收到項目設施方案初稿后的2周內,分別與不同的項目團隊協商、修改、完善、確定項目實施的最終方案,以此作為項目實施和考核總結的依據。
3.3.2 項目實施階段
3.3.2.1 資料收集整理
資料收集整理是課外文化體驗項目的基礎。項目團隊自行采用分工合作或集體參與等形式,多渠道收集、整理、翻譯相關文化知識和信息,必要時尋求其他團隊的協助,甚至是教師的幫助,努力使相關文化知識和信息收集整理完整、翻譯表達得體。
3.3.2.2 現場文化體驗
現場文化體驗是課外文化體驗項目的核心。團隊成員根據項目規劃攜帶準備的資料、配備相應的設備,利用雙休日或五一、十一等節假日,走出課堂,并全程記錄現場文化體驗過程。現場文化體驗可以是風景名勝、古跡遺址、民族風情等民族文化感悟,可以是古典園林、水鄉風光、文化古鎮等地方文化體驗,也可以是建筑藝術、傳統工藝、歷史名人等家鄉文化介紹等。
3.3.2.3 體驗成果總結
體驗成果總結是課外文化體驗項目的提煉。現場文化體驗之旅結束后,項目團隊一方面后期制作或完善由全體成員參與、以英語為媒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時長為5-8分鐘的視聽作品,另一方面完成由體驗過程、體驗成果、體驗感悟等3部分內容組成的體驗總結報告的撰寫。
3.3.3 項目后階段
3.3.3.1 體驗總結演講
在學期結束前的1-2周內,項目團隊代表就各自的課外文化體驗項目進行大約5分鐘左右的體驗總結演講。體驗總結演講主要包括介紹體驗過程、分享成果收獲、共享理解感悟、提出改進建議等。

3.3.3.2 體驗作品展示
項目團隊代表進行體驗總結演講后,播放項目團隊制作的現場文化體驗視聽作品,解釋和回答其他團隊成員和任課教師在觀看過程中提出的問題。

3.3.3.3 體驗成果評比
在所有項目團隊完成體驗總結演講和體驗作品展示后,由各項目團隊代表、任課教師、以及平行班級代表組成的評比小組對所有體驗作品進行評比。評比(具體欄目見下表)既關注多媒體制作技術的應用和思想內容的完整性,又考察其文化知識信息的準確性和英語表達的得體性,并特別注重體驗作品文化主題的思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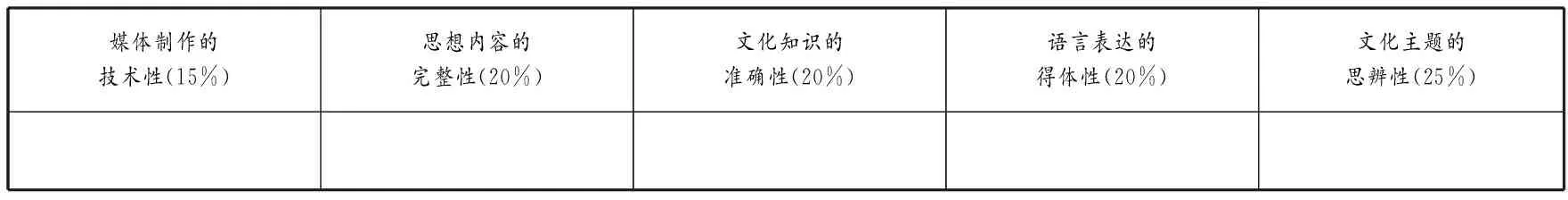
媒體制作的技術性(15%)思想內容的完整性(20%)文化知識的準確性(20%)語言表達的得體性(20%)文化主題的思辨性(25%)
4.0 結語
作為2009年國家精品課程、2013年國家精品資源共享課——“大學英語應用類課程”的特色課程以及“十二五”江蘇省高等學校重點教材立項建設(2015年)支撐的課程,“中國地方文化英語教學”積極嘗試基于項目學習的教學模式,以特色文化為教學內容、以文化主題為教學單元、以交互性課程學習網絡資源為平臺,克服了內容繁雜、知識點分散(陶雙雙,2010)等項目整合過程中的難點,有助于培養大學英語學習者的自主學習能力、團隊合作精神、以及在真實語境下傳播中華文化的英語應用能力,得到了學生們的充分肯定(見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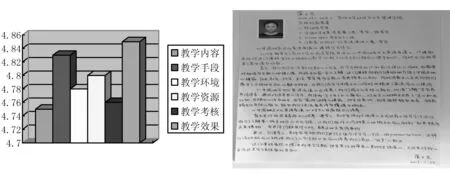
但是,“中國地方文化英語教學”只是大學英語教學眾多課程中的一門,其基于項目學習的教學模式也只是大學英語中華文化教學的一種可選模式。基于項目學習的“中國地方文化英語教學”實踐發現,怎樣組建和優化項目學習團隊,最大限度地降低學生因學習能力和水平參差不齊給學習帶來的負面影響(李立、杜潔敏,2014)以及怎樣激勵項目團隊成員積極參與項目實施過程,促進自己、他人及團隊學習效果的最大化,是基于項目學習的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進一步探究的教學難題。
注釋:
① “中國地方文化英語教學”2014年前的名稱為“中國地方文化英語導讀”,配套教材是《中華文明與地方文化英語導讀》(蘇州大學出版社,2009年)。2014年,“中國地方文化英語導讀”立項學校3I工程課程建設,改名為“中國地方文化英語教學”。
② “中國地方文化英語教學”正在建設江蘇省在線課程,與其配套的教材《中國特色文化英語教程》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出版。新出版的教材配備PC端Abook服務平臺和二維碼微學資源。
[1] Alan, B. & F. L. Stoller. Maximizing the benefits of project work in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s[J].EnglishTeachingForum, 2005,(4):10-21.
[2] Beckett, G. H. & T. Slater. The project framework: A tool for language, content, and skills integration[J].ELTJournal, 2005,(2):108-116.
[3] Black, P. & D. William. Developing the theory of formative assessment[J].EducationalAssessment,EvaluationandAccountability, 2009,(21):5-31.
[4] Fried-Booth, D. L.ResourceBooksforTeachers:ProjectWork[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5] Grant, M. M. Getting a grip on project-based learning: Theory, cases and recommendations[J].AMiddleSchoolComputerTechnologiesJournal, 2002,(1):1-3.
[6] Johnson, D. W. & R. T. Johnson. Cooperative learning: What special educators need to know[J].ThePointer, 1989,(33):5-10.
[7] Johnson, D. W., R. T. Johnson & M. E. Stanne.CooperativeLearningMethods:AMeta-Analys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8] Knight, P. T. Summative assess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Practice in disarray[J].StudiesinHigherEducation, 2002,(3):275-286.
[9] Richards, J.ReflectiveTeachinginSecondLanguageClassroom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0] Richards, J. & T. Rodgers.ApproachesandMethodsinLanguageTeaching[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1] 丁言仁,劉海平. 探索英語寫作教學中“項目教學法”的應用——寫在《寫作教程》第五、六冊出版之際[J]. 外語界,2011,(2):11-13.
[12] 高艷. 從社會文化理論的角度論語言教師的中介作用[J]. 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08,(3):93-96.
[13] 高艷. 項目學習在大學英語教學中的應用研究[J]. 外語界,2010,(6):42-48.
[14] 教育部辦公廳. 關于印發“精品資源共享課建設工作實施辦法”的通知[Z]. [2012]2號.
[15] 教育部高等學校大學外語教學指導委員會. 大學英語教學指南(討論稿)[Z]. 2015.
[16] 李立,杜潔敏. 大學英語分科教學背景下學術英語PBL教學模式研究[J]. 外語教學,2014,(5):55-58.
[17] 李麗君. 基于項目學習模式的大學英語自主學習研究[J].教育探索,2009,(8):23-24.
[18] 劉和林,吳慶華. 項目式教學對應用型外語人才實踐能力的培養[J]. 當代教育實踐與教學研究,2016,(3):269-271.
[19] 瞿少成,黃俊年,周彬. 基于項目的學習過程建模與研究[J]. 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2,(5):550-554.
[20] 陶雙雙. 對項目教學法應用中若干問題的反思與建議[J]. 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10,(11):27-29.
[21] 王勃然. 項目學習模式對大學英語學習動機的影響因素分析[J]. 外語電化教學,2013,(1):37-41.
[22] 文秋芳. 構建“產出導向法”理論體系[J]. 外語教學與研究,2015,(4):547-558.
[23] 武和平,張維民. 后方法時代外語教學方法的重建[J]. 課程·教材·教法,2011,(6):61-67.
[24] 楊華,文秋芳. 課堂即時形成性評估研究述評:思考與建議[J]. 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13,(3):33-38.
[25] 張文忠. 本土化依托項目外語教學的“教學”觀[J]. 中國大學教學,2012,(4):47-51.
[26] 張文忠. iPBL——本土化的依托項目英語教學模式[J]. 中國外語,2015,(2):15-23.
(責任編輯:馬煜)
On PBL-Centered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of the Chinese Culture:A Case Study of English Teaching of Local Chinese Culture
GU Wei-xing, YE Jian-m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With a teaching task design on cultural themes, a supporting platform of net-based interactive learning resources,EnglishTeachingofLocalChineseCultureadopts project-based teaching in classroom instruction and extracurricular experience of culture. It aims to renovate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mode and cultivate college English learners’ autonomous learning, team cooperation spirit, and all-round English application abilities to promote the Chinese culture.
project-based teach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culture promotion; English application ability
10.16482/j.sdwy37-1026.2017-04-004
2016-10-02
本文為國家精品課程(2009年)和國家精品資源共享課(2013年)——“大學英語應用類課程”以及“十二五”江蘇省高等學校重點教材立項建設(2015年)——《中國特色文化英語教程》的部分研究成果。
顧衛星(1963-),男,江蘇丹陽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國英語教學史、大學英語教學。 葉建敏(1963-),女,江蘇蘇州人,副教授。研究方向:應用語言學、大學英語教學。
H319
A
1002-2643(2017)04-002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