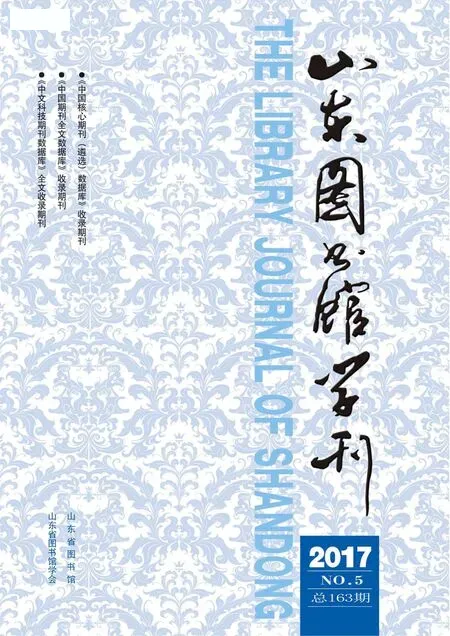沈從文圖書館求學經歷的考察與啟示
陶榮湘
(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圖書館,廣東廣州 510665)
沈從文圖書館求學經歷的考察與啟示
陶榮湘
(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圖書館,廣東廣州 510665)
沈從文是現代文學史上頗具傳奇色彩的作家之一,他學歷低淺,全憑自學成才。沈從文的知識積累與圖書館有著深厚的淵源,他不僅長期在圖書館求學,更有多次在圖書館的工作經歷,還有以圖書館生活為題材創作的小說。考察沈從文的圖書館求學經歷,發掘文化名人利用圖書館自學成才的典范,對于彰顯圖書館的社會價值和文化功績具有重要的意義。
沈從文 圖書館
沈從文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位頗具傳奇色彩的作家。他的“傳奇性”在于:“僅受小學教育,無任何學位”,完全依靠自學,卻能 “用一支筆打出一個天下”,他是我國現代作家中成書最多的一位,也是 “極少數在全世界得到公認的中國新文學家之一”(朱光潛)[1]。建國后因種種原因,他中斷了文學創作轉而從事文物史研究,在長達三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他先后發表了如《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國絲綢圖案》《中國漆器工藝》等學術巨著,為我國文物史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沈從文與圖書館頗具淵源,他不僅曾長期在圖書館求學,圖書館在他知識積累的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更有多次在圖書館的工作經歷,還創作了以圖書館生活為題材的小說。考察沈從文的圖書館求學經歷與治學影響,不僅可以發掘文化名人利用圖書館自學成才的典范,彰顯圖書館的存在價值和社會意義,還可以籍此總結圖書館建設的經驗得失,為圖書館事業發展提供可資借鑒的參考。
1 沈從文與圖書館的淵源
1.1 熊希齡圖書室的自學經歷
熊希齡(1870—1930),湖南湘西鳳凰人,著名教育家、實業家和慈善家,曾任民國第一任民選總理。20世紀前期,湖南湘西的教育一直非常落后。科舉制度下,湘西鳳凰除了翰林學士熊希齡外,也僅出過兩名進士。沈從文幼年所受的是舊式的私塾教育,但他并不喜歡舊式教育中死記硬背、陳詞濫調等種種弊病,所以經常逃學。有關這段幼年求學經歷,沈從文在小說《在私塾》中有過詳細的描述。早年的教育對沈從文后來偏愛文學可以說影響甚微。由于沈家與湘西的熊氏家族有姻親關系,沈從文得以有機會進入到當時的熊希齡公館的老宅,那里有間幾乎荒廢的圖書室,沈從文在那里閱讀了《史記》《漢書》《天方夜譚》以及林紓用古文翻譯的《賊史》《冰雪姻緣》《滑稽外史》等西方文學名著。西方小說中的故事情節、社會現象和人文情感與他之前所接受的那種說教式的古文知識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并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用熊府那幾十本林譯小說作橋梁,走入一嶄新的世界,偉大烈士的功名,鄉村兒女的恩怨,都將從我筆下重現,得到更新的生命。”[2]熊公館圖書室的閱讀經歷對沈從文以后走上文學之路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在國內新文化運動尚未發起之前,沈從文就已深受文學變革思潮的影響,用獨特的想象比喻來取代舊式文言文中的陳詞濫調,這種啟蒙效應將沈從文引領到一個全新的文學世界。
1.2 陳渠珍私人圖書館的求學經歷
陳渠珍(1881-1952),號玉鍪,祖籍江西,后遷入湖南鳳凰。他出身寒微,任職新軍,曾畢業于湖南武備學堂,1919年執掌湘西軍政大權,在湘西推行自治運動,并大力推行文化教育改革,在湘西頗有聲望,史稱“湘西王”。1922年,因寫得一手好字,沈從文得到陳渠珍的賞識,被他調到身邊作書記官。但陳渠珍并不是要沈從文為他辦理新政事務,而是負責管理他的私人圖書館,為其藏書古董分門別類編制目錄。陳渠珍本身也是一個文學修養極高的人,行軍打仗之余,他大部分工作時間都花在讀書和自我修養上。當陳渠珍需要閱讀某一書或摘錄書中某一段時,就由沈從文預先備好,圖書館的分類編排、編號等工作,藉由沈從文來做。他在這一過程中所接觸到的中國歷史、文學和藝術作品,對他以后從事文學創作和文物史研究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浸潤在他創作中的中國古典文學修養、從事文物史研究必需的學識素養,乃至他對中國書法歷史的透徹了解和深厚功底,幾乎都能在這一時期找到最初的源頭。此外,在陳渠珍私人圖書館工作期間,除了管理圖書和學習之外,沈從文還接觸到了《新青年》《新潮》《改造》等宣揚“五四運動”新思想的刊物。那些新潮思想的影響,促使他開始思考“如何做人”“怎樣愛國”之類的問題,“相信了報紙上的說法,以為北京有的是上學的機會。”[3]并最終下定決心離開湘西,前往北京求學。
1.3 京師圖書館的求學經歷
1923年6月,受新思潮的影響,沈從文離開湘西來到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求學。最初他的本意是進入一所大學求學,并投身于國內的文化復興運動。但對于只有小學私塾教育和古文根基的沈從文來說,大學入門考試就是一道難以逾越的門檻。由于入學無門,這一時期沈從文花了大量時間在京師圖書館自學。初建于1909年的京師圖書館是當時國內最大的公共圖書館,當時的京師圖書館不僅對外開放,最重要的是冬天還提供暖氣,彼時沈從文的經濟狀況極其窘迫,寒冬季節經常是裹著棉被埋頭創作,郁達夫在《致一個文學青年的信》中就描述了沈從文當時的窘況。京師圖書館對于沈從文來說無疑是絕佳的閱讀場所,“那個小小閱覽室不僅有幾十種新報刊,可以隨意取讀,還有取暖飲水等設備方便群眾。我幾乎每天都去那里看半天書,不問新舊,凡看得懂的都翻翻,看了不少的書,甚至于影響到此后大半生。不少圖書雖只看過一兩次,記下了基本內容,此后二三十年多還得用。”[4]
1.4 香山慈幼院圖書館的工作經歷
沈從文離開家鄉前往北京求學,本意就是想獲得個人獨立,加上他又并不愿意依附他在北京的那些顯貴親戚,經濟狀況一度十分窘迫。由于入學無門,他想一面干活一面讀書,加上他在湘西原本就曾管理過圖書,于是就想到圖書館謀求職位。他還托朋友幫忙參加一所大學舉辦的圖書館講習班學習,只是后來計劃告吹。1925年,沈從文發表在《晨報副刊》上作品引起了北大教授林宰平的注意。通過他的引薦,沈從文得以進入香山慈幼院圖書館工作,他的遠房親戚,慈幼院創辦人熊希齡還專門送沈從文學習編目和文獻學知識,師從后來出任京師圖書館館長的袁同禮教授。但沈從文顯然志不在此,他堅持認為文學創作才是他的唯一出路,圖書館這門學問怎么也引不起他的重視,這一期間,除了自學、寫稿之外,他開始嘗試和一幫作家朋友創辦文學雜志,并最終離開了圖書館,成為一名職業作家。
2 圖書館求學經歷對其治學的影響
2.1 圖書館經歷對其文學創作的影響
圖書館自學的經歷令沈從文受益匪淺,并對他從事文學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湘西地處窮鄉僻壤,自古以來文化底蘊就十分薄弱,教育非常落后,一般農家子弟很少有讀書上學機會,當兵是年輕人的一條出路,很大程度上也是唯一的出路。由于家庭的緣故,沈從文幼年還上過私塾和新式學校,但他經常逃學,因此學校教育對于他后來成長的影響極其有限。他在文學創作領域所取得的成就,除了天份之外,與他后來堅持不懈利用包括圖書館在內的各種自學機會密不可分。
沈從文沒有上過新學,通過在圖書館的求學經歷,使得他從小就養成了博覽群書的習慣。他從童年時起就讀了大量的古典白話小說,如《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封神演義》,還有《聊齋志異》《隋唐演義》《今古奇觀》等。正是在這種大量閱讀的基礎之上,沈從文逐漸培養了獨特的閱讀興趣,他對白話小說的愛好遠勝于古代散文及文言文。同樣,這樣的閱讀興趣也把他引領進了西方文學,在熊希齡圖書室的閱讀經歷,使得他接觸到了大量林紓譯本小說,由于這一類小說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經歷過艱難時世磨練的孤苦兒童,使得沈從文閱后常有惺惺相惜之感,西方文學中的故事情節、社會現象,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陳渠珍私人圖書館工作期間,由于經常替陳渠珍翻檢抄錄古籍摘要,日積月累,為他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基礎。正是憑借這些古文根基,使得以往只是善于捕捉生活經驗和自然現象的沈從文,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領會,發生了寬廣而深刻的變化。他開始有意識地模仿古典文學中的簡練筆法,并仿效舊體詩學習遣詞造句,這對于后來他寫小說時十分注意錘煉詞句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這一期間沈從文不僅所學十分豐富,更重要的是隨著自身學識的提高以及對外鄉新生事物的興趣,逐漸使沈從文的思想發生了明顯轉變。在與他舅舅的談話中,沈從文曾如是寫道:“談一切我所不知道的卻愿意知道的問題,這種談話顯然也使他十分快樂,因此每次所談時間總很長很久。但這么以來,我的幻想更寬,寂寞也就更大了。”[5]久之,這種“幻想”和“寂寞”使沈從文意識到:他在部隊的經歷已走到了盡頭,“六年中我眼看在腳邊殺了上萬無辜平民,除了對被殺的人留下個愚蠢殘忍印象,什么都學不到!作官的有不少聰明人,人越聰明也就越縱容愚蠢氣質抬頭,而自己儼然高高在上,以萬物為騶狗,我實在呆不下去了,才跑出來。我想讀點書,讀好書救救國家,這個國家這么下去實在要不得!”[6]
2.2 圖書館求學經歷對其文物史研究的影響
沈從文之所以對文物研究產生興趣,主要還要歸功于他在陳渠珍私人圖書館的經歷。陳渠珍的私人圖書室與其說是一所圖書館,倒不如說是一所博物館更為貼切。那里除了藏書之外,里面還收藏了大量的古瓷、銅器、碑帖和古代書畫作品。沈從文工作就是對這些收藏品進行分類、編號、登記和編制目錄等等。正是這段經歷使沈從文對文物產生了濃厚興趣。“舊畫和古董登記時,我又得知道這一幅畫的人名時代同他當時的地位、或器物名稱同他的用處。全由于應用,我同時就學會了許多知識。又由于習染,我成天翻來覆去,把那些舊書大部分也慢慢的看懂了。”[7]由于工作比較清閑,每當無事可做的時候,沈從文就獨自欣賞那些古舊字畫,學習從文字和形狀上認識銅器的名稱和價值,倘若對作者、時代缺乏了解的時候,他就借助一本《四庫叢刊》按圖索驥,從而對文物慢慢有了新的認識和了解。到了北京以后,沈從文對文物的興趣一度中斷。但他搬出香山慈幼院后,借住在一個湘西人開辦的酉西會館,恰好鄰近北京有名的文物街琉璃廠,那些在靠街的櫥窗中陳列出來的古代瓷器和元明清古軸畫,“也就能夠使他忘卻一切,神往傾心以致于流連忘返了”[8]。
文物史研究涉及到考古、藝術、服飾、歷史和工藝美術等諸多學科門類知識,加上文物及考古類型學中有關類、型、式的劃分,這些學科與文獻學、目錄學知識有著諸多相通之處。正是得益于沈從文早年有過文獻學和目錄學的學習經歷,加上他本身閱歷豐富,知識淵博,使得他在從事文物研究方面得心應手。入行不久,他就相繼發表了《中國絲綢圖案》《戰國漆器》《唐宋銅鏡》《明錦》等論著,并逐漸摸索出一套文獻與實物相結合的文物考古學研究理論。“文革”之初,沈從文開始著手《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資料收集和編寫工作。動亂年代,他的研究接近告成又幾度中斷,辛辛苦苦收集的資料也全部被抄走遺失。1971年,沈從文幾經輾轉,才得以被批準回到北京繼續他的文物史研究。憑借超強的記憶力,以及走訪各種圖書館和資料室,他又把遺失的資料重新整理出來,對于有關文物的雜說筆記,工藝百家之言,他無不加以詳細研究和考證,編寫了大量的資料卡片,這才使他的研究得以繼續下去。1981年,《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在這部巨著中,僅說明文字就高達25萬字,其中還包括800多幅插圖,該書出版后,很快引起了國內外考古學界的高度關注。此外在長期的研究過程中,沈從文高度重視對相關文獻資料的收集。他還大力倡導建立文物資料館,1954年他提出“高教部和文化部目下就應當考慮到全國每一個大學或師范學院,有成立一個文物館或資料室的準備”“個人深深盼望北京圖書館附近不久能有一個收藏實物、圖片和模型過百萬件的‘歷史文物館’一類的研究機構出現”[9]等等。這些觀點都反映出沈從文敏銳的學術眼光。
3 以圖書館經歷為素材的文學創作
沈從文以圖書館工作經歷為素材創作小說主要集中在香山慈幼院圖書館工作期間。彼時他應熊希齡之邀暫時在該館謀生,并用這一期間的生活經歷為題材創作了《棉鞋》《用A字記下來的故事》《狒狒的悲哀》和《第二個狒狒》等一系列小說。當時沈從文的小說還處于初創階段,手法并不圓熟。囿于創作題材的缺乏,加上彼時國內盛行的日本“私小說”的影響,沈從文以自己的真實生活經歷為素材創作了大量小說,這也是當時他最得心應手的題材。由于他經常采用第一人稱的表述方式,所以很容易給人留下“對號入座”式的聯想。小說《棉鞋》刻畫了一位家境貧寒的圖書管理員,因為買不起體面的鞋子,在大庭廣眾之下被館長羞辱,而讀者也對他挖苦嘲笑。小說以鞋子構想出中心懸念,設置了很多潛臺詞式的獨白,如:
“想來借幾本書/好吧。管事先生口上說著,眼睛一下就盯在我腳上/哈哈,你眼力不錯,看到我腳上——我心里想起就好笑。”
這篇小說充滿了自傷貧賤的情緒,同時又富有幽默感。小說中的主人公用辛辣的語調譏諷了管事先生愚蠢、教育股長的阿諛勢利,還用自我嘲諷的方式試圖探討嚴肅的社會話題。《用A字記下來的故事》描述了作者在慈幼院圖書館工作期間經歷的一場盛宴:賓朋滿座的生日宴會上,主人公卻總覺得氣氛跟自己格格不入,里面的男賓客個個看起來令人討厭,而那些穿著時髦的太太小姐們,卻爭先跟他搭話,于是令他產生了一些曖昧的想法。[10]按照當時的社會風氣來說,在小說中用講故事的方式對上流社會的女士的曖昧挑逗,是非常失禮且讓人討厭的;“他憎恨香山那些仕紳,甚至希望口袋里的鉛筆能變成手槍,把他們一個個全部打死。”[11]在這里,沈從文塑造出一個完全反面的角色,在面臨社會不公、心情受到極度壓抑時的沖動和反抗。《第二個狒狒》和《狒狒的悲哀》用輕侮的筆調,影射慈幼院的教育股長。小說描寫的是主人公與“狒狒”在香山看戲的故事,主人公看到空位就落座,而“狒狒”則主動挑選位置差的座位,因為他知道前排座位是預留給“老爺”的。果然,“老爺”準時來到,還帶了兩個“小玩物”,空座上“即刻就填上了兩個奇麗肉體”。
彼時沈從文小說中的主人公大都是陷入困境中的青年,由于長期處在不平等的條件下競爭,對社會不公抱有強烈的反抗情緒。從小說的內容和基調來看,更像是自傳,也含蓄表達了沈從文彼時的心境:前途渺茫,不得不寄人籬下,而他的個性又敏感易怒,總覺得自己跟那些同僚——包括他的那位遠親之間有說不清的鴻溝,他對圍繞在圖書館以及慈幼院的上流社會圈子,“總懷有一種混合著自卑與自尊、羨慕與不滿的復雜情緒”[12]。這一類故事很容易將沈從文在圖書館的窘迫處境聯系起來。此外小說還明確指出了主人公的姓氏,他在稿末分別注明了故事發生的時間和地點:“8月14號晨,于香山石壩灣(《用A字記下來的故事》)”“8月16號作于香山慈幼院(《第二個狒狒》)”,因此引起了圖書館同僚們的極大反感:小說中他們全都成了貪圖勢力的小人[12]。這也成為他離開香山慈幼院圖書館的重要原因之一。
4 對圖書館作用的認知及貢獻
正是得益于圖書館的自學經歷,使得沈從文對圖書館重要性的認識經歷了從忽視到高度重視的轉變過程。在離開湘西之前,沈從文還只是一個接觸了少許新思想的文學青年,盡管此前他有過一定的古學根基,但畢竟沒有經過系統化的學習,且相當雜亂,他甚至還不知道斷句。盡管早前在熊希齡藏書室和香山慈幼院圖書館的經歷使他獲益匪淺,那時候他還沒有意識到圖書館對他未來事業的重要性。也沒有將圖書館工作視為畢生奮斗的事業,而是將其視為邁向文學創作的階梯。他在圖書館自學和借讀,目的只是為了實現他的文學夢。
沈從文對圖書館重要性的認知轉變始于轉行從事文物研究期間。由于常年在歷史博物館工作,他在對文物做分類、標簽的同時,為了盡快適應新的工作,需要經常利用圖書館和資料室查閱各種資料。正是在這一研究過程中,沈從文開始認識到圖書館的重要性,并將其視為“免費的學校”。為此他還專門撰寫了《我為什么強調資料卡片》,專門提到了當時歷史博物館使用卡片查詢資料的事項。此外他經常利用出差的機會奔赴各地圖書館查閱資料,并多次強調地方文物資料室對于開展文物研究的重要性:“這個文物資料室還是有必要存在的,并不斷充實以新材料,他日的作用,將和中文圖書館相同。在某些問題上,或者還比圖書館好,因為從舊書中受教育,不會比從文物受教育簡便”。[13]
1980年沈從文應邀赴美講學,期間他參觀了包括哈佛大學圖書館在內的眾多美國知名大學圖書館。他一眼就看出了美國大學圖書館與國內圖書館的差距:“它有個很好的,值得我們參考的地方,就是圖書館的制度”[14]此外在與美國學者金介甫進行學術交流的過程中,他很快就意識到了對方制作的聯合目錄對于開展學術研究的便利,此后并利用各種機會宣傳國外先進的圖書館理念和管理制度。[15]晚年沈從文對圖書館有一種特殊的情愫,他曾多次對后學提及圖書館對他的重要影響。也正是這種切身體會,讓他意識到圖書館對于那些寒門學子的重要性,他捐獻出《沈從文文集》的全部稿酬,特意在家鄉的鳳凰小學修建了一座圖書館,還捐贈了一批圖書,對家鄉的后輩學子傾注了極大的關懷。
圖書館因為典藏人類文化遺產而與社會生活發生了密切聯系,因而文獻記載和文學表現十分豐富,這些記載和表現是人們利用圖書館的履歷,也象征著人們對圖書館使用與審美的漫漫歷程。沈從文在圖書館求學的經歷告訴我們:圖書館不僅是知識的載體,也是歷史的陳列室。通過對故舊歷史的追溯,方能做到以史為鑒。近代圖書館踐行對外自由開放的宗旨,自此使得圖書館不再像以往僅供少數人閱讀,而成為萬千寒門學子實現其理想的階梯。只有具備了等視眾生的胸懷,圖書館才能最大限度地貼近讀者,為社會大眾提供用之不盡的精神食糧,只有充分利用圖書館,莘莘學子才能在知識的海洋中尋覓夢想,實現自我。
〔1〕 朱光潛.從沈從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藝術風格[J].花城,1980(5):23-24〔2〕〔3〕〔4〕〔5〕〔7〕〔8〕〔9〕 沈從文.沈從文全集[M].北京: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128,129,237,337,356,421,263
〔6〕〔10〕〔12〕 金介浦著,符家欽譯.沈從文傳[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5:94-95,89,96
〔11〕 凌宇.沈從文傳[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8:94
〔13〕 盛巽昌.從圖書館起步的學者型作家[J].出版人圖書館與閱讀,2010(5):1-3
〔14〕 王亞蓉.沈從文晚年口述[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267-268
〔15〕 宋劍祥.沈從文利用圖書館鉤沉[J].圖書情報研究,2011(1):31-35
InvestigationandEnlightenmentofShenCongwen’sLibraryStudyExperiences
TaoRongxiang
Shen Congwen is a legendary writer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ough with lower degree, he became talented through self-study. Shen Congwen’s knowledge accumulation has a deep relation with the library. He not only studied in the library for a long time, but also had many library work experiences and created novels about library. Reviewing Shen Congwen’s library study experience can help us to explore how cultural celebrities used library to become talented, and has vital significance in revealing the library’s social value and cultural achievements.
Shen Congwen; Library
G259.29
A
陶榮湘(1980-),館員,湖南東安人,從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及圖書館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