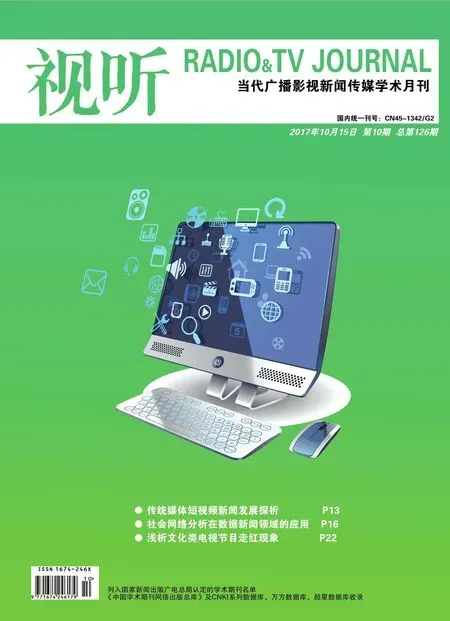《靜態自殺》中的結構與風景敘事
□高 昶
《靜態自殺》中的結構與風景敘事
□高 昶
詹姆斯·班寧在《靜態自殺》(Landscape Suicide,1986)中以真實的法庭證供與警察審訊資料為文本背景,選取其中片段由演員重新演繹審訊過程。影片中穿插大量的案發現場周圍環境與風景的鏡頭,用縝密的碎片式非傳統敘事結構呈現出兩個謀殺犯的犯罪背景與心理狀態。對于兩個似乎有精神和社交問題的罪犯——艾德·蓋恩(Ed Gein)和伯納黛特·普羅蒂(BernadetteProtti)①,影片試圖讓觀眾去思考他們生活的環境和他們的暴力罪行之間是否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
詹姆斯·班寧;實驗電影;結構;風景敘事
在處理謀殺案的影片中,傳統電影處理方式往往關注情節與驚悚、懸疑等元素,演繹化地再現案發現場,以富有戲劇化的燈光、表演與蒙太奇技巧吸引觀眾。而在影片《靜態自殺》(Landscape Suicide,1986)中,詹姆斯·班寧以碎片化的演員表演結合真實證詞重現司法審問中的人物狀態,以案發現場周圍的靜態環境填補并豐富了人物生活背景,使得影片凸顯了人物而弱化了犯罪情節。班寧沒有囿于暴力行為本身,而將關注點置于當罪犯承認自己罪行時他們如何審視自己以及他們如何看待事件發生之后的事情。同時,班寧將時而穿上被害者人皮以取得自己變態性快感的連環謀殺犯艾德·蓋恩(Ed Gein)和殺害了同班啦啦隊長的青少年伯納黛特·普羅蒂(BernadetteProtti)進行了對比,試圖將故事與觀點藏于靜態風景鏡頭并引發觀眾思考暴行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影片《精神病患者》(Psycho,1960)中的諾曼·貝茨、《德州電鋸殺人狂》(The Texas Chainsaw Massacre,1974)中的屠夫以及《沉默的羔羊》(Silence of the Lambs,1991)中的野牛比爾均以本片兩個主角之一艾德·蓋恩為原型創造。②
一、平行對照結構
詹姆斯·班寧將伯納黛特·普羅蒂與艾德·蓋恩的故事整體分為兩幕講述,但其中均采用采訪、受害者生活場景再現、靜態風景的切入等相同的處理手法,在相同的結構中將兩者故事進行平行對比。平行對比下不僅凸顯出不同人物狀態,也豐富了不同場景下的風景內涵。
在納黛特·普羅蒂的故事中,首先出現的是一個在雨天以第一視角在車內拍攝加州北部奧林達的一個住宅區的鏡頭。兩分鐘的鏡頭,隨著車子的移動,觀眾從關注逐漸到進入一個植被豐茂的中產階級住宅區,對普羅蒂的生活環境有了切身的體會與認知。同樣一個在車內第一視角拍攝的長鏡頭出現在艾德·蓋恩的故事中。而此鏡頭中,觀眾看到的是散落在皚皚白雪中顏色暗淡的民居與與農場。在影片僅有的兩個移動鏡頭中,威斯康辛州的小鎮中肅殺的景象與綠植豐茂的北加州環境形成鮮明對比。在普羅蒂故事中的長鏡頭中,車內無線電播放的是上帝創造人類的贊歌,是人們應該敞開胸懷擁抱上帝的宣傳;而艾德·蓋恩故事中車內無線電播放的是對人在缺乏對上帝認知的情況下人性暴劣導致戰爭頻發的控訴。首先無線電廣播的內容與態度與案件主人公及罪行暴力程度成正比關系。其次,對于基督宣傳的引用也暗合影片中兩地教堂的鏡頭。尤其在普羅蒂案件中,教堂為兩人沖突的始發地。無線電廣播的內容將看似碎片化的結構處理暗中對照聯系起來,使得整體結構疏中有密。
《靜態自殺》延續了詹姆斯·班寧在早期影片中慣用的插入黑屏的手法,打斷了傳統敘事的連貫性,使得影片敘事碎片化,同時也為觀眾提供了自主思考與“客觀”觀看的主動性。在本片中,結合采訪內容,黑屏的插入有了更為深刻的含義。在班寧對于人物狀態的關注下,普羅蒂與蓋恩在采訪時都凸現出一個遺忘的過程。技術圖像創造了一個能覆蓋任何對白和對事件記憶的表象。當首席檢察官助理羅伯特·薩頓開始提問的時候出現了黑屏,而且緊接著黑屏的剪輯中我們聽到敲打金屬罐子的聲音(審問中蓋恩提到當他低頭看下方的時候聽到有敲打金屬罐子的聲音)。這種在聲畫上的機械重復展現了審問中重新覆蓋的構造形跡。③于是審問中的不含情感流露的表演也因之相得益彰。
為了凸顯故事并置并使觀眾對比思考,兩個并置部分我們均能看到當事人的真實照片、被害人的日常生活場景的演繹重現、案發地的地圖分析以及案件相關地富有孤獨感的環境風景等,甚至在不同兩地構建模樣相同的水塔也參與了對比。而影片中對于風景的大量關注不僅向觀眾呈現人物生活環境,也將案件的獨特性消解,將敘事泛化向此環境中甚至此類人群中的類似案例。
二、看與聽
“從最一開始,我的影片就一直在關注于‘看’和‘聽’,并且我相信學任何東西都需要時間,也就是說一個人必須得去練習關注。我的作品為觀眾提供了去關注事物的經驗。”④
在第一部分普羅蒂的故事中,長鏡頭對案發空間的探索、長達20余分鐘的審問再現以及案發后普羅蒂寫給父母的日記等都為觀眾介紹了案件的緣由、當事人事后承受的痛苦及其在面對自己罪行時的狀態。當觀眾對人物及案件有了基本了解之后,隨著畫外音的引入,班寧開始以靜態風景鏡頭帶著已有主觀情感期待的觀眾去感受奧林達這樣的地方。從對這個城市的遠景至對城市交通與生活環境的白描,再到學校、加油站、小區、教堂、墓地和醫院的凝視,11分鐘內的26個風景鏡頭不僅是對這個城市立體的展現,伴隨前文故事的鋪墊,風景與環境鏡頭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內在敘事,也為觀眾提供了可以置身的敘事空間。至此,風景鏡頭巧妙而意韻十足地參與了影片的整體敘事。
緊接著的第二部分蓋恩的故事中,基于上半部中風景鏡頭的敘事功效,在畫外音的簡介下,影片從靜態環境的鏡頭開始構建并介紹整個敘事空間,其后再加入人物介紹與審問場景。相同的結構只是改變的鏡頭序列,給了觀眾不同的觀影體驗。影片最后肢解鹿的場景的隱喻表現與蓋恩在影片中的采訪形成互文,含蓄但有力地表現了蓋恩謀殺案中的血腥與變態暴力。
影片中在不同鏡頭下的聲音處理也各有不同:在風景鏡頭中利用環境音營造真實感,以打字的聲音拓展鏡頭外的空間,在臥室的場景中加入受害者在葬禮時播放的音樂《回憶》以示哀悼的同時加強了影片的內部聯系等。班寧對聲音的處理和對圖片的處理非常相似,即將它們作為影片中不同的組成元素。“我想抓住對那個場地的感受,對聲音和圖片的后期操作處理是為了更好地表現出我在那個地方的體會,因為有時候一些極端的噪音會影響你對某個地點的感情表達。”⑤班寧在此表示并非反對超現實等藝術處理的聲音,這一切處理方式取決于電影的目的,而班寧對聲音的處理是為了更好地表達對一個地點空間的個人體會與感受。
三、總結
有著數學學習背景的詹姆斯·班寧對影片中各元素的運用以及影片結構的構建向來精巧,他對城市及自然風光的靜態長鏡頭處理更是為人稱道。“當幾分鐘過去之后,班寧的靜態長鏡頭開始有力地影響觀眾。他典雅的構圖隨著時間的流逝變得超越現實,我們不再是在景邊觀看,而是進入了這個景色。”⑥
注釋:
①伯納黛特·普羅蒂為朗達·貝(Rhonda Bell)飾演;艾德·蓋恩為埃利恩·薩克(Elion Sacker)飾演。
②Scott M acDonald:A Critical Cinema2,interview sw ith independent Filmmaker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O ctober 26 1992,P223.
③Dirk de Bruyn,Communicating the Unspeakability of Violent Acts in Cinema,in R Fisher&D Palatinus(eds),8th G lobal Conference:Violence and the Contexts of Hostility Conference,Budapest,Hungary,2009.
④James Benning Interview at AV Festival: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Technology,M usic and Film,2012.
⑤James Benning Interview at AV Festival: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Technology,M usic and Film,2012.
⑥Danni Zuvela:Talking About Seeing:A Conversation w ith James Benning,Senses of Cinema,O ctober 2004.
(作者單位:南京郵電大學傳媒與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