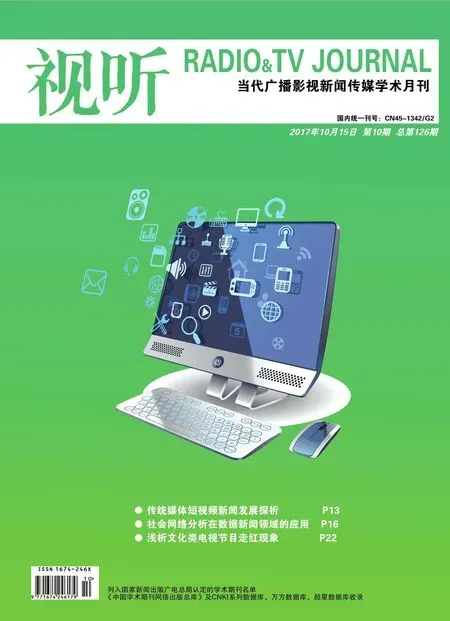網絡綜藝節目《奇葩說》的后現代性分析
□程 可
網絡綜藝節目《奇葩說》的后現代性分析
□程 可
互聯網時代興起的網絡綜藝節目已然摒棄了傳統電視節目的傳播方式,立足網絡探索出新的出路。由馬東團隊制作的《奇葩說》節目以其極具后現代性特征的“奇葩”風格成為近幾年互聯網中的現象級節目,本文試以《奇葩說》為例探討網絡綜藝節目的后現代性特征。
網絡綜藝節目;后現代性;《奇葩說》
一、空間上的后現代表征
(一)現場的空間安排
同傳統媒體相比,互聯網帶有的反傳統的特質十分明顯,其一反電視媒體的保守與嚴肅,具備強烈的后現代表征。《奇葩說》作為新興媒體的自制節目,其自身具有許多互聯網特征,首先在節目現場的空間安排上就與傳統的電視節目存在著很大的不同。
傳統的電視節目,如《魯豫有約》《實話實說》等,都秉持著風格統一的節目現場空間安排。其空間的安排上,主持人和嘉賓坐在舞臺上,觀眾坐在與之相對的位置,是被動的信息接受者。我們的視覺和注意力的主體都在主持人和嘉賓身上,主持人的表現力是整個節目的核心與關鍵,而且傳統的談話節目中,主持人和嘉賓的肢體語言很少,基本是坐在沙發或椅子上靜態地進行交談,雖然觀眾與主持人嘉賓的距離在逐漸拉近,但明顯缺乏更多的互動,此時的觀眾只是作為節目的觀看者與現場氣氛的營造者而存在。
《奇葩說》的舞臺不同于傳統的電視節目舞臺,它的重心已由主持人和嘉賓轉移到了那些“奇葩”選手身上,舞臺成半開放式,他們可以在節目現場的空間里自由隨意地走動,打破了相對封閉的空間,與主持人嘉賓以及受眾進行互動。《奇葩說》節目的主體已經不再是主持人,甚至無法分辨誰是主持人,馬東作為節目的把控者,其主持人的身份不斷被弱化,和每季的隊長及嘉賓一起成為了觀眾,舞臺交由選手們隨行發揮,舞臺倒錯的特征在《奇葩說》中表現得十分明顯。
(二)色彩豐富的服裝
《奇葩說》現已制作到第四季,一直保持著“奇葩”的風格。除去在選拔選手時宣揚的“奇葩”宗旨外,每個選手在參與節目時的服裝也表現出這個節目的特別之處,并與布景相呼應。選手服裝的搭配其實不僅僅帶來視覺上的感受,其真正的用心是演化成了選手身份的一種符號和標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節目包容這種多元化的個性,這也是后現代性的突出特征。范湉湉的蝴蝶結、顏如晶的西裝領結、馬薇薇的眼鏡、肖驍的裙裝,這些都成為他們“奇葩”特質的一部分,在這個節目里,每個選手都是本真的自我,肆意發表自己的觀點,用身上豐富的色彩來彰顯自己的個性。
(三)“孩童化”的風格
波普藝術在20世紀初的時候有另一個名字,叫做“奇葩藝術”,波普將通俗文化與藝術相聯系,與《奇葩說》容納不同的價值觀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因此《奇葩說》的現場布景擁有著波普藝術的風格,迷幻豐富的色彩、炫目的燈光、卡通的形象與選手、主持人以及嘉賓的服裝都相得益彰,仿佛身處一個幼兒園的教室之中。網絡時代的到來,使我們的語言也在慢慢發生著變化,網絡化特征越來越明顯,“孩紙”“寶寶”“棒棒噠”等這種兒童化的語境在我們的生活中被普及與應用,節目中選手大量運用這些“網化”的兒童話語,毫無顧忌地發表自己的看法和觀點,仿佛回到了孩子“童言無忌”的時光。《奇葩說》中不論從場景的設計上還是參與者的服裝與語言都呈現出“孩童化”的風格,反傳統、反權威的后現代性表征在節目中被展現得淋漓盡致。
二、程序設定與奇葩風格
(一)去程式化的開場
與傳統的電視節目不同,《奇葩說》中馬東那些逗趣的語言和花式念廣告的開場很深入人心。《奇葩說》節目把馬東塑造成了一個“奉承金主”卻不惹人反感的可愛形象,與他在央視的正統主持人形象大相徑庭,他不再以主持的功力來迎合受眾,而是以自嘲的語言和喜感的花式廣告口播贏得了觀眾的喜愛。
《奇葩說》開場總是在幾位嘉賓的調侃中拉開帷幕,高曉松的“顏值”、馬東的“眼袋和體重”,甚至還不放過每期請來的男神與女神嘉賓,“馬曉康”組合總能用夾雜著風趣語言的開場瞬間點燃觀眾。馬東、高曉松、蔡康永等的自黑恰恰適應于網絡的大環境,正是因為這種風格,才使得觀眾在他們的嬉笑中以娛樂的態度欣然接受廣告的植入與選手和嘉賓的“奇葩”。
除了第三季中的“穿衣用有范,爭取不犯二”、第四季中的“腦子進水,不如臉上不睡,歐萊雅清潤補水精華”這些與節目風格相契合的廣告詞外,馬東時而簡單粗暴,時而使用故弄玄虛的花式播報方法,讓廣告也成為節目特色的一部分。馬東就是以這種大家心知肚明的方法告訴觀眾,我在讀廣告,我就是為了掙錢,不僅不讓人生厭反而博得滿堂彩,同時選手也會在辯論的過程中加入廣告詞,達到有趣的節目效果。
(二)去規范化的辯論過程
我們總能聽到馬東在節目中說“這是一場嚴肅的辯論”,然而通常這句話之后就是大家的哄堂大笑。《奇葩說》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辯論,它利用辯論的外衣,實則核心要達到游戲與娛樂的效果,所以在《奇葩說》中我們可以看到,作為專業辯手的馬薇薇、顏如晶等人,并沒有把辯論場上的技能都帶入到節目中,而是通過許多風趣的行為和語言,傳達給受眾不同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受眾在選手和嘉賓的思維碰撞中進行自己的思考和感悟。已經制作到第四季的《奇葩說》在辯論規則上不斷地改進,沒有一味地遵循傳統辯論場上的規則,不論是新老奇葩的對決還是加入“奇襲”的環節,都讓這個節目具有娛樂性和可看性。
(三)去原則性的選拔機制
《奇葩說》的辯論機制更加網絡化與娛樂化,現場的觀眾是比賽輸贏的決策者,此節目的結果由現場觀眾投票的“跑票”數來決定,也就是說即使哪位選手的支持票數很高也不見得能得到最后的勝利,因為觀眾在選手辯論的過程中可以隨心所欲地投票,最后和開始的選擇可以隨意更改,他們的標準可以說“毫無原則”。他們更多地以哪個選手辯論得有趣或能感同身受來進行判斷,這個決策完全沒有依據可循,只由觀眾當下的心情來決定。選手們也無所不用其極地發揮自己幽默且有理有據的辯論能力來得到觀眾的認可。
(四)拼貼式的后期剪輯
一個完整的節目,節目內容作為核心不可忽視,但節目的后期剪輯卻也有著如虎添翼的作用。首先,《奇葩說》節目奉行“剪臟字不剪觀點”的原則,節目中讓選手肆意發揮,包括“說臟話”等情緒的展現,之后用效果來掩飾這些臟字,一方面正確引導受眾,另一方面這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方法也為節目增添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娛樂效果。同時,純網綜藝網絡元素的加入是必然。字幕上網絡流行語的應用、選手和嘉賓辯論時表情包的使用,以及加入許多因為網絡而再次爆紅的影視素材,都以拼貼的方式運用在節目中,給觀眾以強調的直觀感受,使得節目極具個性化與游戲性。
三、人物身份的多元化
(一)性別寬容
在《奇葩說》中一反我們傳統對性別的定式認知,可以看到果敢、思維敏捷的馬薇薇,在辯論場上的她堪稱“女漢子”,完全沒有女孩較弱的樣子,金句頻頻,很多尖銳的觀點都透露出女權主義的立場,“女漢子”的標簽在現代社會頻繁地被使用,也說明現代女性不斷強大、不斷中性化的特征。
中國社會還沒有像國外一樣對同性戀的容忍那樣開放,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已然對這一群體多了一些包容。《奇葩說》在選手的選拔上并沒有歧視任何一個群體,只要你會說話,有自己的觀點,就可以是“奇葩”中的一員,隨著幾季節目的播出,肖驍、姜思達等也得到許多觀眾的喜愛,這種對性別的寬容使節目吸納了不同人群的觀點,在思維的碰撞中產生出許多精彩的瞬間和火花,這也與網絡時代多元化的特征如出一轍。
(二)身份消解
身份,指出身和地位,也指身價或本領行為。一個人的身份包含著許多信息,如年齡、性別、職業、籍貫等,都能淺顯地描繪出你是一個怎樣的人。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在判斷一個人的身份時總是從一些標簽上來尋找答案,如金錢、職位等。《奇葩說》在選拔選手時并沒有局限于某一領域或某一范圍,其旨在“尋找最會說話的人”,也就是說,只要你勇于表達且表達得還可圈可點,《奇葩說》就會給你一個盡情發揮的舞臺。
通過幾季節目,可以看到,有許多熟悉的選手在舞臺之外有許多頭銜,從事著不同的職業,如大學教授陳銘、英語老師艾力、演員范湉湉、職業辯手馬薇薇等,但在《奇葩說》的舞臺上,他們這些身份都已經被消解,沒有人在意他們的真實身份,反而更多的人喜歡舞臺上的他們,而他們也在自己需要扮演的角色中獲得快樂。范湉湉的少女心和嘻哈風、馬薇薇的復古眼鏡女漢子形象、顏如晶的鍋蓋頭學生氣都成為他們各自的標簽,或者說這些形象體現了他們真正的內心和面貌。《奇葩說》營造的那種追求自我、暢所欲言的氛圍,讓觀眾體驗到現場的真實和鮮活的個性。
四、節目內容的去工具化
(一)話題生活化
《奇葩說》的核心是“說”,也就是辯論的過程是節目的重心所在,而每期話題的選擇就至關重要。正式的辯論場上的話題通常都是“人性本善還是性本惡”等這些關乎哲學思辨、社會發展等方面的主題,與人們的日常生活距離很遠,而且辯論的技巧和語氣都有固定的程式和規范。《奇葩說》話題的選擇有明顯的去工具化的特征,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首先是話題去熱點化,從未設置過與當下社會熱點和焦點事件相關的話題;其次是話題去重要性,《奇葩說》話題的選擇不關乎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最后話題去時效性,這和前兩點息息相關,既不涉及熱點,固然也就不存在時效性一說。“分手后還能不能做朋友”“要不要選擇做單親媽媽”這些話題都與人們的生活有密切的聯系,這些話題通過各大平臺進行傳播,呈現出“反傳統”且具有爭議性的特質,人們在這些話題中都可以反觀自身,有所感觸和共鳴,因此更加易于傳播和討論。
(二)Show大于Talk
Talk Show翻譯為脫口秀,發展于美國,如今網絡的普及,更是在網絡節目中遍地開花,《奇葩說》也可稱為脫口秀節目。脫口秀節目由Talk和Show組成,在我們熟悉的節目中,大部分的重心在于前者,也就是說主持人和嘉賓的談話更為重要,而“Show”只作為配角。但是《奇葩說》打破了這種傳統配比,使得Show大于Talk,從開場馬東與兩位議長以及嘉賓的相互調侃,到花式廣告的無縫插入和幽默植入,再到選手在辯論過程中毫無顧忌地表達自己,最后拼貼網化的包裝剪輯,我們看到一檔畫風有趣、色彩絢麗的節目。整個節目都為了Show而樂在其中,為觀眾呈現了一個狂歡化、游戲性的富有后現代性特征的網絡自制節目。
五、結語
《奇葩說》在空間安排、程序設定、人物選擇、內容選取上都有著鮮明的后現代性特征,打破傳統娛樂節目的程式,順應了網絡環境的發展,成為極有話題性和影響力的網絡自制節目,為研究更多的網絡自制節目提供了范本,同時也為網絡自制節目今后的發展與制作提供了參考。
1.高旭.《奇葩說》的網絡文化特征分析[D].陜西師范大學,2015.
2.劉姝君,孫曉.“奇葩”說廣告,淺析口播廣告的另類讀法[J].科技傳播,2015(11):68.
3.謝擇月.后現代美學視閾下《奇葩說》的網絡文化特征[J].視聽,2016(06):40-41.
4.郝玉佳,何春耕.后現代視域下的網絡綜藝節目及其反思[J].新聞世界,2016(10):72-74.
5.唐英,尚冰靚.大數據背景下網絡自制綜藝節目的特征及趨勢探析——以《奇葩說》為例[J].新聞界,2016(06):49-52.
(作者系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