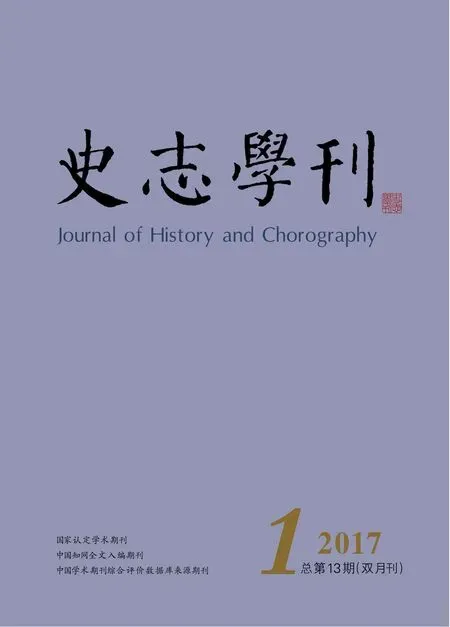中美和解與中越關系的發展(1969—1972)
李桂華
中美和解與中越關系的發展(1969—1972)
李桂華
(中國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100083)
1960年代末期,隨著中蘇關系的不斷惡化,兩國發生戰爭的危險逐漸加大。面對危機,中國及時調整了中美關系,與美國達成和解,但也因此引起了越南的不滿與猜疑。事實證明,在此過程中,中國沒有背叛越南,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中國的利益以促成越南和平的實現。
中美關系 中蘇關系 中越關系 地緣政治
1960年代末期,隨著中蘇之間分歧與摩擦的不斷增多,兩國發生戰爭的危險亦逐漸加大。面對危機,中國對包括中美關系在內的諸多領域做出重大戰略調整,最終使中國轉危為安,并對此后的中美關系、中蘇關系及中越關系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對于此問題,海內外學者從不同視角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代表性的著述包括:沈志華、李丹慧:《戰后中蘇關系若干問題研究:來自中俄雙方的檔案文獻》,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呂桂霞:《遏制與對抗:越南戰爭期間的中美關系1961—197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沈志華、李丹慧:《中美和解與中國對越外交(1971—1973)》,《美國研究》2000年第1期等。)但是,以1969年后中國的危機處理過程為研究內容,系統性地梳理與研究此間中美和解及其對中越關系影響的著述卻較為匱乏。因此,筆者擬以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利用涉及該問題的中外檔案資料,梳理中蘇關系破裂后中國對美政策的系列調整,并初步探討此番調整對中越關系走向的影響。
一、危機來臨:中蘇關系的惡化與戰爭危險的迫近
1950年代末期,中蘇兩黨及兩國之間的分歧日益增多,黨際與國家關系均受到了嚴重損害。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單方面決定召回在中國工作的所有蘇聯專家[1]王泰平.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P235-236)。中蘇國家關系宣告破裂。1966年3月,中共中央致信蘇共中央,拒絕參加蘇共二十三大。此后,兩黨關系亦宣告中斷。隨著中蘇關系的日趨惡化,蘇聯加緊對中國周邊國家進行拉攏,企圖以此孤立和封鎖中國。1964年底,蘇聯正式放棄其在越南問題上的“脫身政策”,宣布將向越南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此后,蘇聯不斷加強與越南的戰略合作,在越美和談和對越援助等諸多領域強化其影響力,并借機離間中越關系。1966年3月,蘇聯“提出了要日本幫助它開發西伯利亞的四項龐大計劃”。日本方面認為,蘇方對于此事所表現出的“期待”和“熱情”,使日本“大吃一驚”。對此,日本方面甚至評論說,蘇聯此舉是出于“對共產黨中國的政策”需要,有著“國防上的理由和政治上的理由”[1]蘇聯領導聯日反華已到不擇手段地步.人民日報,1966-3-25.。蘇聯還加大了對印度的支持力度。從1962年到1970年間,蘇聯向印度提供了1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1971年8月,蘇聯又同印度簽訂條約,規定:“在任何一方遭到進攻或受到進攻的威脅時”,“應立即共同協商,以便消除這種威脅,并采取適當的有效措施”。對此,葛羅米柯指出:“從蘇聯邊界以南形成的局勢來看,這具有特殊的重要性”[2]劉志青.恩怨歷盡后的反思——中蘇關系七十年.黃河出版社,1998.(P439)。此外,蘇聯還不斷尋求與美國和平共處與共管世界,不斷在越南戰爭及中國核試驗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支持美國立場,對中國進行指責。
除在外交上封堵、孤立中國外,蘇聯還明顯加強了在中蘇、中蒙邊境的布防,在軍事上威懾中國。1963年,蘇聯重新開始在蒙古布防。1966年1月,蘇聯與蒙古簽訂《蘇蒙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在中國北部邊界中段形成了一個對中國華北、東北和西北三個方向都能構成軍事威脅的龐大區域,其最南端至北京的直線距離只有560多公里。按照蘇軍的作戰理論計算,蘇軍只需10多天即可抵達。在此期間,蘇聯還不斷向中蘇及中蒙邊境增兵。據中方的情報顯示,在1961年時,蘇聯在其遠東戰略區的兵力只有12個不滿員的師和兩百架飛機。但是,到70年代初,蘇聯在該地區的兵力已增加到54個師,作戰總兵力118萬,占其軍隊總額的27%。除大量向與中國鄰近地區增兵外,蘇軍還經常舉行針對中國的軍事演習,在中蘇、中蒙邊境地區制造緊張氣氛[3]王仲春.中美關系正常化過程中的蘇聯因素(1969—1979),黨的文獻,2002,(4).。
在外交上封堵及軍事上威懾的同時,蘇聯與中國在邊境地區的沖突亦明顯增多。來自中方的文件顯示:“1964年以來,蘇聯政府大量增兵中蘇邊境,變本加厲地破壞邊界現狀,進行武裝挑釁,制造流血事件”。從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僅由“蘇聯方面挑起的邊境事件竟達4189起之多,比1960年到1964年期間蘇聯方面挑起的邊境事件增加了一倍半”。在一系列沖突中,“蘇聯軍隊侵入中國領土,殺人放火,打死、軋死手無寸鐵的中國漁民、農民,甚至活活把他們扔到江里。”[4]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人民日報,1969-5-25.與此同時,蘇聯方面則聲稱:“在1965年和隨后幾年里,中國方面侵犯中蘇邊界的次數明顯地增加了”。他們“成批地侵入蘇聯領土”,“舉行反蘇示威”,“企圖挑起邊界武裝沖突事件”[5](蘇)普羅霍羅夫.關于蘇中邊界問題.商務印書館,1977.(P214)。而且,伴隨著雙方沖突的加劇,雙方逐漸將爭奪的焦點置于中蘇東段邊界上的吳八老島、七里沁島和珍寶島之上。雙方不斷在這些地區對罵、推搡和群毆。對峙手段也從一開始的口頭爭辯發展到后來的棍棒相加,直至動用沖鋒槍和裝甲車進行對攻[6]徐焰.1969年中蘇邊界的武裝沖突.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共和國重大歷史事件述實.人民出版社,1999.(P225-226)。雙方沖突的激烈程度不斷上升,中蘇邊境的緊張局勢正逐步加劇。
1969年3月2日,中蘇兩國在珍寶島進行了兩國之間的第一次邊界武裝沖突。中國方面擊退了蘇聯軍隊的進攻,自1947年以來第一次改變了該島的控制權。珍寶島事件發生后,蘇聯多次試圖登島奪回控制權,但均遭到中國軍隊的頑強阻擊。此后,顯然是出于報復中國的考慮,蘇聯于是年8月13日在新疆鐵列克提地區對中國進行了軍事打擊,并造成了中方的重大犧牲。與此同時,蘇方開始以核武力對中國進行恫嚇。在珍寶島事件后不久,莫斯科電臺即威脅性地指出:“蘇聯的核導彈是強大的,可能造成千千萬萬人的悲慘命運”。隨后,該電臺又接連多日大談蘇聯核力量的強大以及中國核力量的弱小[7]沈志華.中蘇關系史綱.新華出版社,2007.(P390)。8月18日,蘇聯通過其駐美國大使館官員向美方提出:“如果蘇聯對中國的核設施發動襲擊,美國會作何反應?”[8](美)亨利·基辛格著.陳瑤華等譯.白宮歲月(第1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P239)至此,中蘇已經走到了戰爭的邊緣。整個世界都開始密切關注中蘇關系的走向,以及兩國發生常規戰爭甚至核戰爭的可能性。
二、應對危機:中美關系的改善
針對來自蘇聯的戰爭威脅,中國開始在內政及外交等系列問題上做出改變,轉化“敵、我、友”的戰略態勢,形成新的戰略格局。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舉措包括強化三線建設、“一號命令”疏散、中日和解、中美和解等。其中,對戰略格局影響最大的,莫過于中美和解。
其實,在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的心目中,美國一直不是中國可以依靠的力量,而是中國在亞洲及世界最重要的敵人之一。新中國成立后,為防止美國對中國的威脅,中國多次直接或間接與之對抗。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中國派出志愿軍開赴朝鮮,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兵戎相見,以保護中國東北邊疆。1950年至1954年,中國派出援越顧問團支援越南的反法斗爭,又與美國進行了一次間接對抗。1964年“北部灣事件”爆發后,特別是1965年初越南戰爭升級后,中國對美國入侵中國的擔憂進一步升級。中國開始重點研究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的問題,并開始在中越邊境地區部署兵力,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三線建設”。
中蘇關系惡化后,基于對世界格局的認識,中方將“帝國主義”與“修正主義”相提并論,認為美蘇已經勾結起來,共同對中國進行封鎖和包圍。直至中共九大召開,中國方面仍然堅定的宣稱:“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可……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決不可以忽視美帝、蘇修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性。我們要作好充分準備,準備他們大打、準備他們早打。準備他們打常規戰爭,也準備他們打核大戰。”[1]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1969-4-28.雖然中方不斷強調美蘇均為中國的敵人,但是,自中蘇交惡以來,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更強烈地感受到了來自于蘇聯的戰爭威脅。特別是1968年8月蘇聯出兵占領捷克斯洛伐克并發表“有限主權論”以及1969年3月間發生中蘇珍寶島沖突之后,中國領導人對蘇聯威脅的憂慮明顯增多。基于這種情況,毛澤東等人開始重新審視中國所處的地緣政治格局,謀劃外交策略的重大調整。
1968年11月,中方向美方建議恢復自同年1月中斷的中美大使級華沙會談。1969年2月,毛澤東提出要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和葉劍英等人研究國際問題[2]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P281)。周恩來告訴幾位老帥,應“協助主席掌握戰略動向,供主席參考”。而且,“這個任務很重要,不要看輕了”[3]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P165-166)。是年7月11日,陳毅等人將題為《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的書面報告報送周恩來。報告指出:美國由于經歷過侵朝和侵越兩次戰爭的失敗,而且其戰略重點在西方,因此“不致輕易發動或參與反華大戰”;蘇聯則出于對美國因素的考慮及對中國力量的忌憚,對于侵略中國也有“很大顧慮和困難”。同時,“蘇修假借反帝的名義或利用反華的掩蓋進行擴張”,“在北非、中東、東南亞等地占領了一些陣地,甚至伸手到美帝的后院拉丁美洲”。蘇聯“擠壓美帝地盤”的作法必將使“它們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3](P173-177)。在報告中,陳毅等人估計,由于中、美、蘇之間的大國博弈,由美蘇共同或是單獨進行反華大戰的可能性均比較低。而且,由于美蘇矛盾大于中蘇矛盾,中蘇矛盾大于中美矛盾,因此真正的、現實的利害矛盾還是在美蘇之間,而不是在中蘇或是中美之間。實際上,這份報告改變了中方對國際形勢特別是中美及中蘇關系原有的判斷,初步勾勒出了中、美、蘇三方力量相互制衡的國際戰略格局,并為中美關系的緩和提供了理論依據。
就在陳毅等人對國際形勢研究期間,國際形勢又發生著重大的變化。7月21日,美方宣布:放寬對美國旅游者購買中國貨物的限制;放寬美國公民去中國旅行的限制。7月26日,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曼斯菲爾德致信周恩來,要求訪華并結束中美“二十年長期交惡”的局面[1]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P179)。之后,美國總統尼克松亦多次公開表示:美國不同意蘇聯關于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建議,不參加任何旨在孤立中國的行動,并表示愿同中國對話。”[2]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P312)8月27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將蘇聯打擊中國核設施的圖謀公之于眾,以提示中國警惕。9月5日,美國副國務卿埃利奧特·理查森發表講話指出:美國“不打算利用蘇聯和人民共和國之間的敵對來謀求我們自己的好處”,再一次表達了對蘇聯進攻中國的反對[3](美)亨利·基辛格著.陳瑤華等譯.白宮歲月(第1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P239)。在美國不斷向中國示好的同時,蘇聯則不斷對中國發出戰爭威脅,戰爭已一觸即發。9月1日,蘇聯總參謀長兼國防部第一副部長馬特維·扎哈羅夫在蘇聯機關報《消息報》上發文指出,蘇聯的“戰略火箭部隊”“隨時準備立即開動”,“出其不意地進行打擊”,“使敵人措手不及”[4]衛東思.核訛詐救不了新沙皇的命.人民日報,1969-9-12.。9月10日,蘇聯通過其駐聯合國代表向美國表示,蘇聯在軍事上具有對中國的壓倒優勢,如果中國現在的敵視態度繼續下去,一次軍事較量可能是無法避免的。9月16日,英國倫敦《新聞晚報》刊載了經常透露蘇聯重大決策的維克托·路易斯的文章。該文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一直在討論一場中蘇戰爭的可能性。而且,如果戰爭發生,“世界只會在戰爭爆發之后才能得知”。該文還提到,蘇聯有可能對設在羅布泊的中國核試驗基地進行空襲[3](P241-242)。
在對國際形勢發展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上,陳毅等人于9月17日將新的研究成果《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報送周恩來。報告對中、蘇、美三國的局勢進行了大膽的預測,并進一步在戰略意義上點出了中國與美國改善關系的可能性與可行性。報告指出:“雖然蘇修確有發動侵華戰爭的打算”,但由于美國反對,而且“表示要同中國改善關系”,這就使蘇聯“深怕我國聯合美帝對付它”。因此,“在中、美、蘇三大力量的斗爭中,美對中、蘇,蘇對中、美,都要加以運用,謀取它們最大的戰略利益”。在上交報告后,陳毅又向周恩來口頭建議,中國應該在“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打開中美關系”[1](P185-187)。目前尚缺乏有關毛澤東等人對報告態度的資料。但是,從此后事態的發展可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最終與報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12月7日,中國政府釋放了兩名誤入中國海域的美國游客。12月11日,中國駐波蘭大使館主動邀請美國駐波蘭大使到中國大使館做客[5]王永欽.1969年—中美關系的轉折點.黨的文獻,1995,(6).。1970年初,中國駐波蘭大使王國權向美國大使建議把中美會談轉至北京舉行,而且中國將歡迎一位高級官員擔任美國代表團團長。”[6](美)理查德·尼克松著.裘克安等譯.尼克松回憶錄(中).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P654-655)是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會見斯諾時表達了歡迎尼克松訪華的意愿[7]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P592-594)。4月,經毛澤東提議,中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并在國際上引起巨大轟動。
在中國不斷向美方釋放善意的同時,美方也積極回應,表示愿意與中國進行會談。隨著雙方的持續互動,中美和解的大門最終打開。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并與周恩來進行了會談。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并于28日發表《中美聯合公報》。尼克松訪華和《中美聯合公報》的發表,標志著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開始。此后,盡管雙方仍有不少問題有待解決,但由中美主導的新型世界格局已經建立起來了,而此后包括中蘇對峙等系列危機也隨之得以解決。
三、背叛與否:中越關系的嬗變
為應對蘇聯的戰爭威脅,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領導人審時度勢,適時地調整了中美關系,建立了“聯美抗蘇”的地緣政治格局。對于中國方面的這一轉變,越南方面無法理解。他們多次就此事批評中國,認為中國“背著越南與美國進行談判”,并“無恥地背叛了越南人民”[1]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The Truth About Vietnam-China Relations Over the Last 30 years. Foreign LanguagesPress,1979.(P46)。為打消越方疑慮,周恩來先后兩次趕赴河內,向越方通報中美會談的情況。但是,越方始終不肯相信,亦不愿原諒中國。那么,中國在中美和解過程有沒有背叛越南呢?
關于中美會談的詳情,中方的資料至今未予解密。據美國及越南方面的解密檔案顯示,在中美談判之前,美方即認為中國在印度支那問題上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美國政府曾多次對中國在越南問題上的影響力進行評估。詳見于:Kissinger to Nixon,18 April 1970,FRUS,17,PP.195-196;Airgram Are from Hong Kong,7 January1971,enclosed in Hold ridge toKissinger 18 January1971,Kissinger Papers,BoxCL11 Chronological Files, 2 Jan-16 Feb,1971,Manuscript Division,the Library of Congress,Washington DC;SNIE 13-10-71,18 February 1971,FRUS,117,P.267)。因此,在與周恩來會見的當天,基辛格就向周恩來指出,“我們相信,印度支那戰爭的結束將會加速我們之間關系的發展”。“我們準備在這場沖突結束之后的一段時間內,撤出我們在臺灣參與這些沖突的部分軍隊”。而且,基辛格特意強調,他并沒有把臺灣問題“作為條件提出來”的意思[2]Memcon,Kissinger and Zhou,9 July1971,4:35-11:20 PM,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box 1033,China HAK Memcons July, 1971.(P20)。雖然基辛格極力辯解,但他將臺灣問題與印度支那問題相聯系以迫使中國向越南施加影響的意圖已非常明顯。對于基辛格的上述提議,周恩來堅定地予以拒絕。他強調指出:“應該由印度支那三國人民決定他們各自的命運”。美國應該“立即完全地撤出所有軍隊,把問題留給印度支那三國人民來決定”。這是美國“撤出印度支那最體面、最光榮的辦法”[2](P21)。對于周恩來的上述回答,基辛格極為不滿,他轉而明確提出了希望中國在越南問題上施壓的意見,并威脅越南戰爭的繼續將妨礙中美關系的發展。但是,周恩來依然堅定地予以拒絕。在結束此次會見回國后,基辛格的特別助理溫斯頓·洛德在整理會談記錄時提到,“在印度支那問題上,即使在他(周恩來)認識到你(基辛格)把這件事與臺灣問題相提并論之后,他的語言仍是相對克制的,他對他的朋友(越南)堅決支持并保持不干涉態度”[2](P21-25)。
在此次會談結束后的第三天,周恩來就趕赴河內向越南通報會談的情況。在會談中,周恩來向越方指出:“印度支那問題是我們與基辛格會談中最重要的議題。基辛格說,美國已經把印度支那問題的解決與臺灣問題的解決聯系起來。只有當他們可以從印度支那撤軍的情況下,他們才會從臺灣撤出軍隊。就中國而言,從南越撤出美國軍隊是頭號問題,而中國加入聯合國的問題居于其次。”[1](P47-48)對于周恩來的上述解釋,越方并不相信。據越南的檔案顯示,黎筍認為:在侵略越南的戰爭中,“美國是一個意外接著一個意外”,始終無法準確獲知越方的戰略意圖,因而才會在戰爭中屢屢受挫。但是,中美達成和解后,中國就會出賣越南,把越南的計劃告訴美國,美國也就不會再有任何意外了[3]“Discussion between Zhou Enlai and Le Duan”,77 conversations.(P177)。其實,不只是越南領導人不相信,基辛格對此亦表示懷疑。7月14日,基辛格在致尼克松的匯報函件中即指出:盡管周恩來在越南問題的談話中態度強硬,但周恩來卻在送別他本人的時候“令人驚奇地”表現出對美國的“同情與開放的態度”。他希望美國與越南在巴黎的談判能夠取得成功,而且答應會在美國宣布總統訪問北京后與河內進行溝通,等等。因此,基辛格得出結論:周恩來將“與河內溝通,并可能對他們施以影響”[1]Kissinger to Nixon,14 July1971,FRUS,17.(P453-455)。此后,隨著中美的進一步接近,美國的官員及媒體也開始認為,只要中國愿意向越南施壓,美國就可以體面的結束戰爭,從越南撤軍。因此,在與周恩來的第二次會見中,基辛格再次提出了將臺灣問題與印度支那問題捆綁解決的建議,以向周恩來施壓。對此,周恩來不但沒有接受,甚至轉而向基辛格施壓指出:“希望美越關于結束越南戰爭的談判能夠在尼克松訪華時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否則,中美的聯合公報將無法表達雙方對印度支那所取得的任何共識。”[2]Memorandum ofconversation,Kissinger and Zhou Enlai,21 October 1971,4:42—7:17 pm NSC Files,ox1034,Polo II—HAK Ch ina Trip 1971 Transcript ofMeetings,NPMP.
最終,基辛格沒有說服周恩來同意向越南施壓。因此,基辛格對即將訪華的尼克松提出:中國領導人不可能對他們的朋友過于強硬。因此,美國應該歡迎北京對如何結束越南戰爭采取具有“建設性意義”的態度,但應同時向北京說明,這不是改善兩國關系的“前提條件”[3]“The President’sBriefing Paper for the China Trip”,Indochina-Vietnam,NSC Files,Folder4,Box847,NPMP.。對于這一建議,尼克松沒有采納。他仍然希望能說服中國領導人,使他們同意以臺灣問題為交換,在印度支那問題上向越方施壓。在飛往北京的途中,他就在他的“談話要點”記錄中寫下:1.“臺灣=越南=交換”,“你們的人民希望我們在臺灣有所行動。2.我們的人民希望你們在越南有所行動”[4]Nixon’spersonal notes,16 February 1972,Folder 1,Box 7,President’sPersonal Files,White House President’sFiles.NPMP.。1972年2月22日,在尼克松抵達北京后的第二天,他就在與周恩來的會談中指出:“目前,我們在臺灣的軍隊中有三分之二是為了支持東南亞戰場”。“我已經決定,一旦東南亞的問題得到解決,無論我們在這里談得怎樣,我們都會從臺灣撤走這批軍隊。而留下的那三分之一,也會在和平解決問題取得進展后,進入撤離的程序。”[5]Memorandum ofconversation,Nixon and Zhou Enlai,22 February 1972,Tuesday,2:10-6:00pm,President'sOffice Files,Memora nda for the President,Box87,“Beginning February 20 1972”,NPMP.對于尼克松提出的“交換條件”,周恩來再次予以回絕,他指出:“對于這一問題,只有印度支那人民才有權與你們進行談判”。而且,既然確定了“從越南體面撤軍”的目標,美國就應該“采取更大膽地行動”。只有這樣,美國才能在這些地區“獲得民心”,并在該地區產生更大的影響。至于臺灣問題,周恩來指出:“我們已經等了20多年了,我們還可以再等幾年”[5]。
可見,在經歷了基辛格、尼克松的多次勸說后,周恩來并沒有同意將臺灣問題與印度支那問題捆綁解決,而是建議美國與越南進行談判,并盡快從印度支那撤軍。也就是說,中國不但沒有背叛越南,犧牲越南,而是在談判中不惜以延后中國臺灣問題的解決為代價,促成印度支那問題的優先解決。但是,越方始終不愿相信中方的解釋。他們傾向于認為,中美之間一定有關于印度支那問題的“陰謀”。而且,由于中越兩黨、兩國之間不存在正常的黨際與國家關系,而是以意識形態的同質性為基礎建立起了一種畸形的“共產主義”關系范式,因此,在越南看來,在其與美國交戰期間,中國與美國進行和解的舉動本身即意味著對越南革命事業的“背叛”。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中美和解后不久,越南《人民報》即發表《“尼克松主義”一定破產》的社論,對中美會談進行影射批評[6]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P469-470)。之后,越方甚至在黨內下達通知,稱基辛格到北京是“尼克松主義”的擴大,是“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制造分裂”“搞和平演變”。至此,越南已經徹底失去了對中國的信任,中越關系也在懷疑與排斥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責編:張佳琪)
The Sino-US Reconcil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ino-Vietnam Relationsduring 1969 and 1972
Li Guihua
李桂華(1980—),男,山東東營人,中國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歷史學博士,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當代中國史。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處理中越關系的歷史梳理及經驗研究”(項目編號:13CDJ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