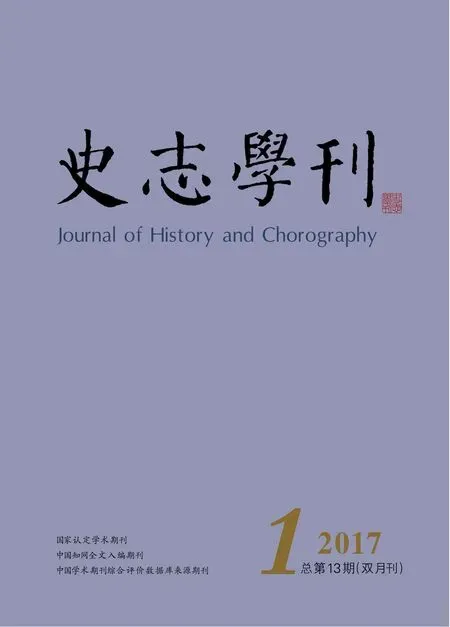中西農業文明下的牛耕與馬耕
陳桂權
中西農業文明下的牛耕與馬耕
陳桂權
(四川文理學院巴文化研究院,秦巴文化產業研究院,四川達州635000)
10世紀前西歐以牛耕為主,之后馬耕逐漸推廣。歐洲的馬耕推廣是技術進步、三田制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的共同結果。比較而言,馬耕在中華農業文明中始終不太普遍,主要是因為馬的軍事用途更被看重,犁地主要依靠牛來完成。中西農業文明中對于牛耕與馬耕的不同依賴,既是各自不同農業發展結構的體現,也是由不同社會經濟特點所決定的。
中西農業文明 牛耕 馬耕 犁地
英語中常會用“to work like a horse”表示要努力工作,“work for a dead horse”表示“徒勞無益”;漢語中常用“牛一樣的勤勞”“老黃牛一樣的精神”來夸獎一個人。牛與馬這兩種與人類關系密切的動物,在東西方文化中有著不同的用途與地位,圍繞著它們這種差異也形成了相應的文化寓意。對于牛與馬這兩種動物,從與農業相關的角度來考察,那就是犁地了。因此,本文就“牛耕”與“馬耕”在我國與歐洲農業中的不同地位,做一分析探討,以期闡釋不同農業發展模式下的技術選擇問題。對于中西農業發展結構的不同,曾雄生先生在《中西農業結構及其發展問題之比較》一文中已做了精當的闡釋,文中稱中國農業耕地以牛耕為主,西歐在使用牛耕的同時,也廣泛使用馬耕,主要原因是三圃制的實施能為馬提供更為充足的燕麥飼料[1]曾雄生.中西農業結構及其發展問題之比較[J].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3,(3).(P49-58)。該文指出了中西方農業在畜力使用方面的差異,是本文進一步闡釋的重要參考。除農作制度不同外,還有其他諸如社會經濟成本、地緣政治、人地關系等多種因素,導致了中西農業文明下在犁地時對畜力使用的不同。
一、10世紀前歐洲的牛耕
在古典時代與中世紀前期的歐洲,拉犁主要還是公牛的任務,偶爾在一些土壤表層較淺或窮人的地里,能看到用母牛或驢子在耕地的農民。據一份來自1086年的英國農業調查顯示,當時各領主土地上“馬的比例僅占畜力的5%”[2](美)John Langdon.中世紀英國農業的一場悄悄的革命:公元1100年至1500年的馬耕[J].農業考古,1998,(3).(P183),當時的畜力主要包括牛、馬、驢子、騾子。這時候,馬的主要用途還是充當坐騎及運送旅客。至于為何此時未用馬來代替牛耕地?學者們認為可能主要有這樣兩點原因:
其一,這個時期實行的“兩田制”不能生產出足夠的糧食來養馬。歷史上歐洲的田制有一個由“兩田制”到“三田制”的變化過程,中世紀是轉變期。相比兩田制,三田制在作物播種總面積與輪作類型上更多樣,其收獲物也更多了。因此,利用三田制的農民有足夠的糧食與飼草來養家畜。
其二,適合馬耕的技術裝備尚不健全。那時的馬還沒有釘馬掌,脆弱的馬蹄經不起地里各種小石頭的折騰,即便不下地,日常運輸也不能長途進行。人們通常用一些保護物纏在馬蹄上,羅馬人還給馬穿上了“蹄靴”。另外,在古典時期的歐洲,人們給馬戴的軛套是直接套在它的脖頸上。這種軛套勒住了馬頸下的主動脈,使得它們極其不舒服,自然就使不出力量來。而牛就不一樣了,它們那聳起的肩膀,較適合安放牛軛,即便沒有這種肩部的套具,還可以套在牛角上。1170年,一本叫《開心果園》的書中提到,在法國的阿爾薩斯地區,牛角是挽犁的地方。這種挽牛角的做法,相較于勒馬脖子的技術要先進些,但仍舊不能使牛發揮出最大的潛力。
所以,歐洲大規模使用馬耕的歷史是在12世紀以后。美國學者John Langdon在《中世紀英國農業的一場悄悄的革命:公元1100年至1500年的馬耕》中,對馬耕如何在英國逐漸取代牛耕有比較全面的論述。在他的論文中,我們可以看到馬耕取代牛耕的過程并不是那么容易。農民對此有成本的計算,還有習慣性的問題。當然,最重要的是與當時社會經濟需求是否適應。歐洲的馬耕最終能取代牛耕,是因為它適應了社會的普遍需求。在當時“擁有少于10英畝土地的農民比較偏好使用馬耕地,因為他們較輕便的犁頭更合適用馬拉,而且馬在耕地之外還可用作乘騎、拖拉貨物”[1](美)克萊頓·羅伯茨,戴維·羅伯茨,道格拉斯·R.比松著.潘興明等譯.英國史上冊[M].商務印書館,2013.(P110)。也就是說,相比于牛,馬的用途更廣。雖然養馬的成本較高,但因農作制度革新之后,糧食的產量也大幅度提高,這就使對馬的飼養有了物質基礎。同時,馬耕的推廣又促進了農業總產量的提高。
二、牛耕與馬耕之優劣比較
對于牛耕與馬耕各自優劣的比較,人們通常從成本與收益角度來進行分析比較。13世紀農學家們對此的看法是“馬吃更多的燕麥,馬得釘掌,而牛不用這些。因此,養馬的費用比牛多4倍。而且牛的脾氣更溫順、老了還可以賣給屠夫吃牛肉,而馬只能賣皮,甚至有一段時期,馬是不允許被宰殺的。所以,馬的價值折損費較大,而牛的保值性卻較高。”[2](英)波斯坦.劍橋經濟史(第1卷).中世紀的農業生活[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P125)另外,馬更容易生病。北魏賈思勰所著《齊民要術》卷六中記:“常系獼猴與馬坊,令馬不畏,避惡,消百病也”。這就是民間一種防止馬生病的措施。吳承恩給猴頭孫悟空安個“弼馬溫”的官銜,其文化寓意就源于此。馬的優勢主要體現在廣泛的用途上:駝、騎、拉,民用、軍用都可以。相比之下,牛在這方面要遜色多了。雖然牛也拉車,但畢竟不如馬常用。此外,馬在速度與炫耀性消遣上,又比牛有優勢。故而,我們似乎可以解釋為什么中世紀早期,領主的土地上多用牛耕,而農民反而喜歡馬耕的現象了。因為,馬對于領主而言是坐騎,是騎士耀武揚威的裝備,至于像拉犁、拉磨那些苦活累活還是讓牛去干合適些;而農民喜歡用馬,除了我們說的馬用途更廣之外,或許是他們還想在農閑之余,體驗下策馬奔騰的感覺。
再者,馬耕在速度上也具有優勢,16世紀的法國農業家們對此給予高度贊揚,他們聲稱:“馬一天干的活是牛的3倍甚至4倍”。對于農民而言,快速犁完地當然是好事。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馬耕比牛耕更快的論斷,還要視情況而定。耕地是人與動物相互配合的協作式勞動,其效率的高低是兩者合力的結果。因此,單看動物勞力大小、速度快慢,或者犁地者技術的好壞,都不足以說明問題。從速度上看,馬定是快于牛。只是,耕地時,馬的步伐快慢需要與耕地者的步伐協調一致。若馬拉的步伐太快,耕地人無法適應,最終也不能保證耕地的效率;而牛的腳步也不可能太慢,因為犁地速度的控制權掌握在人的手中。此外,還有些因素會影響到耕地的速度,如土地平整度,犁平地比犁坡地快;耕者技術的高低;犁頭的類型,這也很重要。歐洲常用一種輪犁,這種犁頭操作起來更為輕便,且速度更快,能很好地適應馬耕;我們中國的多數犁頭,既不是為馬耕設計,速度自然就快不起來。故,馬耕更適合歐洲,這是技術、社會、經濟等因素綜合的結果。再后來,當現代農業機械化生產要普及時,那些推廣耕地機器的宣傳者們又把馬耕說得一無是處。如蘇聯上世紀50年蘇聯作家伊林《五年計劃故事》中有段關于工廠與農民所有的“引擎”對比的記錄:
谷類工廠有曳引機,農民有什么引擎呢?馬。馬是所有機器中最貪食,最嘴饞的。他要嚼掉農民田里出產的一半。在烏克蘭草原地方,農民為他的馬一年要花費五十金鎊——跟他給全家人所花費的一樣多。
馬是一種最貪食的引擎,同時它是一種最孱弱的引擎。一部曳機可以做二十多匹馬的工作,并且用馬耕地不能像曳機耕得深。但是,連這種孱弱的引擎給農民用還是太強了。普通的馬給農民做活,還沒有用出全部精力。想一想馬全部閑散著的日子吧。一年當中只勞動一百天,可是一年到頭,天天都得喂它。曳引機只是在工作的時候才用汽油。并且馬做起活來,也太少了。因為在農民的田里并沒有充分的工作使得馬忙。那又是為什么呢?因為田地太小了。半匹馬就夠耕窮農民所有的那點土地[1](蘇)伊林.五年計劃故事[M].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P154)。
這是一段鼓吹集體化農業的文字,其核心觀點是說集體農業可以推廣機械生產,可以最大限度利用勞動工具。在規模較大的農場上犁地,自動化的農機相較于馬更具有優勢。這是農業專業化之后的結果,但對于小農而言,馬多樣化的用途,使他們不愿意輕易地放棄馬耕。可以說,在技術史上并沒有最好的技術,只有更合適的技術。當社會經濟條件發生變化時,原來的最優可能變成次優。
三、“戎馬生涯”“放馬南山”“卻走馬以糞”:從常用短語看馬在漢民族中的主要用途
《老子》中有這樣一句話“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這是對馬在農耕社會中的主要功用轉化的扼要說明。對于“卻走馬以糞”的解釋,學界前輩有充分的討論,在此就不贅言。無論何種解釋,放馬田中去糞地也好[2]曾雄生.“卻走馬以糞”解[J].中國農史,2003,(1).(P12),用馬去運糞也罷[3]游修齡.釋“卻走馬以糞”及其他[J].中國農史,2002,(1).(P103-106),都說明平和期間馬的主要功用不在于軍事。也就是說,相較于農用,馬的軍事用途在我國古代是第一位的。我國對于六畜的排列順序:馬、牛、羊、豬、狗、雞,馬之所以居于首位也是因為它的軍事用途所決定的,從社會經濟角度而言,牛應該居首[4]曾雄生.中西農業結構及其發展問題之比較[J].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3,(3).(P54)。
在中華農業文明圖景中,牛耕是必備元素之一。東漢應劭在《風俗通義》中強調:“牛乃耕農之本,百姓所仰,為用最大,國家之為強弱也”。即強調牛于耕地的重要性。在戰國牛耕推行前,土地主要是靠“耦耕”來翻地。學界對于“耦耕”還未形成統一的解釋,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這是一種人力的耕地方式。戰國時期,耕地主要靠牛力,孔子弟子冉耕、司馬耕皆以牛為字,就可為證。到了漢代,在北方關中地區出現“二牛抬杠”的耕地形式。再后來,隨著犁具的改進,牛耕的效率越來越高。當然,農民除了用牛耕之外,也還是有用馬耕地。據《鹽鐵論》卷三《未通》稱,西漢時:“農夫以馬耕載”,同書卷六《散不足》記:馬“行則服軛,止則就犁”。只是養馬的成本很高,不是普通農家可以支撐的,據《散不足》稱當時養馬一匹“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故而中原農耕區少有馬耕,其主要是在邊緣地區,或者少數民族地區存在。《唐會要》卷一百記載,在突厥北部,距離長安一萬四千里的地方,有個“駁馬國”。此國擁兵三萬,馬萬匹,地寒積雪,但冬天樹木卻不凋零,待春天冰雪消融后,當地人“以馬耕種五榖,馬色并駁,故以為國號”。顯然這個國家以斑駁色彩的馬來耕地,對于唐朝人來說,這僅是一種域外風情。清代盛京地區的旗人也用馬耕,如《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百記:“盛京侍郎朝銓奏奉,省所屬藉馬耕種,兼資旗人當差,嗣后如有偷竊馬匹者,民人俱照盜牛及宰殺例治罪”。在此,作為農耕的馬與牛的地位相當。當今,在西藏地區的加查縣馬的主要用途還是:“乘騎和運輸,在部分缺牛耕的村用馬耕地”[1]加查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加查縣志[M].藏學出版社,2010.(P314)。可見在藏區馬耕也僅是牛耕的一種補充。明代文人徐渭把自己的不得志,說成“于文不幸若馬耕”[2](明)徐渭.抄代集小序.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五)[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由此可見馬耕在漢文化中的地位。
對于中華農業文明中不普遍使用馬耕的原因,排除動物生理特點、技術因素,還受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中華農耕文明周邊是被游牧民族包圍著的,從殷商征伐鬼方,到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再到秦始皇修筑長城,至漢匈奴戰爭,五胡亂華,唐代與突厥的戰爭,宋代與西夏、金、蒙古,明代與漠北蒙古,清代對西北的用兵,樁樁件件都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對抗。這種文明的沖突是地緣政治在擴張中的交織與對抗。在這樣的大歷史背景下,馬多數時候充當的是“戰車”角色。漢人用騎兵的技術天然不如游牧民族高超。蒙古鐵騎能橫掃歐亞大陸,靠的就是卓越的騎兵。馬是騎兵的關鍵,沒有好馬,騎兵的威力會大打折扣。在不同兵役制度下,對馬的管理方式也是不同的。馬匹,尤其是好的馬匹,在戰時要被國家征用。不僅如此,歷代對馬的管理有一套制度,叫“馬政”。由此也可體會到馬的軍事用途更被重視,正如牛的農業用途被重視一樣。《商君書·去強》說:“強國知十三之數:竟內倉、口之數,壯男、狀女之數,老弱之數,官士之數,以言取食之數,利民之數,牛、馬、初槀之數。欲強國不知強之三之數,地雖利,民雖眾,國愈弱至削。”[3](秦)商鞅.商君書[M].中華書局,2009.(P41)為了強國,政府需掌握確切的“牛、馬之數”,這就是“農戰”思想的體現。另外在中國農業的結構中,北方農業以旱地為主,南方以水稻田為主,稻田的土壤粘重,犁耕時更費力,而耐力更好的東亞黃牛、水牛能適應耕犁稻田的需要。
且不說馬耕了,就連牛耕到后來在南方人口稠密的農業區也不普遍。取而代之的是“人耕”或用“鐵塔翻耕”。明人趙統對“人耕”這種形式,表現出驚奇態度的同時,也分析了緣由,他說:“人耕,其法用三人一杠,杠中依于犁,一人柄后,一人掲前,又一人別繩牽牛轅,大抵窮而通牛之變。”[4](明)黃宗羲.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五)[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此外還有如:土地零碎化,勞動力夠多,養牛成本大,每家擁有耕地少,牧地被侵占、養牛的空間被壓縮等。曾雄生先生從“放牛”到“縻牛”的視角,來解讀了我國“跛足農業”形成的原因,就是對此最好的說明。明清之后南方農作區人地關系更加緊張,養牛的空間再被壓縮。宋代農學家陳旉曾提出在陂塘的埂上種樹,用來綁牛的辦法。到了明清時,江南地區養牛的農民更少,耕地則要靠鐵塔進行。連對空間要求不高的牛的活動空間都不斷縮小,就更沒有足夠的空間與成本來養馬。
綜上所述,對比中西農業文明下牛耕與馬耕后,我們可以得出以下三點結論:
其一,馬耕并不是歐洲農業自古以來的特點,10世紀前牛耕才是他們翻地的主要形式。
其二,馬耕與牛耕沒有更好,只有更合適。工具、使用習慣以及社會文化象征意義都會限制先進技術的推廣。
其三,牛耕是中華農業文明的特點之一,這主要是由地緣政治與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模式所形成。
(責編:高生記)
Cattle-plowing and Horse-plowing in Chinese and Western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Chen Guiquan
陳桂權(1986—),四川平武人,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博士,四川文理學院巴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國農史、秦巴地區社會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