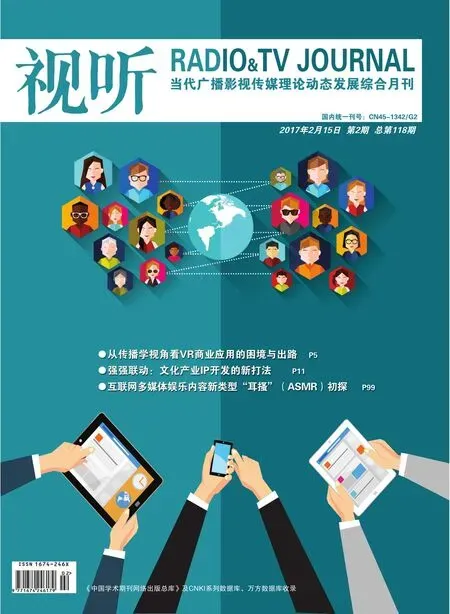論朋友圈的自我形象建構陷阱
□羅佳
論朋友圈的自我形象建構陷阱
□羅佳
朋友圈作為個人發聲的場所,是構建網絡自我形象的重要場地。網民在編織自己朋友圈的時候,過程正是和“議程設置”理論揭示的過程相像,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情,經過我們的精心挑選(正面評價多的)、加工整理(美圖,美顏等)后,發送到朋友圈,成為別人了解自己的一個窗口。然而要認識一個人,除了朋友圈這個“窗口”之外,還需輔以現實生活中的互動作為主要的認識途徑,否則便會掉入虛擬互動的陷阱。
符號互動;議程設置;朋友圈;自我形象
一、朋友圈的自我形象建構
現代社會,人們利用社交軟件進行溝通的機會甚至超過了現實生活中面對面的交流溝通。現實社會中,我們要獲取他人的全面的信息可以通過談吐、面容、朋友、家庭、生活環境來了解,具有全面性和連續性,而在網絡社會中的交往,除了文字信息之外,幾乎沒有更多途徑來交流,朋友圈作為個人發聲的場所,是構建網絡自我形象的重要場地,翻看一個人一年的朋友圈信息,基本上能判斷出這個人的喜好、性格、身份階層等信息。不過,網絡的匿名性和虛擬性也使得朋友圈信息的真實性存疑。
想想你在發朋友圈的時候,是喜歡發一些可能引起大家的贊賞的消息呢,還是喜歡發那些有可能引起大家的反感的消息?會有意避免發一些對自己形象有損害的消息嗎?會傾向于去發那些對自己的形象有提升作用的消息嗎?筆者在本文中探討的就是“發朋友圈”這件小事。其實很多時候網民轉發的與其說是一則信息,不如說是在轉發自己的朋友圈形象。那么,作為構建網絡自我形象場地的朋友圈,構建出的自我形象值得信賴嗎?我們應該如何正確看待朋友圈中的“朋友”呢?這些問題值得思考。
二、被利用的形象建構動機
2016年11月25日,微信公號的一篇文章《羅一笑,你給我站住》在朋友圈開始轉發,據說每轉發一次,某公號就會自動為白血病患兒羅一笑捐贈1元,短短幾天時間,轉發量達到破百萬的數額,超過11萬人打賞。
想想這樣的一則消息出現在你的朋友圈,你會不會去轉發到自己的朋友圈消息中呢?
11月30日,有消息稱這完全就是一場炒作,羅爾(羅一笑的父親,文章作者)擁有3套房產,還有一個公司,完全可以支付得起這些醫療費用,而且治療費中的大頭都可以報銷。
這時,你的內心是怎么樣的呢?
《紐約時報》曾調查2500位讀者,分析他們轉發文章的動機,得出的結論中第二名便是定位和展示自我形象。傳播學中的符號互動論認為,一件事的意義不僅僅在這件事本身,還在于與這件事所聯系的其他內容。轉發《羅一笑,你給我站住》這篇文章的人轉發的不僅僅是這篇文章,更是這篇文章背后所折射出來的你對他人的同情心,你對于這種募捐方式的認可,甚至你贊成其他人參與這項內容等夾帶的信息,轉發這篇文章的人成為自帶有愛心、有同情心光芒的人,轉發這篇文章的同時,你也在展示自己的形象,這種類型的文章利用的便是網民展示自我形象的動機和需要。這背后隱藏的是網民對自己朋友圈內容進行編織的一個過程。凡是能展示自己正面形象的文章,網民都更樂于把它們轉發到自己的朋友圈,以展示自己的良好形象。所以,很多時候網民并不只是在轉發一則信息,更是在轉發自己的朋友圈形象。
三、千人千面的形象建構需要
一則消息具有的屬性很多,一篇文章具備的屬性更多。關于羅一笑的這篇文章,有的人看到的是有一個小孩生重病急需幫助,有的人看到的是營銷套路,有的人看到的是一則騙人的信息。千人千面。
對于羅一笑這篇文章,也有大量的網友選擇了不轉發到自己的朋友圈,根據筆者的訪談,不轉發的原因有:防備心比較強,看到網絡上瘋傳的消息反而不感冒,更多地會去懷疑它的真實性;習慣性不轉發;覺得厭煩,認為國家做得不好;要為朋友圈的人對自己的信任負責,不愿意為其做信任背書;怕隱私信息泄露;怕受騙。
據筆者對他們的了解,這背后的原因確實與他們自己的性格以及行為習慣有關,這么說來,確實印證了朋友圈文章與定位和展示自我形象有關,并不是這些訪談對象不希望表現出自己的樂于助人,而是不希望通過這篇文章來展示這一種形象,他們會通過轉發投票信息,轉發朋友的廣告的方式來展現自己樂于助人的一面。僅僅對于這篇文章而言,它太具有營銷性和欺騙性,早已蓋過了助人的屬性,轉發這樣的一則文章,不利于經營自己值得信賴的形象。這一點和議程設置的內容很相像。
大眾傳播時代,為了經營和展示對外形象,媒體會有自己的一套選擇素材或話題的標準,按照那套標準來對文章或話題進行優先性和重要性排序。也就是說,傳播媒介對外部世界的報道不是“鏡子”式的反映,而是一種有目的的取舍選擇活動。①這便是“議程設置”理論所揭示的內容。
四、朋友圈形象建構的選擇性陷阱
對于同一則信息內容,之所以有人轉發,有人不轉發,是因為每個人對于同一則信息內容的評估看法不一樣。網友對于自己朋友圈內容的選擇會傾向于選擇符合自己價值觀、有利于展示自己形象的內容。那么這種選擇是一定的嗎?網友選擇的標準又是什么呢?為此,筆者做了一個小型的深度訪談,逐一詢問某個人某條朋友圈消息轉發的原因,之后又做了一個100人的問卷調查,更加印證了這個觀點。
訪談結果表明,所有人對自己的朋友圈內容都是有所選擇的,即使是那些基本不發朋友圈的人也會有所選擇,而選擇內容的傾向是對自己的形象有正面提升的內容。問卷中包含3個問題,分別是:你注重自己的朋友圈形象嗎?你會對信息進行選擇之后發送到朋友圈嗎?你會傾向于發送正面的消息到朋友圈嗎?問卷中100%的人注重自己的朋友圈形象,91%的人是會對內容進行選擇,95%會傾向于選擇正面的內容。
訪談問題:你發朋友圈信息的時候是有選擇性的嗎?談談你一般是怎么發朋友圈的?
對象一:當然啦,不過一般我都不怎么發朋友圈信息,以免打擾到別人。
對象二:是的,我一般在很開心的時候會發朋友圈,低落的時候不會發。而且我發了朋友圈之后不久就會刪除,我不希望別人以后通過翻我的朋友圈來了解我,因為不真實、不全面。
對象三:當然啦,我不會發自己很雜亂的桌子,沒收拾時候的樣子,反正那些不好不正面的東西我是不會發的,這是我選擇內容的底線,我一般會在朋友圈發自己最近在做的事情,當然也是正面的啦,讓朋友了解最近在干的事情嘛,如果有共同話題就可以聊起來啦。
對象四:是的,我一般不怎么發朋友圈,發朋友圈都是為了幫助別人。
對象五:當然,我發朋友圈之前會評估一下這條信息引發的正面評論多些還是負面評論多些,我會選擇那些正面評論多的信息來發。發的信息都要經過斟酌和美化一下的,比如會選擇美圖作為配圖,自拍會用美圖呀什么的,當然是希望看到我積極正面的一面。
對象六:是的,不過我一般都不怎么發朋友圈,我都在新浪微博發。不過我非常注重隱私,個人信息的話一般只會對自己可見,我不喜歡別人通過朋友圈來了解我。只有我想了解別人的時候才允許別人來了解我。
五、網絡互動+現實互動的認知途徑
網民在編織自己朋友圈的時候,過程正是和“議程設置”理論揭示的過程相像,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情,經過精心挑選之后,擇一些自己認為會引起正面評價多一些的信息(高雅的愛好、展示有愛心的信息等),經過加工整理(美圖、美顏等)后,發送到朋友圈,成為別人了解自己的一個窗口。所以,如果只通過朋友圈和網絡聊天來認識一個人,缺少現實社會中真實的互動,你可能只看到了那個人較好的一面,而沒辦法獲取那個人的全部。當然,你可以選擇通過這個“窗口”去了解一個人,輔以現實生活中的互動作為主要的認識途徑。但不能完全依賴這個“窗口”去認識別人,因為從窗口看進去,只看到了陽光的一面,還有更多的陰暗面——它們是人格中不能被忽略的組成部分。就像周源源所說,每一條朋友圈的發布都像是一場正在演出的戲劇。②只有等到戲劇落幕的時候,孰真孰假,才可分辨。
注釋:
①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②周源源.擬劇理論視域下大學生微信自我呈現研究[J].思想理論教育,2016(09):84-88.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