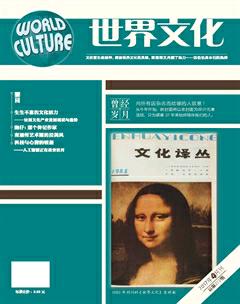鮑仔:那個傳記作家
毛旭

鮑斯維爾生氣地踢了椅子一腳,發現沒人注意到他的這一舉動,又狠狠地踢了一下,其實心里又害怕約翰遜博士會責備他的無禮。都怪那個用心險惡的賽雷爾夫人,把他的位置安排在離約翰遜十萬八千里的地方——全倫敦誰不知道,他吃飯時一定要緊鄰博士而坐?賽雷爾夫人的惡作劇讓客人們心里樂開了花,都等著看好戲。
鮑斯維爾干脆不吃飯了,把椅子拖到約翰遜的后面,氣鼓鼓地坐下來。博士一開口說話,他立馬把腦袋伸到約翰遜的肩上。同桌的女作家芳妮·伯尼寫道:“鮑斯維爾瞪大了眼睛,仿佛有什么東西蟄疼了他。他張大嘴巴,下巴快砸到地板上了,唯恐漏掉了博士說的任何一個字。”約翰遜意識到有人在他耳邊吹氣,扭過頭來說:“鮑仔,你不吃飯在這兒干什么!坐到我旁邊來。”鮑斯維爾這才開心地搬著椅子坐在博士身邊。
兒子與情人
詹姆斯·鮑斯維爾1740年10月29日生于蘇格蘭的一個貴族家庭。他的母親比父親小10歲,性格溫柔內向。她是個忠誠的加爾文教徒,相信地獄的存在,信奉禁欲主義。她用地獄嚇唬不聽話的小鮑仔,讓他在孩童時期就患上了折磨他一生的抑郁癥。
小時候的鮑仔柔弱多病,小學上了不到三年,輟學的原因是“怕黑”,害怕上學路上的黑胡同里有鬼魂在游蕩。為了不上學,他長時間垂著腦袋直到患上頭疼病,吃了藥之后又想辦法把藥吐出來。實在沒辦法,父母只好給他請了家教,讓他在家里上學。
這樣一個孤僻、體弱、內向的孩子,或許是因為愛情的力量或者說性的覺醒,在12歲時性格竟然向著相反的方向轉變。在莫弗特的溫泉地療養時,他變得活潑、外向,談了第一場戀愛。從此,他成了戶外型的人,喜歡陽光和運動,尤其是爬樹。
進入青春期后,母親仿佛從鮑仔的生活中消失了。在他那等身的日記、書信中,他只提到過她一兩次。占據他生活的是那個永遠悶悶不樂的父親。弗洛姆在《愛的藝術》中寫道:母愛原則是“我愛你,僅僅因為你是我的孩子,不管你變成什么樣,我都愛你”,父愛原則是“我愛你,條件是你像我,你得滿足我的期望”。鮑仔的父親是蘇格蘭的15位大法官之一,他希望鮑仔能和他一樣在政治和法律上有所作為,于是在鮑仔13歲時就把他送進了愛丁堡大學學習法律。
鮑仔深愛父親,終其一生都想成為父親那樣的法律和政界權威。但這是不可能的,他倆的性格完全相反:父親沉穩,鮑仔嘚瑟;父親討厭文學,鮑仔熱愛藝術;父親信奉實用主義和理性主義,擁護當權的漢諾威王室和蘇格蘭、英格蘭統一,鮑仔是個浪漫主義者,他懷念那個逝去的蘇格蘭獨立的時代,那個貴族騎士為世仇家恨拔刀相向的時代。
鮑仔在愛丁堡大學學習了5年,他不好好研究法律,而喜歡研究女演員,還在報紙上發表詩歌,令父親氣憤不已。為了遏制鮑仔的放蕩,父親把他轉到偏僻的格拉斯哥大學。鮑仔在那里過得十分郁悶,時常受到抑郁癥的折磨,決定逃到倫敦投奔天主教,幻想它可以拯救自己。
19歲的鮑仔在倫敦發現了生命的意義。約翰遜曾經說過:“誰厭倦了倫敦,誰就厭倦了生命。”相比愛丁堡,倫敦是個真正的大都市:紳士們10點才起床吃早餐,玩到下午5點。晚餐時間持續到9點,然后出門見朋友,在酒吧里待到凌晨。這里有美酒,有劇院,有文人,最關鍵的,有夜生活。鮑仔沒有投入天主教的懷抱,而是投入了女人的懷抱。
父親做出了妥協:鮑仔可以在倫敦自由發展,條件是先回愛丁堡完成法律學業,否則就剝奪他的繼承權。鮑仔在倫敦狂歡了三個月后又乖乖回到了蘇格蘭,在無聊的學習中打發了3年,時不時地和一大堆女人談情說愛。
愛星人和星星
22歲的鮑仔身高168厘米,胖乎乎的,皮膚黝黑,一頭卷發。他通過民法考試后,第二次來到倫敦,希望能結識一些名人。塞繆爾·約翰遜博士無疑是英國文壇群星中的大熊星座,18世紀下半葉甚至是以這位文壇領袖的名字命名的——約翰遜時代。他綽號“狗熊”,長相其丑無比,當家教時曾經嚇哭過孩子。作為追星族的鮑斯維爾一直想認識這位巨人,不過困難在于,約翰遜極度討厭蘇格蘭人,曾在《字典》中這樣為“燕麥”下定義:一種谷物,在英格蘭喂馬,在蘇格蘭喂人。
1763年5月16日,當鮑仔在托馬斯·戴維斯的書店喝茶時,約翰遜也來了。鮑仔在《約翰遜傳》中這樣描述:“戴維斯透過我們坐著的客廳玻璃門,看見約翰遜向我們走過來。戴維斯站起來,用洪亮可怕的聲音宣布他的到來,就像霍拉旭向哈姆雷特宣布他父親鬼魂的出現:‘看吶,我的殿下,它來了!”戴維斯介紹兩人認識:“這位是詹姆斯·鮑斯維爾。”鮑仔小聲提示:“別說我是蘇格蘭人。”戴維斯使壞地大聲嚷道:“從蘇格蘭來的!”鮑斯維爾只好哭喪著臉補充說:“先生,我的確來自蘇格蘭,不過我對此實在無能為力啊。”約翰遜哼哼道:“你們那兒的人都是那么無能為力。”鮑斯維爾只好沉默地坐在一邊,聽他們兩人聊天。當約翰遜談到自己的學生大衛·加里克時,鮑斯維爾終于鼓起勇氣插了一句:“先生,加里克應該不是個小氣的人吧?”約翰遜冷冷地回答:“我比你熟悉加里克,你沒有資格和我談這件事。”
這樣不順的開頭也在預料之中。約翰遜博士屬于慢熱型,而且喜歡唱反調,常常為了反對而反對,跟他聊天就像辯論一樣,而且必須讓他占上風,否則有可能被拳頭伺候。所幸鮑斯維爾很有耐心,盧梭曾這樣評價他:“大多數人受到我的冷遇會走開,鮑斯維爾是唯一一個留下來的人,他陪我度過不幸,縱容我使小性子。”正是這一點,使鮑斯維爾在第二次登門造訪時與博士熱乎起來,后者給他取了一個著名的昵稱:鮑仔。
鮑仔的父親可不喜歡兒子在倫敦與文人交往。這次他下了死命令:去荷蘭學習法律一年。約翰遜專門抽出一天一夜陪他。他們劃船,在酒吧聊天。當話都說完時,兩個人相對而坐,默默看著對方——兩個爺兒們如此心心相印,畫風實在是詭異得很。這時,一只飛蛾撲到蠟燭上,約翰遜趁機調侃道:“這只蛾子自作自受,它的名字肯定叫鮑斯維爾。”
鮑仔的父親讓鮑仔去人生地不熟的荷蘭,這樣就可以安心學習法律了。父親的如意算盤打錯了,鮑仔反而趁此機會開啟了他的大陸旅行——一種在歐洲公子哥中流行的旅游路線,從荷蘭出發,途經德國、瑞士、意大利、科西嘉、法國,直至返回。在瑞士,他拜見了盧梭和伏爾泰。
當時,52歲的盧梭因為《愛彌兒》中的革命觀點遭政府通緝,和女友黛萊絲隱居在瑞士的莫蒂埃,生活十分窘困,鄉民們受教士的挑唆每晚都向他家扔石子。鮑仔是盧梭的超級粉絲,上學時常爬到山頂大喊盧梭的名字。他手里有一份盧梭好友的介紹信,但為了顯示自己的獨特,他決定棄之不用,寫了一封自薦信。素來閉門不見客的盧梭竟同意接見鮑仔。他們共會面五次。日后,盧梭憑借《懺悔錄》成為現代自傳之父,而鮑斯維爾則憑借《約翰遜傳》成為現代傳記之父。
前兩次見面不算成功。盧梭病得很厲害,他暗示自己不喜歡訪客:“我討厭人。黛萊絲說當我孤獨時心情總是很好,有人來拜訪時會很低落。”臉厚的鮑仔卻轉移了話題:“先生,你覺得我這個人怎么樣?”……回到旅社之后,鮑仔寫了一篇自傳,由黛萊絲轉交到盧梭手上,其中講述了自己與父親的關系以及折磨他的抑郁癥。這篇自傳敲開了盧梭的心門,使接下來的拜訪柳暗花明。盧梭甚至邀請他一起吃晚飯。告別時,他請求盧梭承諾給他寫信,為了保證信用,他跟孫猴似的從頭上拔下一根頭發,讓盧梭拉了拉,表示這是他們之間的紐帶。

相比之下,鮑斯維爾到伏爾泰家的造訪就很難算得上成功了。畢竟,他和盧梭氣質相近,屬于浪漫、易感的人,而伏爾泰則理性、深沉,很像鮑仔的父親。這個71歲的老頭兒生活富有,住在豪華的大城堡里,脾氣很壞。鮑仔死皮賴臉地要住在人家家里,伏爾泰含沙射影:“某人和堂·吉訶德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堂·吉訶德把旅館當成城堡,而某人把城堡當成旅館。”伏爾泰家高雅的貴族習氣讓鮑仔倍感無聊,讓他聯想起自己的家庭。伏爾泰沒有說什么好話,倒是一直在罵他的宿敵盧梭。
當鮑仔在意大利游玩時,收到了母親去世的消息,他這才中斷了旅行往蘇格蘭趕。
“我的心在高地”
26歲的鮑斯維爾在愛丁堡干起了法律。他不是個好律師,賺不了多少錢,因為他只擅長動之以情,不會曉之以理,而且他感情用事,喜歡幫貧窮、弱勢或者已經定了死罪的人辯護。“道格拉斯案件”顯示了他的能力,也斷送了他的律師前途。道格拉斯公爵膝下無子,死后其爵位及田產由其在巴黎的外甥阿奇布德繼承。幾年之后有人提出異議:阿奇布德不是道格拉斯妹妹的親兒子,是她領養的冒牌貨。鮑斯維爾支持阿奇布德,他不能忍受貴族的既得利益被損害,因為他自己也深受此方面的困擾:父親動不動就以剝奪他的繼承權相威脅。
這雖然不是他的案子,但他為阿奇布德四處奔走。在蘇格蘭法庭裁決剝奪阿奇布德的財產后,他跑到倫敦的上訴法院大法官處陳情利害,竟把案子掰了回來。凱旋之日,他領導愛丁堡的民眾在夜間歡慶游行,并放出話來:所有涉及此案的蘇格蘭大法官都必須在窗前點一支蠟燭,否則就把玻璃砸碎。鮑仔的父親是站在阿奇布德一邊的,但為了向同行表示團結,他也拒絕點蠟燭。鮑仔路過家門口時,撿起一塊石頭,猶豫了一下,然后把他爹房間的玻璃砸碎了。父親大怒,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要求把這不肖子抓起來蹲大牢,被朋友勸止。
如果說道格拉斯案件讓父子關系急轉直下,那么鮑仔的婚姻則讓爺倆兒徹底鬧掰。父親選擇兒媳婦有很明確的要求:要有錢。鮑仔有個青梅竹馬的表姐,時年32歲仍舊單身。她陪28歲的鮑仔去愛爾蘭追求一位富有的遠房表妹,在坐船渡海時,鮑仔發現自己一直深愛著表姐。可問題在于,那表妹不僅擁有大筆財產,而且每年收入1000英鎊,而表姐幾乎一無所有,是個典型的窮親戚。鮑仔已經考慮到自己蹩腳的賺錢能力,但浪漫的他還是選擇了愛。為了表示抗議,鮑仔的父親宣布他也要結婚,并且和鮑仔同一天舉行婚禮,這樣彼此都不用參加對方的婚禮。
表姐瑪格麗特是個體貼、聰明的妻子,盡管還沒聰明到婚前就看出鮑仔是個情種。婚后兩人定居愛丁堡,鮑仔對妻子十分恩愛,只是每年春秋兩季法庭休庭時,他常常跑到倫敦去找約翰遜博士,以及妓女們。他把這些事寫在日記里并拿給瑪格麗特看,后者讀了十分傷心。鮑仔就是這么怪,他曾經一面向一個女孩兒求婚,一面又在報紙上罵她。
每次見到約翰遜,他都哼唧著讓約翰遜到蘇格蘭游玩,描述那兒的古城堡有多么壯麗。約翰遜終于被他說動了,1773年啟程去他討厭的蘇格蘭,開啟了英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旅行。
不過瑪格麗特打心底里討厭約翰遜,因為他是鮑仔每年都去倫敦的主要原因。為此,瑪格麗特諷刺這古怪的一對兒:“我常看到人牽著熊,從來沒看過熊牽著人。”
幾天后兩人離開愛丁堡,騎著小馬,找了向導,向蘇格蘭高地進發。相對于愛丁堡的文明,高地則完全是蠻荒之地,山路崎嶇,霧蒙蒙一片,此時又是寒冷多雨的9月。對于64歲的約翰遜來說,一路騎行實在是個不小的考驗。行進時約翰遜的馬在巖間踩空了,人和馬都受到了驚嚇。向導是個非常單純的農家漢,他像哄小孩似的哄起了博士:“別怕怕……”鮑仔笑得牙都碎了,博士則滿面怒容:“我現在就要回愛丁堡,然后再不和你來往。”住宿條件也極差,兩人在地上鋪點草就睡了。當抑郁癥襲來時,鮑仔獨自在一間屋里守夜,約翰遜為了取暖,和一條大黃狗相擁而眠。
在旅程接近終點的斯凱島,博士終于喜笑顏開了:當地的貴族們熱情接待,美麗的麥克勞德夫人甚至許諾把一個小島送給博士,條件是他一年來住一個月。約翰遜快樂得像一個得到新玩具的孩子。鮑仔寫道:“他經常談起這座小島,說要在上面建大城堡,加固它,還要裝上大炮,然后造船出海,攻占別的島嶼。他從沒有這樣歡快地大笑過。”
那本傳記

約翰遜常對鮑仔說,這次旅行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事實上,這也是鮑斯維爾最后一次開心的旅程。他的律師工作仍然既無聊又沒有成果。父親意識到鮑仔已經不可塑了,便對之愈加冷酷。當鮑斯維爾讓自己的孩子們去看望爺爺時,后者竟把他們拒之門外。當時下著瓢潑大雨,孩子們哭著回到家中。
1784年6月,鮑仔與約翰遜最后幾次見面。約翰遜的身體每況愈下,鮑仔便暗地里和幾位好友商量,請求國王提高博士的年金,讓他去意大利療養。鮑仔對這件事的描寫讓人讀了十分動容:“我們把籌款的計劃告訴他。他沉默了一會兒,淚水開始在眼睛里滾動,然后大聲說:‘上帝保佑你們!我也落下了淚,不知說什么好。他突然站起來離開房間,出去平復一下激動的心情。”不過年金沒申請下來,約翰遜于不久后辭世。對于博士之死,鮑仔是最受打擊的一位,這意味著他又失去了精神上的父親。
那時鮑仔的生父也已去世,但他那雙失望的眼睛仿佛還在盯著鮑仔。鮑仔仍渴望著金錢、地位,不得不服侍各位爵爺和首相于左右。一連串的失望導致一連串的放縱:他狂飲,有時醉倒在馬路邊躺到天明;他嫖妓,不像以前那樣還問問人家的名字,聊聊天;他對看戲失去了興趣,證明他對生命失去了興趣;他連日記都很少記了。
當鮑仔不忙“正事”的時候,就坐下來寫作《約翰遜傳》。寫作初稿用了16個月,加上修改一共用了3年零5個月。1791年5月16日,是鮑仔和博士相遇的28年紀念日,《約翰遜傳》出版了。這本傳記在當時被稱為“本世紀最有趣的書”,其聲譽在后世更加如日中天。在英語中,“書”前面加個定冠詞“那本書”表示《圣經》,而在“傳記”前面加個定冠詞“那本傳記”,則代表《約翰遜傳》。它被稱為“天下第一傳記”。
要想排名第一,要么做到“人無我有”,要么做到“人有我優”。就“人有我優”而言,這本書有很多優點。比如生動,“約翰遜笑起來跟愉快的狼嚎似的”;比如誠實,傳記史上優缺點并收的傳統就是從《約翰遜傳》開始的;比如對人物心理深度的洞察,鮑仔在心理學尚不發達的時代就已經能抓住約翰遜強迫癥的根源了。孰優孰劣的程度比較是主觀的,要想在藝術上爭第一,就必須有別人沒有的東西。這樣說來,《約翰遜傳》的確可以稱為“天下第一傳記”。鮑仔分到的撲克牌中有大小王,而所有別的傳記作家都沒有。
首先,鮑仔認識他的傳主。在傳記中,幾乎所有最好的傳記都是傳主的朋友寫的。第二,鮑仔不僅認識約翰遜,他還在日記中記錄他的言行,也就是說,他不是通過多年之后不可靠的回憶來寫一本《和約翰遜在一起的日子》,而是以驚人的毅力每天都記載下約翰遜說的話,也就是說,這部傳記非常精確。第三,鮑仔不僅是個書記員,而且他還是個導演,有意為約翰遜安排一場場演出。他想方設法讓博士去見各類人,看他在戲劇沖突中能說出什么格言。為了不讓博士沉默,鮑仔已經達到了瘋癲的程度,他甚至能問出這樣莫名其妙的問題:“先生,如果把你和一個嬰兒關在一個房間里,你會怎么辦?”難怪博士經常被他煩得破口大罵,罵得嗓子都啞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約翰遜傳》里面不僅有傳主約翰遜,而且有傳記作家鮑斯維爾。二者有著非常大的性格差異,這就有了好戲看:鮑仔雖有抑郁癥,但總體而言比較外向,為人謙和,性情多變,適應性強;博士則有嚴重的強迫癥,性格內斂,牙尖齒利,脾氣暴躁。《約翰遜傳》的第一部分寫得很好,第二部分則好得讓你想哭,因為在第二部分鮑仔登場了。其實,《約翰遜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鮑斯維爾的自傳,有些文字與其說揭示了博士的性格,不如說揭示了鮑仔的心理活動:
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對那只小貓“哈奇”的縱容。每次他從外面回來,總要買點生牡蠣喂貓,唯恐仆人因為怕麻煩而虧待了它。不幸的是,我是一個最討厭貓的人,只要房子里有一只貓,我就感到渾身不自在。坦白說,我經常因為哈奇在身旁而覺得有說不出的難過。我記得有一天,哈奇在約翰遜懷里撒嬌,他一面逗笑,一面輕輕吹著口哨,抓抓貓的背,拉拉貓的耳朵。我看到這只貓很乖,便說:“我過去養的貓比這只可愛多了。”后來覺得有點不大對勁,趕緊補了一句:“不過,它的確是一只好貓,真好!”
《約翰遜傳》的出版讓鮑仔名聲大噪,所有的大門都向他打開,他受到各種宴請。但鮑仔喝了酒之后就撒酒瘋,跳到椅子上唱歌,弄得主人十分尷尬。他已經50多歲了,仍喜歡逛妓院;在法院遇到其他律師,他總是羞愧地躲著走,因為人家有客戶和案件,他卻什么都沒有。1795年5月19日,55歲的他死于腎衰竭和尿毒癥,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相比葬在西敏寺詩人角的約翰遜,他只能被運回蘇格蘭的家族墓地安葬。在生前,他就被人們視為跳梁小丑,直到20世紀初,一位耶魯大學的教授發現并出版了他的十二卷日記——當代最重大的文學考古發現之一——人們才意識到他是一個可愛而且值得同情的天才。
鮑仔的晚景是凄涼的,但并不孤苦。他一生都被父“子”關系困擾,所幸老天有眼,賜予他融洽的“父”子關系。他的兩個兒子非常孝順懂事,尤其是小兒子吉米,當鮑仔整日坐在桌旁,飽受抑郁癥的折磨時,吉米陪伴著他。吉米在15歲時就能寫出下面的信,實在了不起,可以用來總結鮑仔一生的失望和成就:
求求你,爸爸,不要再痛苦了。你的性格不適合成為那種“成功人士”。那些有地位、有金錢的人都過著無聊的生活,他們沒有你的天才,更沒有資格成為約翰遜的傳記作家。如果你是一個成功、富有,但無趣、乏味的律師的話,還會跟約翰遜、盧梭、加里克那樣的人成為朋友嗎?每個人選擇的人生道路都有利有弊,你不可能榮華與藝術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