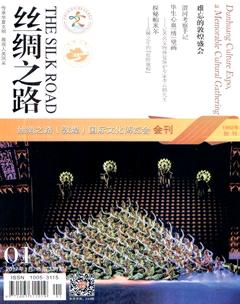探秘帕米爾
孟昭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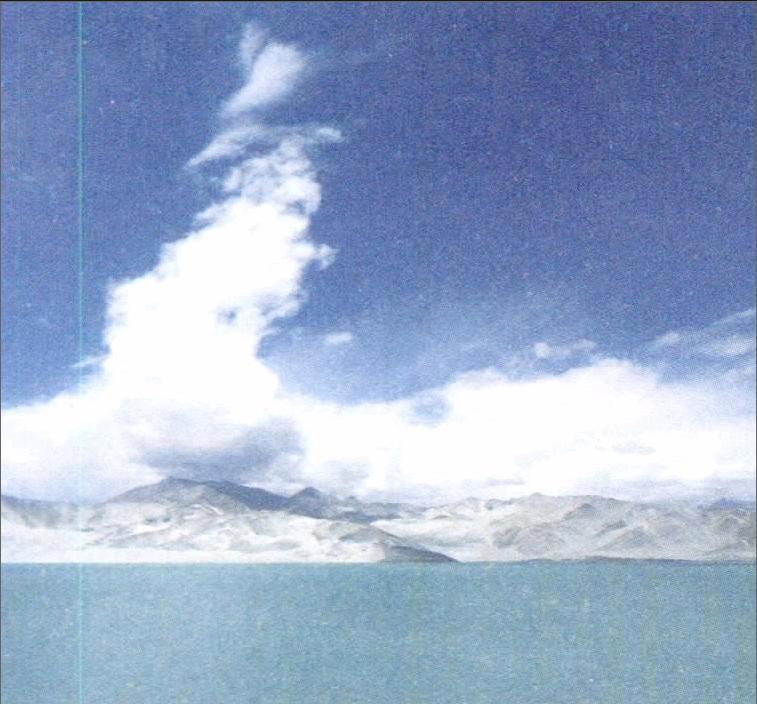
天津《今晚報》副刊2016年4月2日登載了一篇李憶莙寫的小文《美麗的旅程》,我讀后產生了一定要去南疆帕米爾高原紅其拉甫口岸的沖動。帕米爾當地語為“U型河谷”,帕米爾高原古稱“蔥嶺”,是五條山脈扭結之處,號稱“山結”。它是古代聯系東西方世界的樞紐,也是古代東西方主要經濟、宗教、文化的交匯處。至今,它依然蘊藏著無盡的奧秘,如絲綢之路穿越帕米爾的具體路線、唐代高僧玄奘去天竺取經歸國的路線等,這些都使人產生不盡的遐想。帶著這些誘惑,2016年7月中旬暑假期間,我經過周密的計劃和準備,終于如愿以償地踏上了被諸多親友稱為古稀之年的“危險旅程”。
下午從天津機場出發,傍晚到達烏魯木齊轉飛喀什。由于當地與北京有兩個小時的時差,所以到達目的地時,雖已是晚上8點多鐘,但天還亮著。出租車穿過喀什舊市區,一路上人來人往,熙熙攘攘,一派歌舞升平的安定景象。第二天清晨,我和同去紅其拉甫口岸的幾位年輕朋友,坐上越野車在喀什疏附縣烏帕爾附近的快餐店吃了早飯,買好路上的食物和水,順著平坦開闊的314國道(又名中巴友誼公路)直奔目的地而去。
可是好景不長,過了烏帕爾不遠,路況使我開始不那么樂觀了,終于在一個有“中國郵政”標志的既賣郵品又賣土特產的店鋪門前,司機告訴我們前方不遠就要進入修路地段了。由于順應“一帶一路”戰略和經濟發展的要求,中巴友誼公路重新整修,從前方不遠開始有100公里左右的路段要修。本來喀什到紅其拉甫只有430公里左右的路程,五個小時足以到達,但是現在這100公里左右的路程就要花費四個多小時。汽車一路顛簸,異常艱難地前行著,車內的乘客上下起伏、左搖右晃,車外塵土飛揚。到達帕米爾高原山區以后,公路進入蓋孜峽谷,汽車沿著路左的蓋孜河前行。首先見到的是類似于吐魯番火焰山一樣的紅山矗立在公路兩邊。紅色的龐大山體突兀在眼前,令人望而生畏。偶爾能看到一兩匹孤獨的駱駝無奈地站在路邊的煙塵中。原來的公路有的路段需要拓寬,重新鋪設;有的路段需要改道,繞開山洪沖決的地段;有的路段則是重新設計,改為高架路,所以有時要單方向行駛,有時還要下車步行,或因山坡太陡峭,或因車多路窄,總之各種情況都有。偶爾能看到高山上由洪水沖刷而形成的砂石流,猶如掛在天際的巨大瀑布,讓人驚嘆不已。走到整修路段一半左右的地方,在左側蓋孜河對面,隱隱約約可見到殘存的棧道和幾處用石塊圍起的低矮的方形院落,其中還有幾處殘破不堪的石頭建筑,司機告訴我們那是驛站的遺址,傳說唐玄奘東歸時曾路經此地。
走出這段正在整修的公路,車速明顯快了起來,前方道路的視野也逐漸變得開闊。突然在道路右側,我們看到一片湖水,聽說這是一個大水庫,叫布倫湖,碧藍藍的天、綠泱泱的水和遠處淺黃色的山巒映入眼簾。對剛剛受到艱難路況摧殘的我們來說,眼前的景象猶如一副醒腦劑。定睛仔細看,更讓人驚奇,原來湖對面出現的一片連綿起伏、丘陵狀的黃白色山上竟然全是細沙。司機告訴我們那是白沙山,一種黃色的細沙被經過湖面的大風從山下吹向坡上,翻卷而上,就像大沙漠的沙丘一樣,夾在藍天、綠水之間,顯得異常美麗,真是鬼斧神工,大自然的造化令人難以捉摸。沿途遠處的公格爾山峰,云里云外,躲躲閃閃,神秘莫測。高聳入云的慕士塔格峰上雪白晶瑩的冰川,曾經令19世紀瑞典著名探險家斯文·赫定一見傾心,從此它便有了“冰川之父”的美稱。它是想去紅其拉甫的探險者繞不過去的障礙,汽車一直在它的陪伴下疾行。再往前就可以看到由冰山雪水融化而形成的美麗的喀拉庫里湖了,倒映在水中的雪山之影讓同行的旅伴心醉而流連忘返。我們走馬觀花式地穿行在這一路的美景之中,不知不覺已抵達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寬闊無人的大道兩旁,用中、英兩種文字寫成并印有兩國國旗的“熱烈慶祝中巴建交65周年”的大紅標語牌直通遠方,提醒著人們已經臨近國境線了。
這座口岸新城像鑲嵌在帕米爾高原上的一顆明珠,海拔超過3000米,人口約有3.5萬,其中近83%都是英勇的塔吉克族人,他們有著歐羅巴人種的特征,語言屬印歐語系,伊朗語族,帕米爾語支。生活在我國境內的塔吉克人有悠久的歷史和獨特的文化傳統。他們長期生活在我國的西部邊陲,在廣泛吸收希臘文化、佛教文化、伊斯蘭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基礎上,創造出獨具特色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充滿了神奇美妙、絢麗多彩的迷人魅力。汽車行駛在安靜、平坦、街燈高懸的馬路上,一路望著天邊低垂的藍天白云,有一種心曠神怡的舒暢感。我們不敢耽擱時間,因為還要盡快去塔縣邊防支隊管轄的紅其拉甫邊防檢查站,辦理到紅其拉甫國門和參觀界碑的通行證。有時通行證會因為天氣原因而暫停發放。今天我們很幸運,跑了幾百里路總算在接近5點鐘時排上隊,依次檢查身份證、照相,集體辦理了一行12人的通行證,可滯留三小時。在拿到通行證以后,汽車像有了護身符一樣,猶如脫韁的野馬在曲折蛇行、一眼望不到盡頭的高原公路上飛馳。
“紅其拉甫”意為“血谷”,在古代它不僅是各種盜賊強人的出沒之地,也是戰爭頻發之地。在那些特殊的年代,暴力也是文化交流的一種變異形式。紅其拉甫邊檢站的前哨班即駐扎在國門。它位于東經75.5度,北緯37度,平均海拔5100米,是世界上最高的邊境哨所之一。這里空氣稀薄,含氧量僅占平原地區的48%,水的沸點不足70℃。此地的氣候惡劣,瞬息萬變,全年無霜期不足60天,平均氣溫-20℃,素有“天上無飛鳥,地上不長草,風吹石頭跑,氧氣吃不飽,六月下大雪,四季穿棉襖”的“生命禁區”之稱,因此吸引了眾多的探險者。盡管條件如此艱苦,前哨班的官兵們還是為打造世界著名邊境品牌而努力著,常年堅守國門,向世人展示了“國門第一哨”的良好形象。他們曾多次亮相春節聯歡晚會,讓世人感奮不已。因處于高寒地帶,紅其拉甫口岸一般每年只在5~9月開放,10月份關閉,期間有時還因氣候變化等原因不能開放。幾乎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游客淡季時四五百人左右,旺季時可近千人)不遠千里甚至萬里慕名而來,參觀屹立在雪山懷抱之中的雄偉國門。這座新的國門是2009年國慶節前建好的,外形酷似中國古代城門,是個上窄下寬的兩層高大水泥建筑,高約30米,寬約50米,中間的扁長方型門洞寬約15米,高約10米,是紀念建國60年大慶的獻禮。國門外還有著名的“7號界碑”,是來訪者朝思暮想的重要景觀。
我們的汽車經過了上下起伏的盤山道以后,緩慢爬上了5000多米高的山頂。在車內并沒有感到有什么異常,只發現窗外雨點噼噼啪啪地打在車窗上,車里開著熱風,車窗上霧氣一片。當車停下來的時候,有人迫不及待地打開車門,一股冰冷的空氣夾雜著雨點刮進車內。先下車的幾個年輕人莫名其妙地蹲在車下,有的倚在車廂上,剛才還是歡聲笑語、活蹦亂跳的年輕人突然間變得悄無聲息了。因為我去過西藏,心想他們可能是因為缺氧,一會兒就適應了。于是我慢慢走下車來,從背包里拿出沖鋒衣穿好,戴上帽子,緩慢地一步一步走向數百米外的國門。高大雄偉的國門,以它的氣勢和威嚴,讓人從心底生出一種自豪感和敬意。我請人幫我照相時,身邊不時有從中國開往克什米爾巴基斯坦控制區的載重卡車通過。我冒著冰冷的小雨緩步穿過國門來到著名的7號界碑前,看到對面有許多巴基斯坦人。他們幾乎都是男性,有老人,也有青年,見到中國人就熱情地握手。此情此景,讓我回憶起前幾年去巴基斯坦的經歷:所到之處,無不受到人們的友好接待,打招呼、握手、擁抱、合影留念都是常有的事,親身體驗了巴基斯坦大街上懸掛的標語——“中國兄弟,鐵哥們”的深情厚誼。在這里,我又找到了同樣的感覺。7號界碑是雙面的,中方一面是中文,巴方一面是巴基斯坦文和英文,上面有各自的國徽,下面寫著建成的年份“1986”。我跨過一段拖在地上手指般粗的繩索,走進巴基斯坦人群,許多巴方的朋友和我合影留念,他們有尊敬老年人的習慣和傳統。我請他們為我站在巴基斯坦一面的界碑前照相。由于天氣的原因,山頂的光線漸漸暗下來,中方的武警也招呼人們趕快回來。我心滿意足地回到國境內,完全沒有了缺氧的感覺。在下山去乘返程的汽車時,大家突然驚呼起來,因為看到了雨后的彩虹,在夕陽的余暉照耀下,它像掛在天空的彩練,色澤是那么鮮明、清晰,宛如中巴兩國人民心中的友誼橋梁,難能可貴。
上山艱難,下山易。我們還沉浸在順利來到國門的喜悅中,汽車就像“輕舟已過萬重山”一樣開進了塔城。我們住的是“塔縣旅游賓館”。大門上方“旅游賓館歡迎您”的霓虹燈標語,給我們一種賓至如歸的幸福感。賓館餐廳承包給了一個二十七八歲的河南小伙子,他因家境貧寒投靠親友,已來塔縣十幾年了,現在已有一定的積蓄,但是還沒有結婚。他說這里很安定,就是漢人少,有時感到孤獨,想娶一個內地的女孩一起在這里發展。這個誠實、能干的小伙子給我做了一碗地道的面湯,炒了一盤雞蛋西紅柿,吃得我渾身發熱,舒舒服服。我想如此能干的小伙子,扎根在這里一定會有美好的前途。
第二天早晨,我們一行來到塔縣阿拉爾國家濕地公園。入口處豎立著一塊巨石,上面刻寫著“絲路潮涌,深塔放歌”八個大字。可見塔縣和絲綢之路的關系非常密切。這片水草豐茂之地遼闊無比,一直延伸到周圍山影下的天際。濕地遠方星星點點地分布著一些白色的帳篷,飄灑在綠地草灘上。一群群牛羊散落在綠毯似的草地上,猶如一幅巨大的草場油畫。為了讓人們能近距離地感受到濕地良好的生態環境,草灘上還鋪設了木板路,水深的地方還有簡易的索拉木橋。這一大片天然的原生態草灘綠地,讓游人樂不思蜀、依依不舍。
遠望濕地的西邊,有一處像小山一樣的古城堡,近看依稀可辨它矗立在藍天白云之下逶迤雄渾的身姿,那就是著名的石頭城遺址。它處于塔縣的東北邊緣,海拔3100米左右,是古代絲綢之路交通的必經之路。這處古城遺址與遼寧石城、南京石城并稱為中國古代三大著名石頭城建筑,現在已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考古發現證明,石頭城曾先后是漢朝蒲犁國、朅盤陀國,唐朝位于龜茲的安西都護府(現今新疆南疆阿克蘇地區的庫車縣,和北疆奇臺地區吉木薩爾的北庭都護府齊名,都是唐朝對西域實行事實上管理與統治的重鎮)管轄下的“蔥嶺守捉”,清朝的“色勒庫爾回莊”和“蒲犁廳城”的遺址所在地。它一直是塔什庫爾干葉爾羌河流域河谷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和交通中心,有文字記載的歷史距今已有2200余年。現今的石頭城遺址目測高度有50米左右,城墻有修繕的痕跡,還有新鋪設的木板梯可攀登,城堡不是很大,登高遠望,四周群山環繞,有的山峰頂端白雪皚皚。下面四周地上落有大量的石塊,還有一些殘垣斷壁,似乎在向來訪者述說那些古老而不平凡的歲月。蒼穹之下仔細端詳這座黃色的古堡,不禁讓人產生一種歷史的滄桑感。
塔縣石頭城遺址下面的大道邊上修建了一組關于塔吉克族歷史文化的大型浮雕群,主要分為“漢日天種”、“拜火教儀式”、“石頭城”、“絲綢古道”、“張騫”、“班超”、“玄奘東歸”、“馬可·波羅”、“斯坦因”和“冰山上的來客”等10余個主題。這些主題主要說明了塔什庫爾干和塔吉克民族在絲綢之路上的咽喉地位和豐富的歷史文化。“漢日天種”講述的是一個塔吉克族傳說,相傳塔吉克民族是太陽中的男神與一名漢族公主的后裔,浮雕上表現的是一位年輕俊美的異裝男子騎在長著雙翅的馬上,腳下是朵朵祥云,從太陽里面順著陽光的照射奔向一位漢裝的美麗公主。“拜火教儀式”描繪的是塔吉克民族有崇拜火的信仰傳統,這種習俗明顯是受了波斯祅教的影響,是他們先民向往光明的一種心理反應。“石頭城”主要介紹的是漢代史籍中關于朅盤陀國的記載。“絲綢古道”則主要表現了古代絲綢之路上往來的著名人物的事跡。如張騫鑿空西域,始有絲路交通的可能;班超投筆從戎,招降西域諸國,絲路得以暢通。“玄奘東歸”雕刻的是唐代高僧玄奘自天竺取經歸國時,在經過塔吉克民族居住地時受到熱烈歡迎。“馬可·波羅”反映了700多年前馬可·波羅經過塔吉克民族住地時的歷史情景。“斯坦因”則是一副學者模樣,穿著西服,戴著禮帽,腳下放著古代的字畫文物等。100多年前,這位英國籍匈牙利裔的探險家、“文物竊賊”曾途經塔吉克民族居住的瓦罕谷地。他認為玄奘也曾從這片土地經過,引來玄奘東歸路線的爭議。“冰山上的來客”曾是電影的名稱,浮雕主要說明了塔吉克民族作為中華民族的重要一員,和解放軍一起軍民聯防駐守邊疆的內容。這幅大型浮雕全面系統地介紹了塔什庫爾干和塔吉克民族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可見,此地作為綠洲絲綢之路南道的重要節點是眾多貿易客商、傳道求法高僧和探險家等旅人的必經之地。
從塔縣回喀什的公路還要路經戰略要地瓦罕走廊東端,確切地說應該叫作瓦罕谷地的東端,即公主堡遺址。它是中國通向阿富汗的唯一通道,像一條橫亙在帕米爾高原的“天路”,屬于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管轄。這個突出于中國西部邊陲的狹長地帶,長約400公里,東端近100公里在中國境內,西端屬于阿富汗。它類似一個走廊,從北向南依次和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接壤,號稱“雞鳴三國”,是十分重要而又敏感的戰略要地。塔什庫爾干這種“一縣鄰三國”的嚴峻形勢,使之成為中國最復雜的邊境地區,堪稱絲路南道的咽喉與地標。學者不僅認為馬可·波羅、斯坦因等人途經這片谷地,而且還有人認為玄奘東歸時也經過此地。現在有學者又根據《舊唐書·高仙芝傳》考證,公元747年,唐朝邊關名將高仙芝從位于龜茲(今庫車)的安西都護府出發,跨越蔥嶺,經過長途跋涉,繞道塔什庫爾干的石頭城,再折向東南經瓦罕,兵分三路襲擊了吐蕃人駐守的連云堡,占領了小勃律(今巴基斯坦吉爾吉特地區),樹立了合理利用絲路克敵制勝的成功范例。可惜的是,由于瓦罕走廊尚未開放旅游,我們這些普通游客也無緣到達中國境內走廊東端往西的盡頭克克吐魯克,這也成為我這次古稀之年“危險旅程”中最遺憾的事,但愿它不要成為我終生的憾事。
帕米爾高原的U型河谷是古代商旅和原住民出入的必選通道,徒步、驢馬等行走的路線蛇形蜿蜒于其中。這些古代絲綢之路與現代公路雖然并不完全重合,但是我們的汽車在河谷縱橫、山口棋布、高峰峻嶺中穿行,仿佛覺得古代遍地的草場、牛羊依稀在目,古代的商旅和驢馬正在蹣跚來往,伴我們同行。
跨越帕米爾,歷來就被視為一種壯舉,今天仍然如此。從帕米爾高原探秘歸來,還有那么多的謎團尚未解開,還有那么多的遺憾存留腦際,這可能就是它無窮的魅力所在,正等待著后來者去探索、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