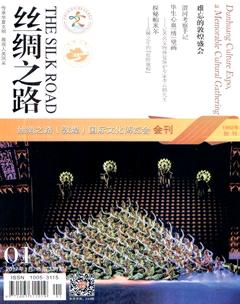張掖大地,另一種抵達
舒眉



西游遺跡覓蹤
深秋的天空,蔚藍澄澈,黑河變得安靜清澈,靜靜地穿過張掖腹地,河兩岸的樹木暈染著大片大片五彩斑斕的色彩,深綠色、金黃色、橙色、大紅色、深紅色、醬紫色……這豐富而絢爛的美,是黑河給予張掖這片土地最豐厚的饋贈。偉大的黑河孕育了絲路古道上的古城,也孕育了生生不息、代代相傳的絲路文明。民間傳說、歷史故事、經典詩文、神話演義,就像璀璨的星辰在歷史的天空里閃耀著光芒,雖然歷經時間的流逝、時代的興衰,但文明的超常強韌使許多遺跡沒有隕滅于草叢石堆間,數千年之后還在為后代開拓前途。在張掖大地上,《西游記》的故事不僅僅是家喻戶曉,更有許多留存的遺跡和不同于書本故事的情節,引發我們的思考和探究:張掖是否就是《西游記》的發源地?
時令已至深秋,張掖市《西游記》文化研究會的20多個會員,在多紅斌會長的帶領下,再次沿著黑河,一路向西,從甘州到臨澤,探尋《西游記》文化的蹤跡。存在與想象之間,需要一條通道抵達。而我們現在的考察研究,是從既成的瑰麗奇特的想象回溯。這樣的抵達,比依據現實的想象更具有挑戰性。而我始終認為,尋訪、捕捉、探究本身就是對文化遺產的傳承和發揚,比想象更具有詩意。
最先抵達的是牛魔王洞。牛魔王的故事是《西游記》中最為精彩的篇章之一,牛魔王也和孫悟空、豬八戒一樣成為中華大地上婦孺皆知的經典形象。沿著黑河一路向西,仿佛我們也要去取經一般,有一種神圣的使命感。在車上,多會長告訴我們,30年前,他曾一個人騎著自行車,背著水壺,從求學的張掖師范來尋訪牛魔王洞。30年前,或者更早的300年前,牛魔王洞就在這里了,當時老鄉告訴多會長關于牛魔王洞的許多故事,說是老一輩人代代流傳下來的。多會長的一席話,讓我們肅然起敬,他對文化的熱愛,是來自骨子里的、發自內心的。現在,他又帶著更多的熱愛者來這里探尋、研究。30年的時光悄悄染白了他鬢間的發絲,卻沒有消磨掉他心中的激情和熱忱。這份熱忱和激情,更點燃了大家對《西游記》文化研究的興趣。
牛魔王洞就在張掖通往臨澤的公路旁,初看上去只是一個大土堆,下面有一個用土坯壘砌的圓形拱門,小而且殘缺。走近了,才能看到拱門下面坍塌之后的洞口,也不大,已經被土掩埋了。洞上面是一個小山包,上面有幾堵墻,墻上依稀有壁畫的痕跡。有研究壁畫的專家細細看過,說這些壁畫應該是近代的,時間不會太久遠。但牛魔王的故事在這里已經流傳很久了,等候在這里的臨澤縣文聯劉主席介紹,小的時候,他就聽說過牛魔王洞的故事,說這個洞很深,是無底洞,人一旦進去就再也出不來。劉主席是聽爺爺講的,爺爺是聽爺爺的爺爺講的。臨澤板橋這一帶,大家都知道這個故事,情節大同小異,人物名稱卻不變,關于牛魔王洞,大家都玩笑:這個洞,肯定是通往玉面狐貍的洞里去了嘛!
拍照,測量,仔細查看,專家學者們甚至拿了放大鏡仔仔細細看墻上壁畫的線條和色彩,似乎想從這僅存的遺留中找到西游文化的穴位、經絡。深秋的風吹到臉上,帶著絲絲寒意,路邊的楊樹上不斷有葉子落下來,黑河兩岸的莊稼地里,是收割過的玉米茬;遠處,還有放羊的人趕著羊群。在旁邊地里干活的80歲老人張鳳香興致盎然地走過來,再次給我們講了關于牛魔王洞的故事。她說這個小小的洞口,神秘詭異,侵吞了許多牲畜和小孩的性命,許多人因為好奇探秘,進去之后就沒有再出來。另有傳說,這洞一直往西,出口在嘉峪關,曾有一只狗,從這洞口進去,數日之后自嘉峪關那邊洞口出來,渾身狗毛全無,只剩下一身紅皮。傳說離奇,想象似乎也符合西游故事的思路,老人講得認真,我們聽得仔細,并不覺得這是一個笑話。老人年歲已高,但身輕體健,非常健談,對牛魔王洞的傳說深信不疑,因為這是她從小到大聽了許多遍的故事。還因為,牛魔王洞的西北不遠處就是火焰山,整個山體都是鮮紅色,就像燃燒的火焰。她說他們這里的人都相信,這個洞就是《西游記》里面的牛魔王居住的洞穴。老人還說,當年毛主席“深挖洞、廣積糧”時,曾有人試圖清理此洞,不料挖出兩條大蛇來,從此誰也不敢再動這里。這些傳說是和留存的遺跡互為補充、互相印證的。
看著這荒廢了的遺跡,想想《西游記》故事的浪漫色彩,不能不讓人感慨時間的荒蕪和強大。文化的傳承、發揚,不僅需要具體的實體,更需要抽象的精神力量。
接下來,去老人所說的火焰山——板橋的紅溝。火焰山離牛魔王洞自然不遠,不然牛魔王也不會娶了鐵扇公主。沿著公路繼續往西,再往北拐,大約一個小時車程就到了紅溝。紅溝就是紅色的丹霞山,連綿起伏的群山不高,卻全是紅色的。猝然之間領受這壯觀綺麗的氣勢,似在靜僻之中撞見奇跡,我們不得不停下腳步來調整呼吸。如果有誰對牛魔王洞的傳說還有所懷疑的話,到了紅溝,一定會確信,這里的的確確就是火焰山!所有的山都是正在燃燒的火焰,赤色、深紅色、橙黃色、醬紫色,深深淺淺,濃淡交錯,不僅顏色像火焰,形狀也像極了火焰。站在山腳下,似乎也能感受到火焰燃燒的呼呼聲。驚嘆中,大家跟著劉主席就近爬上一座山,到了山頂,更是令人驚嘆不已——正是上午11點,紅色的山體在金色陽光的照耀下,像連綿起伏的火海,一直燃燒到天邊,遠處的、近處的,高處的、低處的,不同顏色、不同形狀的火苗在陽光下變幻著不同的色彩!如果沒有看見過這一片連綿起伏延伸到遠處的火海,怎能產生火焰山這樣綺麗傳奇的故事?
紅溝是本地人形象質樸的叫法,任何瑰麗奇異的想象,都來自實實在在的存在。無疑,這紅溝就是火焰山,就是鐵扇公主、芭蕉扇這些傳奇故事的真實范本。每一個來過這里的人,都會如此確信。
紅溝往北,是羊臺山,傳說是蘇武牧羊的地方。汽車在茫茫戈壁上顛簸了一個多小時,遠遠地看到了藍天之下的羊臺山。時近正午,天空像被水洗過一樣碧藍,有幾抹淡淡的云彩飄浮在上面,藍天之下,羊臺山如一座安靜的城池,靜默不語,山下的殘磚斷瓦訴說著曾經的喧囂興盛。羊臺山下有人家,養駱駝,一群群白色的、黃色的駱駝高昂著頭,在籬笆墻下的轆轤井旁等候我們的到來。這樣的場景讓我們感覺穿越了時空,有如隔世。張掖市文聯陳洧主席和幾個作家即興創作劇本,故事曲折,情節離奇而又合乎情理。其實,任何浪漫的想象都有催生它的土壤,真正偉大的作品絕不是憑空杜撰的,《西游記》的誕生,應該也缺不了這樣蒼茫遼闊中的樸拙柔美場景吧!
下午,去高老莊,尋訪豬八戒墩。一路上聽劉主席介紹,我誤以為是豬八戒洞,及至到了高莊村,遇見田邊勞作的村婦,一路問過去,還是說豬八戒洞,順著田埂七彎八拐,終于到了,卻只看到一個不大的土墩。夕陽下,土墩的顏色是黃褐色的,上面夾雜著青黑的沙石。墩周圍不過3米就是莊稼地,玉米已經收割完了,田野里一片空曠,不遠處,就有人家,有棗園。劉主席介紹,這個豬八戒洞也是古跡了。當地流傳,豬八戒洞很深,但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深,因為許多放牛的孩子都被這個洞吸走了,人不歸,牛也不見了。當地人害怕,請高人做法收拾,填了洞,又在上面立了個墩,算是鎮住了,從此不再有人失蹤。故事里沒有高小姐,也沒有豬八戒,但這個墩確實就叫“豬八戒墩”,高莊村的祖祖輩輩就是這么叫的。往回走的時候,我們從一戶楊姓人家的后院穿過來,老楊又給我們講了一遍豬八戒墩的故事,和先前劉主席講的一樣。老楊還告訴我們,村名高莊,但這個村里沒有一戶人家姓高。大家都笑說估計是被豬八戒嚇跑了吧。老楊說他也不知道,在他小時候,爺爺就是這么講的,那個墩也一直就在那里。
任何存在自有來歷,并不是每一處遺跡都能與傳說那么貼切,如果是那樣,我們的考察與研究也就失去了意義,變成牽強附會的生拉硬套了。掩埋于荒草殘垣間的遺址和依附在這些遺址上的謎一樣撲朔迷離的傳說和故事,都是黑河文明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值得我們蹲下身來,把心放在低處,反復尋訪、探究、揣摩、學習、解讀,這才是更有意味和意趣的行走。
夕陽西下時,我們結束了行程,整整一天對《西游記》文化遺跡的尋訪,讓我們每一個人對西游文化的產生都略有感悟。我想,無論什么時候,不管什么地方,如果忽略了文化遺跡的發掘保護,不去作實地考察,那么任何學術研究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安陽,《甘州歌》
寒冬。臘月。甘州。
出甘州城南40公里,離祁連雪山更近的安陽大地,主調不是虛張聲勢的蒼涼感,也不是故弄玄虛的神秘感,更不是炊煙繚繞的世俗感。天藍得澄澈,盡管整整一個冬天都沒有下雪,但不遠處的祁連雪山依舊巍然屹立,似乎伸手可及。清新的空氣中透著白雪一樣干凈的清寒,讓人忍不住要深深地吸一口氣,再緩緩地呼出去。落光了葉子的樹木并不顯得蕭瑟,枝干挺立,直指藍天,更有一種別樣的風骨。沒有了繁茂枝葉的遮蔽和掩映,冬天的大地景物是通透的,視線可以延伸到數百米之遠。站在魁星樓上向四下里看去,黃色的村莊在藍天、雪山的映襯下,顯得有點蒼涼古樸,也多了些神秘。房屋、車輛、樹木、結了冰的澇池、澇池里鑿開的冰窟窿、從冰窟窿里擔水的人,還有遠處枯黃沉寂的田地、三三兩兩站在門口聊天的老人、居民點上追逐打鬧的幾個孩子、田地里靜默的三兩只肥牛和緩緩移動的羊群……一切都被冬日的悠然綜合成一種有待挖掘的詩意,看上去那么質樸而又淡泊。遠離了城市的喧囂,村莊像一幅巨大的默片,靜謐而安詳,不遠處的雪山作為永恒的背景,更使這詩意變成了一種需要用心體味的空靈。
如果我們的心足夠安靜,一定能感受得到村莊的靜美。
這是安陽的賀家城。這個小小的村莊可以算得上是離市區最遠的村莊了。從某一個角度來說,足夠遠的距離也許是一種幸運,一種天然的保護屏障,使古老的傳統得以留存。我們此行的目的就是探訪古老的鼓樂演奏《甘州歌》。賀家城村有一個叫賀勝的人,他帶領的鼓樂班子會演奏這一古老的民間音樂。張掖市委黨校的任教授在張掖文化方面頗有研究,這次探訪就是他為我們聯系的。他介紹說,賀勝和他帶領的鼓樂班子不僅是甘州,還是西北地區唯一流傳下來的最古老、最純粹的民間鼓樂演奏班子。在別處,再也聽不到這樣傳統的演奏了。面包車出了城一直往南走,祁連雪山仿佛就是映在車窗玻璃上的一幅水粉畫,賀家城就是這幅畫里的一個村莊。任教授說,出了甘州城10里之外才有真正的文化。這雖然是一句玩笑話,但也不無道理,任何一種藝術形式的存在,都必定要有適合留存的環境。安陽賀家城地處城南40公里之外,離城區較遠,離現代文明的浸染就遠一些,民風淳樸,保留了許多古老傳統的風俗習慣。
賀勝早就在自己家里等候我們的到來。這是一個典型的西北漢子,臉龐黑紅,身材魁梧,方臉大眼,濃眉厚唇,臉上滿是忠厚實誠的笑。他家里收藏了許多關于道教的珍貴典籍,大多是手抄本,最早的一本是明朝崇禎年間的,紙頁已經泛黃了,但上面的字跡依然清晰,筆畫遒勁有力。有《萬神則感應矣》、《天尊說圣姥孔雀明王經卷》、《黃帝地母經》、《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等百余本,賀勝介紹說,他家是祖傳道教鼓樂班子,演奏道教音樂,替人做法事、搞祭祀,到他這里已經是第五代了。也就是說,近300年來,他們鼓樂班子演奏的歷史及其文化品性沒有斷裂過,不管王朝更換、時間摧毀,始終用一種強韌的力量將這特殊的音樂形式與這片土地相容,將他們的演奏放進了人心里和塵世間,除了“文革”期間,幾乎沒有間斷過。尤其是近些年來,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鄉村葬禮越來越重視傳統儀式,賀勝和他的鼓樂班子也越來越火。雖然這樣的演奏僅限于喪事和祭祀活動,但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大抵是滋生于生活現場的,唯其如此,才更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我們要聽的鼓曲是《甘州歌》。我們一行20多個人,大多數沒有聽過。賀勝的鼓樂班子也就四五人而已,平常各自忙活,務細莊稼,也打工掙錢,遇到哪家有事來請,才臨時組合到事主家里去,演奏只是繁亂的喪事或者祭祀活動的一部分。忙亂之中,能用心來聽的人并不多,其真正的作用是想通過鼓樂演奏營造一種隆重悲涼的氛圍。今天,他們特意在村里的禮堂里為我們演奏。賀勝他們早已經做好了準備,幾個人都穿了紅色長袍,戴了黑色的方形道帽,嗩吶、大鼓、銅鈴等器樂一應俱全。演奏之前,任教授又作了簡單介紹,《甘州歌》其實屬于“西涼之聲”,是西涼樂、宮廷樂、龜茲樂三種音樂的融合,“雜以秦聲”,主要特色就是以鑼鼓為主的梆子,加上嗩吶,兼有說唱,節奏快,曲調熱烈激昂,正所謂“鏗鏘鏜鏜,洪心駭耳”。任教授說,此音“可爭天籟”。
果然!鼓樂氣勢震人肺腑,似千軍萬馬橫空騰躍,直擊得人心也跟著鼓點“咚咚咚”狂跳,裂帛一樣高亢悲涼的嗩吶聲,索性將胸腔里那顆跳躍的心一直往上提,直要沖破喉嚨,不覺間我已經淚流滿面,整個人都被這酣暢淋漓的演奏感染了,似通了電,通體舒暢,發燒了一般,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動與痛快。
這是一種難得的享受,如同暢飲甘冽的美酒,讓人醉得痛快酣暢。現在,娛樂充斥著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但像這樣能真正打動人心,使人震撼的演奏已經不多了。所有的人都被鼓樂聲牽動著,帶領著,進入了一種微醉微醺的狀態。
比我們更陶醉其中的,是演奏中的賀勝本人。自演奏開始,他好像變了一個人,完全沉浸在音樂之中,無論是吹嗩吶,還是擊鼓,他都微微閉著眼睛,陶然忘我,似乎對周圍的世界已經渾然不覺。他不是在表演,更不是在演奏,而是在享受,享受已經融入他生活和生命中的這份摯愛。這份愛,可以說是與生俱來的,五輩人近300年代代相傳的文化,已經深深扎根、流淌在他的血液之中,使得他身上散發著有別于其他演奏者的一種特殊精神氣質。也許,感染了我們的正是這種精神氣質,而并非他精湛的演奏技巧。這個世界上,真正讓人感動、觸及我們內心深處的,是執著,是堅守,更是全身心的投入和熱愛。缺少了熱愛,任何優秀的文化傳承都不會有恒久持續的生命力。有這種精神氣質打底的演奏,不僅打動人心,更讓人肅然起敬。
從第一場《西番贊》開始,到《哭長城》、《千里渡行》,不覺間,兩個小時過去了,正午的陽光透過窗戶射進來,小小的禮堂里已經擠滿了聞聲而至的村民,先前還有點陰冷的禮堂變得暖洋洋的,似有熱氣在沸騰,演奏者和聽眾都意猶未盡,這酣暢淋漓的鼓樂演奏仿佛把現場的所有人——無論是聽者還是演奏者都帶到了遠離現實卻又是最世俗的生活現場。這樣說似乎是矛盾的,但現實是全民物質化、功利化、表面化的,我們的內心,其實期待著能回到一種有文化傳統和精神歸屬的俗世。
也許,某一刻,地處偏遠的安陽賀家城,因為有了像賀勝這樣的民間藝人和《甘州歌》這樣的文化傳承,可以算得上一個理想的俗世吧!音樂,或者任何文化的真正傳承,甚至創新發揚,不在曲高和寡的高檔演奏廳里,而在民間。
我們心有期待。期待,會成為一種文化傳承和延續的生命線,“預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只要愿意聽,一切都能延續;只要能夠延續,一切都有改觀。就像張掖的《西游記》文化研究一樣,我們期待文化的傳承,更期待文化的拓展、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