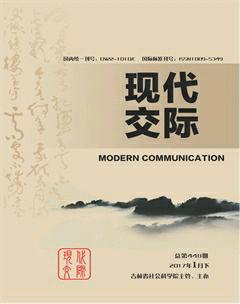淺談托克維爾關于“多數暴政”的觀點
趙妍
摘要:縱觀人類政治史,雖然發生多數暴政的次數遠低于少數引發的暴政,但政治學家們并沒有忽略這一社會事實。托克維爾在美國考察期間也注意到多數的無限權力所產生的暴政,針對這一民主社會的弊端,他在《論美國的民主》中表達了對無限權威的否定態度,為各國民主社會的發展提供借鑒。
關鍵詞:托克維爾多數暴政無限權威
中圖分類號:D091.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7)02-0041-02
一、關于“多數暴政”
早在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在對政體進行分類時,就表現出對“多數”的極大關注。他將統治人數的多寡與統治者利益取向相結合,劃分出六種政體,其中由多數人掌握政治權力并以自身利益為核心的平民政體更像托克維爾的“多數暴政”的論述前身。在這種政體下所有的政事都要通過召開公民大會予以裁決。無論是具有法律常識還是以道德標準衡量一切的公民,都能“對國內較高尚的公民橫施專暴”,民眾的臨時決議能代替法律擁有絕對權威。這種以多數決議的民主原則發展到現代成為民主共和制的核心。
托克維爾在他的著作中稱,“民主政府的本質在于,多數對政府的統治是絕對的。因為在民主制度下,誰也對抗不了多數”。“多數”在民主政體中的“自然力量”決定了無論多數對錯,都要尊重多數的權利。人民的“多數”既擁有“在管理國家方面有權決定一切”的實權,又擁有強大的道德影響力。因此,在“多數”面前,從不存在任何阻礙或延緩其發展的障礙。“多數”無論提出什么議題,最終都會得到實施。這樣處理問題的方式,導致了“多數”的無限權威。
二、“多數”的無限權威
托克維爾論述,“不管任何人,都無力行使無限權威。”,因為“多數”的無限權威“是一個壞而危險的東西”。
首先,美國的立法者在不間斷的新舊更替中修正法律條文以及“多數”的無限權威在美國快速而絕對地執行意志的方式,不僅在立法過程中“造成法律的不穩定,并且對法律的執行和國家公共管理造成了同樣的影響”。
其次,“多數”所擁有的權威同時包含物質和道德兩個層面壟斷了人的思想和行為,這種集所有力量于一身的絕對統治的力量遠比君主專制在任何一方面的統治力量強大的多。在民主制的美國,“多數”在劃定的思想周圍筑起一圍高墻,在高墻內,人們可以自由活動,而一旦超過活動界限。“他肯定會遭受公眾的蔑視并飽受眾人的謾罵”,“暴政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實施,人的身體是自由的,但靈魂卻受到奴役。”而這種“多數”對個人思想自由的限制與民主的初始追求相違背。
最后,托克維爾指出,美國自由體制如果在未來遭到破壞,一定是“多數”的無限權威所致,因為“‘多數的權威終將使少數陷入絕境。進而迫使其進行武力反抗”。
三、1812年美國上演的“多數暴政”
托克維爾在考察期間發現了一個令人震驚的關于“多數暴政”的實例。它發生在1812年位于美國大西洋海岸的巴爾的摩市。當時美、英關系緊張,國內不同勢力在對英政策上存在分歧。巴爾的摩起初非常支持戰爭,但當地一家報紙提出了反對意見,從而激怒了當地居民。民眾集結起來毀壞了印刷機,攻擊了報社編輯的房子。有人想召集民兵平息風波,但無人遵守命令。拯救被暴民圍攻之人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將其作為罪犯丟人監獄。然而,這種方式也于事無補,暴民在夜間再次集結攻擊監獄。地方官員試圖召集民兵,但再次失敗。其中,一名報社編輯當場死亡,剩下的人也只能坐以待斃。而肇事者在接受審訊的時候,被陪審團無罪釋放。
美國是典型的由“多數”統治的民主國家。托克維爾舉例說,某人的觀點如果被公眾認為在“政治上不正確”,那么無論他的政治和社會地位原本有多高,他在美國的公共生活中必將聲名狼藉。而這種政治上的正確性不是由政府來判斷。而是由代表“多數”的公眾來判斷。這是美國社會的“大眾政治法庭”。在這個“法庭”上,任何在美國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個人或黨派。無論他們申訴的事項有多么不公正和荒謬。都得選擇盡量服從“多數”的無限權威。
四、如何削弱“多數暴政”
托克維爾洞察到了民主社會“多數暴政”的弊端,他論述“多數暴政”并非是要反對民主,而是希望民主能揚長避短、做得更好,他認為“多數”的無限權威是可以削弱和克服的。
(一)法學家團體
托克維爾走訪美國時發現。“美國的法律制度賦予法律人士的權力以及這些人能夠對政府產生的影響。是目前能夠對抗極端民主的最有力的保障。”
一方面,從法學家們自身來說,他們對公共秩序的熱愛超過了其他任何事物。因為一般來說。凡是對法律有研究的專業人士,都會在工作中養成遵守秩序的習慣。這種講求規范的職業習慣會使他們與“多數”產生的極端革命精神與魯莽激情相敵對,一旦民主的弊端顯露,他們便成為公民之間的仲裁者,既會對訴訟者的淺薄激情進行指導,又會蔑視多數的判斷。
另一方面。“法律行業是唯一可以通過非暴力途徑與民主的自然因素相結合的貴族因素。并且這種結合是有利而持久的。”由于法學家的身份和利益出于人民,考慮到自身利益因素時,雖然他們的習慣和偏好源自貴族,但在某些事務的具體問題方面更傾向于人民。民眾也都知道法學家們對服務公共事務感興趣,能夠相信法律人士,聽取法學家的意見。因此,法學家成為人民和貴族這兩個社會階級之間的自然紐帶,把人民和貴族聯系在了一起。
基于以上兩點。法學家們作為民眾唯一信任的知識階層被委以大多數公共職位。同時成為平衡民主因素的最強大群體,抑制任何可能存在的無限權威。
(二)陪審團制度
如果說。就任美國公職的法律人士將專業中的習慣和術語帶到國家事務中,那么在法院以外,陪審團將這種習慣滲透到社會所有的層面。使全社會幾乎所有的人都沾染了法律人士的習慣和愛好。
托克維爾將美國人的政治敏銳感歸功于陪審團制度在民事案件中的長期運用。當陪審團的影響從刑事領域擴展到民事領域的時候,它能關涉群體的所有利益,迫使每個人都要配合其工作,積極參政。同時,陪審團對增進人們的智慧也作出了莫大的貢獻。因為在司法過程中。他們可以通過律師的辯護、法官的建議,甚至是當事人的申訴來使自己學習國家法律。這無形中將陪審團化為一所長期免費開辦的公共學校,用一個漸進的手段使所有公民擁有法官的思維方式,對美國公民起到政治教育的作用。總之,陪審團制度不僅是使人民實施統治的最有力手段。也是教育人民如何統治的最有效的手段。它將法律精神滲透到社會所有階層。為維護社會知識素養和防止多數人的專制的發生提供了強有力的智力支持。
(三)出版自由與結社自由
托克維爾認為在“多數”原則下形成的強大的國家權力系統面前,有關個人方面的保護制度是非常有限的。因此,為了有效地保護個人的自由,必須尋求社會領域的幫助。出版自由與結社自由在個體權益的保障上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
托克維爾對于出版自由的贊成。“首先是因為它能防止社會弊端,其次才是它本身的種種好處。”假設某種隱晦的尚未得到立法的違法事件發生。違法者被交給作為“多數”代表的陪審團后并未受到懲罰,但由于事件的廣泛影響。社會公眾需要一個途徑和公開平臺來自由表達觀點。這時出版自由便擁有了社會公斷的權威。在民主國家,出版自由比其他國家顯得更加可貴。因為一方面,出版自由可以保護被孤立和無助的人免受政府的迫害,讓他們使用報紙向本國的公民和所有人類尋求幫助與支援;另一方面,它使人們和各種社會團體的利益得到充分有效表達。這對緩解社會矛盾發揮很大的作用。
社團首先是一群持有相同觀念的個體的自愿集聚。共同的思想將他們聯系在一起形成一個有統一目標和指導核心的有機團體,這些社團被賦予自由組織活動的權利。托克維爾指出,“當今時代,結社自由已成為對抗多數人暴政的必要保障。”他認為,一個政黨一旦掌權,就意味著掌握了一切公眾權力,也會很快控制各級行政機構。那時少數派中,即使最優秀的人也不能扭轉當下局勢。因而,結社自由以“少數”形成的共同意志成為限制“多數”無限權威的有力手段。必須說明的是,結社自由與出版自由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四)宗教信仰
在法國。宗教精神與自由精神始終處于水火不相容的境地。然而托克維爾發現,美國的宗教與自由二者關系融洽,共同統治著這個國家。在美國,很多州的法律都明確禁止教會人士進入政界。教會內部的大多數人也自愿遠離世俗事務,將不擔任任何社會職務當成自己的一種榮譽。雖然教會人士有時也會抨擊政界人士的野心和不忠實的信仰,但是,他們對所有黨派幾乎都謹慎地保持著距離,堅持政教分離。因為在美國的民主制度下,宗教信仰作為獨立的精神力量。無需任何其他幫助就能生存。而當它試圖幫助任何政治權力的時候,都要放棄另一部分公眾的支持,反而對自己的生存不利。因而,宗教信仰作為道德紐帶扮演民主社會的捍衛者角色。對防范“多數”民主的弊端。彌補政治紐帶的空缺,治理民主國家有積極的能動作用。
五、結語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將“多數暴政”作為民主社會的弊端加以論述并不是反對民主。而是希望民主能克服“多數”的潛在威脅。“‘多數并不意味著萬能和無限權威”。托克維爾“對他們民主制度缺乏對抗暴政的措施而感到真正的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