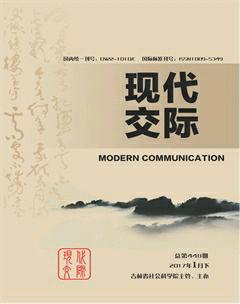彝漢雜居村落彝族通婚圈變遷研究
茶劉英
摘要:云南漾濞水竹坪村屬于彝漢雜居村落,在我國(guó)經(jīng)濟(jì)體制急劇變化的60年里,其通婚圈也隨之發(fā)生了重大變遷。建國(guó)初期到改革開(kāi)放前,該村以村內(nèi)婚和族內(nèi)婚為主;改革開(kāi)放后,該村出現(xiàn)了跨省通婚和族際通婚,通婚的區(qū)域和民族逐步多元化,并有進(jìn)一步擴(kuò)大的趨勢(shì)。
關(guān)鍵詞:當(dāng)代彝族村落通婚距離通婚民族變遷
中圖分類號(hào):H217;H102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文章編號(hào):1009-5349(2017)02-0088-03
通婚圈即婚姻的選擇范圍。它包括某一婚姻個(gè)體在擇偶時(shí)可能選擇的地域范圍或群體范圍。通婚的地域范圍主要是指通婚的地理范圍。例如杜贊奇對(duì)20世紀(jì)前期河北良鄉(xiāng)縣吳店村和欒城縣寺北柴村通婚圈進(jìn)行的研究認(rèn)為。“從村莊距市場(chǎng)遠(yuǎn)近的資料來(lái)看。新娘所在村莊多散布于以市場(chǎng)為中心的方圓10里以內(nèi),由此看來(lái),兩村(新郎及新娘所在村莊)均位于同一市場(chǎng)之內(nèi),他們很可能是因?yàn)榧兄薪槎嗷フJ(rèn)識(shí)最后聯(lián)姻的。”同時(shí)又認(rèn)為“我們對(duì)以上材料亦可作另一種解釋。即出嫁閨女的村莊坐落于結(jié)婚娶媳婦的村莊的‘聯(lián)姻范圍之內(nèi)。這一范圍可能獨(dú)立于集市圈之外,其輻射半徑可能以一定時(shí)間內(nèi)步行可到的距離為準(zhǔn),亦可以原有聯(lián)姻范圍為準(zhǔn)”。通婚的群體范圍主要是指通婚的等級(jí)或族群等文化與社會(huì)范圍。婚姻的本質(zhì)是文化的、社會(huì)性的制度。婚姻的締結(jié)不是生理本能的驅(qū)使,而是“文化引誘的結(jié)果”,直接受到各種社會(huì)習(xí)俗、道德、規(guī)范和制度的影響和制約,如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認(rèn)為“印第安人波洛洛(族)村落歸根結(jié)底可以看做是分成三個(gè)族群,每個(gè)族群均內(nèi)婚”。在不同的歷史時(shí)期,通婚圈受地理、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呈現(xiàn)出不同的時(shí)代特征。故對(duì)一個(gè)民族的通婚圈變遷進(jìn)行研究,有利于我們了解這個(gè)民族不同時(shí)期的政治、經(jīng)濟(jì)與文化。從這個(gè)意義上來(lái)看,要對(duì)村落社會(huì)進(jìn)行深入研究,通婚圈是我們無(wú)法回避的關(guān)注點(diǎn),我們不僅可以從中了解不同歷史時(shí)期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模式。還可以在動(dòng)態(tài)中認(rèn)識(shí)社會(huì)變遷的軌跡。文章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縣龍?zhí)多l(xiāng)水竹坪村彝族臘羅支系為例。通過(guò)對(duì)其當(dāng)代通婚地域和通婚族群變遷的研究。得以了解在社會(huì)發(fā)生急劇變化的情況下彝族村落婚姻變遷的軌跡。
一、水竹坪村概況
水竹坪村屬于山地型村落,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縣龍?zhí)多l(xiāng)。漾濞彝族自治縣位于云南省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中部,總?cè)丝跒?04602人,其中彝族人口為52159人,占總?cè)丝诘?9.9%,分別屬于臘羅、羅武和諾蘇三個(gè)支系,其中臘羅支系人口就達(dá)4萬(wàn)多,主要分布在該縣中部和南部山區(qū),包括雞街、瓦廠、龍?zhí)丁㈨樺ā⑻健⑵狡?個(gè)鄉(xiāng)(鎮(zhèn)),其他鄉(xiāng)鎮(zhèn)間有分布。口碑中,臘羅支系的好幾個(gè)姓氏都記述自己與南詔王室有淵源關(guān)系。龍?zhí)多l(xiāng)位于漾濞縣南部山區(qū),東抵瓦廠鄉(xiāng),南至雞街鄉(xiāng),西連永平縣龍街鄉(xiāng),北靠順濞、太平二鄉(xiāng),鄉(xiāng)政府駐地龍?zhí)洞澹嗫h城85公里。水竹坪村村委會(huì)位于龍?zhí)多l(xiāng)西北,距龍?zhí)多l(xiāng)政府所在地12公里。到鄉(xiāng)道路為土路。交通不方便,距縣城上街鎮(zhèn)66公里。下轄小新村、河邊、趕馬臘、大浪潭、大堆子、大伙房、中村、對(duì)門等8個(gè)村民小組;人口以彝族為主,除了大伙房是漢族聚居的自然村落外,其他7個(gè)都是彝族聚居的自然村。現(xiàn)有總戶數(shù)234戶,總?cè)丝?17人,彝族人口592人,占總?cè)丝诘?2.6%,為彝漢雜居的行政村。水竹坪村的彝族自稱“臘羅巴”,屬于我國(guó)彝族的臘羅支系。臘羅支系是我國(guó)彝族的一個(gè)重要支系,主要分布于滇西的大理、保山、臨滄、普洱等地,自稱“倮頗”“羅羅”“納羅”“臘羅”“魯潑”,使用彝語(yǔ)中部方言和西部方言。人口占彝族總?cè)丝诘奈宸种蛔笥摇!芭D羅”是該支系彝族的自稱,男女稱謂又有所區(qū)別,男性自稱為“臘羅巴”,女性自稱為“臘羅嫫”,在彝語(yǔ)中“臘”是老虎的意思,“羅”是龍的意思,“巴”具有“人”和“公、雄性”的意思,“嫫”具“母、雌性”的意思。故“臘羅巴”在支系內(nèi)部專指男性。在支系外部則是對(duì)該支系人口的總稱。
20世紀(jì)80年代以前。水竹坪村的彝族以山地農(nóng)耕為主要生計(jì)方式。村民的日常生活基本上是圍繞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開(kāi)展的,經(jīng)濟(jì)收入也絕大部分來(lái)自農(nóng)業(yè)。除大面積種植玉米和種植少量水稻外,還種植豌豆、蠶豆、蔬菜等,大多數(shù)人家飼養(yǎng)牛、山羊、豬、雞等畜禽。總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jīng)濟(jì)是這一時(shí)期當(dāng)?shù)卮迕裆a(chǎn)活動(dòng)的真實(shí)寫照。但是,隨著改革開(kāi)放的不斷深入,這種自給自足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被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逐步打破,外出務(wù)工、種植烤煙、栽培核桃、種植土豆、蔬菜、養(yǎng)羊、養(yǎng)雞等都成為村民的重要經(jīng)濟(jì)來(lái)源。伴隨著水竹坪村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的不斷發(fā)展與變化。該村彝族的通婚圈也隨之發(fā)生了變化。
二、建國(guó)初期到改革開(kāi)放前的通婚圈
建國(guó)初期到改革開(kāi)放前。水竹坪村彝族通婚的地域范圍十分狹小。在這一時(shí)期,村民的主要婚配對(duì)象來(lái)自本村或鄰近自然村。其通婚地理范圍大致都以當(dāng)?shù)刈匀淮迓錇橹行摹R?5公里為半徑的區(qū)域內(nèi),并且90%以上集中在10公里以內(nèi)的地域范圍內(nèi)。也就是村民步行三四個(gè)小時(shí)能夠到達(dá)的地方。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主要是村民的活動(dòng)和交際范圍較窄。因?yàn)樵撔姓宓母鱾€(gè)自然村都分別分布于云貴高原崎嶇丘陵的大山山頂以及半山腰上。村民居住格局十分分散,加之地形復(fù)雜多樣交通閉塞、出行困難,年輕人相互接觸的機(jī)會(huì)不多,主要是在婚喪嫁娶、共同勞動(dòng)、趕集、春節(jié)廟會(huì)、放牛以及走親戚等場(chǎng)合才有所接觸.而不像現(xiàn)在的年輕人大多是在上學(xué)、打工的過(guò)程中認(rèn)識(shí)的。雖然,這一時(shí)期村里的幾個(gè)年輕人到外地去就業(yè),但是其通婚的范圍還是沒(méi)有跨出本村。例如,建國(guó)后先后有幾個(gè)村里的男性成為國(guó)家干部和事業(yè)單位的工作人員。離開(kāi)村子到鄉(xiāng)鎮(zhèn)或縣城工作,但他們并沒(méi)有在工作地?fù)衽迹侨蓟卮迦⒘吮敬宓墓媚铩_@些人有的將妻子留在村中生兒育女、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照顧老人,有的把妻兒帶到工作地去生活。再如,1964年昆明有些軍工廠曾到漾濞招工,當(dāng)時(shí)水竹坪村有兩名女子被招收。后來(lái)其中一人放棄工人的工作崗位,回到村里嫁給了本村的男子。筆者在調(diào)查中了解到,一般情況下,現(xiàn)年55歲以上的女性外嫁的都不多。由于建國(guó)初期到改革開(kāi)放前這一時(shí)期,水竹坪村的村民社交范圍較窄,所以導(dǎo)致了其通婚的地理范圍較小。當(dāng)然,這種現(xiàn)象不僅僅出現(xiàn)在水竹坪村,應(yīng)當(dāng)在當(dāng)時(shí)的廣大農(nóng)村都是比較普遍的。因?yàn)檫@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國(guó)在廣大農(nóng)村推行集體經(jīng)濟(jì)制度的結(jié)果。
建國(guó)初期到改革開(kāi)放前,水竹坪村彝族幾乎不與外族通婚。這一時(shí)期,與外族通婚的僅有兩例。一例是20世紀(jì)50年代,本鄉(xiāng)密古村的一名白族離婚婦女嫁到本村,據(jù)其家人講,這名婦女的丈夫在建國(guó)前娶有兩位妻子,她是其中之一,建國(guó)后推行的《婚姻法》要求全國(guó)實(shí)行一夫一妻制,她的丈夫必須與他的一名妻子離婚,她沒(méi)有生育兒女,便主動(dòng)提出離婚。退出這個(gè)家庭。后經(jīng)親戚介紹就嫁到了水竹坪村。然而,雖說(shuō)是和白族通婚,但實(shí)際上與彝族通婚差別不大,因?yàn)楸距l(xiāng)密古村的白族早在明朝時(shí)就遷入該地生活,在周圍彝族的影響下,生產(chǎn)、生活和語(yǔ)言等已與當(dāng)?shù)嘏D羅人無(wú)異,只是其有相關(guān)的族譜等證明其是白族罷了,所以本人認(rèn)為婚姻的締結(jié)是以同質(zhì)性為基礎(chǔ)的,人們樂(lè)于同與自己有相同文化生活、經(jīng)歷的人締結(jié)婚姻。同時(shí)我們也可以看到在當(dāng)?shù)厝丝谳^少的民族。在周邊人口比例占絕對(duì)優(yōu)勢(shì)的強(qiáng)勢(shì)民族文化的影響下,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出現(xiàn)了文化的自然涵化。另外一例是20世紀(jì)70年代初期,本村的彝族男子娶了本村的漢族女子為妻。這是本村彝漢通婚的第一例,具有開(kāi)創(chuàng)性的意義。村里至今也很少有當(dāng)?shù)匾妥迮c漢族通婚的情況。究其原因,主要是彝族與漢族之間在文化生活方面的差異。因?yàn)樵撔姓宓臐h族都是從四川搬來(lái)不足百年,他們?cè)谏盍?xí)慣和喪葬儀式等方面都和周邊彝族有很大的差異,口音也帶著濃重的四川口音,所以當(dāng)?shù)氐囊妥宥冀兴麄兛图胰恕F湓谒衿捍迦烤劬佑诖蠡锓看迕裥〗M,與村里的河邊村民小組直接接壤。當(dāng)然,在漾濞縣,像這樣彝漢雜居的村落很多,很普遍。在這種情況下,在建國(guó)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兩族互相都有一定的敵意,彝族認(rèn)為漢族說(shuō)話口音難聽(tīng)、做人過(guò)于小氣,蔑稱他們?yōu)椤昂淖印保欢鴿h族也覺(jué)得彝族霸道蠻橫不講道理、不講衛(wèi)生,叫他們“土羅羅”。在那個(gè)時(shí)期,村里的彝族和漢族都不愿互相通婚。僅有的這一例主要是因?yàn)橐妥迥凶由线^(guò)中學(xué)、參加過(guò)紅衛(wèi)兵小將到北京的參觀活動(dòng),而該漢族女子也于16歲就因招工到州府軍工廠工作,與上海等地的人有所接觸,兩人都算是見(jiàn)過(guò)世面,思想都比較開(kāi)放,能夠沖破世俗的偏見(jiàn)而最終結(jié)婚(他們相識(shí)在1968年,于1974年結(jié)婚)。
由此看來(lái)。建國(guó)初期到改革開(kāi)放前。水竹坪村彝族的通婚空間范圍相對(duì)狹小,多集中于本村和臨近村落,并且主要實(shí)行的是族內(nèi)婚。
三、改革開(kāi)放后的通婚圈
改革開(kāi)放后,特別是20世紀(jì)八九十年代,水竹坪村彝族的通婚地理范圍有所擴(kuò)大。但在2000年后又呈縮小的趨勢(shì)。在20世紀(jì)的八九十年代,水竹坪村彝族的通婚空間范圍擴(kuò)大。主要源于數(shù)十名河南平頂山未婚大齡男子與當(dāng)?shù)匾妥迮酝ɑ椤_@一時(shí)期,河南平頂山未婚男子的介入,解決了當(dāng)?shù)卮簖g未婚女性(這些女性主要因?yàn)橛猩砣毕荻诋?dāng)?shù)厥艿交橐鰯D壓)的婚姻問(wèn)題,這些男子絕大多數(shù)也是由于家庭貧困和自身缺陷在當(dāng)?shù)卣也坏较眿D的結(jié)婚“困難戶”,他們中的90%以入贅的形式在當(dāng)?shù)囟ň酉聛?lái),生兒育女,耕作山地。當(dāng)然,同時(shí)也有幾名才貌出眾的年輕女性。懷著對(duì)外面世界的好奇和對(duì)美好生活的向往嫁給了河南人:同時(shí)。還有部分智力低下的女性被拐賣到外地去,但是本文主要研究的是自由婚姻引起的通婚圈變遷。故對(duì)這些被迫引起的婚姻變遷因素暫不做考慮。水竹坪村彝族女子與河南男子締結(jié)的婚姻很快就出現(xiàn)了一些問(wèn)題。由于兩地生產(chǎn)、生活的差異較大,這些夫婦的家庭生活條件往往都比當(dāng)?shù)厝瞬詈芏啵蚴呛幽夏行圆贿m應(yīng)高原艱辛的農(nóng)耕生活,無(wú)法養(yǎng)家,而回到河南,水竹坪村的這些彝族女性又適應(yīng)不了那里的生活習(xí)慣,所以這樣的家庭會(huì)在兩地交叉著各生活幾年。無(wú)論在水竹坪村還是河南都無(wú)法扎下根來(lái)好好生活。鑒于村中女性與河南人通婚的種種問(wèn)題。從2000年以后村里只有個(gè)別女性嫁給河南人。再?zèng)]出現(xiàn)20世紀(jì)八九十年代那樣大批外嫁的現(xiàn)象。這一時(shí)期,除了與河南人通婚外,村里一些外出工作、打工的青年男女也擴(kuò)大了其通婚范圍,本村女性與山東、四川男子通婚的各有一例。
這一時(shí)期,水竹坪村彝族通婚的族群范圍也有所擴(kuò)大。與白族、納西族和漢族都出現(xiàn)了通婚的現(xiàn)象。村中有兩名女子與白族通婚。一例是本村女子財(cái)校畢業(yè)后在縣城的工商銀行工作,和本單位大理白族男子結(jié)婚,婚后在縣城買房生活。另外一例是本村女子在醫(yī)學(xué)院畢業(yè)后到本鄉(xiāng)醫(yī)院工作,她的丈夫是鄰縣(洱源縣)白族,他們?cè)诋厴I(yè)實(shí)習(xí)時(shí)認(rèn)識(shí)(當(dāng)時(shí)都在漾濞縣第一人民醫(yī)院實(shí)習(xí)),她丈夫后來(lái)到大理市中醫(yī)院就業(yè),他們?cè)诋厴I(yè)兩年后正式結(jié)婚。村中有一名男子與麗江納西族女子通婚。這名男子是部隊(duì)轉(zhuǎn)業(yè)后到麗江林業(yè)局當(dāng)司機(jī),與水竹坪村的女朋友分手后,到麗江當(dāng)?shù)丶{西族女子家去上門(入贅)。這一時(shí)期,一名本村大伙房社的漢族女子嫁給了本村中村社的彝族男子(兩人在上學(xué)時(shí)認(rèn)識(shí)),并于2011年結(jié)婚。村中有兩位女性與山東和四川漢族結(jié)婚。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水竹坪村的族際通婚范圍在逐步擴(kuò)大。
綜上所述,由于上學(xué)、就業(yè)等原因引起水竹坪村人口的流動(dòng),擴(kuò)大了該村通婚的空間范圍和族群范圍。
四、結(jié)語(yǔ)
綜上所述,水竹坪村彝族通婚圈由小到大的變遷過(guò)程,反映了當(dāng)?shù)匾妥迳鐣?huì)在其自身的發(fā)展過(guò)程中發(fā)生的變化以及與外界社會(huì)聯(lián)系的狀況。
20世紀(jì)80年代以前的水竹坪村通婚圈。呈現(xiàn)出同村婚與族內(nèi)婚的形態(tài)結(jié)構(gòu)。“同村婚”與“族內(nèi)婚”占絕對(duì)的主導(dǎo)地位,表現(xiàn)出了與自給自足自然經(jīng)濟(jì)的密切關(guān)聯(lián)性具有一定的封閉性與穩(wěn)定性。在水竹坪村,通婚圈成為村落之間互相聯(lián)系的重要紐帶,在本村和相鄰村落親戚多成為村中人夸耀的資本,因?yàn)樾∞r(nóng)經(jīng)濟(jì)在遇到問(wèn)題或出現(xiàn)麻煩時(shí)需要親戚的幫助。在遇到天災(zāi)人禍時(shí)更需要親戚的資助才能渡過(guò)難關(guān)。在商品經(jīng)濟(jì)極端落后的社會(huì),農(nóng)業(yè)是村民生存的根本,在生產(chǎn)工具極為落后的時(shí)期,勞動(dòng)力是家庭興旺發(fā)達(dá)的基礎(chǔ),所以絕大多數(shù)村民愿意與本村或附近村落通婚,以便在特殊情況下相互幫助與扶持。
但到了20世紀(jì)80年代以后。水竹坪村自給自足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逐步被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所打破。人們不再僅僅以農(nóng)業(yè)為生。人們的謀生手段逐步多元化。所以交往方式和交往對(duì)象不斷擴(kuò)大。人們可以通過(guò)農(nóng)業(yè)以外的生計(jì)方式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故傳統(tǒng)的建立在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基礎(chǔ)上的就近通婚規(guī)則被打破。因而,水竹坪村彝族的通婚圈在當(dāng)代呈擴(kuò)大化的趨勢(shì)。并隨著村落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和人口流動(dòng)的加劇而有繼續(xù)擴(kuò)大的趨勢(sh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