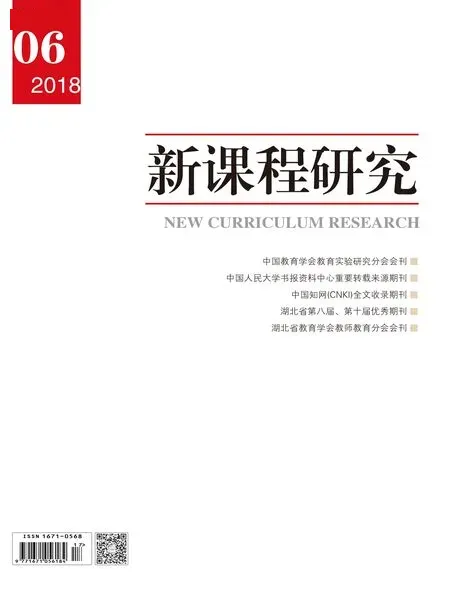成果導向本科課程評價標準體系建構初探
一、學生學習成果的界定及評價意義
1.學生學習成果的界定。學生學習成果(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指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之后,學生被期望學到的和學生實際學到的東西。學生學習成果包含學生應該知道什么,能夠做什么,以及在課程結束之后學生獲得了什么。美國教育評價標準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ttee on 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 Evaluation)認為,“學生學習成果是對學生特定學習的期望,即學生經過學習、發展等過程之后獲得的各種結果”。也就是說,學生學習成果表達對學生學習的期待——學生通過完成課程取得學位之后,被期望知道什么、理解什么,以及運用課程所學能夠做些什么,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知識與理解力、實際技能、情感態度與價值觀及個體行為。[1]知識與理解力適用于基本的認知內容、核心概念或問題、探究的基本原則、廣泛的歷史或各種各樣的學科技術。實際技能集中于應用基礎知識、分析和綜合信息、評估信息的價值、有效溝通和協作的能力。態度和價值觀包含情感狀態,個人的、專業的、社會價值觀和倫理原則。個體行為是知識、技能和態度所表現出的具體反應。科羅拉多梅薩大學學生學習評估手冊(Student Learning Assessment Handbook 2016-2017)中根據布魯姆的學習目標分類將學生的學習成果定義為六個維度:知識、理解、應用、分析、合成、評價,[2]知識維度的是對學生回憶、認識其所學到的近似形式的信息、思想或原則的評估;理解維度是對學生根據先前的學習來理解或解釋信息的評估;應用維度是對學生選擇、轉移以及使用數據和原則來完成問題或任務的評估;分析維度是對學生區分、分類并能夠聯系到相關知識的假設或結構的評估;合成維度是學生對知識的收集、整合,并能夠將整合的結構應用到新的領域中的評估;評價是對學生基于特定標準評價或批評的評估。
2.我國高校本科學生學習成果評價的意義。我國高校本科階段人才培養一直注重質量問題,多年來我國學者一直致力于人才質量評價的研究,高校根據教學目標、課程目標培養出來了一批批的畢業生,如何衡量這些畢業生是否符合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對于人才的需求標準,是促使學者們不斷地探索新的思路和方法來進行更加合理的人才評價的動機。1979年艾瑞納的“學習成果”術語的提出,為課程評價的研究打開了新的思路,尤其是美國的學者,在這之后出現了學習成果評價研究的熱潮,學習成果為導向的課程評價研究在美國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我國學者借鑒其理念,結合我國高等本科教育的基本國情,展開相關的研究,對我國高等本科教育課程評價、課程改革以及人才培養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在整個課程的運作體系當中,學生學習成果評價不是獨立存在的,評價的動機也不是為了評價而評價,評價的動機是為了達到評價的目的,一方面評價學生的實際獲得的學習成果,另一方面是為了通過評價學生改進課程,促進課程不斷優化,在課程不斷優化的過程中學生的實際學習所得不斷提高,逐漸接近預期的學生學習成果,這樣就形成一個有機的循環。在課程體系運行的過程中收集學生學習成果的相關數據,再對數據進行評價分析,獲得評價結果,再根據評價結果對課程進行反饋(如圖1)。

圖1
圖1直觀地展現了學習結果評價在整個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通過評價獲得的結果來決定接下來的教學如何進行。如果獲得的結果與期望的結果一致,就可以證明整個課程體系符合成果導向的課程評價體系的標準,將所得學習結果設定為成功的結果和標準,根據這個標準繼續運行課程體系;如果獲得的結果與期望的不一致,就說明課程體系的某個環節不符合成果導向課程評價體系的標準,以此找到不合理的地方,從而有針對性地對其進行調整,再將調整的部分對應到課程大綱的相應環節,對課程大綱進行不斷改進。
二、本科學生學習成果評價現狀
20世紀80年代,課程評價理念進入我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課程評價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評價活動趨于多元化,評價主體、評價指標、評價內容等都體現了實用性和有效性的特點。盡管如此,我國課程評價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如理論性研究所占比例大于實踐性研究所占比例,評價標準多基于理論分析,忽略了具體驗證標準的有效性;再如,部分學者將研究的重點放在課程實施后的效果評價上,這就容易混淆課程評價和教學效果評價。另外,構建課程評價指標體系時,對每一個評價指標的具體設計也相對較少。
20世紀90年代末,隨著高考擴招政策實施,我國本科階段的人數在幾年內激增,面對龐大的本科人數,如何衡量其是否符合培養標準成了我國本科教育所要面對的首要問題。20世紀8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以結果為導向的學生學習成果評價逐漸顯示出它的優越性,借鑒美國人才質量評價的相關經驗,我國高校人才質量評價逐漸向成果導向的評價方式轉變,學生學習結果評價逐漸成為我國人才質量評價的主要趨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目前我國高校學生學習成果評價通過直接評價和間接評價兩種方式,對學生在認知和非認知兩個維度進行評估。[3]雖然我國高校對于學生學習成果評價具有相對成熟的評價方式和維度,但是相對而言,我國高校學生學習成果評價工作還存在一些問題,首要的就是評價標準不夠完善。以成果為導向的學生學習成果評價與教學是緊密聯系的,通過不同的評價方法,在各個維度中獲得相應的學生學習成果,通過學習成果的評價,獲得評價反饋并改進教學目的。如何對學習成果進行評價?評價的標準和尺度是什么?評價的維度有哪些?這些問題沒有解決,就很難產生有價值的反饋,也就很難促進課程的改進。因此,完善評價標準在我國本科學生學習成果評價工作刻不容緩。
三、成果導向本科課程評價標準構建
1.評價理念設定的標準。成果導向的本科課程評價理念應遵循兩個基本原則。首先,以學生為中心的課程理念。以學生為中心包括以學生的成長為中心和以學生的需求為中心,學生的成長又包括學生的知識、技能和情感態度的養成,即學生作為一個受教育者所應該具備的基本素養。學生的需求指的是學生作為具有社會屬性的人,需要在社會上生存和發展,而能夠生存和發展的前提是具備社會發展需要的專業技能,此時學生的需求等同于社會發展的需求。成果導向的教育,滿足學生對于自身成長、發展的需求,成果導向的課程評價也要遵循以學生為中心的理念。其次,以學生學習成果促進課程改革的理念。學生完成相關課程的學習之后通過評價反饋學生獲得的成果,形成“課程設計-教學實施-課程設計”的良性循環。成果導向課程評價是以成果為導向進行課程評價,隨著社會的發展,對于人才的需求規格也會發生變化,學生的需求也會隨之變化,此時學生的學習成果也會相應地變化,因此,課程評價對于課程的反饋就要與時俱進。
2.評價目標設定的標準。成果導向的本科課程評價目標設定時,需要注意以下幾點:首先,確定明確的課程目標。通過課程的學習,明確目標的學習成果是什么,美國科羅拉多梅薩大學對于學習成果目標的確定十分明確,相較于我國本科專業對于課程目標的確定,其對于課程目標的描述更加具體,采用動詞代替名詞來具體描述學生通過課程的學習能夠獲得的學習成果,避免因為課程目標不明確或者含糊不清,導致學生獲得無效的學習結果。其次,成果導向課程目標要具有可驗證性。課程目標涉及的層面很多,但是每一個維度上的課程目標都具有可驗證性,模棱兩可的設定及不便于檢驗的課程目標是不符合成果導向課程理念的。再次,成果導向課程目標要具有代表性。課程所產生的效果是多方面的,同一課程對于學生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那么課程的主要目標就需要明確的確定,明確課程的重點,有的放矢地設定具有代表性的課程目標。最后,成果導向課程目標要有反思性。評價結果除了評價學生的實際學習結果,還要能夠反饋課程,在成果導向的課程目標設定過程中要考慮到設定的課程目標是否體現了反饋課程的特點。具備了以上的特點才是合理的課程目標。[4]
3.評價的程序標準。成果導向的本科課程評價應具備完整性,它與一般的課程評價具有一些共同點,都由課程理念、課程目標、課程設計、課程實施和課程評價等課程要素組成,不同之處在于所有這些課程要素都是以學習成果為導向確立的,而且在課程評價的過程還要具備反饋課程、促進課程改革的環節。也就是說成果導向的本科課程評價在具備評價課程的功能的同時還要具備通過反饋課程評價促進課程改革的功能。針對這兩個功能,成果導向本科課程評價既要包括課程評價的基本程序,又要包括促進課程改革的程序。
實施成功的學習成果評價,一方面,要對成果導向的本科課程進行評價(如圖2)。大學總的育人目標是成果導向中預期的學習成果,各個院系以此為導向針對本專業實際情況制定相應的專業目標,即院系層面上的預期學習成果,各個專業涉及的課程再以此為導向結合課程的自身特點制定課程的預期學習成果,再以預期的學習成果為導向實施課程,獲得實際學習結果。接下來的數據收集是針對學習成果進行的,課程實施過程中會產生很多學習成果,收集數據的過程中要注意以預期學習成果為導向,抓住課程目標的重點。再將實際獲得的學習結果與預期的學習成果進行比較分析,從而找出兩者之間的差距,通過對產生差距的原因進行分析,追根溯源找出產生實際學習成果的環節,從而獲得課程目標的相應反饋,將涉及課程的反饋意見反饋給相應的課程實施環節和數據收集環節,再將涉及目標的反饋意見反饋給院系目標和課程目標,通過反饋將整個課程完善成一個完整的回路,在課程不斷進行的過程中不斷完善,最終使實際學習成果不斷接近預期學習成果。

圖2
另一方面,要運用評價促進課程改革(見圖3,P15)。在明確院系教學目標的前提下,理清院系目標和課程目標之間的關系.院系目標是課程目標確定的前提,根據院系的目標指導課程目標(即預期學習成果)的建立。評估獲得的學習成果,找出課程目標(即預期學習成果)與獲得的學習成果之間的關系,通過對兩者的比較,找出課程中的不足,相應地對課程進行改革,改革之后的課程再次獲得學習成果,將獲得的學習成果反饋回課程目標(即預期學習成果),課程目標再對院系目標進行反饋,從而又形成一個有機的閉合回路,在整個循環過程中,獲得的學習成果與預期越來越接近,課程也得到了不斷改進,從而形成了成果導向課程評價促進課程改革的良性循環。[5]

圖3
總體而言,我國本科課程評價標準體系建構工作任重而道遠,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這個問題,隨著研究的增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成果導向課程評價理論這一指導思想在課程評價標準體系構建上越來越凸顯優勢,我國本科院校雖然嘗試根據成果導向課程評價理論來構建本科課程評價標準,但目前還沒有成熟完善的理論聯系實踐的研究成果,各個國家的學者都處在不斷探索的過程中,而我國高等本科教育具備自身的特點,需要培養的人才質量也不能用統一的標準進行衡量,因此,在成果導向本科課程評價標準體系建構的過程中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還有很多實際問題需要進一步地研究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