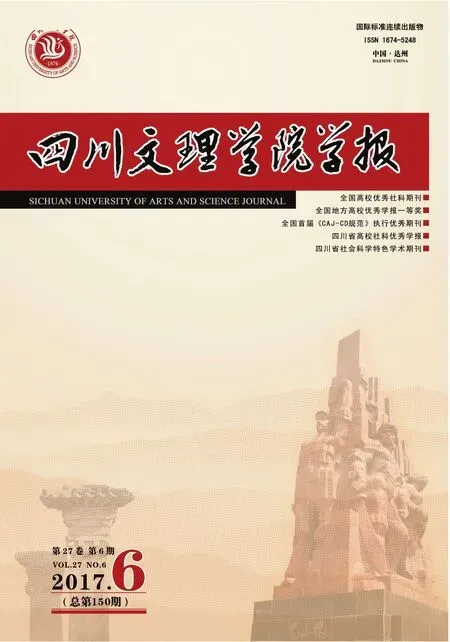純粹的美與絕對的美
——中西審美思想探析
譚文旗
審美是人類情感世界的凝聚體現。在人類思想文化發展過程中,因為地理空間的分隔,審美呈現出不同樣態。不同族群雖然在不斷地交流、融合,但是在幾千年的歷史沉積下,還是分化構成了不同形態的審美思想。當前,現代信息技術突飛猛進,資本世界超速擴張,時空壓縮所帶來的他者文化不斷生成而又不斷地彼此擠壓,原有的審美思想文化不斷地受到挑戰而又不斷地延異轉變。該如何面對當前的審美文化?不同的審美文化思想該如何行進?本文主要選取中國古典審美思想和西方古典審美思想來言說審美的兩種主要范式——純粹的美和絕對的美,并對這兩種審美思想的進一步發展作出展望,從而給予全球化語境中的個體生存以審美啟示。
一、純粹的美
從中國古典審美思想看來,審美不是認知世界,也不是意志世界,而是“我”與世界無目的、無功利但卻有理趣的情感相通、呈現;審美視域中的世界既不是客體、物質性的對象存在,也不是主觀、精神性的意志表達,而是“天人合一”的充滿著人類原初情狀的生存樣態;審美世界的“世”作為時間、“界”作為空間不是指物理意義上的完全客觀化、外在化的時間、空間,而是指與個體“我”緊密關聯的人生在世的生存性時空;作為有“我”、有“你”,有“他”“它”的世界成為審美世界,就是不斷去除外部事物對“我”的束縛、遮蔽、扭曲,不斷自我化,又不斷純粹化的過程。這是一種純粹的美。
純粹的美具有以下幾方面特征。
(一)沒有一種獨立的、客體對象性的美
或者說,沒有一種外在于人的、實體化的美。中國古人一般不推崇獨立于“我”的客體對象,所謂“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認為這樣的境地不高、韻味不足。所以,中國古典審美思想反對一味地對外在客體事物的摹寫,認為對物體“形”的摹寫最重要的是去顯示“神”,藝術創作的“技”最主要的是要去通達“道”,如,顧愷之的“以形寫神”,蘇軾的“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中國古典美學思想中的這種“神”不是柏拉圖所說的先在的、絕對的、永恒的,獨立于“我”的“理念”,而是“我”與天地萬物息息相通,在相通中呈現出來的一種“韻”“味”“妙”“趣”,是一種通達天地萬物的“覺”和“悟”。
(二)美是“我”“心”的敞開展現
中國古人的世界總是一種“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宋·陸九淵),“天下沒有心外之理”、“天下沒有心外之物”(明·王陽明)的狀態。宇宙(時間與空間)的呈現與“我心”總是息息相關的。這類似于海德格爾的“我在世界中”。這種“在……中”不是書在抽屜中、桌椅在屋子中似的物理狀態,而是主客無隔、“一氣流通”的生存關聯性,是一種共在相通狀態。于此,美的世界呈現,總是以“我”為窗口綻放出來。“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于空山矣。”(唐·柳宗元·《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中國文化思想一方面總是在消解實體性的、客觀無我、絕對永恒的本體世界:“生生之謂易”(《易傳》),“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經》),“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慧能);另一方面又總是從“我”“心”的視角去言說“道”的通達、“仁”的實現、佛義的覺悟:莊子的“心游”“心齋”,孔子的“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為仁由己,而由他人歟”,禪宗的“即心即佛”“明心見性”。于此,審美總是關乎“我”的情意,“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藝術創作過程總是從“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然后才是“筆下之竹”。
(三)審美的過程,或者說美的世界呈現的過程是一個自我不斷純粹化的過程
“純粹”就是去除經驗、不雜經驗。“我”,總是在世界中,總會被世俗生活、功利雜塵所纏繞,操心、操勞、煩神,所以,審美就需要“滌除玄鑒”“澄懷味象”。這是一種擺脫知識、意愿、欲念,自我不斷“心齋”“坐忘”,“味無味,事無事,為無為”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由于自我不斷地拋開個人偏狹的視角、自我固有的心理,達到一種物我兩忘、“相看不厭”的境地,所以這種境地一方面是最自然本真的,另一方面又是新穎別樣的。蘇軾說的“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知此凝神”就是自我純粹化的一種審美情態。
(四)純粹化的審美過程最終通達的是一種“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齊一”的天地之境、宇宙之本
當把自我單一固有的視角消除,擺脫了世俗欲念的困擾糾纏時,在純粹化世界中,“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這是一種天地萬物在“我”心中,而“我”又在萬物天地間的完全消融狀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當一切的喧囂和躁動都蕩去時,呈現出來的就是一個本真、原初的世界,至靜至深、地老天荒的宇宙本體。中國古典審美活動追尋的就是這樣一個個體的“我”與天地共在狀態下不斷純粹化從而自如其是、純然同一、永恒自在的宇宙本體世界。
二、絕對的美
人人都能感受到美的存在,但是,什么是美?是什么使得人、物、山林、天空成其為美?或者說在那美的事物里面是否有一種美的本源?如果有,那是什么?這些問題促進了人們以“絕對”的方式來言說美的存在。
(一)作為本源性的絕對美
古希臘哲人認為,變動不居的現實世界有一個不變的本源,萬事萬物就是從這個本源而來。例如,泰勒斯的“水”,畢達哥拉斯的“數”,赫拉克利特的“火”,德謨克里特的“原子”。“美”也不例外。在柏拉圖看來,美不是作為我們能夠直接感知到的現象呈現,如漂亮的小姐、美的湯罐、美的豎琴,也不是恰當就是美,和諧就是美,而是漂亮的小姐、美的湯罐、美的豎琴背后起決定作用的美之為美的“理念”。這種美的理念使“一切美的事物都以它為泉源,有了它那一切美的事物才成其為美”,“這種美是永恒的,無始無終,不生不滅,不增不減的”,“它也不是隨人而異,對某些人美,對另一些人就丑”。[1]這種先在的、永恒的,不隨人而異的“美”我們稱之為“絕對的美”。西方審美藝術中的模仿說——現實世界是對本源的理念世界的模仿,而藝術又是對現實世界的模仿,一直占主導,這和他們認為存在一種本源性的絕對美是緊密相關的。
(二)作為神性的絕對美
“古代‘希臘七賢’之一的哲學家泰利斯·封·米勒特曾經說過:‘神充斥一切!’他指出,古代的希臘人幾乎都認為世界是神祇創造并由神祇統治的。”[2]其實,對大多數民族來說,沒有神祇的世界是不可理喻的。神經常以神諭的方式啟示凡人,而凡人從中獲得覺解與力量。所以,作為超越凡人、永恒自在的“神”就是人類“絕對的美”,審美就是對這些絕對、永在的神的傳達與表現。可以說古希臘藝術和神都有關聯,除了直接的神話、神廟,其他的悲劇、史詩、雕刻都主要表現神的存在,乃至以后西方的許多藝術作品都是從這些“神”中得到靈感。在后來的西方世界中,源于古希伯來的宗教文化占據主導位置,世界的本源集中體現在宗教世界里,審美就是對宗教故事、人物所寓含的絕對、永恒、無限的追尋與表現。文藝復興時期大多數藝術家與宗教關聯密切,對他們來說,上帝、圣母、耶穌是一種絕對的存在,是美的源泉,是美本身。
(三)作為理性的絕對美
西方近現代從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開始,主體性粉墨登場,高歌猛進,人們開始擺脫宗教獨斷而展現出人的理性之光。笛卡爾的“我思”是一個絕對不可質疑的起點,而這個起點引發了西方哲學思維的轉變——從先驗的本體論轉向以人為出發點的認識論,理性成為絕對的法則。康德的“哥白尼似的革命”進一步論證強調了主體在認識中的地位和作用,推斷出人的理性所具有的一種先天綜合判斷能力;黑格爾通過嚴密的“精神現象學”演繹,展現出人類最后也是最高的階段——絕對精神。緣于此,西方近現代文學藝術創作主要展現人的理性光輝。雖然,1750年鮑姆嘉通就建立感性學(Aesthetics,翻譯為“美學”),以期與哲學的理性相區分,但是西方近現代主流的審美觀念是黑格爾的“美就是理念的感性顯現”。
(四)不斷“延異”的絕對美
西方現當代時期,哲學思想界一方面猛烈地反理性、反主體,反邏各斯,反人類中心主義,另一方面又不斷提出更本源的“絕對”存在。尼采喊出了作為絕對的“上帝死了”,要“重估一切道德價值”,相應地又提出另一個絕對存在——“超人(The Super person)”。弗洛伊德一方面大力批判絕對理性,另一方面又揭示出非理性的“無意識”。海德格爾批判舊的形而上學,提出了作為世界敞開的窗口——“此在”,又提出了比此在更原本的“存在”。而各種審美思想總是關聯于這些新的絕對者。20世紀下半葉在解構主義思潮下,西方思想文化界進一步對一切形而上學大加摧毀、消解,主體性、同一性、結構性衰落,他異性呈現。“列維-斯特勞斯對原始文化的關注,拉康對無意識話語的解讀,福柯關于理性與非理性關系的論述,德里達對邏各斯中心論的解構,針對的都是他者和他性問題,都表現為對絕對他性的承認。”[3]列維納斯更是直接以“絕對他者”作為世界呈現的原初方式。而審美思想就從這些他異性中尋找源泉根基。“物(Thing,或Das Ding),也稱為不可能之物,是齊澤克哲學和美學理論的核心概念”,“在物的概念燭照下,齊澤克思考了崇高美的本質、崇高化、崇高對象和崇高藝術等一系列問題,實際上已經建構了一個以不可能之物為核心的崇高美學理論。”[4]西方現當代在如此“延異”中展示出一種異質性的絕對美來。
三、在后現代狀況下中國古典審美方式與西方古典審美方式的發展路向
(一)純粹的美不同于絕對的美
雖然純粹的美最后通達的也是一種萬物之源、宇宙之本,但是這種源和本總是與“此在”息息相關、處處相連的,所謂“萬古長空”總是關聯于“一朝風月”。而絕對的美雖然總是在不斷地演變,從柏拉圖的“理念”到基督教的上帝,從黑格爾的絕對理念到列維納斯的“絕對他者”,等等,但是這種“絕對”總是先在、先驗,與“此在”總有些區分。另外,絕對的美呈現出來的雖然是一個不斷地從外在的物像走向內在的心靈,從絕對的神走向經驗的自我,從對絕對理念的模仿走向一種“自我”表現的過程,這是一種擺脫外在物像不斷探視、顯示內宇宙的過程,但是我們要說,這種過程是一種對絕對美的追尋和期望過程,這是一種執著的美,與中國擺脫束縛、去除雜思的破執的美還是有實質區別的。
(二)中國古典審美思想對絕對的美——絕對的理念、絕對的神、絕對的物自體、絕對的他者等關注不夠
中國古典審美對“絕對”的呈現不管怎么說都顯得薄弱,因為,純粹美總是與“我”關聯在一起的,是以“我”的“澄懷”來“味象”,那種完全區別于“我”、完全絕對狀態的美是不被認可的。中國審美思想一直講究的是神、韻、意、趣,對完全以絕對他性的面貌呈現的事物以模仿,對某個事先就存在的理式進行展現,是貶斥的。這造成中國藝術過多地以簡單的色彩、簡化的線條去展現自我空靈的存在情形,而對紛繁的物象、思辨的時空缺少深入的探索、細致的表達。這種“大道至簡”的“空無”觀念使得中國古典藝術持續發展不夠,表達方式不多。另外,在后現代時空壓縮下,絕對他者的存在不可回避,自我的純粹其實是無法擺脫他性的糾纏的。因此,中國現代審美不能以自我的純粹來忽略乃至抹除他者之在,只有真正思考如何與他者的共存才能切實解決日常生活審美化問題,建構中國的現代審美體系。
(三)從幾千年西方審美思想的發展路向上看,雖然西方古典審美方式——對絕對美的不斷探尋,實質上是一種向人、向心不斷回歸溯源的過程,但是這種內宇宙總是作為一種客體存在,總是與個體偶然的“我”有區別
對這種“絕對理念”浮士德式的審美追求有時會把我們弄得不知所措,比如當代的波普藝術、行為藝術、觀念藝術、抽象藝術,以及藝術終結論等。對此,中國古典審美方式——自我的純粹化,或許能夠帶來“他者”的啟示。面對拉康的不可捉摸的實在界、福柯的異托邦空間、德里達不斷延異而無最終所指的能指鏈,或許“道法自然”——天地自然而然地變易,萬物如其所是地生長,是探尋絕對美的現代方式。“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自我內心的寧靜與純粹就在通達絕對的美,或者說,對絕對美的探尋須得注意回歸到自我純粹的一切如其所是的“道法自然”狀態。
面對天地萬物、人事紛繁,審美的人生一面是不斷地自我純粹化的過程,一面是不斷地探尋絕對他者的過程。表面看起來這好像是矛盾對立的,實質卻是一種“道者反之動”——不斷行進的過程中轉化、生成,提升、超越。這或許就是中西幾千年的審美思想帶給后現代時空壓縮下的人們最簡明的啟示。
[1](古希臘)柏拉圖.柏拉圖文藝對話集[M].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249.
[2](德)古斯塔夫·施瓦布.古希臘神話故事[M].趙燮生,艾 英,譯.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0:1.
[3]楊大春.語言 身體 他者[M].北京:三聯書店,2007:303.
[4]韓振江.論齊澤克“不可能物”與崇高美學[J].美學,2016(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