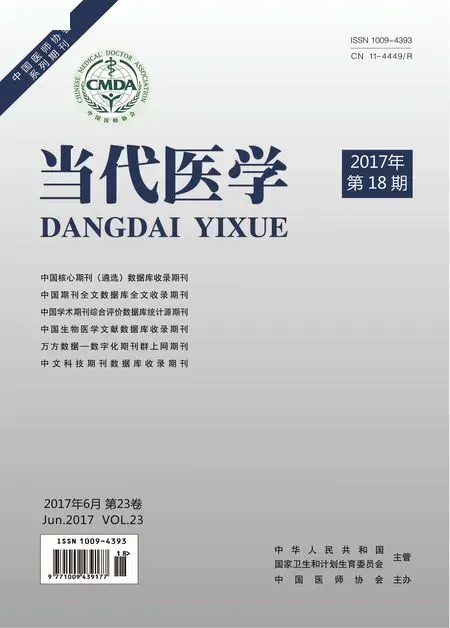骨質疏松骨折基礎和臨床研究方法進展
李志軍
(廣西鹿寨縣人民醫院骨科,廣西柳州545600)
骨質疏松骨折基礎和臨床研究方法進展
李志軍
(廣西鹿寨縣人民醫院骨科,廣西柳州545600)
骨質疏松是一種以骨量減少、骨退行變為特征的代謝性骨病,目前基礎研究主要涉及骨微結構、骨微損傷與骨折的關系;骨結構相關研究的臨床應用包括定量計算機斷層掃描(QCT)應用于骨骼評價、QCT聯合有限元分析(FEA)應用于骨質量評價,獨立于骨結構的骨折危險因素研究有骨折危險性預測工具(FRAX)、血清標志物[血清I型原骨膠原蛋白N-端肽(s-PINP)、血清Ⅰ型膠原蛋白c末端交聯端肽(s-CTX)、基質金屬蛋白酶(MMPs)]等;要充分預防骨質疏松,需充分了解相關因素對骨代謝的調節的生活過程,并針對性進行干預。結構因素結合代謝途徑可能是骨折風險預測的一個新方向。
骨質疏松骨折;骨微損傷;骨結構
骨質疏松是一種以骨量減少、骨退行變為特征的代謝性骨病,其可引起骨脆性增加,骨折風險增加。骨抵抗骨折的能力主要與骨量、骨結構和骨質量有關[1]。對骨質疏松的診斷主要依靠骨密度的測定,重視骨量的變化,但其敏感度及特異性較低。近期,許多研究從骨結構的微觀角度來探討骨質疏松的發生機理,以影像學方法測定骨量和骨結構,依次作為臨床預防骨質疏松的依據[2]。隨著研究的深入,很多與骨結構相對獨立的危險因素逐漸在預防該病過程中得到關注。
1 基礎研究
1.1 骨微結構皮質骨和松質骨在微觀上均以骨單位構成。標準的小梁骨是通過受力線方向有內部連接的桿狀、片狀結構構成。骨質疏松除了骨量丟失外,還伴有骨結構的損害。松質骨與骨髓細胞較近,而后者在骨代謝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故松質骨能在早期反映骨量的丟失。骨質疏松狀態下,骨皮質變薄,多孔性特征明顯,且骨小梁由盤狀結構變為細小的桿狀結構。其原因是因破骨活動增強,成骨活性降低引起,這種機制在絕經后女性骨質疏松中表現更突出。有研究表明,切除卵巢后,大鼠松質骨內的骨小梁形成腔-管結構[3]。對骨微結構可通過高分辨CT、顯微CT、活體顯微CT及高分辨核磁共振成像(MRI)進行評估,顯微CT分辨率較高,但需活檢獲得骨標本,高分辨CT、活體顯微CT、MRI可作為非侵入性掃查,然而高分辨CT的分辨率相對偏低,MRI多用于軟組織的檢測,活體顯微CT的價格較為昂貴[4]。上述方法目前主要用于基礎研究,還需一段時間方可用于臨床,但可用來預測糖皮質激素誘導的骨質疏松骨折風險和評價藥物療效方面。
1.2 骨微損傷與骨折的關系骨對機械性負荷具有適應性外形改變的能力,這可在成骨細胞和破骨細胞對骨重建過程中實現。人骨組織在日常活動中會受到超過骨適應能力的疲勞損傷而引起微損傷。通過顯微鏡可發現這種微損傷,即骨基質的破壞,其反映了骨力學性能的降低及切除卵巢大鼠骨結構變化和雌激素的療效。骨小梁的微損傷可影響其局部力學性能,最終影響整體骨組織結構性質和力學性能。有研究發現,應用顯微CT、數字散斑等技術可觀察到切除卵巢大鼠的骨微損傷改變[5]。有研究用顯微CT觀察大鼠骨微結構及微損傷修復的變化來評價經染料木素治療的大鼠的療效[6]。Magni等[7]研究報道,甲狀旁腺激素(pTH)治療可影響骨微結構及膠原含量改變,降低了骨折的風險。在微損傷損害整體功能之前,骨組織可探測并修復微損傷,這與微損傷附近的骨細胞凋亡和骨吸收有關。若骨對微損傷的修復能力降低,則會引起更多的微損傷而不能完整修復,引起小梁骨及整骨疲勞骨折。對骨微損傷的檢測為創傷性檢查,使得以骨微損傷作為指標應用于臨床受到了限制。
2 骨結構相關研究的臨床應用
2.1 定量計算機斷層掃描(QCT)在骨骼評價中的應用傳統對骨骼的平均主要采用DXA,而近期有研究發現,QCT相對于DXA具有一定的優勢,其對低骨密度的診斷敏感性更高,降低了漏診率。一項研究采用QCT對老年男性骨折的危險因素進行研究,作者對股骨近端不同區域皮質及小梁骨密度進行檢測,發現股骨頸、股骨粗隆的小梁骨骨密度為髖骨骨折的獨立危險因素[8],因此認為,QCT可應用于骨折風險的評估。Wei等[9]采用QCT等技術來觀察雷尼酸鍶等抗骨質疏松藥物對機體微結構的影響,結果認為QCT在骨骼評價中具有較高的臨床應用價值。QCT能測定皮質骨和小梁骨的骨密度,因此能更好的了解骨骼強度的結構參數,但尚無專業的數據軟件對人體掃描進行處理。可用雙源CT掃描來解決QCT的放射性問題[10]。
2.2 QCT聯合有限元分析(FEA)應用于骨質量的評價FEA實際上只是一種微分方程的數值求解法,通過相關軟件處理骨組織的三維圖像來分析受力分布等力學特性。其與QCT結合是把結構與力學性能進行檢測,在臨床應用中屬于無創檢測,對骨質疏松性骨折具有一定的預測價值。Lee等[11]建立近端股骨側向摔倒QCT/FEA的斷裂負載模型,發現預測的最大張力區多為實際試驗中出現的應力損傷區,一般在股骨頸與大轉子連接處。在未出現小轉子碎裂時,QCT聯合FEA對股骨頸的骨折預測正確率可信度高。盧玉等[12]通過二維放射性影像建立三維FEA模型,發現FEA對破壞載荷的預測達80.4%,而骨密度僅為54.5%,說明QCT聯合FEA對骨質量預測的可靠性。張俊等[13]分別用QCT聯合FEA、活體的顯微CT、DXA對椎體骨質量進行評價,發現輕度的椎體變形多表明早期骨質疏松性骨折。吳秀云等[14]對男性類固醇性骨質疏松進行研究發現,QCT聯合FEA法能較好區分早期椎骨骨折情況,效果比DXA佳,這是由于QCT提供的微結構模型可觀察皮質骨及小梁骨結構,故可能準確反映骨折的嚴重性。因QCT聯合FEA法對骨質疏松骨折具有良好的預測作用,因此也可用來監測藥物治療對骨結構及骨強度的變化。
3 獨立于骨結構的骨折危險因素研究
3.1 骨折危險性預測工具WHO在2009年制定了骨折風險評估(FRAX)工具,該工具是對患者進行問卷調查,了解患者的相關危險因素暴露情況,推測其在10年內發生骨折的風險度[15]。FRAX可用于臨床及人體健康保健中,但僅僅對各流行病學因素進行統計分析,未將骨質量納入其中,未內充分闡述骨折的發展規律,且其敏感性較低,只能用于初發骨折,應用于再骨折的效果較差。陳玉平等[16]使用FRAX結合骨密度測量,把腰椎骨密度與股骨頸骨密度的差值對10年內骨折進行預測,使該工具的應用范圍得以擴大。
3.2 血清標志物血清中存在可測的骨生化指標,目前多項研究表明,這些指標能預測患者的骨折風險,結合FRAX和臨床危險因素,能提高骨折風險的預測準確性[17]。對絕經后骨質疏松患者,絕經前期骨吸收標志物高于正常,被認為是骨折的危險因素之一。血清Ⅰ型原骨膠原蛋白N-端肽(s-PINP)是一種骨形成指標,而血清Ⅰ型膠原蛋白c末端交聯端肽(s-CTX)是一種骨吸收指標,前者對骨折風險度預測效果優于后者[18]。通過血清股轉化標志物的檢測能了解治療的效果,但無法了解治療的不良反應。其是否可用來預測骨折的風險度還需國際化的參考標準。國外大量研究對骨轉化標志物在預測骨折危險性及藥物療效的評估中的作用進行了研究,認為有一定的作用,可用s-PINP和s-CTX作為參考指標,這對臨床治療的反應評估及指導有一定的作用[19]。除了s-PINP和s-CTX外,還有部分與骨折風險有關的新的血清標志物亦在臨床上開始受到臨床學者的關注。Wnt信號途徑在骨內環境和骨重建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其對成骨過程及骨折愈合發揮重要作用。Wnt信號途徑中LDL受體相關蛋白Lrp4多態性與髖骨骨折率的升高有關,而Lrp5、Lrp6突變會引起骨密度降低和骨質疏松骨折[19]。硬化蛋白是Wnt信號途徑的阻斷劑,絕經后女性血清硬化蛋白含量隨絕經時間的延長而增加,所以此指標可用來評估老年女性骨質疏松患者的髖骨骨折風險和PTH對骨質疏松治療效果。破骨細胞通過高表達破骨細胞分化因子(RANKL),并與骨保護素競爭性結合受體,促進破骨細胞分化。由此可見,血清骨保護素含量越高,骨折危險度越低。骨折術后患者血清及尿骨保護素含量升高,說明該指標在骨折修復過程中發揮一定作用,可作為骨折治療效果的判斷指標。骨鈣素是成骨細胞合成的一種多肽,可結合鈣離子,能反映骨骼生存率。血清骨鈣素降低表明骨折發生風險增加。成骨細胞內含量豐富的基質金屬蛋白酶(MMPs),尿MMP-9濃度可用來評估骨折愈合情況[20]。這些血清標志物在將來具有較廣闊的應用前景。
3.3 骨折相關生存質量調查研究骨質疏松骨折難以康復,致殘、致死率極較高。有調查報道,對40~64歲女性骨質疏松患者,加強體育鍛煉是最合理的選擇,而對>65歲老年婦女,骨密度篩查和合理的藥物治療是最佳選擇。近期有研究者認為,在評價骨質疏松的治療方式利弊時,可逐漸重視患者的生活質量及骨折的危險度[21]。田鵬等[22]研究結果顯示,椎骨成形術在疼痛緩解、機能恢復、生活質量改善方面優于傳統治療,但會使骨折的危險度增加。
4 展望
近10年來,雖然骨質疏松骨折風險的預測研究已取得了極大的進展,但仍存在許多問題:(1)目前,臨床上并未特殊有效預測指標:骨密度是骨質疏松的診斷指標,但其對骨質疏松骨折風險預測能力欠佳,而骨活檢由于創傷大而不宜用于臨床,QCT聯合FEA等方法用來診治骨質疏松還需較長的時間。(2)國際上骨折預測指標還需完善整合:FRAX工具僅統計流行病學因素,缺乏骨質量的評估和血清標志物等指標。骨轉化標志物對骨質疏松骨折風險的預測能力還需國際化的參考標準。(3)把骨代謝與骨質量作整體來思考。研究表明,骨質疏松是一種代謝性疾病[23]。骨細胞可對負荷、應力及藥物做出反應,但其機制尚未明確。故要充分預防骨質疏松,必需充分了解相關因素對骨代謝的調節的生活過程,并針對性進行干預。結構因素結合代謝途徑可能是骨折風險預測的一個新方向。
[1]王曉平,丁洪流.老年糖尿病女性繼發性骨質疏松及其相關骨折[J].中國循證醫學雜志,2014,35(1):42-43.
[2]Armstrong ME,Caims BJ,Banks E.Different effect of age,adiposity and physical activity on the risk of ankle,wrist and hip fractures in postmenopausal women[J].Bone,2012,50(1):45-46.
[3]Fang Jing,Li Wenge,Li Duo.Baseline proteinuria,urinary osmotic pressure,and renal function as positive predictors of corticosteroids plus cyclophosphamidetreatmentefficacyinIgAnephropathy[J]. Chinese Medical Journal,2014,47(3):99-101.
[4]Nuttapol R,Benjamas C,Apiradee S.Prevalence of osteoporosis and osteopenia in Thai COPD patients[J]. J of Med Ass,2012,8(8):725-732.
[5]Ogawa M,OgawaT,Inoue T,et al.Effect of Alfacalcidol Therapy on the Survival of Chronic Hemodialysis Patients[J].J of Inte Soc for Aph,2012,3(3):540-547.
[6]TakashiIto,StephenW.Thepotentialusefulnessof taurine on diabetes mellitus and its complications[J]. Amino acids,2012,5(5):63-71.
[7]Magni P,Dozio E,Galliera E,et al.Molecular aspects of adipokine-bone interactions[J].Curr Mol Med,2010,10(6):522-532.
[8]張國棟,廖維靖,陶圣祥,等.股骨有限元分析賦材料屬性的方法[J].中國組織工程研究與臨床康復,2014,35(2):61-62.
[9]Wei S,Kitaura H,Zhou P,et al.IL-1 mediates TNF-induced osteoclastogenesis[J].The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2005,2(2):451-459.
[10]楊春菊,張鉥纓,吳遠.深圳市居民4 123人骨密度分析及骨質疏松患病率調查[J].中國組織工程研究與臨床康復, 2015,72(2):925-932.
[11]LeeKI.Relationships of Bone Density with QuantitativeUltrasoundParameterinBovineCancellous Bone[J].J of Korean Phy Soc,2009,1(1):52-60.
[12]盧玉,郭紅,劉波,等.老年男性骨密度與骨代謝指標分析[J].中華老年醫學雜志2013,75(3):76-77.
[13]張俊,葛寧,黃曉麗,等.骨質疏松癥的藥物治療評價[J].中國實用內科雜志(前沿版),2015,37(2):61-62.
[14]吳秀云,尹文強,莊立輝.婦女骨質疏松癥篩檢工具應用效果探討[J].中國骨質疏松雜志2015,98(2):41-42.
[15]Ferris HA,Kahn CR.New mechanisms of glucocorticoidinduced insulin resistance:make no bones about it[J]. J Clin Invest,2012,122(2):854-857.
[16]陳玉平,劉雪琴,蔡德鴻.骨質疏松癥知識問卷的信度和效度測定[J].中國骨質疏松雜志,2014,701(11):44-45.
[17]黃衛民,孫健玲,李小鷹.絕經后婦女骨質疏松與心血管病危險因素的相關性研究[J].PJCCPAVD,2012,20(9):46-55.
[18]Celczyńska BL,Horst SW,Bychowiec B.The effects of osteoprotegerin(OPG)genepolymorphisminpatients withschaemicheartdiseaseonthemorphologyof coronary arteries and bone mineral density[J].Kardiologia Polska,2011,69(6):65-72.
[19]卓鐵軍,榮滬光,季宏.定量超聲和雙能X線骨密度測定診斷骨質疏松的比較[J].中國骨質疏松雜志,2013,61(2):32-33.
[20]GaoX,Hofmau A,Hu Y,et al.The ShanghaiChangfeng Study:a community-based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of chronic diseases among middle-aged and elderly:objectivesanddesign[J].EurJEpidemiol,2010,25(12):885-893.
[21]楊衛紅,俞潔菲,張瓊.老年骨質疏松患者對骨質疏松認知程度和生活質量現況調查[J].中華老年醫學雜志,2015,11(2):41-42.
[22]田鵬,馬信龍,王濤,等.骨質疏松癥對腰椎間盤突出癥的癥狀時間的影響[J].實用醫學雜志,2014(24):72-80.
[23]BuizertPJ,vanSchoorNM,LipsP.Lipidlevels:a link betwee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osteoporosis?[J].Jofboneand mineralresearch,2009,6(6):48-56.
10.3969/j.issn.1009-4393.2017.18.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