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不通”看錢鐘書的“詩(shī)性”觀
和 慶 鵬
(南京師范大學(xué) 文學(xué)院,南京 210024)
中國(guó)的文學(xué)批評(píng)一直順承著經(jīng)驗(yàn)式、直感式的批評(píng)道路沿襲下來,從古典詩(shī)歌閱讀到現(xiàn)代新詩(shī)賞析,詩(shī)歌評(píng)論的維度始終圍繞著評(píng)論者自身展開。西方現(xiàn)代闡釋模式的傳入,對(duì)這種現(xiàn)象稍稍反撥,可無論是在批評(píng)界還是普通接受者群體里,經(jīng)驗(yàn)式的批評(píng)模式仍然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然而,在上世紀(jì)30年代,錢鐘書就已經(jīng)開始了中西貫通的治學(xué)模式,充分吸收西方文學(xué)理念,并和我國(guó)古典詩(shī)歌現(xiàn)象加以對(duì)比例證,探索中西普遍的詩(shī)學(xué)觀念。在其看似經(jīng)驗(yàn)式、直感式的表面形式之下,掩藏著其對(duì)詩(shī)學(xué)理念的深刻認(rèn)知。尤其是在古典詩(shī)歌的批評(píng)中,他更是在只言片語(yǔ)中透露出對(duì)詩(shī)學(xué)理念的深入思考。“不通”正是錢鐘書提出的具有建設(shè)意義的觀念之一。本文嘗試從錢鐘書的詩(shī)學(xué)理念出發(fā),并引入雅各布森的詩(shī)性理論深入闡釋“不通”,以深入挖掘重現(xiàn)這一理論對(duì)中國(guó)闡釋模式的重大意義。
一、“不通”與中國(guó)古典詩(shī)歌
錢鐘書在《管錐編·毛詩(shī)正義》的《雨無正》篇中討論語(yǔ)法程度時(shí),以“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四句為引,指出這四句乃是省略句,原文應(yīng)為“夙夜在公,朝夕從事”,從而提到不同文體之間的語(yǔ)法問題。最后,錢鐘書給出的結(jié)論是:“故歇后、倒裝,科以‘文字之本’,不通欠順,而在詩(shī)詞中熟見習(xí)聞,安焉若素。此無他,筆、舌、韻、散之‘語(yǔ)法程度’(degrees of grammaticalness),各自不同,韻文視散文得以寬限減等爾。”[1]291也就是說,同散文相比,詩(shī)詞更多時(shí)候具有“不通”的特點(diǎn),因此不能按照散文的語(yǔ)法來要求和苛求詩(shī)詞。由此,“不通”的概念被正式提了出來。簡(jiǎn)單來說,“不通”就是詩(shī)歌中的語(yǔ)法擾亂現(xiàn)象。隨后,錢鐘書援引了很多例子來佐證自己的觀點(diǎn),從《詩(shī)三百》到后世經(jīng)典詩(shī)詞,不乏“不通”之作。《詩(shī)經(jīng)·七月》篇中有“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乍看不通,實(shí)際上是運(yùn)用了倒裝的手法,正常的語(yǔ)序應(yīng)為“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入我床下”,這樣排列更容易理解。后世詩(shī)句中也有類似情況。白居易《長(zhǎng)安閑居》中有一句“無人不怪長(zhǎng)安住,何獨(dú)朝朝暮暮閑”,按照日常用語(yǔ)經(jīng)驗(yàn),此句讀起來是完全不通的。錢鐘書按照正常的語(yǔ)法排列重新組合,指出此句應(yīng)為“無人不怪何(以我)住長(zhǎng)安(而)獨(dú)(能)朝朝暮暮閑”。由于字?jǐn)?shù)、韻律的限制,不得不對(duì)字詞進(jìn)行調(diào)整,形成跨句倒裝,也就形成了這樣獨(dú)特的“不通”的詩(shī)句。與此類似的還有黃庭堅(jiān)的“不知臨水語(yǔ),能得幾回來”(“臨水語(yǔ):‘不知能得幾回來’”)、杜甫的“綠垂風(fēng)折筍,紅綻雨肥梅”(風(fēng)折筍垂綠,雨肥梅綻紅)等等。除此之外,詩(shī)詞中常用的省略手法也會(huì)造成詩(shī)詞的“不通”,其中最極端的例子要數(shù)《詩(shī)經(jīng)》了。例如《大東》有一句“大東小東,杼柚其空”,其中的“大東小東”讓人不明所以。后世鄭玄作箋:“小亦于東,大亦于東”。原來,在西周時(shí)代,鎬京是天下中心,因此統(tǒng)稱諸侯國(guó)為東國(guó),其中近者為小東,遠(yuǎn)者為大東。正是因?yàn)榇司涫÷赃^多,不合日常語(yǔ)法,才造成了接受者理解上的困難。
錢鐘書提出的“不通”是一種廣泛的詩(shī)學(xué)現(xiàn)象,在《管錐編》中,錢鐘書僅討論了因?yàn)榈寡b和省略造成的詩(shī)詞的“不通”。實(shí)際上,在《七綴集》中,盡管并未明確出現(xiàn)“不通”這一說法,但其中仍舊探討了大量“不通”的詩(shī)句,并且錢鐘書還總結(jié)出造成這種“不通”的另外三種原因:“畫不就”、比喻、通感。
“畫不就”指的是,當(dāng)把一首詩(shī)轉(zhuǎn)化成一幅畫的時(shí)候,會(huì)存在一些畫不出來的情況,強(qiáng)調(diào)詩(shī)歌藝術(shù)具有繪畫藝術(shù)所不能達(dá)到的某些效果。在《七綴集》中,錢鐘書論述詩(shī)畫關(guān)系時(shí)曾提到詩(shī)歌的這一“畫不就”的特性。比如詩(shī)人在描寫某種事物時(shí),經(jīng)常會(huì)幾種顏色混搭使用,有時(shí)這幾種顏色甚至彼此相悖不合常理,這時(shí)就涉及到顏色的“虛實(shí)”之分了。同數(shù)字一樣,顏色字也有虛實(shí)之分,實(shí)字就是真正的詩(shī)人要突出的顏色,而虛字就是假的顏色,用來襯托主顏色的。錢鐘書援引了蘇軾的名句“一朵妖紅翠欲流”來說明這種顏色之間的矛盾。一朵花怎么可能又“紅”又“翠”呢?實(shí)際上,這里的“翠”只是一個(gè)虛字,是形容花朵鮮亮的外貌,并不是真實(shí)的顏色。在這句詩(shī)中,真實(shí)的顏色字只有一個(gè),那就是“紅”。“翠”字作為虛字,起到了很好的襯托作用,如果將其替換掉,詩(shī)味就會(huì)大大降低。與此類似的詩(shī)句還有很多,如高適《別董大》“千里黃云白日曛,北風(fēng)吹雁雪紛紛”中的“黃”為實(shí)色,“白”則為虛色。白居易的《憶江南》中的“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碧如藍(lán)”中的“紅”“碧”為實(shí)色,而“藍(lán)”為虛色,是作為“藍(lán)草”來襯托江水之碧。“文字藝術(shù)不但能制造顏色的假矛盾,還能調(diào)和黑暗和光明的真矛盾,創(chuàng)造新奇的景象。”[2]42錢鐘書為此引用大量詩(shī)句。無論是《金樓子》第二篇《箴戒》“兩日并出,黑光遍天”中的“黑光”,還是徐蘭《磷火》“別有火光黑比漆,埋伏山坳語(yǔ)啾唧”中的“火光黑比漆”,都描繪了一幅十分奇特的景象:光與暗在強(qiáng)烈的對(duì)比沖突中漸趨融匯,達(dá)到一種渾然一體的平衡。這樣的詩(shī)句自然也屬于“不通”的范疇。
比喻是錢鐘書提出的第二種造成詩(shī)歌“不通”的原因。比喻是文學(xué)語(yǔ)言的特點(diǎn),在詩(shī)詞中運(yùn)用比喻早已屢見不鮮。諸如岑參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忽如一夜春風(fēng)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李后主的《虞美人》“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等,都是廣為流傳并為人稱道的運(yùn)用比喻的經(jīng)典詩(shī)句。尋常的明喻并不會(huì)使詩(shī)歌產(chǎn)生“不通”感,只有當(dāng)喻體和本體之間差距過大時(shí),比喻才會(huì)新奇險(xiǎn)僻,詩(shī)歌才會(huì)“不通”。在西方,詩(shī)人艾呂雅曾寫過“地球藍(lán)得像個(gè)橙子”這樣“不通”的詩(shī)句,在中國(guó)古詩(shī)中,也不乏這樣的例子。《錦瑟》是李商隱的代表詩(shī)作,也被視為李商隱最難解讀的作品之一,歷來就頗多爭(zhēng)議。這首詩(shī)的意義之所以如此繁豐,原因在于其本體和喻體之間的差距過大,從而形成文本內(nèi)部的割裂。從全詩(shī)的尾聯(lián)“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dāng)時(shí)已惘然”來看,詩(shī)人似乎是在追憶往事。那么這種往事究竟是什么呢?詩(shī)人采用了一種非常委婉的借喻的方式來闡明。如果將詩(shī)人并未點(diǎn)破的往事或者說往日的情思作為本體,那么前面提到的莊生夢(mèng)蝶、杜鵑啼血、滄海明珠、藍(lán)田玉煙,都是作為喻體而存在的。一般來說,詩(shī)人采用借喻,用一些具體的事物來代指本體,是為了將抽象的情思具體化。然而,在這首詩(shī)中,詩(shī)人采用大量的喻體來代指本體,這些喻體相互之間并沒有緊密聯(lián)系,和本體之間差距又十分巨大,甚至在許多人看來本體和喻體之間毫無關(guān)聯(lián),因此本體所指的具體內(nèi)容仍然是模糊的、多義的。這也是為什么在很多人看來,這首詩(shī)不僅晦澀,更是一首徹頭徹尾的“不通”詩(shī)。
在《七綴集》中,錢鐘書還給出了另一種造成詩(shī)文“不通”的描寫手法——通感。“在日常經(jīng)驗(yàn)里,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各個(gè)官能的領(lǐng)域可以不分界限。”[2]64這種體驗(yàn)延伸到詩(shī)文中,就形成了一種獨(dú)特的通感式手法。最著名的運(yùn)用通感的詩(shī)文莫過于那句“紅杏枝頭春意鬧”了。此句曾遭到李漁的嘲笑:“此語(yǔ)殊難著解。爭(zhēng)斗有聲之謂‘鬧’;桃李‘爭(zhēng)春’則有之,紅杏‘鬧春’,余實(shí)未之見也。”李漁的嘲笑并非毫無道理,紅杏是靜物,無法發(fā)出聲音,更不用說喧鬧了,因此可以說“不通”。然而,將觀望到的紅杏(視覺)和發(fā)出的喧鬧(聽覺)相互貫通,打破彼此界限,這種“通感”的手法就會(huì)將無聲開放的紅杏的茂盛姿態(tài)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紅杏繁茂,簇簇相擁,發(fā)出一聲聲喧鬧,仿佛在爭(zhēng)奪著有限的空間向世人展示著自己妖嬈的姿態(tài),讓人在靜態(tài)的視覺中聽到了動(dòng)態(tài)的聲音的波動(dòng),這句“不通”的句子正是使全詞意趣升華的關(guān)鍵所在。詩(shī)人們能夠?qū)⒉煌母泄僦g的界限打通,靠的是對(duì)日常事物的不尋常的感受,是對(duì)一般經(jīng)驗(yàn)的超越與突破,也正因?yàn)槿绱耍?shī)歌中的“不通”才會(huì)生成。
二、符號(hào)自指與詩(shī)性
如果僅僅將錢鐘書提出的“不通”理解為一種詩(shī)學(xué)現(xiàn)象,勢(shì)必?zé)o法在詩(shī)歌闡釋的路上更進(jìn)一步,甚至?xí)萑肓硗庖环N紛爭(zhēng),即“不通”這種現(xiàn)象真的合理么?對(duì)于這一現(xiàn)象的質(zhì)疑雖然并未直接指向錢鐘書的理論本身,但就大眾對(duì)當(dāng)下先鋒詩(shī)歌探索的態(tài)度(如關(guān)于“梨花體”的爭(zhēng)吵)來看,“不通”仍然是橫亙?cè)谧x者與詩(shī)歌之間的一塊巨石。實(shí)際上,錢鐘書的“不通”理論之下潛藏的是復(fù)雜的詩(shī)學(xué)規(guī)律。錢鐘書通過引用符號(hào)學(xué)家西比奧克的“語(yǔ)法程度”的觀點(diǎn),說明了詩(shī)歌語(yǔ)言的特點(diǎn)是語(yǔ)法程度弱,乃至語(yǔ)法混亂,一針見血地道出了很多人未曾講明的道理。錢鐘書關(guān)于“不通”的論述實(shí)質(zhì)上反映了錢鐘書對(duì)于詩(shī)歌最本質(zhì)的理解,即“詩(shī)何以為詩(shī)”,而這種理解都集中體現(xiàn)在“不通”這一理念上。詩(shī)歌的語(yǔ)法程度說到底還是沒有脫離詩(shī)歌形式這一范疇,“不通”也從側(cè)面反映出錢鐘書仍是在詩(shī)歌的形式范圍內(nèi)摸索詩(shī)歌的特性,因此,引入西方形式論代表人物雅各布森的“詩(shī)性功能”理論,無疑可以幫助我們打開“不通”的大門,探尋錢鐘書隱形的“詩(shī)性”觀。
1958年,雅各布森在一次國(guó)際會(huì)議上發(fā)表了題為《結(jié)束語(yǔ):語(yǔ)言學(xué)與詩(shī)學(xué)》的演講,提出了符指過程中存在的六種因素,以及由于對(duì)這六種因素的側(cè)重不同而形成的六種功能。其中,“指向信息本身和僅僅是為了獲得信息的傾向,乃是語(yǔ)言的詩(shī)的功能”[3]180。也就是說,當(dāng)符號(hào)行為側(cè)重于信息本身時(shí),詩(shī)的功能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詩(shī)性得以實(shí)現(xiàn)。在這種情況下,索緒爾建構(gòu)起來的“能指—所指”的線性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被打破,符號(hào)在指向所指的過程中又反過來指向自身,因此詩(shī)性的根本特征就是符號(hào)的自指性。“符號(hào)自指性”將人們對(duì)“不通”的理解又往前推進(jìn)了一步。當(dāng)符號(hào)指向自身的時(shí)候,一個(gè)封閉的語(yǔ)義結(jié)構(gòu)就誕生了,這就意味著讀者無法從外界現(xiàn)實(shí)中獲得詩(shī)歌解讀的鑰匙,研究任務(wù)必須轉(zhuǎn)向語(yǔ)言結(jié)構(gòu)本身,也就是霍克斯所說的“它的方式是自我指稱的;它就是自己的主題”[4]86。這同時(shí)也意味著,如果某些接受者還執(zhí)著于追求符號(hào)和現(xiàn)實(shí)中某個(gè)對(duì)象的專屬對(duì)應(yīng),那么闡釋的結(jié)果必定會(huì)不盡人意,自然也就導(dǎo)致了所謂的“意義”的缺失。
“不通”透露出錢鐘書的“詩(shī)性”思維,即“不通”扎根于符號(hào)自我指涉的基礎(chǔ)之上,但兩者之間不能直接簡(jiǎn)單地劃上等號(hào)。很顯然,從符號(hào)自指到詩(shī)歌“不通”,中間還有一段路要走。因此,對(duì)于理解“不通”而言,最為關(guān)鍵的一步是找到這條路,找到“不通”生成的方式。
雅各布森曾談到在文本中詩(shī)性功能的呈現(xiàn)方式,借用這一操作原則,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不通”的生成方式。雅各布森定義詩(shī)性功能為“對(duì)等原則從選擇軸投射到組合軸”。在這個(gè)定義中,對(duì)等原則、選擇軸、組合軸是三個(gè)重要的名詞。雅各布森認(rèn)為,語(yǔ)言行為的兩個(gè)結(jié)構(gòu)模式,一個(gè)是選擇,一個(gè)是組合。選擇的標(biāo)準(zhǔn)是名詞間的“相似性”,而組合的標(biāo)準(zhǔn)是依照名詞間的“鄰近性”。那么,這種對(duì)等原則是如何通過兩軸實(shí)現(xiàn)符號(hào)的自我指涉的呢?雅各布森認(rèn)為,對(duì)等原則“通過將語(yǔ)詞作為語(yǔ)詞來感知,而不是作為被指稱的客體的純粹的再現(xiàn)物,或作為情感的宣泄;是通過諸個(gè)詞和它們的組合、它們的含義、它們外在和內(nèi)在的形式,這些具有自身的分量和獨(dú)立的價(jià)值,而不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一種冷漠的指涉”[5]378。也就是說,由于對(duì)等原則的干涉,詩(shī)性功能“通過提高符號(hào)的具體性和可觸知性(形象性)而加深了符號(hào)同客觀物體之間基本的分裂”[3]180。日常語(yǔ)言的組合依靠的是語(yǔ)法關(guān)系和邏輯關(guān)系,而選擇軸上的詞語(yǔ)之間由于具有相似性,因此具有聯(lián)想關(guān)系。通常情況下,對(duì)等原則只適用于選擇軸,是隱形的“不在場(chǎng)”的存在于詩(shī)外的想象空間。而在詩(shī)歌中,如果將對(duì)等原則從選擇軸投射到組合軸,就意味著相似性凌駕于鄰近性之上,從而對(duì)等原則成為指導(dǎo)詩(shī)歌組合的技巧。這樣造成的結(jié)果就是對(duì)等原則從幕后走向“在場(chǎng)”,“對(duì)等原則將這些詞語(yǔ)并置于組合軸上,削弱了依靠邏輯關(guān)系和語(yǔ)法關(guān)系所形成的語(yǔ)義上的線狀承續(xù),而加大了語(yǔ)詞間的聯(lián)想空間。詞與詞之間的常規(guī)語(yǔ)義走向出現(xiàn)斷裂,產(chǎn)生空隙,這個(gè)空隙正是想象的空間”[6]。這恰恰呼應(yīng)了此前雅各布森關(guān)于符號(hào)和客體分離的說法。在這種情況下,能指不再習(xí)慣性地指向日常搭配的所指,從而有了無限搭配的可能性,詞語(yǔ)的“不通”便成為詩(shī)歌語(yǔ)言的特點(diǎn)之一,詩(shī)歌因此更具活力。
總之,通過雅各布森的詩(shī)性功能理論,我們對(duì)“不通”有了更加深刻的認(rèn)識(shí):其本質(zhì)是當(dāng)詩(shī)性占主導(dǎo)地位時(shí),符號(hào)自我指涉的產(chǎn)物,具體依靠對(duì)等原則來生成。從詩(shī)性功能形成封閉的語(yǔ)義結(jié)構(gòu),到對(duì)等原則成為詩(shī)歌語(yǔ)言的組合技巧,“不通”就是在這樣一步步的自我指涉中形成一種普遍的詩(shī)學(xué)現(xiàn)象。由此反觀那些晦澀的古典詩(shī)歌,實(shí)則在“不通”的表面之下潛藏著進(jìn)入“通”之境界的大門。
三、“不通”的闡釋學(xué)意義
錢鐘書提出“不通”,并在其著作《管錐編》《七綴集》中有意無意地枚舉大量的中國(guó)古詩(shī)詞,例證這種現(xiàn)象的存在以及其存在的廣泛性,這顯然證明了錢鐘書這一理論的可貴之處。然而,遺憾的是,由于中國(guó)評(píng)論界對(duì)“晦澀”詩(shī)學(xué)的長(zhǎng)期誤解,“不通”這一重要詩(shī)學(xué)理念始終沒有得到應(yīng)有的重視。長(zhǎng)期以來,關(guān)于“不通”的論述只存在于寥寥幾篇論文之中,而其中大多數(shù)也都只是在例證“不通”的存在,或者單純地將“不通”與國(guó)外詩(shī)歌符號(hào)學(xué)理念做出對(duì)比聯(lián)系,并未深入地挖掘“不通”本身的價(jià)值。這就意味著重新審視錢鐘書提出的“不通”理論,從根本上探討“不通”的普遍詩(shī)學(xué)價(jià)值,是今后應(yīng)該集中關(guān)注的一個(gè)問題。
從古至今,關(guān)于詩(shī)歌“晦澀”之爭(zhēng)從未斷絕過,而“不通”作為“晦澀”的一種典型代表更是為許多人所詰難。可實(shí)際上,晦澀是一個(gè)十分復(fù)雜的詩(shī)學(xué)問題,將所有的晦澀問題一概而論的做法是有欠妥當(dāng)?shù)摹E懦蛯哟位逎安煌ā鼻∏∈窃?shī)歌語(yǔ)言的一大特點(diǎn),在詩(shī)性占主導(dǎo)的詩(shī)歌中,詩(shī)歌的“不通”不僅能增加詩(shī)歌的詩(shī)味,更能將研究者的注意力從外界轉(zhuǎn)向詩(shī)歌文本本身,從而完善中國(guó)傳統(tǒng)的詩(shī)歌闡釋模式。可以這樣說,以往被批判的缺點(diǎn)恰恰是“不通”對(duì)于當(dāng)下闡釋的意義所在。
中國(guó)強(qiáng)大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傳統(tǒng)使得中國(guó)詩(shī)歌闡釋一直沿著經(jīng)驗(yàn)式、直感式的感性批評(píng)道路沿襲下來,即要求詩(shī)歌必須解讀出某種現(xiàn)實(shí)意義,實(shí)際上這種詩(shī)歌闡釋的維度暗暗貼合了索緒爾“能指—所指”的兩元對(duì)立思維。經(jīng)驗(yàn)式闡釋的代表性人物葉威廉就認(rèn)為,對(duì)中國(guó)古典詩(shī)歌的闡釋“不要讓‘思’的痕跡阻礙了物象涌現(xiàn)的直接性”,也就是說,詩(shī)歌闡釋要避免理性的思考與分析,要依靠閱讀詩(shī)歌時(shí)瞬間的經(jīng)驗(yàn)感受。很顯然,這樣的闡釋方式有賴于人們對(duì)古典詩(shī)歌中意境與情思敏銳的審美感受,其缺陷十分明顯,即批評(píng)的角度始終離不開評(píng)論者自身。這樣就導(dǎo)致一旦文本中出現(xiàn)與評(píng)論者日常經(jīng)驗(yàn)不相符的表述,裹挾著晦澀、“不通”等詰難的評(píng)論將紛至沓來。即便之后如王力等學(xué)者提出新的闡釋模式,但事實(shí)上也并未脫離感性批評(píng)的束縛。王力在《漢語(yǔ)詩(shī)律學(xué)》中,對(duì)很多中國(guó)古典詩(shī)歌做了語(yǔ)法分析,試圖利用西方的語(yǔ)法規(guī)則來解讀古典詩(shī)歌。這樣的做法,看似為中國(guó)古典詩(shī)歌的解讀提供了一條相對(duì)嚴(yán)謹(jǐn)?shù)牡缆罚鋵?shí)和葉威廉的經(jīng)驗(yàn)式批評(píng)并無太大差別。可以說,無論是葉威廉還是王力,都只偏重于詩(shī)歌解讀的一個(gè)方面,那就是與現(xiàn)實(shí)世界的呼應(yīng),即只看到符號(hào)表意過程中的語(yǔ)境因素。無論是葉威廉的經(jīng)驗(yàn)批評(píng),還是王力的語(yǔ)法分析,其出發(fā)點(diǎn)都是現(xiàn)實(shí)環(huán)境中的邏輯,背后隱含著同質(zhì)的思維,即詩(shī)歌必須指向現(xiàn)實(shí),區(qū)別不過是一個(gè)以人為中心,一個(gè)以現(xiàn)實(shí)語(yǔ)法為中心。這種只看到符號(hào)指稱功能的批評(píng)方法使得當(dāng)下的詩(shī)歌闡釋難以擺脫現(xiàn)實(shí)環(huán)境的困擾。
現(xiàn)實(shí)傳統(tǒng)的另一影響,體現(xiàn)在中國(guó)自古對(duì)元語(yǔ)言功能的強(qiáng)調(diào)上。古代官本位的思想使得詩(shī)人們的人生抱負(fù)和政治環(huán)境緊緊結(jié)合在一起,再加上生產(chǎn)力的原因,古代的朝代更迭和政治動(dòng)亂頻繁,內(nèi)容反映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和人生感悟的詩(shī)歌(不包括表現(xiàn)手法)成為正統(tǒng)。直到20世紀(jì)新詩(shī)誕生,現(xiàn)實(shí)仍然是影響詩(shī)歌創(chuàng)作與解讀的重要元素。“在雅各布森的符號(hào)‘六功能’圖示中,元語(yǔ)言性與詩(shī)性相反。符號(hào)自指,則詩(shī)性實(shí)現(xiàn);符號(hào)集中于解釋,則元語(yǔ)言功能成為主導(dǎo)。若詩(shī)歌重點(diǎn)在于向讀者解釋、宣傳某種觀念,或者詩(shī)歌傾向于對(duì)大眾進(jìn)行說教,或者詩(shī)歌變成標(biāo)語(yǔ)、口號(hào)的一種形式……那么詩(shī)歌的元語(yǔ)言功能也就壓倒了詩(shī)性功能。”[7]53當(dāng)詩(shī)歌的元語(yǔ)言功能占據(jù)上風(fēng)時(shí),論者自然深陷在社會(huì)元語(yǔ)言的漩渦中不可自拔,詩(shī)歌也就變成了現(xiàn)實(shí)的附庸品,魅力大減。
錢鐘書提出的“不通”理論無疑為我們擺脫這種傳統(tǒng)的詩(shī)歌評(píng)論模式提供了一條新的道路。利用“不通”的思維闡釋詩(shī)歌,實(shí)際上就是利用“詩(shī)性”的思維闡釋詩(shī)歌。詩(shī)性指向符號(hào)自身的特點(diǎn),決定了在詩(shī)歌這個(gè)封閉的語(yǔ)義結(jié)構(gòu)里,所有的思維邏輯必須從詩(shī)歌文本本身展開。在這種情況下,文學(xué)研究的任務(wù)就變成了如何加強(qiáng)對(duì)詩(shī)歌文本中詩(shī)性的掌握與探尋,變成了對(duì)詩(shī)歌能指層面的深入研究。在沒有現(xiàn)實(shí)中實(shí)用、道德、宣傳等因素的影響下,在沒有各種元語(yǔ)言集合的糾纏下,“不通”恰恰是讀者通往詩(shī)歌深層內(nèi)涵的一條必經(jīng)之路。它不合語(yǔ)法,超越常規(guī),打破對(duì)現(xiàn)實(shí)如鏡般的效仿,使詩(shī)歌的闡發(fā)上升到一種新的境界,甚至可以生發(fā)出迷人的“闡釋漩渦”。重新認(rèn)識(shí)發(fā)掘“不通”的意義,正是要將千百年來一直深陷現(xiàn)實(shí)語(yǔ)境的評(píng)論者解脫出來,從而立足于詩(shī)歌文本的平臺(tái)之上,展開全新的闡釋模式。難怪里法泰爾宣稱:“詮釋不需要很多語(yǔ)文知識(shí),不需要博學(xué),也不需要了解某個(gè)時(shí)期內(nèi)的思想規(guī)范或社會(huì)習(xí)俗,只要了解把思想標(biāo)準(zhǔn)和社會(huì)習(xí)俗譯成信碼而加以收錄的詞匯即可。……如果評(píng)論家企圖從心理學(xué)、社會(huì)學(xué)和歷史學(xué)的角度重建批評(píng)標(biāo)準(zhǔn)并以此探測(cè)作者的意圖,那么他所獲得的作品的‘真正的意義’只能是臆測(cè)。”[8]374很顯然,文本所蘊(yùn)含的深層含義無法單從文本外部獲得,這一點(diǎn)里法泰爾和錢鐘書的觀點(diǎn)是一致的。當(dāng)然,錢鐘書的“不通”詩(shī)學(xué)并不是要求每一首詩(shī)歌都包含著“不通”,也并不是說不包含“不通”的就不是好的詩(shī)歌作品,而是要求接受者們正視“不通”,重視“不通”,在詩(shī)歌的“不通”處入手,探尋詩(shī)歌文本的深層內(nèi)涵。可以說,在當(dāng)下,重新提出錢鐘書的“不通”理論,其真正意義在于培養(yǎng)接受者的“不通”思維,迫使接受者改變閱讀策略,從而達(dá)到糾正當(dāng)下詩(shī)歌闡釋模式的目的。
錢鐘書提出的“不通”是一種廣泛的詩(shī)學(xué)現(xiàn)象,通過大量古典詩(shī)歌的驗(yàn)證,這一點(diǎn)已經(jīng)展露無遺。在這種現(xiàn)象背后,蘊(yùn)藏著錢鐘書對(duì)于詩(shī)歌語(yǔ)言特點(diǎn)的深刻認(rèn)知——不通欠順。更難能可貴的是,這種認(rèn)知還反映出錢鐘書對(duì)于詩(shī)歌本質(zhì)規(guī)律的認(rèn)識(shí),對(duì)于詩(shī)歌本身形式的關(guān)注。通過借用雅各布森的詩(shī)性功能理論,我們對(duì)“不通”的生成以及生成機(jī)制有了更加透徹的認(rèn)識(shí)。在接受者仍然被社會(huì)語(yǔ)境元語(yǔ)言糾纏難以脫身的環(huán)境下,重新挖掘“不通”這一詩(shī)學(xué)理念,顯然有助于幫助我們形成新的詩(shī)歌闡釋思維,使得詩(shī)歌研究的任務(wù)轉(zhuǎn)向?qū)υ?shī)歌文本“詩(shī)性”的探尋,從而完善中國(guó)的詩(shī)歌闡釋模式。當(dāng)每一個(gè)接受者都能夠真正做到“不通欠順,安焉若素”的時(shí)候,“不通”的意義將會(huì)得到最大的彰顯。
[1] 錢鐘書.管錐編(一)[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1.
[2] 錢鐘書.七綴集[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2.
[3] (俄)雅各布森.語(yǔ)言學(xué)與詩(shī)學(xué)[A].趙毅衡主編.符號(hào)學(xué)文學(xué)論文集[C].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
[4] (英)特倫斯·霍克斯.結(jié)構(gòu)主義和符號(hào)學(xué)[M].瞿鐵鵬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5] Roman Jakobson,“what is poetry?” in Krystyna Pomorska and Stephen Rudy, eds., Language in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University of Harvard Press, 1987.
[6] 田星.羅曼·雅各布森詩(shī)性功能理論研究[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xué),2007.
[7] 喬琦.形式動(dòng)力:新詩(shī)論爭(zhēng)的符號(hào)學(xué)考辨[M].成都: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2015.
[8] (法)里法泰爾.描寫性詩(shī)歌的詮釋——讀華茲華斯的《紫衫》[A].趙毅衡主編.符號(hào)學(xué)文學(xué)論文集[C].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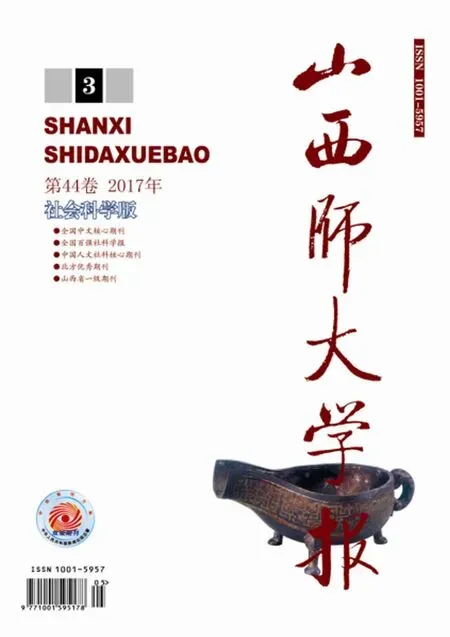 山西師大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7年3期
山西師大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7年3期
- 山西師大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堅(jiān)定社會(huì)主義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的自信
———評(píng)吉志強(qiáng)博士的《社會(huì)主義生態(tài)文明,何以可能?》 - 自控能力在學(xué)業(yè)倦怠與學(xué)業(yè)成績(jī)間的調(diào)節(jié)作用
- 中文報(bào)刊中漢英混用現(xiàn)象的社會(huì)語(yǔ)言學(xué)透視
- 中小學(xué)教師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能力探討
----基于山西吉縣的調(diào)查 - 我國(guó)農(nóng)村留守婦女媒介形象的呈現(xiàn)與建構(gòu)
- 女性/性別外文翻譯出版書籍評(píng)述
----以1995—2014年出版的女性/性別翻譯書籍為例
